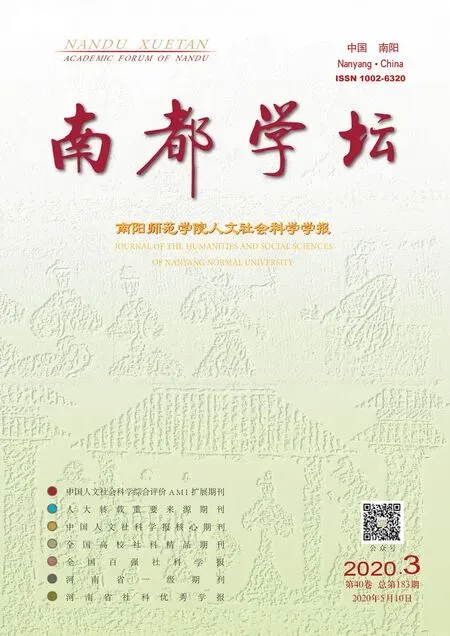汉代谶纬界对“河图”“洛书”概念的重整
——兼论“汉无河图”通说中《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位
2020-12-06郭思韵
郭 思 韵
(新纪元大学学院 中文系,马来西亚 加影 43000)
“河图”“洛书”的概念,在先秦文献中便已数见,至两汉之际则随着以河洛符命为核心的谶纬思想体系之盛行,以河洛名目为篇题的谶纬领域著述之蜂出以及光武帝官定图谶的宣布天下,而一跃成为登场频率极高的时代语汇。然而尽管仍沿用原称,汉世谶纬语境中的所谓“河图”“洛书”,其涵盖面相比最初实已历经极大扩充,其集多义于一身的现象颇为显著,极易引发误读问题,须审慎辨析。但谶纬乃神学、政治、经学间的牵会之作这一认知早为常谈,由此相关的河图洛书的种种内涵变化也素被学者们认为是其编造之一环而未予以深究。实际上,在了解先秦河洛图书之说特性嬗变的基础上,考察汉代谶纬界对固有说法的统合方式与创发模式,不仅能很好地窥见谶纬作者们的编造态度与原则,对谶纬多元内容的形成由来也颇有助益。而明晰汉人所理解的“河图”“洛书”,也可避免因时代语境、概念的微妙区别而导致认知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结论。
一、先秦文献中的“河图” 之说
“河图”一称,存世可稽的最早记载见于《周书·顾命》,其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1]239作为最初的、并非是出自想象的而系藏于“祖庙”、并在“顾命”乃至“大祭、大丧”等重要典礼上必将陈列的“国之玉镇、大宝器”[2],同时也是后世“河图”诸说的渊薮,东序“河图”的真貌基本最为贴近河图的原始形态,惜乎《尚书》并未对其有更多着墨。
此后再次提及河图的是孔子,然而据万斯同、胡渭考辨,东序河图于“犬戎之难,周室东迁”之际就已失落,“无论后人,恐夫子亦不及见”(1)《易图明辨·河图洛书》载:“河图藏诸天府,不知何时遂亡。初意秦昭襄王取周九鼎宝器时,河图并入于秦。及项羽烧秦宫室,与府库俱为灰烬。此其所以不传也。今年客京师,与四明万君季野(斯同)论及此事,万君曰:‘幽王被犬戎之难,周室东迁,诸大宝器必亡于此时。河图,无论后人,恐夫子亦不及见。’余闻而韪之,顷检《周本纪》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赂即珍宝货财也。可见河图实亡于此时。故自平桓以下,凡《顾命》所陈诸宝器,无一复见于传记。而王子朝之乱,其所挟以出者,周之宝珪与典籍而已,天府之藏无有也。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苌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夫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胡渭:《易图明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8页。[3]。亦即《礼运》(2)《礼运》篇见载于《礼记》《孔子家语》,据杨朝明考证,应出于言偃自记,且此次谈论的时间则当在“鲁定公十年到十二年这三年之内的某年十二月”。详见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4]“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5]及《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6]的孔子言中所体现的河图认知,恐更多是建立于传闻与揣度及由祖庙守藏国之玉镇宝器的象征意义所导出的推想上,以其为一种寓意“德祥”的珍稀“宝器”,乃圣王治世德洽之征应(3)《周礼》曰:“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是陈之即藏而非随时鉴省,这就意味着东序河图的用处,是重在摆设式的象征性而非匡辅式的使用性上。结合“顾命”主题,就要义旨归而言,将君王德治与东序河图挂钩,应是顺理成章的。。
在上述基础上延伸发挥,掺入天命授受意味,遂有《墨子·非攻》所载的、显然是就东序河图发辞的“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7],还有《管子·小匡》所称之“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8],以“河图”为享有天命之征,且某种程度具有唯一性。
至于《周易·系辞》所描述的“河图”,则又似是另一番揣度。“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9]云云,表明了此中之“河图”与“洛书”是被看成为应被则效的对象,并意味着其中含有可以被则效的内容。结合《庄子·天运》就“九洛之事”的叙说可知,“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出典本在禹对帝畀治典“洪范九畴”的奉行,则“河出图……圣人则之”理当与此相仿,“河图”应亦被认为是载有圣王所当遵循的关乎治道的天谕范典。
《吕览·观表》中被系于圣人之身的“绿图幡薄”,作为圣人“审征表”以“先知”、“审知今”以“知古”“知后”从而“上知千岁,下知千岁”的成果,无疑便是体现了许多“圣人长见”的著述[10],也即后来《史记·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所言载录了“亡秦者胡也”谶言的“录图书”“录图传”之属[11]252[12]1907。“绿图”乃圣人“审征”的对象,“幡薄”为“审知”的成果[13]。其本质上被视作“帝纪世谶”的载体。
概言之,自东序河图失落后,对原始河图的了解便不免出现游移,《论语》《礼运》《墨子》《管子》《易传》《吕览》等先秦文献之所言及者,承载了各个阶段不同群体对“河图”的认知与变化,深受行世传说与时代思潮的左右。实际上,诸多揣度纷纭众说中的所谓“河出之图”,与已失落的“东序河图”,除了名谓的雷同外,似再无其他证据来说明它们有所关联。
二、先秦文献中的“洛书” 之说
“洛书”一词的出现,则要比“河图”晚得多,存世先秦文献凡三见:《周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庄子·天运》“九洛之事,治成德备”。前两者皆与“河图”配对出现,然而《管子》中并为受命之符的“河图”“洛书”尚能看到一为假龙、一为假龟的粗略区分,而《周易·系辞》仅能看见同为圣人则法的共性,皆不利于探研“洛书”内涵,反而是表面上并未直称其名的“九洛”,最能提供线索。
《庄子·天运》曰:“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14]88这一条宜与《周书·洪范》箕子之言参阅:“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1]187-188《天运》称“天有六极五常”,《洪范》所录“九畴”恰始于五行而终于六极——“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天运》谓“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洪范》载鲧逆之故“彝伦攸斁”,禹得之故“彝伦攸叙”。因而对所谓“九洛之事”,前贤多以“九畴”为“洛书”内涵,最具代表性者如王先谦集解引杨慎云:“九洛,九畴洛书。”[14]88他如郭嵩焘“禹所受之九畴也”,俞樾“其即谓禹所受之洛书九类乎”亦同[15]。《天运》这段文字忠实地反映了“洪范九畴”与“洛书”建立联系的关键枢纽——顺则与治德。就“九畴”所论,“洪范”的定位实是一部天帝赐予的圣王治典,而《系辞》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也正是《天运》中帝王“顺之则治”“治成德备”的“九洛”之说的缘由与前提。正因如此,《系辞》中的“洛书”历来便一直被认同指的是禹得九畴之事,刘歆如此,伪孔亦然(4)此说详见《汉书·五行志》及《周书·洪范》孔传。。
又,此段文字亦是作为独立存在而非“河图”配对来叙述的关于“洛书”之最早可见信息,似乎“洛书”的初始形态就是一部有着明确指向的特定篇典,然而《周书·洪范》对“九畴”之来历及内涵洋洋洒洒而论,却语未及“洛书”一称,亦与洛水无所干涉,可见“九畴”与“洛书”的联系极可能是《洪范》成篇后才冠上的,且从一开始的授受对象便是禹,《系辞》所谓“洛出书,圣人则之”指的便是禹对帝畀治典“洪范九畴”的奉以为法。
三、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河图”
河图在汉代迎来了极其关键的发展高峰,毕竟随着中元元年(56)被光武帝宣布于天下、而后在东汉几与经学分庭抗礼的官定图谶,正是以河洛符命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所谓“《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16]1913是也。“河图”的内涵与形态,借由谶纬文献完成了整合,并自此凝固为汉唐人的共有认知。
(一)对先秦“河图”特性的统合
与谶纬有关的“河图”主要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图谶中缀以“河图”之名的诸篇,二是81篇中对“河图”的具体描述。《河图》诸篇系出于汉人造作,已是定论,而造作的要义,必为取信于世。故个中所勾勒、描述的“河图”,为了回避、减轻可能招来的质疑,不免须得极尽呼应、声援流播时世的相关史料与传说,其中以《尚书中候》对尧受河图一事的记叙最为典型:
龙马衔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临坛而止,吐甲回滞。甲似龟,广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帝乃写其文,藏之东序。[17]19008
何以谓“龙马衔甲”?因为《管子》有“龙龟假,河出图”之语而《礼记》称“河出马图”。何以谓“赤文绿色”?因为《墨子》采用通假字写作“河出绿图”。何以谓“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汉之事”?因为《吕览》宣称“绿图幡薄”承载了“上知千岁,下知千岁”的成果,世亦传“亡秦者胡”谶出自“录图书”。何以谓“帝乃写其文”?因为须得解释“河图”在原物失传的情况下却有时文版本流播的问题,遂有“黄龙负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写,以示天下”“周公援笔以世文而写之”后“书成,文消,龟去”之类的隐秘原型设定[17]19744,19026-19027。何以谓“藏之东序”?因为《周书》明确载录“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但应注意的是,诈伪者显然只着眼呼应“河图在东序”就自以为是“藏之东序”,连原文所记述的是临时陈列、日常归属“天府”所掌“祖庙之守藏”的实际情况都未顾及。
至于谶纬语境中何以包括尧在内的伏羲、黄帝、舜、禹等一众帝王圣者皆曾“受图”而不仅是《墨子》明确声称的“周文武”?因为出没于《礼记》《论语》《管子》的“河图”是逢圣则出的德洽或天命之征符,显然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宝器而是已形成种类的“信物”。如此一来,《系辞》中“圣人则之”的“河”所出之“图”也就不妨碍汉人继续认定其独与伏羲八卦渊源深厚了,既然大家各有各的“河图”,与八卦渊源深厚的《系辞》所载的主人翁理所当然就应是伏羲嘛。如此这般,可谓面面俱到,皆大欢喜。至此,“河图”传世的相关史料与传说基本被囊括殆尽。
(二)汉代“方今无河图”的公论
然而谶纬文献在整合了此前“河图”诸内涵的同时,又为“河图”名谓开发了新分类,造成一称多义的问题。基于谶纬在东汉的影响力,已有共识的时人言语中对此是义界分明、交流无碍的,但于后人而言却是极易误读继而导致理解偏差的。例如王充《论衡·宣汉篇》中令人颇感困扰的这段论述:
儒者称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已来,未有太平……见孔子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方今无凤鸟、河图,瑞颇未至悉具,故谓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帝王圣相,前后不同,则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无凤鸟、河图,谓未太平,妄矣。孔子言凤皇、河图者,假前瑞以为语也,未必谓世当复有凤皇与河图也。夫帝王之瑞,众多非一,或以凤鸟、麒麟,或以河图、洛书,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阴阳和调,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于古,古应未必合于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袭。[18]817-819
此中令人深感费解之处是,在共识上以《河图赤伏符》为光武“受命之符”的东汉时期,究竟是怎么出现“方今无……河图”的说法乃至成为“汉兴以来,未有太平”的论据的?对此,陈槃如是解说:
河图之书,藏于秘府,非一般人所可得而见。王充生当光武建武三年,卒当和帝永元八年,其时河图篇目,已甚繁复矣,而云“瑞颇未悉具”者,盖充于时有所未见。不然则充以此类为“神怪之言”,有所不信,故其辞乃尔也。(《论衡·宣汉篇》又云:“彼闻尧、舜之时,凤皇、景星皆见,河图、洛书皆出,以为后王治天下,当复若等之物,乃为太平。”是必王氏尝见河图矣,盖不信之说是也)。[19]
可无论未见之说抑或不信之说,情理上似都未能自洽。倘说出于未见,光武帝以《河图赤伏符》践帝位,令人校定图谶并宣布于天下,这等已晋级为官方意识形态加以刻意渲染的大事,王充纵未能亲见亦不可能未闻,断不至宣称“今王无……河图”。至于陈槃力主的不信说,以王充对图谶的质疑态度而言,倒也可通,但应当注意的是,王充所力驳的“方今无凤鸟、河图,瑞颇未至悉具,故谓未太平”之说,并非他的个人创见,而是当时“儒者”所“称”,且正如《须颂篇》所言:“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18]84时儒所争议的焦点并不在炎汉有无“河图”,而是未出“河图”的汉室是否可称之为太平,这意味着“汉无河图”在当时乃是世所公认的事实,与王充的个人因素全然无涉。
那么,要如何解释在“河图篇目,已甚繁复”的时代语境下、在《河图赤伏符》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所形成的这个看似矛盾的公论呢?
(三)《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位
应当明确的是,时儒的汉以来无河图之说,至少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首先,河图有古、今之说,“尚存前代河图”和“未出当代河图”是两回事,故无论光武帝所定图谶之《河图》篇目如何繁复,皆为尧、舜等古圣所受而不属于汉世“今王”;其次,也是尤须辨析的一个重点——《河图赤伏符》恐怕并不被视为汉代所出“河图”,而这似乎与传统对光武君臣在图谶利用问题上的固有认知有微妙出入。
从《东观汉记》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作用方面,《赤伏符》是应光武帝的需求而出的谶言载体,且一开始就被群臣界定为“受命之符”“符瑞之应”并直接促成光武帝登基;而来历方面,只说是“强华自长安奉”,本未看到与“河”所出“图”有所关联(5)刘珍等著《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纪》曰:“初,王莽时,上与伯升及姊婿邓晨、穰人蔡少公燕语,少公道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子骏也。上戏言:‘何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时传闻不见《赤伏符》文军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与在长安同舍诸生强华自长安奉《赤伏符》文诣鄗,与上会。群臣复固请,上奏世祖曰:‘符瑞之应,昭然著闻矣。’乃命有司设坛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为建武。”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20]。但后来在张纯为光武帝封禅所撰、代表官方意志的《泰山刻石文》[16]3165-3166中,却明确给《赤伏符》添了“河图”两字为前缀,称之《河图赤伏符》,强调光武帝乃是“河洛命后”。
然而划归“河图”,是否就代表东汉官方将之钦定为时世所出河图呢?这便不得不关注另一个问题——光武帝宣布之图谶中缀以“河图”“洛书”之名的诸篇,其实有所谓“本文”“演文”之分,两者并不能等闲视同。《春秋说题辞》曾有“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王者沉礼焉”[17]19429的论调,《隋志》所引说者之言对此有更周详的阐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21]“本文”与“演文”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乃“天文”——上天授予的符命,传为历代圣人王者在“沉璧河洛”仪式后经由“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所得;后者为“圣意”——九圣增演的著作,意旨核心为佐说“本文”。
内容上,据《泰山刻石文》载,《河图赤伏符》载录的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类符命文字,就形态而言俨然是上天所授予的“本文”模样,甚至《后汉纪》也记述了建武五年时人将《赤伏符》载录光武帝天命一事描述为“上之姓号,具见于‘天文’”[22],似该被界定为光武帝所受之本文“河图”。然而现实中却是,王充笔下的东汉时儒并不这么看,才会扼腕汉以来无河图;《隋志》归纳的汉唐传闻也不这么看,综述本文“河图”才会只截至周文王;这意味着东汉官方实际上是把《河图赤伏符》此篇划归九圣增演之作的行列的。
但这又如何解释它的一副“本文”形态及时人的“天文”称誉呢?不妨注意张纯《泰山刻石文》称引《河图赤伏符》等符命文字之后所声明的“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所谓“正文”,指的恐怕不是“所受本文”诸篇,而系九圣增演之作中,被圣人引据解说的河洛文字,例如“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易纬通卦验》)[17]18885,这之中“亡秦者,胡也”便是“《洛书》正文”,“丘以推”云云则是解说之辞。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张纯所称引的其他“正文”相关著述获得印证,例如《河图提刘篇》,《泰山刻石文》称引的是“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之类符命文字,但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能看到此篇至少还囊括“帝季,日角戴胜,斗焜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明圣宽仁,好任主轸”“帝将怒,蚩尤出乎四野”[23][24]226之类的阐说性内容,可知《河图提刘篇》实属圣人增演之作,张纯所引的是圣人据本的“正文”,《御览》所载则是圣人阐说之辞。
换言之,《泰山刻石文》所提及的包括《河图赤伏符》在内之河洛诸篇,实际上都是被划归为圣人增演之作,至于文中征引作为光武帝受命之符的所谓《河》《洛》“正文”,则均非出自光武帝本人受之于天,而是由“前知千岁,后知万事”[18]1063的圣人传下、转达的。未能亲受并不意味此河洛符命非由天授,它只是经由眷顾汉室的圣人——“为汉赤制”的孔子代述而已,即《春秋演孔图》所谓“邱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17]19197者。而既然是从古河图援引而来,这些“正文”与“本文”形态雷同便也理所应当。这也才好解释载录光武帝受命一事的光武《赤伏符》何以竟非源于“王者沉礼”后的“河龙图发”,其实早自它是由“强华自长安奉”的那刻起,就已无缘被划归汉所出“河图”。
综上所述,汉代谶纬语境中,赤刘河洛天命乃是由孔圣转达的,有汉一代确实并未得授河图。而从《论衡·宣汉篇》可知,时儒倾向于认为一代应有一代之河图,以作为世有“圣帝”“致太平”的证明,于是便难免从“方今无河图”引发“汉兴以来,未有太平”的慨叹。
(四)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河图”类型
概言之,河图有所谓古今之分,有“本文”与“演文”之分,“演文”中又有正文与解辞之分。尽管同称“河图”,但汉儒本身对其中的概念分别与类型分野却有着清晰认知,并未混为一谈,然而具体所指,则需谨慎辨析。基本上,谶纬语境中,“河图”通称所可能指示乃至兼辖的对象,大抵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河图,即流传下来的、皇天降予古圣的“本文”,经“王者沉礼”后“河龙图发”而得,主要为帝王治平的受命录符。
第二,今河图,即皇天降予今圣的“本文”,被视作汉世有无圣帝、治化是否太平的最直观明证。有汉一代,未出此类河图,汉人拥有的、用以象征王录的所谓“河图”,实皆为圣人增演之作。
第三,广河图,即流传下来的、圣人援引古图加以条畅增益以广其意的“演文”,如《易纬辨终备》所称“孔子表《河图皇参持》”[17]18877之类。从光武官定图谶“《河》《洛》五九”四十五篇中囊括“三十别篇”的九圣著述即可知,本文类、演文类在当时确同被称为“河图”,而出现在后者篇中被据本解说的古图原文则被视作“正文”。
第四,一般图瑞,例如《孝经援神契》尝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龙负图,地龟出书,妖孽消,景云出游”[17]19496,此类明显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仅作为普遍祥瑞之一端来渲染。
大抵上,汉世所谓“河图”,更多是一种类别名称。从这个意义上,它近似一种学科门类。
四、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洛书”
洛书的问题则较河图要再复杂一些。基于东汉官定图谶乃是以河洛符命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河》《洛》五九”中并列的另一半,“河图”所面临的歧义问题自也体现于“洛书”之中,其通称背后同样有着古、今、本、演、正、解诸文之分,这方面可由前文比对而出,兹不赘述。“洛书”尤值得关注是,其与“河图”搭配后,作为迁就方所延伸出的、倾向各异的性质之别。
(一)“洛书”之配对属性的深化
周室顾命陈列东序的诸宝中仅有“河图”而无“洛书”,《论语》《礼记》中的孔子以及《墨子》亦只言“河图”不提“洛书”。战国晚期,出现了与“河图”相配对的“洛书”,而从前引《管子·小匡》的“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依稀可以窥见,这很可能是源自对《墨子·非攻》篇载述的“周文武”天命之应“河出绿图,地出乘黄”的增订,折射了“图”与“书”间及“河”与“洛”间相辅相成的本能诉求。尽管由《庄子·天下》得悉,此一后出“洛书”实被看作为禹所受之“洪范九畴”,但比起其本貌、内涵等个体价值,反倒是“洛书”之于“河图”的配对属性与效应更被青睐。自《周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下,“图”“书”并出、“河”“洛”并言渐成套路,《淮南子·俶真训》的“洛出丹书,河出绿图”[12]157如是,甚至《论语·子罕》孔子原本的、有文可稽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被记成了“河不出图,洛不出书”[11]1942,可见这种配对性的影响之深,仿佛“洛书”的存在,便是为了与“河图”相对相成而出现的。而不难看到的是,在这场配对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中,“河图”始终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作为迁就方的“洛书”,其形态、内涵等方方面面的稳定性自然相对要低。
相比“河图”,先秦“洛书”之于汉人实无甚需要统合的特性,袭取“龟假”以外,仅有的大抵便是循着“大家各有各的河图”的路子,使“洛书”这一客体也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倘再进一步寻绎汉世所称之“洛书”具体是什么,则最为明确不变的特征便是与“河图”相对的存在。稽考存世谶纬佚文,“洛水所出丹书”与“黄河录图之书”,似被理解为“洛书”的一体两面。
第一,洛水所出丹书。其一般以玄龟为使,即《河图录运法》所谓“洛水地理,阴精之官。帝王明圣,龟书出文。天以与命,地以授瑞”[17]19747者也,亦是最常见的认知。《尚书中候》所载黄帝的“东巡至洛,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曰威,赤文像字,以授轩辕”[17]19005、尧的“刻璧,率群臣东沈于洛……赤光起,玄龟负书出”[17]19009、汤的“降三分璧,沈于洛水……黑龟与之书”[17]19017、成王的“顾于洛,沈璧……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17]19026,皆属此类。但亦有以鲤鱼为信使,如《河图挺佐辅》载:“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丈,青身无鳞,赤文成字。”[17]19744毕竟鲤鱼与玄龟同为水精,载递洛水之书亦属应当。至于《春秋纬》的“孔子坐玄扈洛水之上,赤雀衔丹书随至”[17]19167以及《尚书中候》的“洛授金钤师名吕”——“吕尚出游,于戊午,赤人雄出,授吾简,丹书曰:‘命由吕’”[17]19021,19022,则是明白展示了所谓“洛书”的统摄对象,终究是以地理归属为重心的,信使身份是次要。
第二,黄河录图之书。录图有书,《史记》便称“亡秦者胡”便出自“录图”之“书”,谶纬文献于此有更多体现,如《春秋感精符》云:“孔子按录书,合观五常英人,知姬昌为苍帝精。”[17]19332“录书”即“录图”之“书”,所指文本盖即载于《洛书》的“成姬仓,有命在河,圣”(《摘亡辟》),孔子因此而“知姬昌为苍帝精”[17]18799。《春秋纬》亦尝称“周图变书”[17]19151(按:“变书”乃“洛书”别称,详见后述)。从这点上,“书”更似对“图”的阐述与补充。
(二)“洛书”之对等与附属特性
若说“洛之丹书”乃是“河之录图”的对等存在,则洛书的“河图之书”此一定位,就隐隐透露出一种地位上的主次——书以辅图的意味了。实际上综观谶纬中对“河图”“洛书”的界定,原就同时存在着对等与主次这两种论调。
所谓相等,即《易纬是类谋》“河龙洛图龟书,圣人受道真图者也”[17]18924、《春秋说题辞》“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王者沉礼焉”之类,河图、洛书,皆帝王圣者授受之应[17]19429。然而两者完全重复的功能使其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于是作为迁就方的“洛书”其内涵也随之而变,如《洛书灵准听》所称,黄河于“王道和洽”之时“吐图佐神”,“接河合际,居中护群”的洛水则分辨情况,究竟是“帝王明圣,龟书出文”抑或为“逆名乱教,摘亡吊存”[17]19781。前者于功效上基本与“河图”混同,后者则是独属“洛书”的特性,其与“河图”的区别,大抵便如《易纬是类谋》所言:“河出录图,洛授变书。”[17]18926河图承载的主要只是“帝王录纪”“兴亡之名”,而洛之“变书”,《尚书中候》的这段记载颇能见其特质:“汤东观于洛云:‘寡人慎机。’降三分璧,沈于洛水……黑龟与之书,黄鱼双跃,出跻于坛。黑鸟以雄,随鱼亦止,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子,商灭夏,天下服。’三年天下悉合。”[17]19017即革变的天意之书,载录改朝易代相关天命。亦即,河之录图,洛之变书,前者为正、为常,后者为异、为变,各有所司。然而为正、为常,实际上就是“为主”,为异、为变极容易落入“为辅”,形成地位的主次差异。
所谓主次,指“洛书”次于“河图”,于两方面体现得尤为显著。首先,在“洛书”作为“变书”方面,《春秋纬》尝称“周图变书”为“赤雀所衔烛下授文王”者,此处“周图”无疑指周室所受“河图”,而“变书”显然被“周图”所统辖,以“洛书”为“周图”之“变书”。其次,谶纬界中还有一种尊“河图”而将“洛书”界定为“假驱”之征的说法。偏重“河图”的倾向,在《易纬是类谋》的“天以变化,地以纪州,人以受图,三节共本,同出元苞”中就已相当分明,至于洛书假驱之说,同书亦曰:“《洛书》假驱,缀渐霸,考龟兴之……”“艮气不效,假驱之世。”郑注云:“假驱,谓在际之代间若秦者。缀渐,言皆有国录,不能纯耳,各繇在尧河洛,穆公授白雀之书,是霸(6)《尚书中候》有《觊期》篇,是“论证秦当为霸者的篇章”,其云:“泰伯出狩,至于咸阳,天震大雷。有火流下,化为白雀,衔录丹书,集于公车。公俯取书,书曰:秦伯,霸也。讫胡亥秦家世事。”详见《纬书集成·解说·关于〈尚书纬〉〈尚书中候〉》,载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郑杰文、李梅训等整理:《两汉谶纬文献》,收自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30页。[25],若因之齐桓。考龟者,谓有名在《洛书》。”“霸在王者之间,故其异不以五行之数也矣。”故《易纬通卦验》载孔子曰:“秦为赤躯,非命王。”《尚书中候》的“皋陶于洛见黑书”云云,亦是建立在洛书次于河图的基础上的[17]19151,18921,18921-18922,18928,18885,19008。
(三)“洛书”与“河图”的相错游移
上述所论种种,似都说明了“河”“洛”各自之间或许所指复杂,但彼此间是有确凿分野的。而事实上,从谶纬文献的叙述来看,河洛图书的界限相当模糊和紊乱。
首先是共通性,如《河图挺佐辅》的“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7)《纬书集成》《两汉全书·两汉谶纬文献》皆从《御览》作“圣人所纪姓号”,然而《艺文类聚》《广博物志》《古微书》等均作“圣人之姓(号)”,当从后者。[24]209、《尚书纬》的“河洛之符,名字之录”与《易纬是类谋》的“河龙洛图龟书……必提起,天下扶”——“言图书必显起者之名姓,及所出之地”[17]18967,18924,皆浑然不见河图、洛书之间有何区别。
其次是混同性,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河出龟书——“汤沉璧于河,黑龟出,赤文题”(《尚书中候》)[17]19017,比如洛出龙图——“黄帝游洛,至翠妫之泉,龙图兰叶,朱文授之”(《河图》)[17]19640,比如龟出图——“尧时与群臣贤智到翠妫之川,大龟负图来投尧”(《河图挺佐辅》)[17]19744,比如龙出洛——“黄龙从洛水出,诣舜前,鳞甲成字”(《河图挺佐辅》)[17]19745,等等不一。
这种混淆甚至还体现在古史传说的记载上,例如仓颉的造字究竟是基于“河图录字”抑或是“洛龟曜书”,《春秋元命苞》与《孝经援神契》各执一词[17]19223,19502。而就存世的谶纬佚文来看,图谶中众河、洛间在内容上亦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差异,反而还偶有文字雷同之处,朱长圻即曾有“河洛二纬,出入互错久矣”[28]之语。
其实在河、洛之流与别的问题中,“洛书”更多是作为一个配合体,往往迁就“河图”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时游移。与其说是河、洛相错,毋宁说是“洛书”更多时候并没有很明确的自我。
五、小结
东序河图失落后,时人对“河图”的了解便不免基于传闻与揣度,《论语》《礼运》《墨子》《管子》《易传》《吕览》等先秦文献提及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各自或同或异的特性认知。而汉人在谶纬文献中所勾勒、描述的“河图”,为取信于世,遂整合出一个兼综全部既有属性的形态,并将“河图”从一个独特的宝器扩大为已形成种类的信物,甚至演化为学科门类。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所谓“河图”,有古今之分,又有“本文”与“演文”之分,其中,“演文”中又有正文与解辞之分。因此在“河图篇目,已甚繁复”的时代语境下,在《河图赤伏符》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仍不妨碍汉世时儒有着“方今无河图”的公论,因为《河图赤伏符》实则被划归为圣人增演之作,乃“为汉赤制”的孔子所代述,并非出自光武帝本人“王者沉礼”后的“河龙图发”。尽管同称“河图”,但汉儒本身对其中的概念分别与类型分野却有着清晰认知,并未混为一谈,后人则须审慎辨析。
汉世“洛书”一称同样有着古、今、本、演、正、解诸文之分,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与“河图”搭配后,作为迁就方所延伸出的、倾向各异的性质之别。战国晚期始出的“洛书”,很大程度是基于“图”与“书”间及“河”与“洛”间相辅相成的本能诉求,其被看作禹所受之“洪范九畴”。但在图书并出、河洛并言的配对套路中,“河图”始终占据主导,“洛书”作为配合方往往迁就“河图”的情况而变,或者说“与河图相对”即是其最为明确不变的特征,谶纬中“洛水所出丹书”与“黄河录图之书”,被理解为“洛书”的一体两面,而“洛之丹书”尚属对等,“河图之书”就已有主次——书以辅图的意味了,遑论谶纬界中还有一种尊“河图”而将“洛书”界定为“假驱”之征的说法。谶纬文献中的“洛书”与“河图”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混同性,与其说是“河洛二纬,出入互错”,毋宁说是“洛书”缺乏明确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