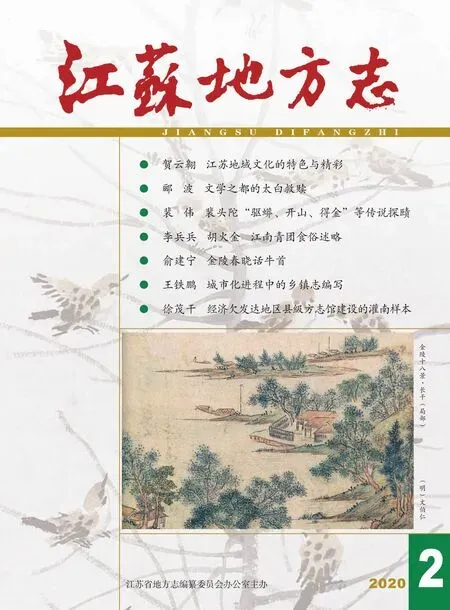《至正金陵新志》的修志思想与修纂体例
2020-12-06韩章训
◎ 韩章训
(浙江衢州324002)
提 要:《至正金陵新志》是元代方志中的名志佳作。方志学界以往对于元志界名家张铉及其所纂名志《至正金陵新志》的研究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文章从方志史的角度,对该志修纂者的思想从主纂素质、编纂义例、体裁运用、记载原则、志书续修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总结,认为其中对续志和城市志的编纂见解尤为独到,于古今编修续志皆有借鉴意义。在谋篇总体思路上,《至正金陵新志》虽然仿效宋代《景定建康志》,但在具体设目中做到了因创有机结合,但志书辅文编纂体例存在不足。
成书于元末的《至正金陵新志》(以下简称《金陵志》)15卷,张铉主纂 。《四库全书》误标为《至大金陵新志》。此志为续宋代《景定建康志》(简称《建康志》)而作,体例谨严,颇具特色,堪称元代续志和城市志之佳构。《四库全书总目》誉之曰:“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1]如此称誉是完全从一般府志编纂角度来立论的。若从续志和城市志编修角度去审视,更是有其独到之处。如注意选择续志续接对象,详载城市,注意反映本城特点等。
一、修纂者修志思想
这里所言“修纂者”是一个集体概念,含主修者索元岱、主纂者张铉和集庆路总管府。索元岱方志思想体现于其《金陵新志序》一文中,张铉的方志思想体现于其《修志本末》一文中,集庆路总管府的方志思想体现于其《修志文移》一文中。综观他们的方志思想,主要有如下诸端:
1.主纂素质说
《金陵志》修纂者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认为担任《金陵志》主纂必须具有“博物洽闻”“学问老成”“词章典雅”和“作事不苟”诸条件。主修索元岱曰:“予闻张君博物洽闻,而作事不苟。”[2]这里所言“张君”指《金陵志》主纂张铉。集庆路总管府所颁《修志文移》亦曰:“续纂新志,非仗大手笔,未易成就。近闻陕西儒官张用鼎,名铉,学问老成,词章典雅,必得其人,事能就绪。”[3]由于张铉具有“博物洽闻”“学问老成”“词章典雅”和“作事不苟”诸条件,所以才被聘担任《金陵志》主纂。
2.编纂义例说
所谓义例包括修志思想和体例两方面。“义例”作为方志编纂学的一个学术用语,是元代严德元首先提出来的。他论《奉化县志》编纂曰:“仇泰然旧为青人,周美成旧为汴人,而子孙皆生长于此也。此不书,故书之义例也。”[4]张铉继承前人思想,率先对修志义例问题进行理性探索。他在《修志本末》中论及写作主旨问题时说:“至于事文重泛,非关义例者,本志既已刊行,不复详载。”一方面,他认为在修志思想上,当以孔子《春秋》为宗,即所记之事必须有意义于“天下”。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诸侯史也。《乘》《梼杌》缺亡,不可复知。以《春秋》经传考之,诸所记载,或承赴告,或述见闻,其事有关天下之故者,虽与鲁无预,皆书于册。其非义之所存,及闻见所不逮者,虽本国事,亦或弃而不录。”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志书体例上,当以《春秋》《史记》为宗。他说:“修《景定志》者,用《春秋》《史记》法,述世年二表。经以帝代,纬以时地、人事,开卷了然。与《建康实录》相为表里,可谓良史,而戚氏讥其年世徒繁,封画鲜述,所作续志悉芟去之。”[5]由此可见,张铉在修志方法是主张以史法为宗的。
3.体裁运用说
张铉对于志书体裁运用问题有三个观点。其一,强调图文并用。张铉说:“古之学者,左图右书,况郡国舆地之书,非图何以审订?”他鉴于戚氏志“屏却旧例,并去其图,览者病焉”之弊,故所修《金陵志》“一依旧例,以山川、城邑、官署、古迹次第为图,冠于卷首,而考其沿革大要,各附图左以便观览”。这些话语都表达了张铉关于图文关系的正确看法。其二,主张综合运用各种体裁。张铉认为,志书基本体裁就是图、谱、纪、志、传。他总结《金陵志》编纂经验说:“今志略依景定辛酉周应合所修凡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图、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张铉在《金陵志》编纂中,辅文体裁也有所创新。如于卷首录存《修志文移》,创设修志《职名》表、《新旧志引用古今书目》。此外,张铉还首次说明了门类设置无题小序的作用。他说:“除图考、通纪外,表志诸篇各有叙,叙所以为作之意。”[6]这些意见和做法都是张铉对于修志经验的精要总结。
4.记载原则说
张铉对于志书记载着重强调两个原则。其一,传信传疑。“传信传疑”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缩语,意谓记事必须实事求是。传信传疑本为孔子《春秋》记事原则之一,故《谷梁传》称:“《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7]后被人们移用到修志领域。如南宋赵汝謩论修志记事曰:“其义当两存者,不敢偏废,亦《春秋》传信传疑之意。”[8]张铉继承前人思想,也主张修志记事必须奉行传信传疑原则。他说:“今自丙子前,杂稽史传归附后,用戚氏续志及路州司县报呈事迹,附以见闻可征者。辑为斯志,信以传信,疑以传疑。”[9]其二,善恶毕著。在张铉之前,揭傒斯曾肯定往昔志书记善不记恶做法。他说:志书“于政教,所书必录其善而遗其不善。此居其乡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10]张铉则一反常见,率先提出志书记人当善恶并书的新主张。他总结《金陵志》编纂经验曰:“人物志析为世谱列传,皆据前史。纂其名实,钜细兼该,善恶毕著,传末例有论赞。”[11]张铉此说对后世修志有较大影响,为后世明康海等人所肯定和践行。
5.志书续修说
自宋始,随着修志事业的不断发展,学界便开始研究续志如何纂修问题。如南宋景定年间,周应合就把续修任务概括为“补、正、续”。[12]张铉继承先贤余绪,继续探究志书如何续修问题。张铉对此问题有两个新见解。一是关于续志续接对象的选择问题。自宋以降,编修续志多以前一部志书为续接对象。如宋《宝庆会稽续志》就以前部《嘉泰会稽志》为续接对象,《开庆四明续志》就以前部《宝庆四明志》为续接对象。至元代,由于有些地方前志质量有优劣之别,故就产生了编修续志如何选择续接对象的问题。张铉曾述金陵旧志状况曰:“至顺初元,郡士戚光纂修续志,屏却旧例,并却其图,览者病焉。今志一依旧例,以山川、城邑、官署、古迹,次地为图,冠于卷首,而考其沿革大要,各附图左,以便观览。”[13]张铉此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郡士戚光”所修金陵“续志”质量低劣,不可作为金陵续志的续接对象。二是说《景定建康志》质量甚佳,当以此志为续接对象,即“今志一依旧例”。此言“旧例”即指《景定建康志》之例。二是关于对于前志的扬弃问题。张铉认为,后人在编修续志时,对于前志应该有扬有弃或有因有创。他在论及《金陵志》与前“周氏、戚氏二志”关系问题时说:“惟《景定志》五十卷,用史例编纂,事类粲然。今志用为准式,参以诸志异同之论,间附所闻,折衷其后。”又说:“历代以来,碑铭记颂、诗赋论辨、乐府叙赞,诸作已具周氏、戚氏二志,不复详载。今辑其篇,第志于古迹卷中。”[14]张铉这两段话均含扬弃或因创有机结合的意思。张铉这两点意见,于古今编修续志皆有借鉴意义。
二、《金陵志》的修纂体例
南宋周应合纂《建康志》,采用纪传体,成为一代名志。张铉纂《金陵志》“略依景定辛酉周应合所修凡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有。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规。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15]《金陵志》在谋篇总体思路上,虽然仿效《建康志》,但在具体设目中还是做到了因创有机结合。对此问题,可从如下两个层面去认识:
1.正文编纂体例
《金陵志》篇目设置主要采用三法。其一,改称或合并。如将《建康志》之《留都录》《城阙志》并入《古迹志》,把《儒学》《文籍》两志并为《学校志》,改《武卫志》为《兵防志》,析《风土志》为《古迹》《民俗》二志。其二,重列或新增。如将《建康志》之《官守志》十五目并为《历代官制》《本朝统属官制》《题名》三目,在《疆域志》中增《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三目。在《人物志》中,删《正学》《直臣》二目,增《仙释》《方技》二目。改《儒雅》为《儒林》,改《隐德》为《隐逸》,改《贞女》为《烈女》等。其三,创设《论辨》一门,内分《诸图论》《奏议》《辨考》三目。从总体上看,如此设置篇目,还是合乎道理和与时俱进的。尤其是把原《留都录》内容并入《古迹志》,充分体现了编纂者深思熟虑。因建康曾为六朝古都,故《建康志》特设《留都录》,以体现本城特色。至元代,六朝古都已经完全沉淀为一种文化古迹,故《金陵志》编者把原《留都录》内容并入《古迹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此外,还把原《儒学》《文籍》两志并为《学校志》,把《风土志》析为《古迹》《民俗》二志,把原《官守志》十五目并为《历代官制》《本朝统属官制》《题名》三目,在《人物志》中把《儒雅》改为《儒林》,把《隐德》改为《隐逸》,把《贞女》为改《烈女》,删《正学》《直臣》二目,增《仙释》《方技》二目,在《疆域志》中增《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三目等,亦皆显得更为合理和科学。当然此志在篇目设置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一些小目设置还有欠合理和科学之嫌。清《四库全书总目》“金陵新志”条曾批评说:“其书略依周《志》凡例,而元代故实则本之戚光《续志》及录、州、司、县报呈事迹。其间如官属姓名已入前志者,不复具录。而《世谱》《列传》则前志所有者仍捃载无遗,体例殊自相矛盾。又其凡例中,以戚《志》删去地图,不合古义,识之良是。至于《世表》《年表》,则地志事殊国史,原不必仿旁行抖上之法,转使泛滥无稽。《戚志》删除,深合体例。铉乃一概訾之,亦为失当。”[16]应该说《四库全书总目》如此指陈不当之处,是基本正确的。
2.辅文编纂体例
《建康志》编者很注意志书辅文的设置问题。其卷首依次设有《序言》《进建康志表》《献皇太子笺》《修志本末》四种辅文。此志这种辅文设置的创新,颇具学术意义。《金陵志》编者继承和发展《建康志》辅文设置之例,在卷首依次设置《序言》《修志文移》《职名》《修志本末》《新旧志引用古今书目》五种辅文。其中创设职名、引用古今书目两种辅文最具学术意义,广为后人所效法。其中所设辅文《新旧志引用古今书目》有不成熟和欠科学之嫌,倘把《新旧志引用古今书目》易为《引用古今书目》那就恰到好处了。因为所言“新旧志”已经超越新修本志范围。其实把新旧志引用书目汇在一起,不仅在实践上很难做到,而且对于新志读者来说也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做法,清末朱绪曾就曾有异议。他认为,如此做法有“虚列”书目之嫌。他批评说:《金陵志》“前列《新旧志引用书目》,然陶弘景《古今州郡记》《帝代年历》、萧大圜《梁旧事》、庾秀才《地形志》、明克让《古今帝代记》《丹阳尹传》之类,元时未必存,亦未见引用。又《金陵百咏》注曾极、陈岩二家,曾诗见《景定志》,陈岩《百咏》,新、旧志不见一首。何以虚列其目?”[17]朱氏如此评说是很有道理的。
此前方志学界,对于元志界名家张铉及其所纂名志《金陵志》虽有一些研究,但这种研究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为促进对张铉及《金陵志》的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谈点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