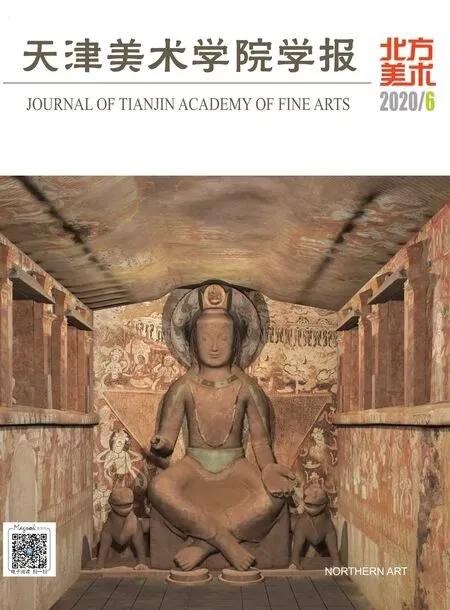宋代“夺真”观下的写真与传奇
2020-12-06文依依WenYiyi
文依依/Wen Yiyi
一、应运而生的“夺真”观
中国古代“写真”的历史十分悠久,现在已知且存世的写真作品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长沙地区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画中人物即为墓主人的形象。到了汉代,写真进一步发展。《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毛延寿等一批汉代宫廷人物画家,毛延寿就是写真高手。汉代有图绘功臣的传统,汉宣帝时有麒麟阁十一功臣像,通过画像来“成教化、助人伦”。到魏晋时期,有顾恺之、张僧繇等大师,出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人物画理论,写真得以长足的发展。至唐宋两朝,写真发展迅猛,最终走向了成熟。但唐代写真沿袭汉代旧制,其服务对象主要为王亲贵族,百官贤士,到了宋代,写真对象才延伸到底层百姓。南宋时,更有赵君寿在临安水埠边为人写像,“争求写真者,无日间断”[1]。说明写真已经进入商业的行列,成为宋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画继》等宋代画史著作的记载,擅长写真的画家便不下几十人,如王霭、牟谷、朱渐、朱宗翼、尹质、释元霭、释维真、徐涛、王思恭、张森、刘纳、王温叔、郭拱辰、王三锡、唐子良、叶光远等,更有许多无名画家。宋代写真相较以往,还出现了正面像,顾恺之传神理论也有新的发展。[2]文人士大夫也积极参与到了写真的探讨中,画像与立赞成为文人们乐此不疲的一种游戏,以及社会文化形式与公共表述的媒介。[3]
“夺真”观正是在这样热烈的写真氛围中产生的。“夺真”一词,主要用来赞扬肖像写真的逼真,苏轼《与何浩然书》云:
人还辱书,且喜起居佳胜。写真奇绝,见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夺真也。[4]
又《记子由论画》:
似尤可贵,况其真乎。……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尝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此言真有理。[5]
诚然,此处的“夺真”,寓意仍十分单纯,苏轼口中的“夺真”,旨在夸赞画家画像之逼真,画像即为写真。宋代对于真的要求有些近乎今日“照相”。因而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说“写真非是画”[6]150,颇有批评之意。陈郁认为“写形不难”“写照非画科比”[7],宋代写真技法的成熟让写真画家做到写形之准已经相较容易,最难的却是传神。
人物画方面的“传神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刘安提出了“君形”说,《淮南子·说山训》:
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矣。[8]
这里的所谓“君形”,概指精神,超越实体,表明了审美经验已由此前单纯的“形”向逾于言表的“神”深化了。这种对主体精神的认识,还要早于顾恺之。之后东晋顾恺之提出“传神”论和“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主张后,影响深远。
在表现传神上,顾恺之也以夸张、虚构来传神,如《世说新语·巧艺》: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9]
苏轼在其《传神记》一文中转述这一段:“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神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10]这篇《传神记》是用来赞扬当时为其画像的画家程怀立的,借顾恺之来赞程怀立,可见其写真功力很深,最后苏轼直言其“传吾神大得其全”[10],直接点出了写真的重点——传神。
苏轼不仅要求写真要传神,他还指出如何才能做到传神:
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众中阴察之。今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会欠自持,岂复见其天乎?[10]
文中“天”即为“神”,其主要意思是,写真要在暗地里观察对象的言行,以便捕捉神情,更好地传出其人之精神。苏轼的话主要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对人写真。传统的写真方式主要采用背拟的手法,画家根据自己视觉记忆去写真,并不需要面对着真人画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便是采用背拟的手法。
宋代写真方面对传神论阐发最为深刻的还属陈郁,他在《藏一话腴》中说:“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也。……夫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倘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杜甫)之貌而是矣,倘不能笔其风骚冲澹之趣,忠义杰恃之气,峻洁葆丽之姿,奇僻赡博之学,离寓放旷之怀,亦非洗花翁。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7]
总而言之,宋代的“夺真观”不仅强调形的逼真,更强调描绘出人物的精神,最厉害的写真画家创造的画中人甚至会令人害怕,所谓“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
二、作怪的“画中人”
因为过于高超的写真技巧,画中人不仅形象逼真,而且精神上“分夺”了被画者。于是出现了作怪的“画中人”,写真也被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两宋之际的邓椿在其《画继》中讲述了这么一位画家:
朱渐,京师人。宣和间写六殿御容。俗云: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11]
朱渐创作的画中人竟然可以分夺活人精神。这种描述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介绍画家张衡时,所言的“畏写”有些相似: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善画。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或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逐去纸笔,兽果出。[12]
“骇神”十分惧怕写真,而害怕的原因未曾明面点出,而在记载中,它“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当是百邪不侵,但却对写真如此恐惧,颇有自己怕自己的意味。这种神秘夸张的描述显然是用来形容张衡绘画功力的高深。回到《画继》,邓椿引用了民间对朱渐绘画能力的评价“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他或许不认为朱渐创作的画中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夺尽精神”。但通过这种民间“迷信”般的俗语可以充分表现朱渐的写真能力之高超。
画家创作的画中人可以分夺真人的精气,而三十岁则作为一个分水岭。这大抵与《论语·为政》上认为“三十而立”[13]15有点关系,《论语》中道:“不知礼,无以立。”[13]242由此推测,不被“夺尽精神”之人,当是知礼之人。
而“礼”又意味着什么?《说文解字》对其定义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4]据此以观,民众认为只有被画者成长到三十岁,具有了在社会生存与立足的成就与学识,才能抵抗被“夺精神”。
朱渐的例子说明了画中人作怪的怪谈早已在民间被认可。程颐《家世旧事》记载:
少师影帐画侍婢二人:一曰凤子,一曰宜子。颐幼时,犹记伯祖母指其为谁,今则无能识者。抱笏苍头曰福郎,家人传曰:画工呼使啜茶,视而写之。福郎寻卒,人以为“画杀”。叔父七郎中影帐,亦画侍者二人,大者曰楚云,小者为仙奴,未几,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15]
此例中仆从的去世,被认为是“画杀”,后又有侍者死去,更加让程家坚信不疑,这是“画杀”。无论是画杀也好,还是朱渐的“夺尽精神”,都反映了宋人对写真能夺主体生命力、折损生者寿命这一奇妙功能的认同。
在宋代《茅亭客话》中曾记载,一位名为勾生的男子,在游览壁画时对画中女子倾心,引得幽魂相会,进而几乎付出生命的故事:
……其中勾生者即云:某不爱乐,但娶得妻如抱筝天女,足矣。遂将壁画者项上掏一片土吞之为戏。既而各退归,勾生是夜梦在维摩堂内,见一女子明丽绝代光彩溢目,引生于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缱绻。迨月余,生舅氏范处士者,见生神志痴散,似为妖气所侵,或云服符药设醮拜章除之,始得生。[6]119
类似的例子在宋代志怪小说《夷坚志》中颇多。另一则故事则更为直接地展现画家的高超绘画能力:
毛绘,遂昌人,善画入神。常至曾山广仁寺院,其徒不之礼。入佛殿画一妇人乳一小儿于壁角而出。遇夜有儿啼声,怪之。一日绘至,僧语之,绘笑曰“若欲绝之甚易!”乃添乳入口,自此啼声遂止。[16]579
毛绘是宋朝浙江名画家,他的画作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画能通神。在这段资料中,人们把画面上的妇女和小儿显然当成了一个正常生活的人来看待,画卷上的小儿会因为吃不到奶,而像寻常小儿一样发出啼哭声,而更为神奇的是, 当画家满足了他的需求的时候, 他立马终止了哭声。
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画中人故事,一方面说明画师的技艺之高超,另一方面又在说明对于画像能通灵、具有人之精神这一民俗是被当时从天子到庶民都认可的。
所谓“未满三十不写真”,类似的观点还曾出现于杜甫《丹青引》。杜甫在赠与曹霸的《丹青引》中写道:“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17]
这句诗在画学上争议颇多,大多观点认为,这句诗是用以谴责韩干画马失去了马的精神,但石守谦对这句诗进行解读,认为恰恰相反,此处是杜甫赞美韩干之句,其原意是赞美韩干画技之高超,使得画马得到了真马的骨气,从而使得真马面临着“凋丧”的危险。[18]此处提及画中的对象虽然不是人,但反映出来的观点还是一如既往:高超的绘画技法、形神兼备的画作是有可能夺走人物的精气神。
在萧兵《图像的威力:由神话读神画,由神画解神话》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典故:相传秦始皇与海神见面,海神警示秦始皇不要描绘其肖像,但是跟随左右而去的鲁班却在见面中途忍不住偷偷用脚摩画了其面容,导致海神勃然大怒,引发灾祸。[19]萧兵表示“初民或认为:形象是生物的一重生命,一副灵魂,一种本性”[19]。这样的观念似乎一直都未过时,人民朴素地相信着。1869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到中国摄影时,不少人认为,照相是剥夺健康的,甚至会猜想照相机是否会收入人的灵魂。因为当时的照相机拍摄时总是伴随着强光和烟雾,拍出来的相片上成像出一个和被拍照者一模一样的小人,因而,照相机是“锁魂机”的说法便不胫而走了。这种认知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扰,以当时的皇室贵族恭亲王的反应为例,身为贵族的恭亲王,在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甚至流露出一丝惧怕的神情。[20]
宋代画史中记录的志怪、民俗小说中的画中人,抛开赞笔和迷信的外壳,是对宋代写真“形”与“神”并重的最佳佐证。
三、传奇画家的消失
宋代之后,似乎很难再找到如朱渐、毛绘这样有名有姓的传奇画家了。明代唐寅创作了大量人物画,好事者将毛绘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传言,唐寅在浙江嘉兴参加朋友婚礼,在闹新房时,于空壁上绘了一幅与毛绘题材完全相同的画,后婴儿啼哭,唐寅在乳尖又添一笔,让婴儿能吮吸母乳,才止住哭声。[16]580这样的故事并不见于画史,元明清三代画史著作中也再难见到对写真画家的传奇描述。只有几处转引《画继》中对朱渐的评价,如明杨慎《画品》云:“未满三十,不必写真,恐夺精神也。”[21]清代诗人屈大均有诗《乞顾生写真·其二》云:“三十重过好写真,不愁朱渐夺精神。”[22]
相反两段有关画家招魂写生的另类例子,将传奇画家引到了极度“迷信”的方向: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宋宪使荔裳琬,幼失恃,每忆母夫人形容,辄泣下。吴门某生,有术能追写真人,殁数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设坛净室中,自书符咒三日,陈丹青纸笔,令宋礼拜,出,扃铺其户,戒无哗。比夜,忽闻屋瓦有声,已夜分,闻掷笔于地铿然,一屋瓦复有声。生乃开户,引视之,灯烛荧然,丹青纵横,笔落地上,而纸仍缄封未启。启视,则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过六十年则不复可追也。[23]
清王逋《蚓庵琐语》也有类似的故事:
崇祯甲申,有吴江薛生号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术又善写照。其法书亡人生死忌,结坛密室,悬大鉴于案南,设胡床于案下,持咒焚七七日,视鉴中烟起,亡魂冉冉从案下而升,容貌如生,对魂写照毕,魂复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24]
两段记录都是在说画家既能施法追魂,又能对魂写照,但功力有所不同,一者可画去世六十年以内的,一者只能画去世四十年以内的。此种事情颇为传奇,但却已经变味,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并没有得以体现。
传奇画家消失,但是关于写真的神奇故事却越发屡见不鲜。在冯梦龙、蒲松龄等人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的画中人的故事。画中人成为志怪小说重要的母题,如,冯梦龙《情史·薛雍妻》中记载:
乡人程景阳夜卧,灯未灭,见二美女绾乌云髻,薄妆朱粉坐于旁。戏调备至,加以狎媟。程老年已高,略不答。二女各批一颊,拿撼之,乃去。明日视之,伤痕存焉。儿曹不知何怪。久之,乃辟所卧枕屏,方于古画绢中得二女,盖为妖者。亟焚之。传云:“物久则为妖。”若画出名手,乃精神所泻。如僧繇、道子,笔笔通灵。况复以精神近之,安得不出现如生也。[25]
画中人作风且不论,文中“若画出名手,乃精神所泻”与“夺其精神”,一夺一泻,皆是精神作祟。《聊斋志异》中类似的例子也有不少,如故事《画壁》《聂小倩》等。这些故事都不旨在表现画家的传奇,而是借由画中人来讲人世间的情爱百态。
当然传奇画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宋之后写真画在技法和理论上的落魄,相反,宋以后,写真技法仍在稳步提升与发展,明末清初,写真技法融入西洋画法,使得在形似上更进一步,而写真方面论著也并不少,如元代王绎《写像秘诀》,清代蒋骥《传神秘要》、丁皋《写真秘诀》等都是重要的写真论著。只是在壮大的山水画科和花鸟画科面前,写真一科实属小科,再也不能引起文人妙笔称赞了,画像赞随着宋代的灭亡一起走向了衰亡。
四、结语
宋代写真艺术上的“夺真”观以及画史、志怪、民俗小说中的画中人传奇,为我们形象地揭示了宋代写真绘画重“形”更重“神”的观念。画中人的母题也在宋之后的小说中得以继续发展。而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兴起的画像赞自宋之后也不再流行,人物画让位于山水、花鸟画,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几乎再难以见到宋式传奇画家的记载。
注释: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19.
[2]大廓.传统写真发展述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1):70-84.
[3]陆敏珍.宋代文人的画像与画像赞[J].浙江学刊,2019(02):208-215.
[4]〔宋〕苏轼.苏东坡全集(5)[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773.
[5]颜中其.苏轼论文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209.
[6]〔宋〕钱易,黄休复.南部新书·茅亭客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陈郁.藏一话腴外编卷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5册:569.
[8]〔汉〕刘安.国学典藏·淮南子[M]. 〔汉〕许慎,注,陈广忠,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00.
[9]〔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6.
[10]东坡文选·东坡诗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32.
[11]〔宋〕邓椿.画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5.
[12]王汝涛.太平广记选(下)[M].济南:齐鲁书社,1987:235.
[13]〔春秋〕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14]〔汉〕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2.
[1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657.
[16]卢润祥,沈伟麟.历代志怪大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7]曾祥波.杜诗考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13.
[18]石守谦.风格与事变——中国绘画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2.
[19]萧兵.图像的威力:由神话读神画,由神画解神话[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19.
[20]徐佳宁,约翰·汤姆逊.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J].紫禁城,2011(03):100.
[21]〔明〕杨慎.画品[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22]〔清〕屈大均.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1)[M]. 陈永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39.
[23]〔清〕王士禛.池北偶谈[M].文益人,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7:395.
[24]岂水.谈何容易:历代笔记中的艺苑风采[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20.
[25]〔明〕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3: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