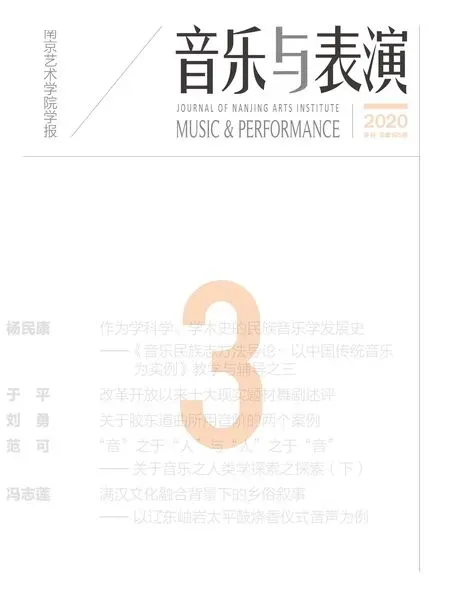汉代乐舞演进及《舞曲歌辞》文本生成①
2020-12-06岳洋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石家庄050024
岳洋峰(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汉代杂舞以庶民乐舞系统为主,兴起于坊间里巷,继而盛行于王公贵族之间。可以说是庶民音乐发展的自然形态,因而并无特有的乐制进行规范。汉代雅舞则在先秦乐舞传统的传承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汉代乐舞的不断发展,促使《舞曲歌辞》文本的形成。结合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许晖认为,汉代乐舞是在“楚声”的基础上而生产的,并且促进了乐器编配的发展;[1]梁海燕通过分析“雅舞”与“杂舞”文本,从而将《舞曲歌辞》歌诗文本的编纂成因进行了再次确认。[2]在此基础上,文章拟将汉代乐舞不断演进为视角,来考察杂舞、雅舞文本的生成模式。
一、汉代杂舞的文本生成
现存汉代杂舞歌辞有《铎舞歌·圣人制礼乐篇》《巾舞歌诗》《淮南王篇》《俳歌辞》四篇,其舞最初皆为民间娱乐所用。就杂舞歌辞的创作方式来看,既有徘倡艺人的嬉游之作,又有出身高贵的帝王所作;就歌辞产生的环境来看,出自闾里方俗之间的作品数量要多一些;而就歌辞的存留形态来看,则出现了“声辞杂写”的情况。
第一,出自方俗之间的杂舞。汉代所用杂舞有《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铎舞》五种,这些最初杂舞产生于方俗之间,后流传到宫廷中,成为宫廷的宴私之舞。《乐府诗集》载:
杂舞者,《公莫》《巴渝》《盘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3]766
《公莫》之舞歌辞本事的由来争议最多。一说为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会鸿门之会时,项伯语项庄:“公莫”,意为勿害汉王,后“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项伯衣袖之遗式。”[3]787一说为蔡邕《琴操》中的《公莫渡河》一曲,非云项伯之舞。从现存《巾舞歌诗》的歌辞文本来看,历经时代泯灭,歌辞已讹异不可甚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认为:“此曲当是西汉人形容寡妇之舞诗,其辞与后人咏陶婴之《黄鹄曲》极相类似也。”[4]278关于歌辞的解读,有众多学者作出了努力。单就歌辞产生来看,其中有“头巾”这一名物,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认为:“所谓‘相头巾’‘头巾’,意思是使用头巾。案,秦汉时,士大夫和贵族戴冠,庶人(平民)戴头巾。”①杨公骥对《公莫舞》歌辞句读、韵脚和章法进行研究,并将舞蹈动作与角色进行析出,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参见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J].中华文史论丛,1986(1)。白平认为:“(《公莫舞》)这篇歌词积谬甚多,其中肯定还有脱、衍、倒等文字讹错的情形存在,尚未被注意到。但是,做到这一步,至少它的基本轮廓可以大致显现出来了。”参见白平.汉《公莫舞》歌词试断[J].山西大学学报,1987(1)。此后,赵逵夫、叶桂桐、姚小鸥等人的文章中对歌辞作了解读工作,却并无定论。具体参见赵逵夫.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J].中华文史论丛,1987(1);叶桂桐.《汉巾舞歌诗》试解[J].文史,1994(39);姚小鸥.《巾舞歌诗》校释[J].文献,1998(4)。平民百姓所用的“头巾”在歌辞中重复使用,可以大致推断出歌辞文本在演唱时是具有较多的民间性的。
《巴渝》之舞,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汉高祖刘邦为汉王之时,命人习巴渝之地的民间歌舞,即为《巴渝舞》。此舞本为巴地特有的舞蹈仪式,经高祖命舞人乐人进行见习之后,遂上升为宫廷所用之舞。至汉哀帝罢乐府员之时,有三十六位巴渝鼓员。《巴渝舞》在汉代是一直流传着的,魏晋时期对还对舞蹈进行了一些改制。
《盘舞》为汉舞,以舞用“七盘”闻名。张衡《舞赋》中“历七盘而纵蹑”[5]见七盘之舞。七盘舞,据《六臣注文选》张铣注曰:“七盘,楚舞。”[6]为起于楚地之舞。马端临《文献通考》:“汉代有橦末伎,又有盘舞。”[7]4419-4420史书中关于橦末伎并无具体说明,大致当和盘舞伎人相类似。《盘舞》大致与《巴渝舞》一样,是起于民间地方的俗舞,后被用于宫廷宴乐。
《铎舞》,《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铎,舞者所持也。木铎制法度以号令天下,故取以为名。今谓汉世诸舞,鞞、巾二舞是汉事,铎、拂二舞以象时。汉代铎舞歌辞《圣人制礼乐篇》中大部分为表声之辞,逯钦立认为:“此曲声辞相杂,不易诠释。”[4]277从歌辞以及史书记载中,亦不能明确歌辞的产生时间。
《淮南王篇》,《乐府诗集》引《古今注》曰:“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并引《乐府解题》曰:“古词云:‘淮南王,自言尊。’实言安仙去。”[3]792据此,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认为:“此则恢诞家为此说耳。不然,亦是后人附会也。”[7]4290整篇歌辞描述淮南王服药升仙之事,或为门客因思恋淮南王而作,抑或为后人附会而作。
第二,帝王亲造的杂舞歌辞。西汉元帝时建昭年间,“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8]3376宫廷之中熟练《鞞舞》技艺之人为数虽然不多,却很受帝王的喜爱。汉代《鞞舞》有歌辞五首,现均已亡佚,分别是《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为东汉章帝刘炟所造。
又据《宋书·乐志》载: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9]551
文献记载中所给出的信息,一为东汉灵帝时能以《鞞舞》而著名的舞人不多,其中要以李坚为代表;二为曹植依前曲改作有新《鞞舞》歌辞五篇,却不能列于黄门之舞,而成为了“陋乐”。曹植所言“陋乐”之称,虽有些谦辞的成分,却所言不虚。但《鞞舞》歌辞既有帝王以及王侯公子所造,其流传的途径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
第三,铎舞歌中有声辞杂写的现象。《圣人制礼乐篇》“邪”“咄”“乌”等明确为表声的字眼,并无实义。表声字与歌辞互为交杂,可以较为明确的将声与辞进行区分。《巾舞歌诗》中,“何婴”“来婴”“何来婴”“意零邪”“意何零”“哺声”为表声辞。其中“哺声”抑或为后人增入的书面说明性文字,意为“此处当有哺喂之声”,因而在整首歌诗与歌辞杂写一处。“转起”“转去”“转南”为舞蹈演出程式的提示词。“明月”“四海”“马客”等为具有实义的歌辞。
声有西音。《圣人制礼乐篇》中的表声辞,清顾炎武《唐韵正》:“以今论之,九麻一韵,亦大抵本西音。故汉时有《圣人制礼乐篇》全以‘邪’字为韵,正如《梵书》所谓‘真言’,而乌孙公主嫁昆弥始有琵琶之制。《世说》王丞相之语胡人曰:‘兰暗兰暗’。”[10]顾炎武将“邪”字音归为麻韵,出自西音。而除了“邪”声字之外,还有“乌”“武”“万”等中原不常用的声字,可以说是西音的代表。而关于“西音”之说,一说以历时性的视野进行划分,为周之音;一说以空间性质来进行划分,为胡音。就汉代社会的郡县划分来看,其中最可能为“西音”之称的,当属胡音。声为“西音”,寄音于舞,可以说是《圣人制礼乐篇》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形成过程。
以上诸首杂舞歌辞,可以说是舞蹈仪式鲜活的文字记录。就整个舞蹈的程式来说,歌辞文本从创作到成为定本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一个向文本过渡的阶段,正如古代“赋诗”仪式一样,在具体的仪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的辅助作用十分明显,尽管在仪式中并不舍弃诗义的表达,但诗承载的内容意义在这一阶段并不彰显。”[11]作为仪式歌辞,其中多掺杂表声之辞,或单纯的表示声音,或为带有指示性的提示用语,均由于时代久远,而无法详细知晓歌辞的原貌。
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影响到杂舞逐步迈向经典化的进程。其一,由于帝王的热衷,以《巴渝舞》为代表的民间普通舞蹈被用于宫廷表演,甚至是被纳入宫廷乐舞系统;其二是帝王亲自造作杂舞歌诗,以汉章帝所造的五首《鞞舞》为代表,帝王参与到杂舞歌辞的创作之中,使得杂舞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三,杂舞进入到了文人的书写系统之中,以傅毅和张衡的《舞赋》为代表,赋作中将盘舞写入赋作长;张衡《西京赋》中在盘舞之外,又花费较大的笔墨对杂舞倡乐的“秘舞”进行铺写。从帝王以及文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杂舞歌辞以及表演形态,均可以看作是杂舞逐渐浸于殿庭的重要反映。
二、《武德舞》的演进模式
在杂舞歌辞以及表演形式之外,汉代的雅舞大多是仿制周代之舞而成。《宋书·乐志》所载:“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9]535周代雅舞在舞蹈仪式上有着较为浓厚的宗教性质,亦多被用于宗教祭祀。雅舞的舞蹈形式与宗教祭祀进行结合,便被保存在祭祀乐舞系统中去,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前代的宗庙祭祀乐舞或有不同。但汉代的雅舞中保留有周代乐舞的旧制,并且这一旧制的因素被继续延续下去。[12]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德》与《文始》《五行》之舞共同奏于高祖之庙,《文始》《五行》之舞分别是经过改作之后的舜、周之舞。
《武德舞》具有考前代而制作的乐舞体例。汉高祖时所作《武德舞》,史书中并未言明是由前代何舞改作而成,但可以推测到的是《武德舞》当由前代之舞改作而成的。可以说,《武德舞》的创制与其他乐舞相同,在因袭前代乐舞的基础上亦有新作。至于所改之舞,很大可能是夏商时期的“干戚之舞”。理论依据是《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武德》者,其舞人执干戚。”[8]138“干戚之舞”由刑天、舜等执干戚而舞之。《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13]《韩非子·五蠢》:“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乃修德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14]《淮南子·齐俗训》亦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僵兵,执干戚而舞之。”[15]《南齐书·乐志》亦载:
汉高造《武德舞》,执干戚,象天下乐己除乱。按《礼》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则汉仿此舞而立也。[16]
同样认为汉高祖时的《武德舞》是对“干戚之舞”的仿制而成的。干戚作为舞器,既与战争之威有关,又预示着战争的胜利。而“武舞”正是具有干戚之舞的“武”的性质,可以说是由干戚之舞发展演变而来的。
基于此,可以认为,汉高祖时所制的《武德舞》与“干戚之舞”同样具有彰显天下大治的“刑德”性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刑德”是杀戮与庆赏的结合体,而汉代君主所要向天下宣示的“刑德”主要是“确立德、刑所在的位置,以趋吉避凶。”[17]《武德舞》在因袭“干戚之舞”的基础上,又有新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是对高祖以武功据有天下的肯定。《汉书·礼乐志》:“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又:“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8]1044《武德舞》以其新作,来“明有制也”;舞蹈模式亦遵循前代的“干戚之舞”,以达到“明有法也”的政治功用。
歌与舞之间是需要紧密结合的,歌诗以咏德行,舞蹈以象事情。音乐与舞蹈之间紧密的结合,构成了乐舞常有的存在形态。《乐府诗集·舞曲歌辞》载:
前世乐饮酒酣,必自起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故知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已后,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世饮酒以杯相属也。灌夫起舞以属田蚡,晋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3]753
“乐”所宣扬的是君主建业之功,而“舞”则是对君主“帝德”的宣扬。汉代《武德舞》,汉高祖刘邦四年(前203)所作,其创作缘由是“秦为无道,残贼百姓,高皇帝受命诛暴,元元各得其所,万国咸熙,作《武德》之舞。”[18]164汉高祖六年(前201),作有《昭容乐》与《礼容乐》,其中《昭容乐》主出《武德舞》,颜师古注引苏林曰:“《昭容乐》生于《武德舞》”。[8]1045以乐配舞的创作模式,体现出对所象之事的生动演绎,“干戚之舞”与《昭容乐》既是如此。
《武德舞》在汉高祖时期创作完成,后舞于高祖之庙;孝景帝时采《武德舞》为《昭德舞》,舞于孝文帝之庙;孝宣帝采《昭德舞》新作《盛德舞》,舞于孝武帝之庙。东汉明帝时期,于世祖庙“进《武德》之舞如故”。[18]165孝章帝时,有司奏请显宗孝明帝之庙与光武之庙“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19]与高庙之舞相同,有《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顺帝薨后,有司奏请:“上尊号曰敬宗庙,天子世世献奉,藏主祫祭,进《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18]113《武德舞》在两汉时期的演进模式大致相似,即后世一般采取遵循前代旧制的基础上进献舞曲。随着汉王朝的更迭,舞曲乐人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也是《武德舞》在演进过程中必须面临的历时性问题,这就要求汉王朝的乐舞系统需要具有更为强大的更新功能。
同时,在舞名方面,西汉时期的《武德舞》经过改编,分别改为了《昭德舞》和《盛德舞》,将《武德舞》进行了重新命名,以示不相沿袭。而东汉时期的《武德》之舞与高祖时期相同,并未有新的改编,可以说是对汉代先王所采《武德》之舞的复归和持守。
在舞容方面,由于舞人的不同,舞姿也会发生变化;时代的更迭也会促使舞程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史书中虽言“如高祖宗庙故事”,并未言明这些由时代、舞人等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在乐舞演进阶段必然要发生的,也是能够加以推测的。在舞蹈行列方面,《东观汉记》载:“节损益前后之宜,六十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18]165用八佾的行列在东汉世祖庙中进行舞蹈,这很大可能是承袭了前代宗庙乐舞的舞蹈行列。曲副八佾的舞数,是天子所用的舞制。这一舞制的目的在于从乐舞本身来彰显天子至尊、至德的地位。这与《汉书·礼乐志》中,“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8]1038的记载本义是相符的。
因此可以说,两汉时期的《武德舞》是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后代或对前代《武德舞》采取承袭的方式,抑或是通过些许改制来证明“不相袭”的乐舞模式。无论乐舞模式改制与否,都不可否认《武德舞》是在周代雅舞的基础上所创制的乐舞形式。从汉初考前代乐舞之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汉代中期至东汉一朝,均对前代雅舞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即便是在东平王刘苍作了《后汉武德舞歌诗》之后的孝和帝时,依然对肃宗孝章帝庙进献《武德舞》。
三、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的文本生成
东平王刘苍《武德舞歌诗》又名《世祖庙登歌》,为了便于与西汉时期的《武德舞》相区分,亦被后世称为《后汉武德舞歌诗》。歌辞作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是现存的有歌辞文本的乐舞歌辞。孝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八月,公卿大臣向孝明帝奏议世祖光武帝庙登歌八佾之舞名。东平王刘苍参与公卿进行商议,认为:
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武畅方外,震服百蛮,戎狄奉贡,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肃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乱,武功盛大。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名宜曰《大武》之舞。……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修之舞,节损益前后之宜,六十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18]164-165
东平王刘苍的奏议在遵循西汉旧制的基础上,对此舞蹈节数进行损益,明帝对此进行了认可。并在同年的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18]165从舞蹈与歌辞创作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当是先有承继西汉而来的《武德》之舞,后有歌辞创作,并被保存在《东观汉记》一书中。
《宋书·乐志》在《东观汉记》的基础上,认为:
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荐之光武之庙。[9]534
《宋书·乐志》将《东观汉记》进行了一些删取,据此,清代钱大昕认为:
《东观书》载:东平王苍议,虽有“宜曰《大武》之舞”一语,而下文即云“不宜以名舞”,其所制歌诗,又仍称《武德舞》,则苍定议,正谓宜名《武德》之舞。所云“庙乐不相袭”者,特谓乐章不宜沿旧辞耳。故明帝诏称:“骠骑将军议可进《武德》之舞如故”也。(沈)休文似未审上下文义,虽删取《东观书》,却失《东观》之旨。[20]
结合《东观汉记》与《宋书·乐志》的两处记载可以看出,钱大昕所言的“《东观》之旨”即是东平王刘苍所定议的《武德舞》之名,其名虽然与前代相同,乐章歌辞却是不同的。“进《武德》之舞如故”亦是在乐章歌辞上依然遵循前代之舞。因此,可以说《武德舞歌诗》是为了与世祖光武帝庙所奏《武德》之舞相配而创制的。《东观汉记》中仅称“《武德舞歌诗》”,“后汉”二字当是后人为了与西汉歌诗进行区分而加进去的。称为“歌诗”,则是《武德》之舞仪式文本形态的体现。
就《武德舞歌诗》歌辞文本来看,整篇纯为四言句式,一章十四句。现录歌辞如下:
於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
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
本支百世,永保厥功。[18]165
将《武德舞歌诗》歌诗文本与《周颂·清庙》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歌诗前六句是对《周颂·清庙》: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21]1257
可以说明东平王刘苍是将《周颂·清庙》进行了改写,具体的创作模式仅仅是对个别字作出了调换。其中“俊乂翼翼”又是“济济多士”的同义之句,仅就前六句来说,《武德舞歌诗》对《周颂·清庙》的因袭比重还是很大的。“建立三雍”以下六句是对东汉光武帝生平功德进行的概括和追述。“本支百世”之句亦见于《大雅·文王》中,“文王孙子,本支百世。”[21]1084“永保厥功”则是对世祖光武帝建立天下秩序之功的颂赞。
在创作模式上,正如东平王刘苍在奏议中引:
《元命包》曰:“缘天地之所杂乐为之文典。”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而诗人称其武功。《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各与虞《韶》、禹《夏》、汤《护》、周《武》无异,不宜以名舞。《叶图征》曰:“大乐必易。”《诗传》曰:“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汉书》曰:“百官颂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18]164-165
东平王刘苍认为,世祖庙登歌当为“称其武功”而作。在具体的创作模式中,则应遵循《诗传》之旨,即用“颂”的模式,用“《清庙》”来作为登歌的范式,这也是符合《汉书》记载的登歌“一章十四节”的句式特征。因此,《武德舞歌诗》开篇即采《周颂·清庙》,在整首歌辞的布局中亦是对登歌“一章十四节”进行了继承,而创作出了十四节的歌诗。
可以说,《武德舞歌诗》主要汲取的《周颂·清庙》的创作思路和文本形制,并对之加入新词进行改造。至于篇幅上较多的超出《周颂·清庙》这一点来看,很大可能是为了与舞蹈的六十四之数相合。《武德舞歌诗》是在对《大雅》《周颂》创作体例进行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而成的。在句式上,承袭了庄严肃穆的四言句式;在祭祀仪式上,是对《周颂》宗庙祭祀乐章“颂”功用的仿制。世祖光武之庙所用《武德舞》,是对前代宗庙祭祀乐舞的承袭。而东平王刘苍所制的带有歌辞的《武德舞歌诗》,这也就否认了“大抵汉、魏之世,舞诗无闻”[7]4353的说法。
小 结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汉代杂舞的舞蹈形式最初产生于民间,是作为庶民音乐系统而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杂舞的音乐及舞蹈形式不断浸染到宫廷乐舞系统之中,与雅舞一道被用于宫廷乐舞之中;杂舞文本的生成模式亦是在不同的舞蹈模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就创作主体来看,上升到了文人乃至帝王的手中。汉代雅舞则主要以《武德舞》为代表,汉高祖时期的《武德舞》是在因袭周秦乐舞的基础上而造作的舞曲,并在不断地更新与演进的过程中,被用于西汉帝王的宗庙祭祀之舞。东平王刘苍所作的《武德舞歌诗》,既是对西汉《武德舞》的继承,亦汲取了《周颂·清庙》的创作模式,并对《周颂·清庙》进行了扩展式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