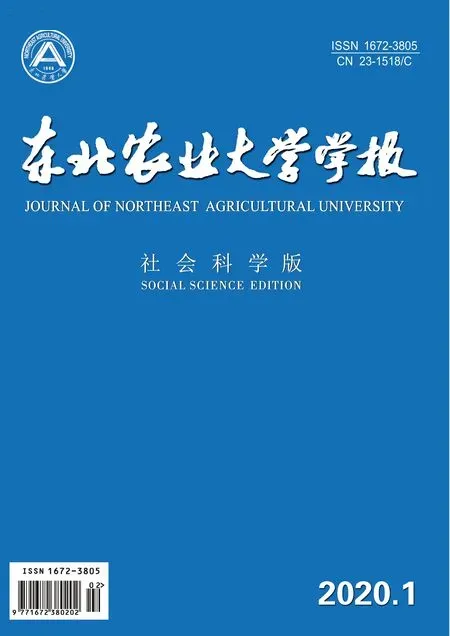困顿与迷失:论晚明性灵派袁中道文学创作转变
2020-12-04贺莉莉
贺莉莉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引言
以袁氏昆仲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的“性灵说”在晚明文学思潮中最为典型,公安三袁此唱彼和、声气相求,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①袁宏道《叙小修诗》评价袁中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反复古姿态,引导文学创新并张扬创作个性,对晚明社会思想文化体系自我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袁兄弟中,袁宗道最长,于性灵说有开道之功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言:“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袁宏道最富才情,是公安派乃至晚明文学新思潮的中坚;袁中道在三袁中年寿最久,于中郎等人身后总结反思整个流派,是公安派最后的擎旗帜者和掌门人。[1]梳理袁中道文学创作历程,可发现极为鲜明的两个阶段:即青年时期的张扬放浪与中年以后的沉郁澹泊,此种反差既源自其独特人生际遇的影响,也体现多元思潮冲击下创作个体的矛盾倾向,透射出晚明文坛变动的历史背影。
相关学者关注到袁中道创作道路转折问题,并就其中某一范围或层面从不同角度对比分析,有的立足文本及思潮研究③戴红贤《袁中道早期诗集〈南游稿〉〈小修诗〉考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5);周群《儒释兼综与小修诗论》,文学研究,1998(8);马宇辉《袁小修与“公安派”之思想变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等。,有的试图挖掘创作个性④刘尊举《袁中道晚年审美旨趣与文学态度转变及成因探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孟祥荣《袁中道: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兼论其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等。,也有人借此探寻公安派衰微的原因及线索⑤周家洪《公安派文学的分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李圣华《京都攻禅事件与公安派的衰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等。等。整体而言,目前已有文献在文体语义层面、文本思想层面研究有余,但对创作转变的阶段性状况及表征,以及变化起伏背后的时代景象和文人心态之间的关联分析尚不深入,从而影响对袁中道个人及公安派历史走向的深入洞察和把握。
作为颇具文学个性的个体,袁中道创作历程转变在三袁中最为显著,浓缩了公安派由兴盛到沉寂的全部历程。本文从袁中道人生历程的阶段性对比切入文学创作研究,立体呈现其所处时代社会生活场景、社会思潮变迁、人生际遇起伏对创作的影响,探讨时代遽变中晚明文坛文化语境下末世文人价值选择的困顿与迷失。
一、早期思想及创作的主要特点
(一)“以豪侠自命”
袁中道天才早慧,束发作诗即有“破胆惊魂之句”[2]。可见其行文风格卓厉张扬,富有创新精神。他曾将世人分为三等:
其一等圣贤,其二等豪杰,其三等则庸人也。圣贤者何?中行是也。当夫子之时,已难其人矣,不得已时思狂狷。狂狷者,豪杰之别名也。……居今之时,而直以圣贤三尺律人,则天下岂有完人?反令一种乡愿,窃中行之似,以欺世而盗名;而豪杰之卓然者,人不赏其高才奇气,而反摘其微病小瑕,以挤之庸人之下,此古今之所浩叹也。[2]——《报伯修兄》
青年时期袁中道的自我人生定位:难成圣人,亦不甘做庸人,当为豪杰。故而与他交往甚深的钱谦益言其“长而通轻侠,游于酒人,以豪杰自命,视妻子如豕鹿之相聚,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一日与居也”[3]。早期文学创作中的豪杰气息,一方面表现为任侠尚义,即不顾世之毁誉,不为饰伪之行,一任本心、卓然自立,颇有其在唐诗中偏好的游侠形象。所交之友亦多负才尚义、放浪形骸的少年才俊,他们危冠绮服、往来游历,视功名唾手可得,视金钱如粪土,此于《回君传》《书王伊辅事》《赠崔二郎远游序》《送兰生序》等文中皆有详述。充满“侠士气”的豪杰风范既宗凭道家放浪派“大器不护细行”之传统,亦效仿同时代王艮以至颜山农、何心隐派“赤手搏龙蛇”⑥见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先生之学,由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之精神,更带有袁中道追随时流的少年意气。另一方面则纵情恣意,常常沉醉于诗酒歌会中的迷狂诱惑与浪情游冶的精神超脱。袁中道自述志向云:“终日谈禅终日醉,聊以酒食为佛会。出入生死总不闻,富贵于我如浮云。”[2]少年时曾与里中豪少余人结为酒社,“相与大叫,笑声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2]。再如《今夕行,同丘长孺、王大壑诸公赋,吋有别意》:
斗酒会。武昌城。歌递代,舞纵横。武昌今夕无限情,为君高歌《今夕行》。一叶飘零寄武昌,武昌城外暂相羊。黄军浦口同飞盖,芳草洲头共举够。九陌三市公子宴,五白六赤少年场。紫蟹如土不值钱,擎出满盘带雪霜。结伴追欢到此夕,天涯兄弟皆来客。我辈意气本豪雄,尊前况有新相识。今夕何夕兴翕习,子夜微歌声转急。击剑人逢击筑人,有情笑与无情泣。天星楼上花枝粲,采珠拾翠杯无算。传说陆郎秣班骓,繁弦急管杂哀叹。君不见黄牛峡朱雀道,山色苍苍水浩浩。此时相逢不尽醉,东西别去令人老。[2]
大量诗文中呈现“豪杰”“奇气”的“健犊子”(《后泛凫记》)形象,个性“简傲直讦”[4],“世烦我简,简则疑傲;世曲我直,直则近讦;同固投胶,异或按剑。夫骨体如此……”[2]“予少时有奇气,相见直坐上坐,扪虱而谭,公待之益恭”[2](《梅大中丞传》),负此奇气,便时时可见“酒后耳热,大骂粉骷髅”的“狂奴故态”(《寄许裕州伦所》)和“醉死便埋我,江山足万年”[2](《携酒登清凉台》)的浪子风流。其时惊世骇俗之论,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
(二)“独抒性灵”的代言者
万历二十四年(1596),受王学左派崇尚张扬个性的个性解放思想影响,袁宏道发展同时期李贽的“童心”说,基于“师心自尚”“宁今宁欲”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作为公安派文学总纲领《叙小修诗》中的主人公,得家门之光的袁中道成为当之无愧的“性灵”重要代言人。
“不拘格套”在于求新求变。早期诗歌显著特点恰如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言,即“多独造本色语”。如《绣林阻风远望》:
雨中新柳净江头,燕子穿花立钓舟。东去湖湘多大泽,春来天地少安流。南平驿路何时尽,北渚风烟渺自愁。石壁沉沉收落日,一痕渔火动沙洲。[2]
新柳、燕子、驿路、风烟等朴素寻常之景之语信口入诗,颇见本色。同时受晚明狂禅之风影响,袁中道文风狂放卓厉,语多险句。如“黑风吹水立,白浪撼山孤”[2](《深公病大作,予亦病,夜述示长孺》),10字之间,陡然呈现一幅江风巨浪图。又“寒江欲雪先无色,起视庐阜如聚墨”[2](《浔阳琵琶亭赋》),凸现出长江山水萧瑟、黯然欲雪的寒冬气象。“插汉千层壁,穿山十里流。天中飞宝阁,松上度骅骝。”[2](《初至恒山纪燕》)如见奇峰绝壁之间的悬空寺,宛若神楼仙宫,凌空危挂。恰如袁宏道评价“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5],凡此“作句”才华[6],皆出自其“立意出新机,自冶自陶铸”[5]的创作旨趣。袁中道早期《南游稿》《小修诗》中,还可见多篇诗歌变体,动辄数百言,最长一首约700言。《登虎丘戏》《示长孺》等均为歌行变体,属有意为之,贵在逆当时文坛拟古潮流[7],为“性灵”文学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样本。
高举“性灵”在于书写真情。袁中道反对复古派模拟剿袭,“束发即知学诗,却不喜为近代七子诗”[2],全力践行公安派“独抒性灵”创作主张,吸收民歌中“不同文而同声,不同声而同气”“慷慨悲怨,如叹如哭”的真情真性元素,主张“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抒其意所欲言”[2]。
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始,袁中道多次参与公安派于北京西郊崇国寺的“蒲桃结社”(葡萄社),创作《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和创作呼应兄长袁宏道“性灵”之学。公安派云者四应,一扫正嘉以来复古积习,文坛一时巍然耸动。如《解说集序》言:
夫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唐宋午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间,有给绅先生倡言复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芜之习,未为不可,而剿袭格套,遂成弊端。后有朝官,递为标榜,不求意味,唯仿字句,执议甚狭,立论多矜,后生寡识,互相效尤……中郎力矫敝习,大格颓风。[2]
可见,中道早期作品充满浪漫的青春气息,挥洒直抒胸臆的自由精神,生动传达出作为性灵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印记和影响,彰显其时、其人与其文之间的契合与互彰。
二、后期创作转变历程及典型作品特点分析
相较于同时期的李贽等思想者而言,袁中道的“狂狷任侠”显然并不纯粹。李贽宁愿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端,也始终矢志不渝,不弃自我主张。反观袁中道,虽有意建构富有独立色彩的本我主体探学求道,但是内心实际并不能实现一贯自持,随着时代环境与人生际遇的起伏不定,其思想及人格心态的矛盾日益凸显。京都攻禅、兄长离世、中年得第以及万历末年的时事乱像,均对步入中年的袁中道产生巨大影响,促使其人格心态与文学创作发生转变。
(一)思潮回落 与世浮沉
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公安派成员固定开展蒲桃结社活动,谈禅赋诗论学、批驳复古派末流,力促文风转变,期间东林党与浙党结成联盟发起攻禅运动。于三袁性灵创作富有启迪之功的狂禅领袖李贽因此入狱,“忽蜚语传京师,云卓吾著书丑诋四明相公(沈一贯)。四明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张问达)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8]而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京师攻禅运动之后,公安派文人团体星散。期间宗道病逝,李贽自刎,与袁氏兄弟情谊笃厚的公安派骨干黄辉、陶望龄牵涉其中,前者归四川南充、后者藏于歇庵。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袁中道随兄袁宏道归公安,栖隐于林下,公安派创新思潮陷入低谷。[9]
“攻禅”事件是整个公安派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的转捩点,给公安派文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10]。袁中道与友人丘长孺书信中言道:
天下多事,有锋颖者先受其祸,吾辈惟嘿惟谦,可以有容。繁华气微,山林气重,终当伴中郎于村落间耳。前者拜李长者坟,泫然欲涕。龙不潜鳞,凤不戢羽,何言哉![2]——《与邱长孺》
政局之凶险,文网之严苛,使袁中道不得不惕然自警,潜鳞戢羽,以求明哲保身,创作中淡去豪侠狂捐之气,代之以对生命存在方式的重新思考和学术思想的重新定位。
首先在思想上放弃自由狂禅,复归心学。在给陶望龄的信中似有反省:
“今之学道者,二十年以前不知有学,二十以至四十,为功名,为诗文,为应酬,为好色,为快活,其杂用心处何多也?偶于一机一境,见些光景,即强附于理须顿悟,舍理行而修事行,何古人之难而今人之易也?”[2]——《答陶石匮》
此时期创作的《李温陵传》中言: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小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籍,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2]
由其对李贽“虽好之,不学之”“可惜可戒”的评价可见,昔日以狂侠闻名的中道,心境转向消沉。论著中开始频现“阳明先生”“龙溪”“近溪”“心斋”“王汝中”“塘南先生”等王学中人[11],“阳明之学,传之淮南而后,近惟塘南先生悟圆而行方,实为摘派,予私淑之久矣。”[2]可见其思想在外向突围受阻、遭受打击后,惶然向内心之地退守。
被后人之称其全面反省之作的《心律》记录此时期思想、心态变化。袁中道在戒律中对己昔所犯分列细目,先戒后悔。针对过往放纵酒色,“以今思之,真非复人理,尤当刻肉镂肌也”;回顾昔日呵斥“世儒”“俗儒”,“缘饰其言以求胜”,或为调笑戏谑而“缩长增短”,或醉后“标已所长”“鼓弄唇舌”[2],皆称妄语。凡此种种,悉应戒之。
但于其内心而言,少年之时的诗酒风流以及讥弹程朱、刻薄七子的恣意谩骂,本为袁中道与其两兄最为快乐适意的时光,此番从心律论角度自我否定,可见些许落荒之征象。
(二)重抒性灵 力振蒤势
小修终生服膺中郎,是袁宏道标举“性灵”旗帜最真诚的支持者和宣传者。自其万历二十六年(1598)作《解脱集序》与江盈科一道呼应袁宏道倡导的文学革新主张,大力挞伐拟古思潮以来,直至五十二岁(天启二年,1622)作《珂雪斋集选序》为止,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在维护这面理论旗帜[12]。
攻禅之后退隐柳浪期间,是袁宏道在世最后一段时间,其深感文网日密而不得不退守,文学主张渐趋于“稳实”,审美情趣渐变为“淡”“适”。袁中道对此颇为赞赏:“潜心道妙,闲适之余,时有挥洒,皆从慧业流出,新绮绝伦。……盖自花源以后诗,字字鲜活,语语生动,新而老,奇而正,又进一格矣。”[2]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去世。令与其感情深厚的袁中道大受打击,悲恸不已。与友人潘景升信中痛言: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遂至于知己同心之慈兄倏而见背。天昏地暗,令人无复生理。自弃捐以来,遂得呕血重症,几不至痊。嗟乎,弟从此如立雪无影人矣![2]凄凉、悲痛之余深切意识到生命之危亡,从而促使其再度参求净土以求慰藉。“中郎去后,世念已灰,愿作一老居士,游行佳山水间足矣,弟往日学禅,都是口头三昧,近日怖生死甚,专精参求。”[2]
与心态转折相应,面对关于公安派日渐增多的非议,在文学领域,袁中道责无旁贷要为其正名。此时,复古主义“倡言排击”的文化语境不复存在,狂飙突进式的心学思潮渐渐平歇,思想和文化界控制愈加严密。袁中道承袭性灵说在宏道“新而老”“奇而正”的基础上,矫正公安派因矫枉过正而致的率易之弊。其在《阮集之诗序》言:
及其后也,学之者浸成格套……先兄中郎矫之,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诗道又复病矣。由此观之,凡学之者,害之者也。多变之者,功之者也。[2]
袁中道重新确立含蓄蕴藉的学古目标,将“任性而发”变为“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诗文规范性上,由袁宏道“不法为法,不古为古”到适度肯定遵“法”、学“古”,在审美立场上由任性狂放到讲求“淡适”,在创作追求上更强调发挥主体“慧”之选择。倡言“情虽无不写,而亦有不必写之情;景虽无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2],以含蓄蕴藉为主,兼之“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的“直摅胸臆”,二者在文本层面实现圆融实际来自于“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显示与七子复古主张部分暗合的趋向[13]。其言“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但愿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诗,而‘令云烟花鸟灿烂牙颊,乃为妙耳’”[2];提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2],与自身晚年遭际一致,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晚明新思潮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的走向。
袁中道晚年曾言:“不敢比于三不朽事,而其意正在三不朽之立言。”[2]可知其后期创作颇有些“以文传世”的压力。以此心态从事创作,很难不受传统诗文理论及主流文风影响。基于此,他偏向贵含蓄、重蕴藉审美趣味的价值取向自然不难理解。但不可否认,“性灵”学说标新立异和狂飙进取的锐气渐趋弱化,推动晚明诗文革新发展的后劲已显不足,公安派性灵精神在文坛衰落,恐与此不无关系[10]。
(三)中年得第 儒释兼综
较之于两兄的功名早成,袁中道的科举进身之路骞滞多磨。长兄宗道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进士,年二十七:二兄宏道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进士,年二十五;而袁中道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庚午方“叨得一第”⑦见《珂雪斋集》中《与愚庵》:“叨得一第,聊了世法”。,时年已是四十七岁。正如其言“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2]。
屡试屡败的无奈结局,令他在落第的阴翳下备受煎熬。钱谦益谓其“操觚立举,怀利刃切泥之叹,久之数困锁院,流离世路,有忧生之嗟。”[3]曾经的浪子才情与名士豪气已逝如云烟,进入仕宦生涯的袁中道但求自适,“弟才入仕途,已觉不堪矣。荣途无涯,年寿有限。弟自谓了却头巾债,足矣,足矣!升沉总不问也”[2]。纵使不问升沉臧否,入仕后普通士子仍需恪守“机关械其内,礼法束其外”[2]的为官之道,应制之作亦终须走向传统,袁中道入仕后创作一定程度向儒家思想回归,表现在进一步强调含蓄蕴藉风格及格律法式的规范,审美取向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并力图取得与庙堂文化认可。《珂雪斋外集》卷十二至卷十五多处可见“夫子曰”“曾子曰”,可见,士人无法孤立于其所在群体的集体意识之外。袁中道虽饱经场屋之苦,一旦仕进,内心深处的儒家传统观念则被唤醒,创作风格倾向中和内敛且更重言志。如《赴句曲送校士》:
余睡扰在目,残梦如潺援。山深滴雾露,侵晨弄微寒。乱峰围沃壤,禾穗亦已繁。微官无远虑,身劳心所安。束带非有苦,不敢话归田。散步绮吟间,岂复异乡园。聊作无心云,异患何能干。[2]
《游居柿录》卷十二有言:“河南入贺宪副孟鲁难来话,深言归山之乐。予曰:‘归山果是第一佳事,但终身不出,则可,若归六七年后,宦情不断,后思一出,则不如趁色力强健时,为朝廷出力耳。’”此时袁中道自称“此身现在儒门”[2],因此劝诫同僚当行儒门之事,即“为朝廷出力”[2]。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或因追随两兄而较早体会到政局之险恶、党争之残酷,《后泛凫记》云:“仆于中外骨肉,由登第至盖棺,皆亲见之,作宦之味亦历知之矣。”宗道视为官如冰火聚⑧参见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二》中《独坐》“投身冰火聚,谁能自腾骞”。、宏道所谓官场竟是活地狱⑨参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中《罗隐南》“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袁中道仕宦十年始终徘徊于仕隐之间,时时担忧祸患之将至。如其《与丘长儒》所言:“今将许多出头胜人意思,渐渐销融,便觉偃旗息鼓,有许多太平气象。[2]于是敛却锋芒,随缘认运。如《答钱受之》:
县令于弟不宜,幸有馆选一途可以藏拙。然秘书有限,非不竞之地,恐亦未可必得也。打叠乞假南归,俳徊山水间半年,至明岁秋初来选,乞两京一教职。青毡我家旧物,尤与懒拙之人相宜,大端我辈毕竟是一肚不合时宜,弟入廛数月,已悉知之矣。况世道日下,好以议论相磨戛,即不能效飞鸟鱼沉,为长往之计,而庶几处非仕非隐间,聊以藏身而玩世。[2]
尽管事实上并未因此息机隐世,但能令其安慰余生,在末世王朝生存的动力已非仕途风云。如其病中的自我安慰“燕雀相逢堪自得,懒随黄鹊薄天飞”[2]。不如继续“雅好山泽游”,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淡然自适之趣,与无情有致之山水,两相得而不厌。故望烟峦之窈窕突兀,听水声之幽闲涵淡,欣欣然沁心入脾,觉世间无物可以胜之。”[2]文学创作趋向平实稳妥、澹泊内敛。
以仕为隐的背后,袁中道在佛学修行中亦不乏矛盾与摇摆。袁宏道去世后本立志净修,归隐山林,欲脱离尘缘、于虚寂之中保全性命。而《答王章甫》中则又言:“混俗和光,潜修密证,亦何必独立孤峰,目视云汉,而后为出世丈夫也哉?”[2]将此种修行思路带入其以仕为隐的生活中,事实上即不舍名利之心及诸般情欲,他对此亦直言不讳:“百事减尽,惟不能忘情于声歌,留此以娱余生,或秀媚精进中所不碍耳。[2]”
(四)时局艰危 忧愤难书
万历末年政局板荡,吏治颓废,辽东战事、矿税风波等内忧外患此起彼伏,较之于两兄早逝,袁中道在三袁中相对年寿稍长,其于晚明末世危机感受更深,忧患意识也更为强烈,诗文创作是其精神世界的投射,记录了晚明王朝无法挽回的崩溃轨迹与危机之下末世文人的困顿、迷茫与不安。
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扬、常镇蝗,山东盗贼大起。[14]同年得第的袁中道上谢表,从因果论出发,劝诫君主体恤民生:
夏暑雨而冬祁寒,农家最苦;春省耕而秋省敛,王道宜先。……十二诸侯之旧地,龟诉无遗;七十二泉之乐邦,云稼蔑有……易子而食,并日而炊。渤海多虞,潢池之兵间起。郑圃不治,萑蒲之盗相寻……欲盗息民安,在家给人足。苟衣食之不继,虞锋镝之潜兴……故欲国无忧隙,必须民有盖藏。[2]——《拟上轸念山东饥荒,发帑金十六万,仓米十二万,特差御史一员前往赈济,务令人人沾被德意,廷臣谢表》
作《主术》,以批判立场评价时政得失:
盖天下之纪纲法度,以方守之则可振,而以圆通之则易坏。末世之人心风俗,以方堤之则犹可挽,而以圆通之则益溃。况今日之世道,其趋于圆融也已极。祖宗权于天理人情之中,而垂为典制,岁月寝久,后人狃安计便反以私为经,而公为纬。圆于徇私者谓之通达,方于奉公者谓之迂拙。故政府六曹之用,舍弛张莫适为主,甚且要路之竿牍如山,幸门之金钱如海,胥吏之狡狯如神,先朝典制,日以夷陵。[2]
《用人》指出科举之弊、期待廉吏行政。
盖古用人取人之法,有乡举,有辟署等法,而今皆不能行,所存者止科目耳。夫古之法皆格而不能行,而独科举资格存者,岂法久弊生,而此独无弊欤?非也。科举之法,乃宋学究科也,士为帖括,糊名易字,任有司甲乙之。即有高才博古通今之儒,而不及格,终身不得沾升斗之禄。……然吾以谓天下之才,诚非科举之所能收,士之有奇伟者,诚不宜以资格拘之。[2]
上述多篇文章本是探究匡扶之策,却意外书写出明末“易子而食、并日而炊”的民生,“以私为经、而公为纬”的官场,“高才之儒,不得升斗之禄”的吏治以及王纲解纽的朝局。
他以天人感应观念观察和解释星象和异闻,将万历四十六年(1618)应天府坠流星石、四十七年(1619)怀宁县产怪犬,称之为“兵象”。在《江南灾异考》中写道:“夫天变于上,人变于下,稽之往代,历历不爽,此愚所为惧也。察其所自招,总之皆阳德蕴郁,阴轸肃杀之由。[2]”此二年恰逢明军在辽东遭努尔哈赤重创而元气大伤,将自然异象异事与时局关联,可见其作为末世文人对王朝命运没落的强烈预感。万历晚期朝廷重要官员空缺已十分严重,以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吏、兵两科甚至无人拿印,盲官与贵戚、近待勾结,排斥正人,言官失去作用[1]。袁中道借此提出治乱之策:“急补大僚,释累臣,任台谏。”[2]他在文中发出预警:“其或否鬲之根不化,则朝廷之元气日削;即夷虏可以幸弭,而阳日衰,阴日盛,国家锋镝之祸,政自未艾。欲化妖孽为祯祥,不可得也!”[2]果然未出三十年,明王朝便土崩瓦解。
天启三年(1623)到天启六年(1626)⑩本文依唐昌泰考证结论,袁中道卒年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见唐昌泰选注《三袁文选》附录《袁中道生卒生小考》,巴蜀书社1988年版。不见袁中道作品存世,有学者认为是因其看到王朝日暮乱象频发,复杂烦乱的心态下书写难尽感慨进而放弃了文学创作。[15]就万历末年天启之初士人普遍心态而言,这种放弃来自置身末世的沮丧与绝望,一如晚明国是之不可挽回。因此,袁中道暮年反复引用罗近溪“锦绣乾坤,翻作凄凉世界”语[16],既可形容时势,也是其心态写照。
后期的袁中道文学创作,在个人际遇与时代挤压中,与早期作品的洒脱与狂放相比,更多体现出落寞、守成、惊悸与无奈,前后作品之间的明显落差值得关注和思考。其中固然存在“学以年变,笔随岁老”的世故洞察,却也不难发现创作转折走向中折射出的晚明末世沉疴的挤压与覆罩。
结语:一人之像折射的时代文坛镜像
纵观袁中道一生创作,因思想驳杂而闪现出独特的光彩。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早年受王学左派影响,轻侠尚义、任性放达,与反复古思潮的袁宗道、袁宏道两位兄长在文学创作上同气连枝、共书“性灵”。后半生困顿场屋,在文网打击、亲旧离逝、国家没落等多重绝望中放弃“狂禅”,靠近心学。为官后一定程度回归儒学正统,但因无意事功且心怀忧惧,故而始终徘徊于仕隐之间。从人生经历积淀来看,袁中道文学思想与创作态度的转变实际更源自京都攻禅、兄长离世、中年得第以及万历末年时事乱象等重大影响,使其不得不放弃对性灵文学中最具创新和进取意义的坚守,摇摆于“变”与“不变”之间。加之晚明各类思潮日趋庞杂,袁中道学术思想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斗争性、复杂性、妥协性并存的特点,即佛分禅、净,儒兼心学,亦收老、庄,综合所谓“性命之学”旨在“了生死大事”。[2]这也导致他在出世与济世、清寂与随俗、戒慎与自适、张扬与内敛等多重矛盾之间徘徊不定,表现为既富有清胜之骨,又无意脱离世俗;既非出于事功,却不乏名利之心及诸般11袁中道在《前泛凫记》中言“天下之乐,莫如舟中”,“予在万历己酉,市一小楼船,曰泛凫,取《离骚》中‘泛泛若水中之凫’意也。”情欲。“永远的矛盾,永远的彷徨,永远的进退失据。”[17]恰如其“泛凫”之命名取义“泛泛若水中之凫”。
将袁中道文学创作转型转变的景况置于晚明末世文坛,可以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群体特征。随着晚明政治社会腐败愈演愈烈,文人普遍存在两种强烈感受:一是宗法混乱带来的恐惧,二是道统大崩造成的绝望,二者构成晚明文人身上挥之不去的浓郁末世状态。此时无论社会对其所在阶层价值属性还是文人本身的自我价值认同均达到最低,无法书写时代抱负的现实使其沮丧、压抑困顿、迷茫,陷入无以调和和排解的矛盾中。于此也不难理解三袁创作缘何由高度认同性灵到不同程度做出让步和转变。袁中道之不同在于,他走过整个公安派盛衰的全部历程,需面对更多复杂的浮生事态,他全面感受到万历至天启年间时代风气从开放包容到封建僵化再逢末世危机的多重遽变,晚明日暮的影响更为深刻,其妥协、摇摆以及软弱性在三袁当中最为突出,更具历史镜像的可透视度。因此,袁中道未能扭转公安派衰败趋势,固然与其能力与晚年斗志不足有关,更多还应是时代因素使然。若将眼光扩展到整个明清文学,两百年之后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亦发出同理之言:“一代文人有厄。”[18]可见,选择和道路虽有多种,但文学书写者在时代之“厄”中终究难以突围,他们生命和创作走向颓败是一个群体不可挽回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