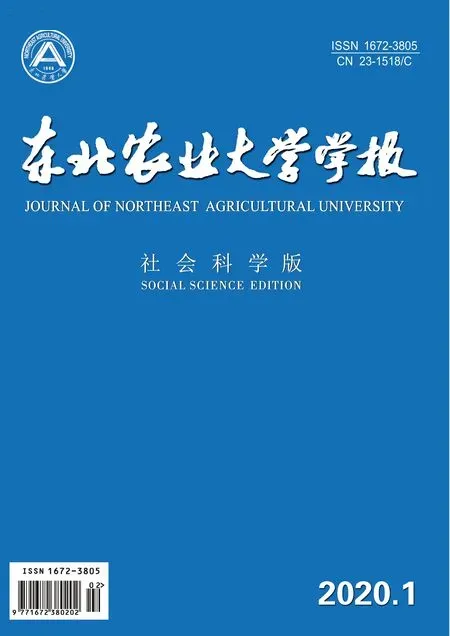入户盗窃罪适用中的疑难问题
2020-12-04赵天水
赵天水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300222
1998年3月10日颁布、2013年4月4日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第4条对“入户盗窃”作出规定①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将其作为“多次盗窃”的情形之一并提出次数要求。不同于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第39条不再将“入户盗窃”作为“多次盗窃”的行为方式,亦不再以“入户盗窃三次以上”作为入罪条件。《刑修(八)》施行后,司法实践中处罚入户盗窃的案例激增,同时也产生诸多疑难问题亟待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2017)云O122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浦某与被害人刘某同住某公司职工宿舍楼内。2016年8月23日上午,浦某窜入刘某宿舍内,盗走刘某放在卧室挎包内的现金1 000余元中的500元②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https://law.wkinfo.com.cn/judgment-documents/detail/MjAyMDUxNTQ2Mzc%3D?searchId=268b9a3947674b659c63a 4b4c942e0d5&index=1&q=%E5%85%A5%E6%88%B7%E7%9B%97%E7%AA%83.2018年10月28日访问。。以本案为引,入户盗窃罪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户”的范围。“户”具有何种特征;对“户”与“住宅”能否同一理解;职工宿舍是否属于入户盗窃中的“户”;能否对入户抢劫、入户盗窃中的“户”作同一解释。
2.对入户目的非法性的判断。入户目的的非法性是仅限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故意还是只要存在犯罪故意即可?如案例二:孙某以偷盗婴儿出卖为目的,乘无人之机,进入赵某家中,后在室内偷抱婴儿时,发现床上有一部手机,遂临时起意,在偷盗婴儿的同时窃走该手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549元)。若将入户目的限于盗窃故意,由于孙某入户时持绑架故意而非盗窃故意,则户内窃取手机的行为难以被评价为入户盗窃;若主张入户时存在犯罪故意即符合入户目的非法性,则上述行为可被评价为入户盗窃。此外,事先有盗窃故意的人欺骗熟人开门,此种经过被害人同意的入户方式能否被视为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如案例三:毛某与王某是好朋友,毛某经常到王某家做客。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某发现王某把存折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存折内夹有密码条,抽屉未上锁。一天,毛某急需用钱,便想到王某的存折,去王某家玩耍时,趁其不备溜入卧室盗走存折,到银行取出800元并使用。
3.入户盗窃既遂标准。在户内取得财物并到达户外时方为既遂,还是只要在户内取得财物即构成既遂,抑或只要非法入户即使盗窃零数额也构成既遂,值得讨论。
4.入户盗窃未遂。案例四:刘某到某村收废品,发现该村王某家无人,遂进入屋内将一台小水泵、一壶食用油装入随身携带的包内。准备离开时,王某返家,刘某见有人回来忙将所盗物品放回屋内,走出屋外即被王某当场抓住。论者认为此时刘某仅构成入户盗窃未遂,不构成既遂[1]。本案与案例一不同之处在于,案例一中被告人已将窃得财物转移到户外,达到控制财物程度,而本案中被告人未将财物带至户外。此时会引发疑问:若被窃财物价值未达到数额型盗窃数额要求,此时被告人是否成立入户盗窃;若成立,行为人构成入户盗窃未遂还是既遂?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入户盗窃是否区分犯罪成立和犯罪既遂;第二,入户盗窃是否存在犯罪未遂。这两个问题本质上属于同一问题,若不区分入户盗窃的犯罪成立和犯罪既遂,也就无需讨论犯罪未遂。在户内窃取财物时被人发现,被告人最终未窃得财物或未将所盗财物带至户外,此时是成立入户盗窃既遂还是未遂?如案例五:彭某驾驶摩托车潜至吕某住处,撬门入户伺机盗窃作案。在进入院子后因未能打开房屋大门,后将厨房门打开,但未发现有价值的财物。其间,彭某被吕某发现,遂弃车逃离现场。同日15时许,彭某返回现场欲取回摩托车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论者认为彭某成立入户盗窃既遂[2]。本案与案例四案情基本一致,但最终结论却不相同,涉及到对入户盗窃既遂标准及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讨论。
综上,围绕“入户盗窃”,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四个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户”的范围;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内容;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入户盗窃的未遂。
二、疑难问题解析
对上述四个问题,理论界及实务界尚未达成共识,给准确适用法律带来疑惑。本文拟以上述问题为线索,以理论观点和实务做法为脉络对疑难问题加以解析。
(一)“户”的范围
1.“户”的特征。根据不同特征,可将“户”分为两类:其一,依据事发时住所是否正在使用,分为“正在使用说”和“不需使用说”。“正在使用说”认为,“户”是正在或可能正在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既包括住所内有人的情形,也包括使用者一时外出随时可能回来的情形[3]。“不需使用说”认为,不要求住所内一直有人居住或行为时被害人在住所中。理由如下:第一,暂时无人居住的住所同样具有“户”的特征;第二,对暂时无人居住的住所实施的盗窃,同样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和居住安宁;第三,在行为人入户实施盗窃行为时,户内是否有人并不影响“入户盗窃”的成立和认定[4]。其二,根据是否需要等同解释入户盗窃、入户抢劫中的“户”,有“对比延申说”“对比等同说”两种观点。“对比延申说”认为,“入户”属于抢劫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但在在盗窃罪中只是定罪要件,因此入户盗窃中“户”的范围应比入户抢劫中的“户”更宽泛,进而将“户”从家庭生活领域延伸至工作领域,强调与外界的隔离性。如集体宿舍、宾馆旅社、临时工棚、办公室不宜作为入户抢劫中的“户”,但可作为入户盗窃的“户”[5-7]。“对比等同说”认为,在同一部刑法典中,入户抢劫中的“户”和入户盗窃中的“户”应是同一含义,其范围也应相同[8-9]。
上述两种观点从不同侧面描述入户盗窃中“户”的特征。笔者认为,应根据入户盗窃侵害的法益理解“户”的特征,因其对认定入户盗窃的着手、既遂具有意义。着手是指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紧迫危险的行为,“户”的不同特征揭示出刑法保护的法益不同,进而影响对着手的判断(是否着手及着手时间)。如“对比延申说”主张入户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是他人的财产权利和家庭生活、工作领域安稳性免受侵犯的权利,此时犯罪人在办公室寻找财物时成立着手。而“对比等同说”主张保护的法益是他人财产权利和家庭生活安稳性免受侵犯的权利,不包括工作领域安稳性免受侵犯的权利,此时犯罪人在办公室寻找财物的行为不仅不能被认定为着手,即使最终控制财物亦不能成立既遂。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住所长期无人居住时若发生入户盗窃行为,依照“正在使用说”无法认定入户盗窃构罪,而依据“不需使用说”则可以认定该行为构罪。
就第一分类而言,笔者认为“不需使用说”较具合理性。入户盗窃属于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内容,通过考量其体系位置及行为方式特殊性,应将其保护法益解释为他人财产与场所安稳性不受侵犯的权利。场所安稳性不受侵犯的权利不因住所内是否有人而不同,因非法侵入会给房屋使用人安全信赖感带来冲击,这种信赖感崩塌并非仅在案发时发生,房屋使用人于事后亦能感知到。“不需使用说”也存在不足。论者主张“暂时无人居住的住所具有户的特征”,其混淆了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同时回避了对“户”的特征的回答。另外,论者认为户内即使无人亦不妨碍认定为入户盗窃,但却没有说明理由。笔者主张“不需使用说”的理由在于该说妥当界定了入户盗窃的法益,即他人财产与场所安稳性不受侵犯的权利。无论场所内是否有人,上述两项权利皆会因非法侵入行为而遭受损害。
就第二分类而言,首先应肯定对比分析的合理性,现行刑法中只有入户抢劫罪和入户盗窃罪将“户”理解为场所。在同一法律中对同一词语的解释应在体系上保持统一性,因此应在对比中解读“户”。“对比延申说”和“对比等同说”均存在可商榷之处:其一,“对比等同说”机械理解体系解释,忽视了“户”在入户盗窃、入户抢劫定罪量刑时的不同意义。但对同一词语作出不同解释,亦是罪刑法定原则下体系解释的必然结论。“同一个刑法用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实亦是体系解释的结果。如果对任何一个用语,在任何场合都作出完全相同的解释,其结论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旨。”[10]应根据“户”在盗窃罪、抢劫罪中的不同意义,判断法益侵害事实是定罪要件还是法定刑加重要件。其二,“对比延申说”把握住“户”在入户抢劫、入户盗窃定罪量刑中的不同意义,在区分定罪、量刑基础上认为“户”在入户盗窃中应作出比在入户抢劫中更宽泛的解释,但理由值得商榷。“户”在入户盗窃中作为定罪要件,在入户抢劫中作为法定刑升格要件,并不能必然得出上述结论。换言之,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对“户”理解上的差异表面上来自于“户”对定罪、量刑的不同影响,实质上来自“户”在各自定罪量刑中所彰显的法益侵害程度不同。立法并未将入户盗窃规定为数额犯,但却将其与数额型盗窃等同处罚,司法实践中盗窃零数额但定罪处罚的案例颇多,这充分说明“户”的特征足以担负起不足数额标准欠缺的法益侵害性。因此,“对比延申说”将“户”从家庭生活领域扩大解释为含办公领域,将原本非犯罪行为纳入犯罪圈,在符合刑法修法目的同时,更保障了盗窃罪内部法益侵害程度判断的一致。
2.“住宅”与“户”的关系。在非法进入他人生活场所窃取财物未果时,司法中面临判定非法侵入住宅罪还是(入户)盗窃罪未遂的困境。此外,在行为人窃取财物既遂时,又面临判定盗窃罪一罪还是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罪二罪的困局。前者如案例六: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刑初415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常某归案后一直稳定供述其到涉案宿舍的目的是为窃取财物,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扰乱他人生活秩序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被告人常某是以秘密方式进入涉案宿舍而非公然闯入,而涉案宿舍是供被害人家庭生活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符合刑法意义上“户”的特征,因此,被告人常某的行为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常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属指控有误。后者如案例七: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刑初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魏某到天津市某小区内采以徒手掰断护栏方式钻入刘某家中实施盗窃未果。后魏某采用同样手段钻入李某家中盗窃现金人民币113 200元、MK牌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960元)、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6 695元)及外币10张(折合人民币182.561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和盗窃罪,应对其数罪并罚。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构成盗窃罪,但并未说明被告人不成立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理由。从上述案例可知,在入户盗窃行为触犯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多认定行为人仅构成盗窃罪一罪。笔者认为,此时认定行为人构成何罪及是否数罪并罚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住宅”与“户”的关系。二者能否等同,存在等同说与区别说两种观点。
等同说主张,“住宅”等同于“户”。“从构成要件的结构来看,入户盗窃,不需要数额较大即可成立盗窃既遂;入户抢劫,成立加重的抢劫。将住宅与户作同等解释,符合入户犯罪的不法加重结构。对入户犯罪加重法定刑的根据,主要不是因为入户犯罪行为使得被害人被侵害的危险进一步升高,而应该是非法侵入住宅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出现,提升了盗窃、抢劫等罪不法的内容。”[11]
区别说认为,“住宅”与“户”不同。在该说内部,根据划分理由不同,存在功能全备说和私生活空间说:功能全备说在区分广义住宅、狭义住宅基础上,主张具备日常生活全部功能的广义住宅(如私人住宅、私人别墅等)是“户”,而只具备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某一方面功能的狭义住宅(如建筑工棚、病房、福利院、托儿所等)不是“户”[5]。私生活空间说将私生活存在的物理空间视为住宅,并认为其范围显然大于“户”。该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规定的“住宅”为依据,认为“住宅”除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房屋外,还包括寄宿宿舍、旅馆等其他私生活在物理空间上的展开场所,其成立也无须具备独立建筑结构或持续性使用等时空要件,并据此得出结论:“非法侵入他人的宿舍或旅馆客房,也构成对住宅安宁的侵犯,可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但根据司法解释,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12]
笔者赞同区别说,但对该说内部的功能全备说和私生活空间说所述理由持不同态度。等同说实质是将非法侵入住宅行为与盗窃行为整体视为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要素,在设定入户盗窃为行为犯的情形下,将非法侵入住宅行为视为盗窃行为违法程度升高的因素,进而符合《刑法》对入户盗窃构罪的违法程度要求。该说在未辨明“住宅”与“户”是否存在区别的前提下贸然将非法侵入住宅行为视为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要素,实为不妥。再者,不能将入户盗窃理解成非法侵入住宅与盗窃行为的结合犯,“‘入户’并不是盗窃行为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限制处罚范围的要素(同时为违法性提供根据)。”[13]功能全备说存在外延自相矛盾问题:论者主张广义住宅属于“户”,此时基于广义住宅外延当然包含狭义住宅的逻辑,狭义住宅的外延应在“户”的范围内。然而,论者颠倒了广义、狭义住宅的外延,其所指具备全部生活功能的场所实为狭义住宅,而仅具备某一方面生活功能的场所应为广义住宅。私生活空间说坚持区分说的原因在于其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户”的范围③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关于入户抢劫的认定”中规定,“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对比延申说结论已证明不能对入户盗窃、入户抢劫中的“户”作等同理解。再者,将寄宿宿舍、旅馆视为住宅,存在与民众生活常识矛盾问题。住宅通常是供人长期生活居住的场所,若将宿舍、旅馆视为住宅,必然造成民众难以认同从而带来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导致犯罪圈不当扩张。
笔者赞同区别说的理由在于:其一,符合立法设置。我国《刑法》在不同法条中分别规定了“住宅”和“户”,说明立法者在设置罪状时认真考虑了二者间不同,因此未在《刑法》中混同使用。其二,法条体系位置不同所致。《刑法》中含有“住宅”字眼的法条只有第245条非法侵入住宅罪,该罪名位于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而盗窃罪属于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内容,“住宅”“户”的内涵应根据其附属的法益理解,即“住宅”依附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而“户”依附于对财产关系的保护。二者分属对不同权利的保障,含义解读必然存在差异。如对“侵入”的理解:由于分属不同章,造成同类客体不同,使非法侵入住宅罪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侵入”存在差异。对“住宅”的理解依附于对公民人身安全的保护,重在保障人对场所的安全信赖感,通常表现为家庭生活关系;而“户”重在描述财产所处场所的隔离性,犯罪人入户盗窃行为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及该场所未经允许不可进入的权利,此处的场所并不要求具备家庭生活的功能特征,只要具备“与外界相对隔离”特征即可。换言之,入户盗窃中“户”的外延大于“住宅”外延。“户”所具备的隔离性特征使得其本身会给人带来场所安稳性不受侵犯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只是基于隔离而产生;而“住宅”带来的住所安稳性不受侵犯的感受不仅基于隔离,更是缘于家庭生活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
(二)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内容
刑法学界针对入户目的需具备非法性不存在争议,但围绕该非法性的内容存在纷争。根据是否应参照对入户抢劫中非法目的的解释理解入户盗窃的非法目的,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肯定论认为,对“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应坚持相同解释路径,对相近方式犯罪行为的解释不宜出现较大差异[14-15]。该论点的主要支撑是复行为犯说,该说主张“应当将‘入户’和‘盗窃’两个行为的结合视为复行为犯,各要素行为在一个统一意图的支配下,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求非法入户时就必须有盗窃的犯意,否则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16]否定论认为,即使不是以实施犯罪为目的,只是以实施一般违法行为为目的入户,入户后实施盗窃行为的,也应认定为入户盗窃[17-18]。在该观点内部,又可进一步分为限制处罚说、目的非法性说和入户非法性说。其中,限制处罚说认为,“入户盗窃既不是非法侵入住宅罪与盗窃罪的结合犯,也不是牵连犯,‘入户’并不是盗窃行为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限制处罚范围的要素(同时为违法性提供根据)。只要是非法进入他人住宅并实施盗窃的,即使非法进入住宅时没有盗窃的故意,也应认定为盗窃罪。”[13]目的非法说认为,“入户的目的必须具有非法性。违法入户是指未经居住人同意而擅自进入或虽经同意进入但在居住人要求其退出时拒不退出的情形,也包括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入户的情形。”[19]入户非法性说认为,“对于‘入户’的非难应在于其入户时的非法性,而不在于‘入户’时的主观故意。行为人在非法入户的前提下,无论其入户时有无犯意,只要在户内实施了盗窃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20]
笔者认为,肯定论的支撑依据不足,但目的非法性说较为合理。对于“户”的理解,入户盗窃和入户抢劫存在不同,理由前已述及,该理由同样适用于此处对入户目的非法性内容的理解。复行为犯说失当地将入户行为和盗窃行为视为一体,限制处罚说的反驳具有合理性。此外,限制处罚说在解释“入户”与“盗窃”内在关系方面具有合理性,但对入户目的非法性内容的阐述较为模糊。该说虽不要求行为人非法入户时具有盗窃故意,但在围绕是否要求行为人入户时具有犯罪故意,抑或仅要求违法心态还是只要是非法入户即构成盗窃罪,存在理解上的多义性。目的非法性说的合理性在于:尊重客观现实,认同行为本义。在现实生活中,未经他人允许,非法进入他人户内时,体现出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存在违法或犯罪心态。入户非法性说忽视客观现实,人为割裂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间的内在关系。行为的本义并非空洞无物,而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结合的基础上,否则会使客观行为的判断流于形式,进而无法分辨刑法中的法律行为与条件反射、梦游等行为的区别。目的非法性说揭示非法入户的主观心态为“非法”,违法、犯罪皆为非法,因此能够涵盖行为人非法入户时的全部主观心态。再者,其在将入户目的概括为违法、犯罪的同时,既涵盖未经允许闯入的行为,亦涵盖通过合法方式进入而拒不退出及通过欺骗进入的行为,达到法益保障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刑法修正后严厉打击入户盗窃的目的。
(三)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
围绕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存在诸多纷争。依据对入户盗窃行为、数额型盗窃行为是否坚持相同既遂标准,可划分成等同说、区别说和折中说。等同说认为,应对入户盗窃行为、数额型盗窃行为坚持相同既遂标准,理论界多持此观点。理论界判断数额型盗窃的既遂存在七种标准:接触说、转移说、藏匿说、控制说、失控说、“失控+控制”说、损失说。控制说认为,入户盗窃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和住宅安宁权,入户物色财物是着手,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作为既遂标准[21-22]。“失控+控制说”认为,“入户盗窃虽单独构罪,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侵犯财产类的犯罪。因此,在既未遂的认定上,入户盗窃与普通盗窃应当是一致的。”[23]区别说主张入户盗窃的既遂不以满足一定数额为必要,只要行为人在户内开始寻找财物,即使最终未取得财物,也构成既遂,实务界多持此观点。“成功入户并且已经选定具体盗窃目标的,不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也不论财物是否属于刑法保护的合法利益,均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既遂。”[24]折中说要求入户盗窃行为至少取得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才构成既遂,并不是指入户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才构成犯罪,而是将仅入户窃取了客观价值与使用价值均低廉的财物之情形排除在外,从而使构成犯罪的入户盗窃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25]。
数额型盗窃的既遂建立在被窃财物满足“数额较大”的前提下。对入户盗窃是否需满足“数额较大”要求,笔者认为,《刑修(八)》对盗窃罪的大幅度修改本质上扩大了盗窃行为类型,各行为的既遂标准亦应体现出不同之处。如将扒窃与数额型盗窃的既遂标准等同,会使扒窃小额财物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规制,进而使扒窃罪形同虚设。因此,对不同行为类型主张不同既遂标准,是立法的题中之义,亦能顾及到不同行为的不同特点。在对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不要求“数额较大”时,是否一律不要求数额,抑或无视数额型盗窃的既遂标准?应当说,等同说和区别说分别走向两个极端,折中说观点更可取,但本文观点与之略有不同。
笔者认为,入户盗窃被规定于侵犯财产罪一章,说明其侵犯的法益是财产权益,因此既遂标准不能脱离财产价值载体——数额。但又因其行为类型与数额型盗窃不同,不能以“数额较大”要求。在肯定入户窃得财物需有价值时,应进一步判断此种价值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抑或二者兼具。此时折中说显示出矛盾之处:折中说以使用价值为要求,在部分情形下会使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依然可成为被窃取对象。但若物品没有交换价值,何谈“数额”?换言之,“数额”的判断依赖于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价值,如果物品仅具有使用价值而无交换价值,则无法估算其数额,会使折中说既要求数额又要求使用价值的主张在部分场合存在矛盾。因此,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在要求财物具备数额之余,亦应兼具交换价值。对于何数额财物能够成为入户盗窃的既遂标准,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行为人对户的非法侵入程度、对户内人员是否存在伤害可能性、是否携带凶器及当地对数额型盗窃既遂标准的规定综合判定。
认定入户盗窃既遂尚需判断是否要求行为人控制财物抑或满足数额型盗窃的其他既遂标准。因入户盗窃属于财产犯罪,保护的是财物占有权人或所有权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并非只有犯罪人控制了被盗财物,才能视为侵犯被害人财产,这是以犯罪人视角为核心,脱离了被害人本位,因此不合理。财产权益依附于被害人,对财产权益是否造成损害,应以被害人视角为中心。只要犯罪行为使合法占有人脱离占有,即使该财物依然在户内,亦可认定被害人因对财物失去控制而遭受财产损失,此时应认定为入户盗窃既遂。对于该问题,有学者提出只有将被盗财物转移至户外方能成立既遂(以下简称“户外转移说”)。“入户盗窃的既遂与未遂,不论是大件物品还是小件物品,都应以是否运出户外为标准。”[26]此观点反映出:入户盗窃既遂关键在于判断何时对财物达到控制状态。笔者不赞同以户的空间范围作为判断入户盗窃的既未遂标准。如果犯罪人在户内窃得昂贵巧克力(价值1万元)后未将其带至户外,而是在户内吃掉,此时户外转移说会认为入户盗窃尚未既遂,而这种结论显然不利于保障被害人财产利益,难以令人信服。因户外转移说以户的空间范围为核心,未以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为核心判断是否既遂,因此其判断结果失当,即在情理之中。本文以失控说作为判断入户盗窃是否既遂标准,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入户盗窃但未窃得财物应如何定性问题的研究意见》中“只有使被害人对财物失去控制后才能认定为既遂”的观点。
(四)入户盗窃的未遂
行为人入户实施盗窃行为时,未窃得任何财物即被房主发现并当场抓获,是否构成入户盗窃?围绕该问题,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犯罪既遂、犯罪未遂、无罪。
笔者认为,由于被害人尚未丧失对财物的占有状态,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且《刑修(八)》增加入户盗窃目的在于严密刑事法网而非严厉打击,因此不能无限制地将上述行为理解为犯罪既遂。此外,主张无罪的学者以《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2条作为理由欠妥当:其一,该条规定的盗窃未遂仅适用于数额型盗窃,不适于其他类型盗窃行为。《解释》于2013年颁布施行后,1998年的《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不再施行。《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第1条第2项规定了盗窃未遂的处罚条件,“(二)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该规定与《解释》第12条规定一致。而入户盗窃单独立法源于2013年,说明在入户盗窃单独立法前,《解释》第12条的法条内容已在《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中出现,唯一解释只能是前后不同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前后刑法文本中均有规定的数额型盗窃。其二,即使将《解释》适用于入户盗窃,亦不能排除入户盗窃存在未遂的可能。《解释》第12条是对盗窃未遂需受处罚的规定,主张无罪的学者误将该规定理解为盗窃未遂具体情形的列举,不具合理性。
笔者主张入户盗窃存在未遂。入户盗窃未遂是指入户盗窃行为已成立犯罪,但因行为人意志以外原因使犯罪未能达致既遂所形成的犯罪形态。探讨入户盗窃未遂时需与既遂标准结合:其一,原则上被害人对占有财物失去控制与犯罪人控制财物同时发生。若被害人对财物失去控制,就应认定为入户盗窃既遂。如被害人未对财物失去控制,则成立入户盗窃未遂。在部分场合存在被害人对财物失去控制而犯罪人亦未控制财物的情形,此时不应以犯罪人是否控制财物为核心,应以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为核心。其二,在分析入户盗窃未遂时,需综合数额、交换价值、失控说三重要求判断。
此外,在分析入户盗窃未遂时,需要判断着手时间。有学者认为,“尚未成功入户的,一般应认定为未遂,未造成实际后果的甚至可作非罪化处理;成功入户,尚未确定具体盗窃目标的,一般也应当认定为未遂。”[24]可见,论者将入户盗窃的着手提前至入户前,实为不妥。笔者认为,行为人入户后开始寻找财物为着手。着手是对刑法保护法益造成紧迫危险的行为,入户前尚未对户内财物造成危险,遑论危险紧迫性。入户后,行为人对财物会带来危险,但这种危险尚未达到紧迫程度,只有开始寻找财物时,这种紧迫性才会体现出来。
从立法角度观察,入户盗窃入罪更多考量的是犯罪者人身危险性而非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这是因入户盗窃并非数额犯,说明其对财产性法益的侵害较普通盗窃弱,但二者均统一适用同一档法定刑,足以说明入户盗窃的人身危险性因素补足其不法性。入户盗窃侵犯的客体应为双重客体,主要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是他人住宅安宁权;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非法入户方式窃取他人财物,在入户目的方面应采目的非法性说;在判断入户盗窃既遂时,应采失控说,且其存在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