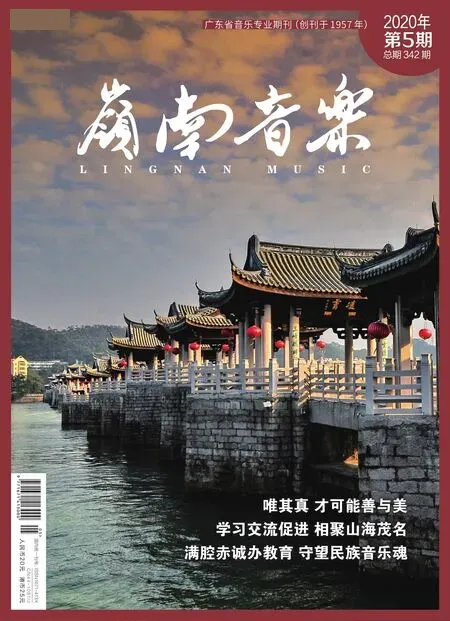施咏康早期管弦乐作品的音乐创作观
2020-12-03文|
文|
在浏览20世纪50—60年代的众多音乐家的创作与音乐活动时,由于天时地利,笔者有较多的机会与便利接触那个时代的历史参与者与见证者——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施咏康先生。在研读施先生的作品时,笔者发现其先后完成于20世纪50—60年代间的三部早期西洋管弦乐作品——交响诗《黄鹤的故事》(1955年)、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1962年)、圆号协奏曲《纪念》(1962年),似乎具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文化象征的普遍意义。作品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国内专业音乐创作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对此,笔者对作曲家的音乐创作观进行了如下分析。
一、本土化构思
《黄鹤的故事》在配器上运用了竹笛音色,流露出清新的乡土气息,对此,作曲家表示:
“我从小生长在江南,耳濡目染着江南丝竹、江南民歌。”(2012年7月1日采访录)从竹笛吹奏的曲调来看,作曲家已将民间音乐的听觉经验融入他的创作中,并演化出新,使曲调保留着传统的韵味。可以看到,在《黄鹤的故事》中,音乐各部分的主题曲调运用了五声调式,一方面体现出各部分主题形象的对比,一方面在材料上具有统一性,这就要求作曲家对曲调素材须具备感性的驾驭。
《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圆号协奏曲·纪念》中的主题曲调中也汲取了民歌的特征,绵延而舒缓。在保留传统民族韵味的基础上,采用持续性和声及五声纵合化和声对主题曲调给予凸显。不仅如此,作曲家在音乐结构上汲取了中国民间音乐发展手法,如“变奏”“重复”“循环”的特征,结合西方传统的大型曲式结构,这在他1999年完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幻想叙事曲》中也可以看到,正如作曲家所说:“我们当年追求的一方面是作曲技法,一方面是民族风格。”(2012年1月4日采访录)而在音乐结构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三部作品均加入了引子。这个引子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板式特征——“散”,即自由的。作曲家说过:“我写东西讲究意境,引子是主题的暗示,是一种情绪的铺垫。”(2012年7月1日采访录)在西方传统的奏鸣曲式中并不经常出现引子①。
二、推陈出新
“作品一定要体现时代的精神风貌。”(2012年7月1日采访录)这是施咏康强调的,他的三部作品折中融合西方音乐技术形态与中国民间音乐形态,形成新颖的五声纵合化和声。《黄鹤的故事》运用竹笛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在中国西洋管弦乐创作史上可谓是首创,这体现了作曲家对新音响的探索,他表示:“故事本身的老艺人会吹竹笛。况且我觉得竹笛与西洋管弦乐的结合不应该有困难。”(2012年4月8日采访录)而《圆号协奏曲·纪念》则是我国第一部为圆号写的协奏曲。作品中,作曲家大胆运用圆号作为主奏乐器,并结合复杂的和声手法、频繁游离的调性,彰显出创作过程的难度,他说过:“我喜欢用复合和弦,喜欢用副三和弦,避开功能性。”(2012年1月4日采访录)的确,早于1957年,他完成的室内乐作品《大提琴与钢琴·回忆》中,已看到双调性的思维及对复合和弦的运用,使得调性尤为模糊,音响具有较大的张力。可以说,《圆号协奏曲·纪念》延续了他求新的创作观念,他说过:“在我的创作中,我最喜欢的是《圆号协奏曲·纪念》,这个作品曾挨过批。直到改革开放后,1979年被出版社拿去,说很新,1982年才出版。当时,大家对这部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好的,一种是片面的,说是‘形式主义’。当时有文艺工作者说过这部作品脱离了《黄鹤的故事》的道路。实际上,我写《圆号协奏曲》,是比较深情,是一种悼念,比较深沉,用简单的手法是不行的。”(2012年7月1日采访录)《圆号协奏曲·纪念》的曲调并不像《黄鹤的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诗·嘎达梅林》《长征交响曲》等作品一样令人易记,采用的主奏乐器“圆号”也不像小提琴、大提琴之类的弓弦乐器擅长演奏如歌的曲调,在句法上更没有同时期一些小型管弦乐曲的规整、或具有舞蹈的律动感。并且,曲调调性的频繁游离与和声色彩的丰富变化流露出一种不安的情绪。这种种技术形态因素似乎与其时群众的审美观念是相悖的,它打破了传统的、以线性进行的旋律美的审美原则,而这种不受传统调性束缚、突破调性组织的线条流动的结构思维与西方现代作曲理论是想通的。
“技术可以模仿,风格不能模仿。我写东西很在意一个‘新’字。”(2012年7月1日采访录)施咏康对音乐创作之新的追求是执着的。甚至在他的音乐教育观中也有所反映:“我在教学中,没有讲‘旋律’这一章,我认为,什么乐器加什么乐器是什么音色,没必要去记得,音色是作曲家自己的爱好,作为学生,没有经验,听的不多,根本记不得里面的条条框框。”(2012年4月8日采访录)无论在实际创作、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施咏康很强调创作思维的灵活性,他说过:“实际上是这样的,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无论是学配器还是学作曲的,不要纯粹从曲式学的角度去分析作品。而学习和声学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和声学的原则,创作的时候则要把它们丢弃掉。在《圆号协奏曲·纪念》中,很难用传统的曲式学去分析,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拿来主义’,可以用就拿来用,要不拘一格。”(2012年7月1日采访录)而当提起20世纪西欧乐坛掀起的“现代风”,作曲家表示:“对于‘现代风’,我并不排斥,有追求过。既然它存在,便有合理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比如《圆号》里面就用了双调性。”(2012年7月1日采访录)可见,在其时的文化氛围背景下,作曲家的创作观念是开放、包容的。
三、音响的趣味性及描绘性
在《黄鹤的故事》中,作曲家对音响的构建基于故事文本提供的场景,让笔者联想起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以及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及《海》,这种描绘性是对配器色彩、和声色彩的细腻把握,流露出个人的审美情趣以及对某种艺术风格的追求。
比如“老艺人”吹笛、“黄鹤”偏偏起舞、“黄鹤”被抓了、“黄鹤”与“官老爷”的对抗,这些故事情节都可以从音响中感受到。此外,乐曲的附属曲式部分,即连接部的音响也具有烘托场景的作用,比如展开部慢板片段之前,插入了充满趣味、具有滑稽性格的音响,其主要通过木管组内声部的八度跳跃、弦乐的拨奏来实现。据作曲家本人提供的关于《黄鹤的故事》的介绍,乐曲的每一部分都附有故事情节的解说。因而,音响具有的描绘性的构思是明晰的。而在《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第一乐章中,作曲家为了象征“老百姓的苦闷情绪”“晦涩的氛围”以及“逐渐看到光明”,主要通过和声色彩的变化来暗示,并且,全曲几处可以看到造型性音响,如“号角声”主题、“队列紧张有序的步伐”,这类音响容易令人联想战争的场面。此外,乐章结构、曲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妥协于故事题材,比如《黄鹤的故事》中的主部主题“老艺人”在展开部中没有得到发展,而着重发展副部主题“黄鹤”,有别于以往的奏鸣曲式;又如《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中,为了象征“追悼后,人们鼓起勇气,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第三乐章与第四乐章之间的音响无间断,达到一气呵成之感。
从几次访谈中可以注意到,作曲家经常言道:“我创作也很讲究幻想色彩。”(2012年11月4日)在《黄鹤的故事》中,作曲家采用交响诗这一体裁,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民间神话故事作为题材,尤其是在音乐技术形态上,调性及和声手法彰显出较自由的进行,不强调主和弦的根音,喜好运用延留音、和弦外音模糊调性甚至形成复合调性、复合调式的和声层次。这些手法彰显出作曲家在创作思维上追求的自由,正如他所说:“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这是一种畅想,是一种本能吧!”(2012年7月1日采访录)作曲家深信诸如交响诗、协奏曲这类纯器乐体裁能赋予他自由的想象空间,或者表达丰富的内涵,在《圆号协奏曲·纪念》中更是有所体现。《圆号协奏曲·纪念》也是充满幻想色彩的,作曲家表示:“这部作品写的时候是很自由的,你感受到什么就是什么。”(2012年4月8日采访录)结合题材中的纪念革命先烈殷夫的诗句,作品以圆号作为主奏乐器,由于圆号的音色本身富于诗意,带有朦胧、辽远的音响特征,且以复杂多变的调性色彩、和声色彩作为背景,赋予作品史诗性的气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此外,在三部作品均可以见作曲家偏好运用装饰性色彩乐器,使音响有神秘、梦幻的意境。可见,作曲家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
四、艺术理性
施咏康的创作固然强调感性把握,他说过:“作曲是无法教的,一定要有感觉。创作很多的时候是靠感觉的。感觉上不舒服的时候肯定有问题,再从理论上找依据。”(2012年4月8日采访录)这体现了他在创作上的艺术理性,“创作的时候会有即兴性,当然要修改、推敲”。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过系统的作曲技术理论训练,也研读过许多作曲家的作品。因而,在他的创作中,首要是遵循无数作曲家实践过的、传统的、既定的某种艺术规则。而他对作品的构思也体现出缜密的职业态度。当他回忆起《黄鹤的故事》的构思过程时,他表示:“一开始酝酿内容的时候是没有考虑曲式类型的,只想着要用大型曲式来写。动笔就以奏鸣曲式为框架,《黄鹤的故事》是奏鸣曲式的框架,但是按照传统的奏鸣曲式是对不上的,手法基本上是奏鸣曲式的手法,但是每一部分是不会按照传统奏鸣曲式去作。记得一开始是酝酿题材,我很喜欢‘黄鹤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就知道,流传在江南一带。”(2012年4月8日采访录)固然,音乐结构的布局有时会妥协于题材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为保持结构的凝练、积蓄乐思发展动力,还须遵循传统的曲式原则或借某种体裁来展现,他说:“创作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按照故事来讲的。只是创造了几个形象。按照奏鸣曲式的要求来创造几个形象。形象的运用与发展合乎故事的结构,最后写在谱子上的每一部分标题是经过我调整的,实际上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一定是这样的,我把它变成再现性的。而故事本身有很多可虚构的东西。是神话故事,适合写音乐,且比较适合写成交响诗。交响诗是标题音乐,有故事性在里面。选了题材后才考虑的曲式。”(2012年7月1日采访录)而说起《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的构思过程时,作曲家也表示:“第二乐章是最先写好的。哪个乐章的构思比较成熟,就先写哪个乐章,其他作曲家也有这样的经历,音乐创作过程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是很灵活的。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构思这部作品。”(2012年7月1日采访录)
施咏康对创作的严谨态度在他的《谈交响音乐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所反映,他强调对专业技巧训练的重视:“过去我们是吃了极左思想的亏的,谁要提倡、强调表现技巧,无形中就认为是不要生活,是所谓‘单纯技术观点’,借鉴了一点德彪西等人的手法,就被看作所谓‘形式主义’,好像犯了大罪似的。而现在应是提倡加强专业训练的时候了。”[13]施咏康在求学期间,对作曲“四大件”的训练尤为重视。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丁善德教授他们复调写作时,全班仅有他和胡延仲练习至八部对位(2012年4月8日采访录)。从三部管弦乐作品的音乐结构还可以看到,施咏康较自如的运用了传统的大型曲式类型,即运用奏鸣曲式、复三部曲式,并融入其他类曲式发展原则。这让笔者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是从学习的角度会学习贝多芬的,如果是审美爱好的话我喜欢听民族乐派写的东西。”(2012年1月4日采访录)从三部作品中对奏鸣曲式的运用,可窥探到作曲家对音乐结构的驾驭能力,尤其是《黄鹤的故事》,汲取了奏鸣曲式中强调的对比与统一,巧妙结合了故事情节。而《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第二乐章及第四乐章,尽管展开部冗长,几处有插入性乐句,但并没有影响到全曲材料的统一性及乐思的凝聚力。他说过:“我在教学中曾注意到学生爱用对比型的单三部形式、复三部曲式与回旋曲式,而不喜欢用展开型的单主题二、三部曲式,对奏鸣曲式当然也感到头痛。他们以为对比型曲式的两个互不相干的主题不通过连接便可很容易地放在一个曲子中。殊不知,这种曲式同样需求两个主题有内在的联系与内在的统一。展开型的曲式则要求更为复杂多样的发展手段,困难也就多些。作曲也好,配器也好,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在变化中求统一和‘以不变求万变’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追求多层次发展的结构思维在他的配器手法上越发凸显。早于1955年,苏联专家阿拉波夫在中央音乐学院授课期间,他与陈培勋、苏夏的配器作业经常被当作示范教学的范例②。施咏康在西洋管弦乐配器法上的努力探索及其教学成果是国内乐界人士有目共睹的。作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学科“配器”课程的带头人,在他早期的三部管弦乐作品中,已可窥探其在配器法上的细腻、新颖,以及对新音响的探索,即追求不同质音色的结合,以营构丰富、渐变、具有动力的音响色彩,各个乐器组的织体写法也较为丰富,相比同时期多数小型管弦乐曲,其配器技法更显娴熟、细致,他说过:“部分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配器臃肿,织体偏满,音响偏重,尤其是全奏过多(过多的全奏对听众来说是‘灾难’),缺乏对比性和清新感。”(2012年11月4日采访录)而他的《管弦乐队乐器法》一著述,作为中国第一本由国人编著的西洋管弦乐队乐器法、至今仍作为国内各大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其不仅对乐器性能作了详细介绍,且结合中外多首作品的谱例,对各类乐器在乐队写法中的具体实践作了介绍及评论。此外,于1961年由文化部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会议上,施咏康已被指定编写乐器法与配器法。由于受到文革、迁居的影响,施咏康与原本文化部的人员失去了联系,拖延了出版的进程。如今,这本《管弦乐队配器法》已面世,附带了大量的谱例分析,汇集了施咏康一生的心血。
注释:
①参见于《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499.)一书。
②鲍元恺在《怀念恩师陈培勋先生》([J].人民音乐,2008(2):54—55.)一书中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