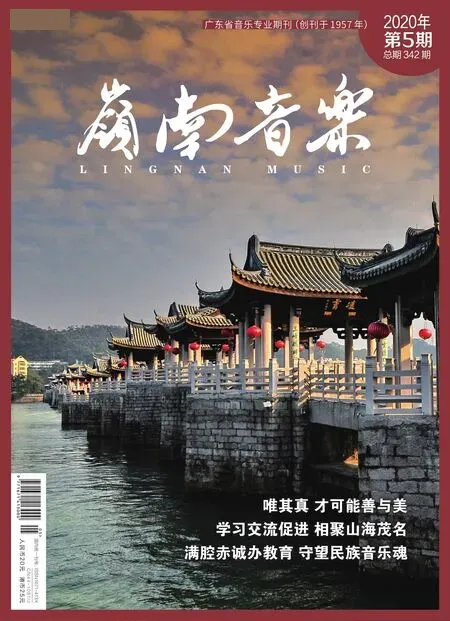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连载4)
2020-12-03文|
文|
10.子大叔
子大叔(?—公元前506年),游吉,字子大叔(亦称:子太叔、世叔)。春秋时期郑国正卿,郑定公八年(前522年)接替子产主持郑国政务,郑献公八年去世。游吉文质彬彬相貌堂堂,内善理政、外长外交,为政先宽后猛。《左传》评价其曰:“子大叔美秀而文。”孔子赞美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论语·宪问》)。
郑国的国君子大叔的音乐批评事迹,都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录在他与赵简子的对话中: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为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与此时的诸位批评家相同,子大叔的音乐批评观念与理论,都是隐藏在对治国安邦的论述中的。他的这些论述,也借用了阴阳五行的理论,所谓的“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这就是把五行观念运用于批评实践的具体表述。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天地的五行历法运转的。对于“五味”“五色”“五声”的享受不能过度,所谓“淫则昏乱,民失其性”,而应当“以礼以奉之”。在音乐的构成法则上,也应当按照五行理论来进行,所谓“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他的批评还比较重视对音乐情感现象的关注,所谓:“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他承认民众正常情感的抒发,认为“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而批评家所作的事情就是:审慎地制定准则,恰当地制定规范,用以约束“六志”,哀乐都不出于规范,不失于礼,才合乎天地的本性,才能够维持长久。子大叔比较注重“五声”等艺术形态现象,他的批评是针对当时社会上过度追求人的声色之娱行为而展开的。他把这种“烦手淫声”的音乐行为,称为:“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意欲弘扬合乎“五行”规律的“五声”,褒扬“五声”的同时,还不忽视“九歌、八风、七音、六律”的存在,只不过它们的地位没有“五声”高,所以就需要以它们去“奉五声”。从此不难看出,他的音乐批评的文化胸襟还是相对宽广的。他没有采用毅然决然地“放郑声”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是,在他的审美理想中,雅乐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
11.晏婴
晏婴(?—公元前500年),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姬姓(一说子姓),晏氏,字仲,谥“平”,史称“晏子”,夷维人(今山东高密)。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辅政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长达56年。聪颖机智,能言善辩。内辅国政、讽谏齐王;外交邻国、不辱使命。生平事迹载于《晏子春秋》①。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疑古派曾经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晏子》八篇”列在儒家类。晏子关于音乐的批评语录,见于《晏子春秋》的内外篇,具体涉及到的内容有:
①对景公赏乐的批评
作为一位尽职尽责的贤臣,齐景公的日常音乐生活也在晏子的观察与评价范围之内,下面这段史料记载了晏子的这种批评行为: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对曰:“君夜发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对曰:“梁丘据扃入歌人虞,变齐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礼而拘虞。公闻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乐淫君。”公曰:“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以请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夫子无与焉。夫乐,何必夫故哉?”对曰:“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纣作《北里》,幽厉之声,顾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轻变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业,不择言而出之,请受命矣。”(《内篇谏上》)
景公接受梁丘据秘密进献的一位演唱新类齐国歌曲(“变齐音”)的歌手,被其深深吸引、彻夜赏乐而不能早朝。晏婴听闻后即刻命令宗祝根据礼法规定拘捕了音乐家,景公闻听后怒而责问缘由,晏婴回答其罪责在于其用“新乐淫君”。景公认为国家大事我可以托付于你参与管理,我自己的饮食与情感生活(酒食、金石)你不可以多管闲事。晏婴便以历史上商纣作《北里》、溺淫乐、亡国家的教训劝谏景公,指出国君的音乐生活事关重大:“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晏婴认为对于精神食粮(音乐)的改变(“变齐音”),可以引出系列的国家治理隐忧,不可大意。在这里表面看起来是国君个人音乐欣赏品种的更换,实际上却是事关移风易俗、改朝换代之大局。
②对仲尼乐德的批评
孔子在世时,就已经美誉于列国。孔子拜访景公,景公非常高兴,意欲封赏之,告知晏子后,晏子即刻予以反对: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
晏子反对的理由很多,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强调“礼乐”的仲尼之“乐德”有亏。具体的“污点”如下:1.傲慢自以为是;2.自己好尚音乐,却“缓于民”;3.自我修身积极,奉献社会消极;4.崇“厚葬”“破民财”,“守丧”日久浪费时间;5.德行修养最难的在于内,其只注重修饰外表。在指出了仲尼的这“一堆毛病”之后,进而“深挖”历史根源:由于“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于是“威仪加多”“声乐繁充”,却导致“世德滋衰”。面对于此,孔丘却“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他们搞出来的这一套繁文缛节的“礼乐”仪规对于世人来说,是“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的。孔丘的这一套,对上是“繁饰邪术以营世君”,对下是“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您却欲封赏于他,用他的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景公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在晏婴的眼里,孔子就是个徒有其表、虚伪奸佞的蛊惑者,他所推崇的“礼乐”体系,更是一个社会管理的“繁饰邪术”。这是对孔子其人、其言、其行的批判,也是对有周一代确立的礼乐制度的鞭笞。这或许是仲尼在世时受到的来自于“同行”最为严厉的贬斥性批评了。
③对和同之辩的批评
据《左传》记载,晏婴在与齐景公对话的时候,继续发展了周朝太史伯在“和同之辨”时确立的批评观念,从音乐的构成原则和审美评价的角度,对“和实生物”的思想,做出进一步诠释:
和如羮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也,君子听之,以乎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年》)
将烹饪的手法比喻“和”的运用,其触类旁通的能力,可见非同一般。在涉及到音乐相关问题的时候,晏子把音乐的各个类型(声学、乐学、律学、曲体学)、各个层面的(情感、形态)艺术特征,做了“相成”、“相济”的处理,最后都统一到音乐审美批评的基本标准——“和”的范畴之内。所谓的“和谐”,并不是简单地将诸多事物拼凑、杂贴在一起,而是不同的事物按照音乐艺术美的规律与法则有机地加以融合。“和同之辨”,由史伯起始,晏子承续展开,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音乐批评标准与方法的论争与探索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基本确立了当时音乐美的评价标准,也确立了以雅乐为代表的音乐艺术的构成法则。
12.单穆公
单穆公,春秋时期单国国君,名旗,伯爵。
《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单穆公劝谏周景王铸造大钟企图的言论:
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且夫钟不过以动声,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
景王欲铸无射律的大型编钟,还想要同时铸造一口能发林钟律的大钟。在征求单穆公意见的时候,单穆公以为“不可”,便讲述不可为的系列道理:1.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此为劳民伤财之举。2.出于人的耳朵听觉上的考虑,“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音乐以及发生音乐的乐器,都是为人的耳朵而存在的:“夫不过以听耳”,“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作为人的听觉艺术的音乐,以听觉感受时,势必会受到人自身听觉能力的局限;人也不可脱离这种局限,制造人的听觉所不能感受的乐器;故:“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这是因为:“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3.出于音乐与政治、社会关系的考虑,“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人”与“乐”都是由禀气而成,为人而生的乐的是否“平和”,对于人的元气与精神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人如果经常聆听“平和”的音乐,就能够使人心和顺、民气通畅、社会祥和;反之,则“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三年之中”“国其危哉”!单穆公立足于当时新兴的“阴阳五行”学说理论,对周景王的铸钟意图展开批评,并以此为话题纵横捭阖言说自我文化价值取向。单穆公从听觉生理到感受心理,从音乐器物到艺术内涵,从抽象个体到具象社会,对音乐的发生、演绎过程所伴生的系列社会心理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且又言简意赅的理性批评。其综合性的批评,是对当时系列批评理论融会贯通地运用的代表性阐述。
13.伶州鸠
伶州鸠,周景王时期(公元前544—公元前520年在位)乐官。
周景王问乐律于伶州鸠,其回答成为中国乐律学史上最早的名篇,也是立足音乐知识展开音乐批评的佳作。伶州鸠向景王灌输乐律知识,并劝谏景王不要“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按“六阳”“六阴”顺序,排列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12个律名,成为最早的十二律记载。《国语·周语下》记录了单穆公与伶州鸠轮番劝谏的这段音乐批评实践(涉及到单穆公的对话,请见上节),在景王对单穆公的话不以为然后,便又去问乐官伶州鸠,作为音乐家的州鸠也不赞成。他的批评除了与单穆公的一致性内容之外,还立足于音乐内部的乐器法则与律学常识来进行:
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今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
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
伶州鸠与单穆公的劝谏角度有所不同,但大的方面基本一致:1.出于经济的考虑,所谓“用物过度妨于财”,“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植财”;2.出于音响形态的考虑,所谓“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3.出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考虑,所谓“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景王一意孤行,最终铸造了大钟,仅仅过了一年,景王就驾崩了。
单穆公与伶州鸠对景王铸钟行为的批评,突出地展现出音乐批评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对矛盾。对此,他们是这样辨析的:
第一,从“乐音→听觉”的生理关系层面上看,他们提出“乐”应从“和”。这个层面的“和”,就是音律的和谐、悦耳。作为谏官的单穆公和作为乐官的州鸠,都具有非凡的“识音辨律”“审音知政”“闻乐知德”的才能。他们对音乐的音响层面的感受与判断能力是异常的敏锐,他们认为“大林”的音频过于低沉,使听众难以接受,即“耳弗及也”。既然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自然也就“非钟声也”。我们都知道,钢琴极低音区的音在作品中是极少使用的,原因就是人的耳朵难以接受这些极低的音,所谓“耳弗及也”就是这个道理。要使“耳之察和也”就需要“察其清浊也”,因为先王制钟的时候,都是考虑到钟的音域适中问题,所谓“大不出钧,重不过石”。所以“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单穆公在这里是把人的听觉对音响感受能力和接受能力,作为音乐评价的基础,来对景王在铸钟行为中的追求宽音域、大规模审美倾向进行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无益于乐”,也就是无益于听众对这种音乐的接受。
第二,从“音乐→心理”的心理关系层面上看,他们主张“乐”应从“和”。这个层面的“和”,就是乐音的和谐、怡神。在他们看来,人的心理的审美谐和感是先在的,这个审美心理对后生的音乐音响层,产生一种谐和音响的审美期待,铸钟行为必须符合这个期待才能够成功。从音响自身来看,人的心理谐和感的满足与实现,又是以乐律学体系的建构、乐器制作工艺学方法的完善为前提的。从这一点上看来,他们的音乐批评有着丰厚的乐律学体系的研究积累和乐器制作工艺的长期实践。我们从他们质朴的批评话语中,不难感受到以上这些信息:单穆公曰:“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以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伶州鸠道:“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乐从和,和从平”。这就是他们对音乐与人心理关系问题所作批评的主旨之所在。在和谐的外在乐音体系中,满足人心理对和谐乐音的审美期待。
第三,从“音乐→政治”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看,他们强调“乐”应从“和”。这个层面的“和”,就是音乐与政治的和谐、共处。乐政关系,是这个时期乃至以后的雅乐批评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单穆公与伶州鸠也不例外。所以,他们都不是从音乐的自律性艺术规律出发,去进行音乐批评的。当然,不是艺术自律性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按照自律的艺术规律思考与批评。他们的批评观念虽然是他律的,但是在批评操作中,他们是非常懂得按照音乐艺术自身的规律说话的。单穆公从听觉和视觉艺术的自身规律出发,以耳目的感受与人心、行为、政治的相互关系,向景王劝谏。指出:“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伶州鸠也是从乐政关系的角度,对景王提出劝谏。认为:“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植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他对“和”的认识,是建立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综合的基础上的,它们的关系是:由听觉生理之“和谐”,进而审美心理之“和谐”,再进而群体社会之“和谐”。把音乐与人心,音乐与社会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14.钟子期
钟子期(公元前413年—公元前354年),名徽,字子期,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汉阳人(今湖北武汉蔡甸区)。相传钟子期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背扁担、拿板斧的樵夫。
琴家俞伯牙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经过汉江时临江鼓琴,钟子期恰巧经过被琴声吸引并发表现场乐评,这便是史上著名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对此,战国·郑·列御寇《列子·汤问》中,是这样记载的: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是这样记载的: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钟子期与俞伯牙之间的批评与表演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子期与伯牙的这段“知音”之交,较早地向我们说明了这样的道理:音乐创作、表演者与音乐欣赏、批评者之间呈现为密不可分互为条件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双方对于对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15.雅俗之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郑风·子衿》
这是被誉为“郑卫之音”的代表作《子衿》。这首诗歌(含音乐)对赋、比、兴手法运用异常娴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臻达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即使今人读来仍会倍感雅致、清新、温馨、缠绵,但该作在它诞生的时代——春秋时期,却被士大夫群体视为“洪水猛兽”。围绕着这类诗歌作品,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甚至是影响至今的音乐批评重大事件——雅俗之争。
雅乐的批评观念来自于周代初期的礼乐治国的“乐”。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治理文化体系,涵盖宗教、文化、艺术、娱乐等整个文化系统。这个系统里的核心构建元素,就是本节所列诸位政治家、批评家所推崇、维护与扶持的雅乐。与之相对而立的就是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时人也称之为“新声”“新乐”),“郑卫之音”在周朝广泛地流传于郑国和卫国的民间。周朝的郑国、卫国,原来就是商朝遗民聚集的地方,“郑卫之音”就是保留了浓郁的商族音乐风格的一种民间音乐。殷商时代是一个“尚声”的时代,追求声色之娱,是这个时代音乐普遍审美价值取向。所以,对音乐的听觉美的追求和内心情感抒发的追求,就成为“郑卫之音”创作与传播的批评标准。这是一种肯定人的主体情感需求的音乐批评观念,对于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音乐活动,《诗经·郑风》是这样记载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魂,秉兰拂除不祥。”这段史料,记述了郑国百姓每年阳春三月在溱河、洧川一带,聚会、祭祀的热闹场景。《诗·郑风·溱洧》还记载了男女互赠香草以示爱慕的活动情况,每当这种活动的事后,都会辅以音乐和舞蹈。
对于这种“尚声”、重情的民间音乐,在周朝中期就产生了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独尊雅乐的周王室部分成员及其雅乐制度的捍卫者对之加以贬斥。贬斥者一般将雅乐沦丧的根源归咎于俗乐的博兴。即使是贵族统治者,也有大批俗乐的追随、拥护者。譬如:齐国的齐景公是一位对音乐有着特殊嗜好的国王,他曾经闹出了“夜听新乐而不朝”的“典故”。他的一句名言:“夫乐,何必夫故哉?”就是对“郑卫之音”之类“新乐”的审美价值的肯定性批评。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这位国君对“新乐”的迷恋,对“旧乐”的唾弃。对于“新乐”的这种诱惑力,魏文侯的一段话也颇具意味:“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魏文侯之后的齐宣王更为直白地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史称“最为好古”,并在诸侯中享有高尚威望的魏文侯,对雅乐和俗乐的评价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郑卫之音”是如何深入社会人心的。对于“郑卫之音”的褒扬式评价,还可以举当时的两位国君——齐宣王和梁惠王为例。喜好音乐的齐宣王对无盐女钟离春说过这样一段话:“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梁惠王毫不掩饰地直言自己的审美批评取向:“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郑卫之音”的盛行,加速了“礼坏乐崩”的进程。推崇礼乐制度的孔子向世人高呼:“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进而《乐记》也认定:“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以对“郑卫之音”的“雅俗之争”作为标志,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的历史进入到一个多元的时代。
第二节 《诗经》
《诗经》②,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为《诗》,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诗经》忠实地记录了周初至末期五百余年的社会面貌。
《诗经》中的作品,全部可以演唱。关于此朱载堉说,可以证实:“《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朱载堉《乐律全书》)。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以诗论乐”“以诗评乐”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由《诗经》开始的。在这里有许多作品的内容,都涉及到了音乐。以下就将之摘录出来,谨对其中音乐批评性的成分予以解析。
①《邶风·简兮》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简兮》乃“十五国风·邶风”之第十三首,史上诸家对其内容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如《毛诗序》、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吴闿生《诗义会通》等,认为《简兮》是讽刺卫君不能任贤授能,使贤者居于伶官,等等。由于古汉语文字的抽象性缘由,关于诗的内容,后人可以不断地给出百般说法。但诗中对于当时乐舞表演场景、人物形象的刻画,却是栩栩如生、细致入微而又客观具体的。总体上看,作者是带着浓浓的爱意,对这场《万舞》的表演现场展开批评的。第一段,是作者对心中“美人”(现代人所谓的“帅哥”)即将登场,吹奏编管乐器(龠)、表演舞蹈作品(《万舞》先是武舞,舞者手持兵器舞蹈;后是文舞,舞者手执鸟羽、乐器舞蹈。毛传:“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陈奂传疏:“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我之帝所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于九奏万舞”)的场景描绘,与心理期待:“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阳光照在他的头上,他站在前排的中央。第二段,是对表演场面的描述与批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肌肉男”,在表演的舞台上,以“武舞”的张力,充分地展现自己的肌体强壮的力度美感;用“文舞”的徐缓,细腻地表现自己身体的内在美感。这里的“如虎”“如组”,就是细腻形象地刻画这位舞蹈者具有雄性威猛张力与柔性细致表演的修辞手段。仅仅两个词,就将表演主体的整体轮廓与精神状态表现得栩栩如生。第三段,是对人物表演、艺术形象的进一步深入地刻画与表现:“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在台上,舞蹈表演者左手执着吹管乐器龠、右手握着雉鸟的羽旄,伴随着音乐的律动,且吹管奏乐、且手舞足蹈,其面色如赭土般红润,其形象与表演将台下观赏的公侯大人们深深打动,并向之赏赐酒水。这是对集乐器演奏者、舞蹈者于一身的“硕人”“美人”多才多艺的表演能力与艺术魅力的深入刻画与赞美。通过“公言锡爵”四个字,就将现场表现的艺术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第四段,是作者内心情愫的袒露部分:“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这是一首以音乐批评的形态写成的爱情诗,作者通过听乐、观舞的现场体验,细致刻画表演者的外部表演形态与内在艺术气质,是《诗经》乃至于中国最早的“以诗论乐”“以诗评乐”的代表作。
②《大雅·灵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廱。
於论鼓钟,於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
《灵台》乃“大雅·文王之什”之第八首,诗中描绘的是鼎盛时期的周王朝建造“灵台”,并在此之上表演“鼓钟之乐”敬天礼地,施行国家仪式的情形。按鲁诗的解析,全诗分为四段,第一段六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写的是规划建造灵台的情形:国君开始规划灵台建筑工程,工程师精细筹划巧妙设计。之后,再由百姓共同出力建筑,时间很短就建设成功。第二段也是六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是对灵台建成后,君王站在灵台之上怡然欣赏“灵囿”里的“麀鹿攸伏”“白鸟翯翯”,在“灵沼”边观察“於牣鱼跃”的美好场景。第三段四句:“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廱。”开始进入音乐批评的状态,前两句是对音乐表演环境的铺垫性介绍:以优良木材建造的悬挂钟鼓的木架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巨大的鼓、巨大的钟(镛钟)坐落其中。后两句是对钟鼓之乐演奏情形的评价:钟鼓齐鸣摄人心魄,恢弘的声响回荡在圆形的“辟廱”(也即“辟雍”,为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之内。第四段也是四句:“於论鼓钟,於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前两句是对第三段后两句的重复,这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意在渲染钟鼓之乐轰鸣,给人的心理带来的震撼与欢愉的感受。后两句是对乐器与乐师的描写:蓬蓬的鼍鼓,是瞽目乐师带着钟鼓乐队的杰作。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时期仅存下来的史诗,而这首《灵台》则忠实地记录了此时祭祀天地、演奏钟鼓之乐的情形,并对其中的乐器、演奏家等音乐表演的主体,给出了言简意赅而又意蕴无穷的批评,是我们了解鼎盛周朝雅乐的乐队建制、演奏方式等,不可或缺的历史史料。
注释:
①《晏子春秋》采用版本: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
②《诗经》采用版本: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