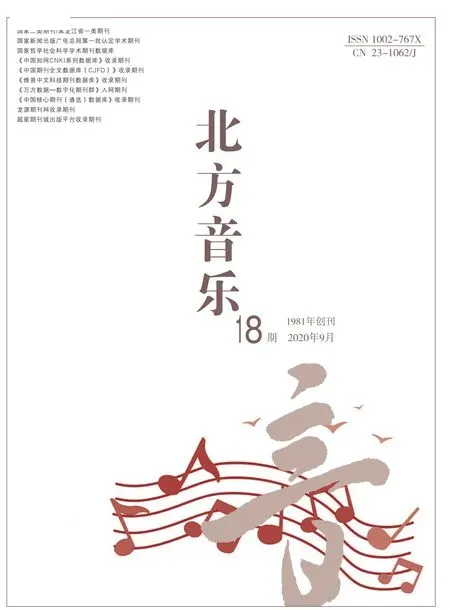浅析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
——苦难不屈的精神
2020-12-02王诗谊
王诗谊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7)
一、苦难精神的形成
历史时期中每一个时代的确立,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成为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征。俄罗斯沙皇的统治制度,就是一种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农奴制是一种极端落后的统治制度,它不仅制约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也束缚了俄罗斯农民的自由,使当时的俄罗斯农民完全成为地主与农奴主的奴隶,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也没有自主权,更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在封建专制的威压下苟延残喘。生产技术的落后与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农民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剥削与奴役,也正因如此,才导致这一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从未停止。
一直以来,沙皇政府都在极力镇压一切与沙皇维护的农奴制相悖的民主进步思想,将独裁暴力的专制意识等同于国家律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极力宣扬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可动摇的地位。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可以说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形成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铸成了俄罗斯人性格中沉重坚忍的一部分。随着18世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启蒙思潮、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俄罗斯人民为摆脱沙皇专制的枷锁,加速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奋起反击,民主解放思想迅速成长。从18世纪后半叶起,到19世纪后半叶的一整个世纪里,俄罗斯都在民主解放斗争的滚滚潮流中激荡前进。历史的进程势必在激烈的斗争矛盾中进行,斗争和失败是每一次革新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只有在这样无数次往复的过程中才能推进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俄罗斯文化中历来有偶像崇拜的传统,为了人类甘愿献身走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以其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基督教和东正教所宣扬的“人生就是苦难”的思想,成为滋生俄罗斯人民接受苦难思想的土壤。古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勃在基辅的政治大动乱中光荣就义,以其基督教式的受难和清白平息了动乱,这也成为俄罗斯文化中圣徒崇拜和苦难崇拜的起源。俄罗斯对民族圣人鲍里斯和格列勃以基督的方式甘愿受苦,并把受苦受难当作清除他人罪孽和上帝罪人的手段,为俄罗斯人树立了不朽的榜样。基督教和东正教中忠、诚、仁、义、舍己、为公、虚心、贞洁、协力、合群、负责、坚毅、谦恭、永不绝望、为国家为义理奋斗至死的人格理念,与自觉承担苦难一起,构成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比如俄罗斯诗人因诺肯基·安年斯基曾在这首名叫《弓与弦》的诗里这样写道:“琴弓和琴弦在亲吻,亲在发出美妙音乐的同时却在忍受剧烈的痛苦。”于是,琴弓悟到:“原来人们所以为的音乐,原本是它们的苦痛。”通过这种隐喻,安年斯基表达了俄罗斯人对于文艺本质的一个重要的看法——诗歌是苦难的象征,艺术是对痛苦的玩味。另一位大思想家瓦·罗赞诺夫说得更加明确:“文学是一种最大的最忘我的幸福,但在个人生活中同时也是一种最大的痛苦。”对于苦难的审美,对与受难的理解,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因此不难发现,这种苦难思想不仅在文学作品中有体现,在音乐作品中也同样得到了传承。
二、格林卡与《伊凡·苏萨宁》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出生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的诺沃斯巴斯克村,这是一个处处充满着俄罗斯民族风情音乐的村庄,格林卡的童年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度过,才得以在日后的音乐创作中获得重要的民族音乐素材。俄罗斯的民间音乐始终是格林卡创作的根基,无论是年幼时保姆的哼唱或是后来与民歌手的交往,都为这位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提供了最初的音乐基础。1812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年仅八岁的格林卡目睹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俄罗斯民众为了保卫家园纷纷奋起反击,在战争中那些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英雄事迹无一不触动着幼小的格林卡。俄罗斯人民激昂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舍身为国英勇果敢的精神,在年少的格林卡心中埋下了民族意识的火种,也为后来格林卡创作民族英雄歌剧《伊凡·苏萨宁》打下了坚实基础。
格林卡创作的这部民族英雄歌剧《伊凡·苏萨宁》(又名:为沙皇献身)是一部五幕歌剧,剧本由编剧罗森编写,1836年首演于圣彼得堡,这也是格林卡创作的第一部民族英雄主义歌剧作品。歌剧以民族英雄伊凡·苏萨宁为主人公,描述了俄罗斯人民万众一心,在莫斯科奋力围剿波兰军队的事迹。主要讲述在俄罗斯与波兰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一支波兰军队偷偷潜入了农民苏萨宁的村庄,将村子包围后的波兰军队以此胁迫苏萨宁帮助波兰军队,英勇的苏萨宁佯装同意,后将波兰军队引入了不毛之地,与波兰军队同归于尽的故事。这部歌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最早尝试俄罗斯民族主义道路的作品。整部歌剧中格林卡使用了很多俄罗斯民间音乐元素,用婉转悦耳的民间曲调表现俄罗斯,用粗野残暴的音调描写波兰军队,两种音调在作品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外,歌剧一开始为观众展现了苏萨宁家乡宁静美丽的景色,此时人们对祖国有着无限的忠诚,军民一心时刻准备着为民族自由献出生命,正是从这里,表达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勇敢无畏,也进一步表现出了俄罗斯人民精神世界里对于苦难的理解。受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人,习惯于把苦难当作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认为只有通过苦难才能得到拯救。他们崇拜苦难、尊重苦难、赞美苦难的精神在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苏萨宁身上得到了体现。苏萨宁是英雄,因为没有经历过苦难的英雄是无法在俄罗斯人心中获得尊崇的。
三、普希金与穆索尔斯基
除了如上述对英雄人物苦难的正向崇拜,还有如《鲍里斯·戈杜诺夫》一样这种“另类”苦难的存在。
创作于1825年的《鲍里斯·戈杜诺夫》是普希金所写的一部历史悲剧作品,鲍里斯·戈杜诺夫时期在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普希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正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社会现实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普希金从鲍里斯·戈杜诺夫时代找到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历史对照和契合点,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抨击沙皇专制和农奴统治。在这部作品里,普希金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民形象,表现出他们的痛苦和反抗,塑造了整体的、人民的悲剧形象。普希金的这部作品不仅使当时的俄罗斯文坛受到了震动,更让整个俄罗斯文艺界都感受到了波动,例如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根据普希金《鲍里斯·戈杜诺夫》这部作品,创作了他音乐生涯中最重要的同名歌剧。
身处俄国反沙皇专制、反农奴制民族思潮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穆索尔斯基,在此时创作了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贯穿全剧的正是各个阶级的斗争与苦难。此时的沙皇政权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断镇压民主运动,使这一时期的许多优秀民主斗士都先后惨遭迫害。于是在这部歌剧作品里首先出现的就是人民与沙皇统治阶级的矛盾,作曲家用音乐表达了劳苦大众在沙皇专制下的愤懑,并将疯僧的悲歌当作全剧的结尾,写下了悲伤的结语。此时的疯僧不仅是受苦受难普罗大众的代表,也是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的代言人。在这里也不难看出对苦难的崇拜,斗争就要有牺牲就要有人为之献身的精神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其次就是对于剧中主人公鲍里斯的塑造,穆索尔斯基表现出了鲍里斯的内心矛盾与冲突。鲍里斯是拥有帝王权杖的暴君,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为良知所折磨的罪人,作曲家通过表现鲍里斯心中对权力野心和人性未泯之间的斗争,深刻展现了鲍里斯必然承受苦难的悲剧性。并用鲍里斯这个与人民对立的形象,揭露了任何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和命运的惩罚,都会遭受苦难。
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写出了英雄与民族的抗争,他们用某一个角色来表现出整个俄罗斯民族,而柴可夫斯基之所以能在世界乐坛占据重要地位,这和他用音乐语言说出俄罗斯人的灵魂和心灵秘密有着很大的关系。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写尽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他们对苦难的超越,对灵魂的涕泣和怨诉。柴可夫斯基的成也在于表现人的痛苦,没有哪一位作曲家能像他一样,把爱的欢乐和痛苦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四、结语
纵观19世纪的俄罗斯,无论音乐或是文学,无论作品表达民族精神或是个人经历,苦难,都是俄罗斯人始终无法回避的主题。根植在俄国人观念里的通过接受苦难获得拯救的精神时刻提醒着他们,眼前的一切无论是幸运也好不幸也罢,全部都是上天的旨意,都应该坦然接受。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只有经受住苦难的洗礼才能获得拯救,对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自身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就是承受苦难。就像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大都奉行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们崇拜像圣愚一样看似疯癫实则怀有圣德承担着苦难的人,正是这种观念,让他们鄙视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福利,鄙视安逸的生活。
众所周知,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受到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极大影响,不管是格林卡、达尔戈梅日斯基还是“强力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里等人思想的影响,如此,就更不难理解19世纪俄罗斯音乐作品中对于苦难独特的审美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虽然较于欧洲其他国家更崇拜苦难的意义,但他们并不是沉溺于苦难中的民族,他们一面承担着沉重的苦难,一面寻找如何走出苦难,无论过程要付出何种代价都在所不惜。这种面对苦难奋而不屈的精神,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