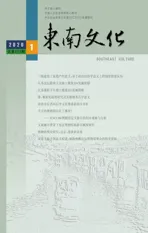博物馆观众研究:过去、现状和未来
2020-12-01约翰福尔克朱迪思科克吴蘅
〔美〕约翰·福尔克朱迪思·科克(著)〔中〕吴蘅(译)
(1.美国创新学习研究所;2.加拿大维多利亚美术馆)
内容提要:博物馆观众研究涵盖多种研究调查,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非正式(或自由选择)教育环境下观众的行为、态度、兴趣、动机和学习情况,以及他们的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绝大多数博物馆观众研究在本质上都是评估性的。尽管观众研究和博物馆评估这两个领域有所重叠,但它们通常采用明显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当前,针对博物馆的自由选择式或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和评估领域有五大重点研究方向:展览研究、博物馆作为社会背景、博物馆观众细分、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博物馆作为促进学习的场所。未来,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可能趋势有如下几方面:确定该领域的模型、框架和一致指标;解决研究人员之间因研究范式、观点不同而形成的紧张关系;最小化学校内外学习之间区别;东南亚博物馆界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将带来的对参观者研究的需求和重视。
一、导言
虽然目前博物馆观众研究尚无统一的定义,但不妨将其描述为:涵盖多种研究调查,以更好理解非正式(或自由选择)教育环境[1]下观众的行为、态度、兴趣、动机和学习情况,以及他们的参与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一个常用同义词是参观者研究。
同样,博物馆观众研究也没有一致的目标和参数来规定哪些应该或不应该包括在其研究范围内,即便对此已有一些相关讨论。例如,美国博物馆联盟的观众研究与评估委员会(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Standing 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曾提出一个非常狭窄的研究范围,即博物馆观众研究是指“系统地从博物馆的实际和潜在参观者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的过程,以在规划和执行与公众有关的活动中增进和利用这些知识”[2]。
从评估角度出发,斯蒂芬·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认为博物馆观众研究包含以下四个基本假定。(1)参观者权益倡导是首要:参观者的意向应在展览和项目设计中起主要作用——假设之前并没有如此操作。(2)多学科的观点:参观者研究融合了展览设计、教育、访客服务、市场营销、娱乐和评估等多方面专家的专业性和观点。(3)正式评估:参观者研究可以回答有关展览或项目的效果和效力问题。(4)科学方面:参观者研究利用一种收集参观者信息的科学模型及一种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市场营销等学科借鉴的关于理论构建的科学模型,来构建基于经验的参观者行为和学习原则。
类似的主题可以在美国参观者研究协会(Visitor Studies Association,VSA,一个致力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专业组织)提出的定义中找到。VSA认为,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在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对人类体验的跨学科研究,并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信息或数据,为诠释性展览和活动提供决策依据”[3]。其应满足以下三项标准:遵循严格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的研究方法;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为之服务;旨在改善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实践。
对照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现状,这三项标准似乎较为苛刻,因为许多研究实例(包括已发表的研究文章)并未能满足其中一项或多项。
虽然大多数原创的博物馆研究都可以归类为基础研究,但绝大多数博物馆观众研究在本质上都是评估性的,因为它主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需要的样本量较小、预算较少,所需的培训或经验也较少。早期的研究或评估更关注传统的博物馆工作的核心——展览和展示。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赞助者们逐渐重视结果评估以证明其影响力,该领域的范围也扩大至博物馆展览和活动参与情况的研究和评估。本文将总结观众研究和博物馆评估两方面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个领域有重叠之处,但它们是不同的,且通常采用明显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二、博物馆观众研究发展概述
尽管参观者研究(非博物馆评估)的文章发表数量在过去25年增长了约500%[4],但这类研究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缓慢的。对非正式或自由选择学习环境下参观者的系统实证性研究约始于100年前,但在此期间这类研究并不多见。最早的较为著名的参观者研究——尤金·罗宾逊(E.Robinson)[5]及其学生亚瑟·梅尔顿(A.Melton)[6]的研究——重在考察参观者在观看艺术博物馆展览时的行为和疲劳度。但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真正展开则花费了近一代人的时间和精力。
早期博物馆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包括:哈里斯·谢特尔(H.Shettel)[7]、钱德勒·斯克里文(C.Screven)[8]、罗杰·迈尔斯(R.S.Miles)[9]、敏达·鲍伦(M.Borun)[10]、罗伯特·沃尔夫(R.Wolf)[11]、莫莉·霍德(M.Hood)[12]和约翰·福尔克(J.Falk)[13]。正是在此期间,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出现了定性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最初运用于评估性研究。正如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科学领域一样,此方法最初引起了争议,被认为缺乏传统的定量假设检验方法应具有的严格性和价值。到20世纪90年代,定量、定性研究之争已基本消失;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并且每种方法都适合在特定条件下回答不同类型的问题。到20世纪末,参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研究人员及其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数量都已大大增加。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多种环境下参观者的行为和学习。但是,多数研究因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U.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主要针对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构,如科学中心、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和水族馆等。代表人物包括:史蒂夫·比特古德(S.Bitgood)[14]、罗斯·鲁米斯(L.Loomis)[15]、贝弗利·塞雷尔(B.Serrell)[16]、朱迪·戴蒙德(J.Diamond)[17]、约翰·科兰(J.Koran)[18]、林恩·迪尔金(L.D.Derking)[19]、亚瑟·卢卡斯(A.Lucas)[20]、盖亚·莱因哈特(G.Leinhardt)[21]、保莱特·麦克马纳斯(P.McManus)[22]、莱尼·雷尼(L.Rennie)[23]和本·加蒙(B.Gammon)[24]。尽管以上大多数均可视为基础研究者,但在此期间,研究与评估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迈入21世纪的这20年,随着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出现了更多的研究人员及更多样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之前,博物馆观众研究成果的发表分散在各类学术期刊上,使得对此主题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寻找各种相关研究。从21世纪开始,新增了好几种专门针对此类研究主题的期刊,或是在现有期刊上开辟了相关栏目。其中,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期刊或栏目:《访问者研究》(Visitor Studies),《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的专栏“日常生活中的学习”(Learning in Everyday Life)和《国际科学教育》(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的第二部分“科学传播和非正式教育”(Part B: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l Education)。纵观其历史发展,虽然目前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该项研究[25],但在美国进行的博物馆参观者研究的数量占比仍较大。
三、博物馆观众评估发展概述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对参观者的研究重点从考察其在非正式或自由选择环境下的学习情况,转向对展览和相关活动有效性的评估,例如参观者如何使用展览、标牌等教育性资源,或展览是否已进行关键信息的传播。这类研究主要在博物馆进行,采用大量追踪计时研究、展览出口处采访及对展览关键要素的集中观察等方法。其他研究则着重考察参观者在参观某个展览时的路线寻找、行为和使用模式,以及探讨不同类型的参观者(如男性/女性、成员/非成员、团体/个人、普通观众/专家等)之间的区别。所有这些研究的目的是帮助机构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参观者是谁,这些参观者做些什么,以及自由选择型学习机构(如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帮助参观者获得成功的参观体验。
如《质疑假设》(Questioning Assumptions)[26]一书所提,随着该领域对学习的理解从行为主义范式转变为建构主义范式[27],博物馆从业人员开始将前端评估[28]纳入实践。这项工作使用的方法本质上往往更具定性,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探索未知——参观者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经验和世界观会带来哪些参观体验。它着重指出:博物馆的工作是有目的的,有特定的学习目标;博物馆的工作已从对专家们认为重要的知识进行传播到创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参观者得以借助专家精心制作的故事自行构建意义。
随着美国问责制标准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重点从对参观者反应的研究(花费多少时间、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转移到对参观结果的衡量上(他们在参观之后发生哪些改变)。同样,由于学界对学习的理解、对博物馆在社区作用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这也要求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的参观结果。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将“成功的参观结果”定义为“为人们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活动参与者所取得的成就,或其技能、知识、态度、行为、条件和生活状况的改变……任何旨在创造此类好处的项目都意在取得成功的参观结果。”[29]
基于参观结果的评估明确了哪些指标能够可靠地证明预期或非预期的变化。它系统地收集这些指标的信息,并以此表明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博物馆等自由选择式学习机构使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推断其活动的影响力,以提高活动质量、支持持续的活动资金或进一步获得财政支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流观点认为在项目完成后进行评估很重要,因为这时可以考察参观者如何使用一份已完工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认识到如果从项目(展览或活动)一开始就引入评估则会取得最好效果。通过清楚地阐明项目要达成的结果及衡量这些结果达成的指标,项目执行人员和领导人就可以按照明确的方向团结起来。通过这个过程,博物馆等机构可以充满自信地陈述其目的,并为实现目的而努力。
理论上讲,综观多个研究,一个机构在社会中的积极角色是可以被树立的;通过汇集整个领域的研究,自由选择式学习的社区或博物馆类机构也可以主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然而,尽管现在已经有了数百项此类研究,然而上述目标仅实现了一部分。由于评估性研究的质量和本质有着高度的变异性,对结果进行直接比较几乎不可能,遑论对结果进行聚合,由此所有研究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低于预期。尽管如此,某些机构进行的单个评估研究仍对这些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借助这些积极成果,全领域的实践和政策也有所改变。
四、“我们学到了什么”概述
在对自由选择式或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和评估领域,特别是在以博物馆为重点的研究领域,出现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展览研究、博物馆作为社会背景、博物馆观众细分、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博物馆作为促进学习的场所。下文对以上五个研究方向中以博物馆为中心的研究进行简要阐述。
(一)展览
大多数与博物馆有关的研究均已对展览、展品和说明牌在教育公众方面的作用进行过探讨。其中一个组织模型是“学习的背景环境模型”(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30],主要针对此方面及其他博物馆研究方面。该模型假定学习始终与所处环境相关,且受三个关键背景因素(个人、社会文化和身体)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背景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学习体验的本质。多年的计时和追踪研究表明,博物馆中吸引最多注意力的部分通常是那些摆着最大件展品、进行最显著居中展示的区域[31]——这一点也许不足为奇。最近一项采用眼球追踪技术以准确追踪参观者真正驻足观看区域的研究表明,博物馆展厅存在大量的参观者从未驻足的区域,这多与该区域的位置有关,而非展示的内容。即使是最大、最闪光的展品,一旦放置在这些“死角”中也会被忽视[32]。同样,说明牌也常被有选择性地阅读,观众花费在阅读说明牌上的时间呈双峰态势——要么完全忽略,要么把说明牌从头读到尾,仅有少数观众处于这两者之间[33]。
但这并不能表明博物馆一般不支持“新”学习方式[34],实际上博物馆是支持的,尤其表现在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活动等预设环境中。例如,楠·雷纳(N.O.Renner)[35]进行的研究发现,参观自然史博物馆的儿童能够建立起对高级抽象科学概念的比较成熟的概念化理解。儿童最初与具体物件和现象的直接互动,会为他们最终建立起抽象概念奠定必要的记忆、特征、类别和因果推理基础。她还发现,与同龄儿童和教育人员的社交互动能大大促进这一过程。
研究还表明,创造出大多数博物馆专业人士希望达到的更高层次的智力成果的展览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精心策划和支持参观体验。例如,美国旧金山探索馆(Exploratorium)的托马斯·汉弗莱(Thomas Humphrey)、乔什·古特威尔(Josh Gutwell)等人员开发制作的展览能够支持参观者“主动 长 期 参 与 ”(active,prolonged engagement,APE),即参观者较长时间地参观、进行多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更多地使用展览(而不仅仅是说明牌)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能够实现这些成果的展览可分为四大类:邀请参观者探索某种现象,邀请参观者探究某事物,邀请参观者观察某种美丽现象,邀请参观者用较小的元素构造事物。让展览设计获得成功的策略包括将展览分成多个可以开展小组参与活动的“站点”(station),或在展览的标牌上提出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乔什·古特威尔和苏·艾伦(Sue Allen)制定了使游客提出“多汁问题”(juicy questions)的策略[36],再次强调要让展览达到这些成果需要大量的额外设计考虑,并且常常需要用到人力帮助和支持。
了解观众参观博物馆后的长期影响有助于博物馆规划未来的实践,收集实现其价值使命的证据,当然这也更艰巨且花费大,但能获得一些重要的实例来证明这些参观的影响。我们知道,参观者在参观博物馆一年后所记住的与其说是参观的内容,不如说是他们的个人体验——与谁同去、为什么去、感觉如何[37]。学校组织的艺术博物馆的实地参观可以增加学生对多元观点的容忍度,这种受益对条件不好的学生更为明显[38]。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参观博物馆的记忆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39];但是社交环境似乎是许多这些记忆的核心[40]。
博物馆评估已产出大量关于展览空间设计、展品放置和展览标牌设计的实用信息[41]。研究成果中既有一般性的总结,如语言选择对展览标牌阅读的影响[42];也有更为具体的事例,如若博物馆提供多个椅子或长凳,使学生可以坐在一起,那么女孩将更频繁地与计算机交互[43]。尽管已有一些关于如何创建有效展览的研究出版,但大多数评估结果仅限于进行该评估的机构内部,只为内部使用,基本上不对外公开。有兴趣了解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参阅一些期刊,如美国博物馆展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eum Exhibitions)的出版物《展览》(Exhibition)。
(二)社会交互
大多自由选择式学习环境本质上都是社会环境,因此,观众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视角来自列夫·维果茨基(L.S.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44]。大多数人都愿意作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来博物馆类的机构参观,研究表明,在这些参观过程中,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同行者身上[45]。参观博物馆过程中的社交互动包括观看展览和阅读展览说明而产生的问题和讨论,以及与博物馆完全无关的对话、浏览和触摸等。这些互动在塑造参观者的参观体验及其从中所构建的意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观看展览外,许多人去博物馆的目的包括参加课程、青少年活动、家庭日、日间营和演讲者之类的活动。相当多的研究已经对社会团体(尤其是家庭团体内部的互动)对学习尤其是科学学习的重要作用作了探讨[46],重点探讨的是对话的作用[47],最近的一些研究更着重考察身份认同的形成[48]。关于以家庭为主的活动对学习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与值得信赖的且同样以支持家庭、年轻人、社区为目标的社区机构相融合时,这些活动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学习环境[49]。
当然,观众在博物馆中所接触的并非都是其所属社会团体的成员。观众既与其他团体的观众互动,也与场馆的工作人员互动。研究表明,观众的这些互动,尤其与其社会团体以外人员(如博物馆讲解员、导览员或其他观众)的互动会对学习的范围和性质产生影响[50]。
类似博物馆的环境也为渴望持续学习、进行社交互动、具有目标感的成年人提供了重要的社交联系。在北美,博物馆的志愿者通常比有薪人员多(以个人数量而非带薪小时计),大型博物馆“雇用”的志愿者数量是有薪人员的两倍。随着博物馆规模的减小,这一比例显著增加[51]。研究表明,成为博物馆志愿者的机会为退休人员——也逐渐为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提供了重要的社区意识和贡献感[52]。
(三)博物馆观众
许多参观者研究重在考察哪些人去博物馆、哪些人不去博物馆,所作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更普遍的社会或社会群体,内部评估人员则主要针对其所服务机构探讨这些问题。早在1983年,霍德在《远离》(Staying Away)中就已描述不同类型的人如何对休闲的目的和实现方式持有不同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他们对于博物馆能否满足其需求的看法[53]。尽管起点很高,但是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类研究主要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例如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来进行,偶尔也探讨特定子群体如非裔美国人对博物馆的使用[54]或家庭团体对博物馆的使用[55]。博物馆用这些数据来创建受众细分框架,用于市场营销和规划决策,但通常投资回报率有限。近来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基于人口统计学的受众研究的局限性,研究转向更偏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话题包括动机认同[56],对思想、人、物的刺激需求[57],以及与马斯洛需求(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层次一致的动机层级[58]。研究已经开始揭示人们为什么(why)参观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做什么(what)及在参观中进行什么样的学习(what learning)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59]。然而,针对非参观者的研究还很少[60]。不过,由于近来对社会中更广泛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关注,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所改变。
(四)技术
科学技术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的生活,博物馆世界也不例外,大量参观者研究已对技术在博物馆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探讨。此外,新技术也在改变观众研究的方式,使得研究人员能够以全新的可能和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了解参观者。
今天的博物馆通常使用多种形式的数字媒体,如视频、音频、动画和计算机演示等[61]。技术和社交媒体使博物馆以更加直接和真实的方式与观众交流、聆听他们,并将观众反馈融入营销、展览和博物馆政策中[62]。以往展览的思想必须完全由展品本身或说明牌来传达,如今博物馆可以使用更多工具来传达信息和关键思想。多维、多感官体验的时代已经来临。参观者可以沉浸在再现的环境中,周围环绕着高清视频图像、高保真声音、虚拟现实、气味、纹理、颜色和振动。实际上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竭力描绘这样一个未来,即游客可以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今天的大多数参观者都承认博物馆对技术和媒体的运用促进了不同深度信息的传达,增加了个人灵活性和选择机会。但是,人们很少认为他们是为了这些多媒体而参观博物馆[63]。人们只有在对话题感兴趣并且有动力去学习更多知识时,才会花时间观看、收听或与媒体互动。若他们对话题不感兴趣,无论多么耀眼、昂贵或精心制作的多媒体,他们都不会关注[64],也不会选择数字化工具[65]。
不管怎样,多媒体已成为21世纪博物馆的固定装置。由于其固有的强大视觉和听觉特性,多媒体能以物品或现象本身无法实现的方式来支持和补充、呈现和解释[66]。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最近的一项研究初步证明多媒体尤能够促进游客的同理心,从而使游客将自身与早期历史时期先驱者的故事关联起来[67]。多媒体还可以为展品创建视觉环境,让展品置于适当的历史和/或文化环境中,进而帮助参观者更好地理解展品并超越其具体特征。最后,对于一些新博物馆而言,多媒体本身越来越成为展品[68]。
关于展览中多媒体的使用,观众研究可揭示出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的总结是观众使用多媒体基于高度的自我选择[69]。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在各种不同机构(包括科学中心及艺术、历史博物馆)中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参观者都能在任何展览中与所有媒体元素进行互动。实际上,多媒体的使用与说明牌的使用非常相似,参观者或全程使用,或完全不使用,很少有中间立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参观者花费大量时间(即使不是大部分时间)与媒体元素进行交互,这支持了多媒体是某些参观者的重要选择这一观点。除了展示的质量和参观者的兴趣外,另有许多因素似乎也会影响博物馆参观者对多媒体的使用[70]。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多媒体所在的物理环境。比如,若有一个区域提供座位,且即使参观者在此多作停留也不会妨碍其他游客,那么参观者就更有可能坐下观看电影;如果电影或互动设施被设置在繁忙的走廊上,且既未预留凹室或空间供人们观看,也没有可供人坐的地方,那么参观者会因感到不舒适而很少完整观看这些演示。虽然随着技术的便捷和普及,参观者观看演示的频率会增加,但是仅因为有可用的技术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会被使用。例如,尽管基于电话的技术(如应用程序导览)已经存在多年,但大多数参观者都仅使用其智能手机上的摄影功能[71]。
技术也在改变博物馆走出馆舍与公众进行互动的方式。现在,无论通过网站还是社交媒体,博物馆都可以通过新方式跨越遥远的距离与人们建立联系。目前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些新技术如何适用或不适用,但这是一个迅速扩展的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72]。
技术带来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博物馆参观者研究中,最简单、最普遍使用的技术是以手持式平板电脑或手机为数据采集设备[73]。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使用射频识别(RFID)标签[74]来追踪博物馆的观众,以更好地了解展览[75]。其他研究人员已将多种技术集成到博物馆,不仅可以追踪参观者的空间移动,还可以追踪其在参观过程中的生理反馈,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检测情绪和参与行为,并放置记录设备以便将来对访问者的体验进行细粒度分析[76]。在这个趋向上走得最远的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赛博实验室(Cyber Lab)。该实验室部署了一整套工具,使用实时预测和评估,定制基于地点的网络学习体验,让参观者得以在学习环境中构建知识,成为研究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工具的数字化性质使得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不仅可以在博物馆进行,也可以由研究人员在远程操作。在使用技术来服务受众研究的这场革命面前,我们现在只是开始。
(五)学习
许多研究人员不仅试图了解参观者与博物馆的展览、活动及其他即时体验之间的互动,而且试图了解这些体验的短期和长期教育影响。博物馆中引人注目的是物——绘画、标本、再现的历史遗迹、动植物、一件科学互动装置、一道美丽的风景。参观者发现“事物”令人着迷,不仅想观看,还想操作。虽然如上文所述,多年的研究已经表明博物馆内最吸引人的通常是最大件的或最显著展示的物件[77],且其基本是公众最期待看到的,因此他们会首先关注这些展品。但讽刺的是,这些展品并不一定带来最有效的学习。在最近的博物馆研究中,一个最反直觉的发现是,对于参观者而言,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展品是参观者期待看到的物件,而非他们从未想过的[78]。比起他们不了解或不希望看到的物件,更吸引参观者的是其“稍微有点”了解且认为有趣的事物。尽管大量资金已被投入创建新的或与众不同的展览中,但正如大多数博物馆营销人员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好莱坞(Hollywood)和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对此已经心知肚明多年——稍具新颖是伟大的,但太过于新颖则不是。最轰动的特展是关于著名艺术家、著名历史时期或著名事件(如古埃及人、恐龙或泰坦尼克号)的展览。人们希望看到新事物,但通常并不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或想过的事物。
在过去30年中,博物馆领域已开始大力重视并推动观众对展览的有意义的参与。之前展览仅是“陈列”或“展示”,如今对学习方式及观众需求的新认识促使博物馆提供能促进社会互动、增加主动参与、增强人际关系能力的博物馆体验[79]。将参观者的角色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意味着对谁“拥有”故事这个问题答案的转变[80]。随着专家和权威之间关系的转变,为回应对主动参与和意义构建的强调,应对信息的普遍性和网络意见进行共享,博物馆和其他自由选择学习环境需要更好地了解观众的“入口处陈述”(entrance narrative)[81]及展览内容与观众的关联。
一种增加参与度的常用方法是安排工作人员(有酬或无酬)在展厅扮演人类动画或担任讲解员。研究表明,工作人员可以帮助观众认识到自己更受欢迎、更舒适,他们也能增进观众与展览元素互动,延长参观时间并促进学习[82]。训练有素的社教人员会根据观众个人的不同需求定制不同的方案,他们会在博物馆入口处与观众见面,量身定制参观体验[83]。
鉴于学习的累积性质,衡量博物馆体验或展览、项目、活动等其他特定体验的“影响”并非易事[84]。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在类似博物馆的环境或许多其他校外场所中的体验,既与科学知识存在密切关联[85],也与科学兴趣存在密切关联[86]。在研究者们试图将博物馆独立于其他教育形式之外阐释其作用时,归因(找到因果关系)当前是且将一直是个难题。这就是许多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在城市或城镇开设新博物馆之前(理想化的情况是该城或该镇上尚未有同类博物馆)就开始这类工作的原因,这样可以追踪该社区教育情况的变化,并将教育和社会凝聚力等结果的变化更准确地归因于博物馆的存在[87]。
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通过自由选择式学习体验进行不断学习。需要多种测量方法和多个时间段来记录学习结果,厘清从何处学到何种知识及哪些资源对个体间的不同学习有所贡献[88]。关于衡量博物馆和其他自由选择式学习体验的长期影响,《非正式科学教育体验的长期、梯级影响》(Investigating the Cascading,Long-Term Effects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Experiences)[89]一书对其当前的理解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最新综述。
五、未来趋势
博物馆观众研究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能被广泛接受的范例及发表地仍然是一个问题。当前正在开展的各种研究代表着各种理论观点,采用了各种可想到的方法和数据收集策略。同时,领域内不仅有持续要做的工作——仍然要对从评估到研究的整个范畴继续进行探讨,也有普遍存在的困惑——研究人员和博物馆从业人员对于不同形式的研究之间的界限甚至是否应该区分不同形式的研究,普遍存在困惑。在一个层面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兴领域尚在努力寻找其中心的例子;缺乏重点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健康的事,因为它鼓励了广泛的思考和多种观点。在另一层面,也有些人认为,现在该是这个领域确定可靠的模型、框架和一致指标的时候了,这些模型、框架和指标可以作为建立未来研究和理解的知识基础。
就像21世纪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样,研究人员之间因其不同的范式观点而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例如,具有更多认知主义倾向的人对那些从社会学或社会文化角度解决问题的人表示怀疑;定量和定性研究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研究人员已公开表示对多种方法的宽容。在这些更具哲学意义的关注背后,隐藏着一种紧张关系,存在于那些认为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目标应主要是评估性的,旨在短期内改善展览、活动和实践的质量的人与那些更多由理论驱动而较少关注即时可用性的人之间。这两个阵营虽不能完全但也可大致按专业区分:前者主要由那些在博物馆、科学中心、动物园和自然公园等机构内工作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人占主导地位,而后者则由高校教育或心理学系的学者主导。目前谈论最终结果是分裂成两个不同阵营,抑或两者之间的某种混合为时尚早,但是推断这些紧张关系最终将需要直接解决应该还是合理的。
另外一个可能会对参观者研究产生长期影响的趋势是,要求最小化学校内外学习之间区别的压力越来越大[90]。随着正式和非正式(或自由选择式)学习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参观者”与“学生”之间在学习、行为方面的界限,以及用以划分正式学习环境研究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研究的理论框架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这并不是说这些环境的学习体验之间没有差异。物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性[91]意味着在博物馆、动物园、自然中心这类环境中提供独特的学习体验,始终需要为这些环境量身定制方法和手段。但很有可能的是,目前用以将博物馆观众研究和其他环境(如课堂)学习区别开来的理论界限,即使不会完全消失,也将越来越模糊。最关键的是未来将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即学习体验和其他博物馆生成的体验将不会受时间和环境所限。这无疑将影响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的方向及在此框架下进行研究的人们。
博物馆和其他自由选择式学习机构,无论其定义如何,正在着手进行必要的工作,以描述和证明其对整个社区的影响。除了就业、旅游消费和采购带来的明确的财务收益外,上述的参观者和志愿者的各种个人收获也为整个社区带来一些非量化的影响和收益。如何最终定义和衡量这些收益将帮助我们更完整地阐述博物馆这一类机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最后,我们可以预见的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东南亚博物馆数量的持续增长及由此将带来的对参观者研究的需求和重视。目前,一个不算庞大但正在增长的观众研究群体已经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展研究,我们预计该群体在未来几年中会有所扩大。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的博物馆观众研究对于确保博物馆获得持续资助和支持、奠定21世纪博物馆据以设定未来工作重点的知识基础,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1]非正式(或自由选择)教育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博物馆、公园、自然中心、动物园和水族馆、植物园等。
[2]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CAR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DB/OL][2012-08-27]http://www.care-aam.org/
[3]Visitor Studies Association.Evaluator competencie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B/OL][2012-08-27]http://visitorstudies.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
[4]J.Falk,J.Osborne&L.Dierking eds.Characterising the UK Science Education Community.Technical Report.The Wellcome Trust,London,2012.
[5]E.Robinson.The behavior of the museum visitor.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Washington,1928:5.
[6]A.Melton.Problems of installation in museums of art.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Washington,1935:14.
[7]H.Shettel,M.Butcher eds.Strategies for determining exhibit effectiveness(Tech.Rep.No.AIR-E59-4168-FR).Americ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Pittsburgh,1968.
[8]C.Screven.The museum as a respon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Museum News,1969,47(10):7-10.
[9]R.S.Miles,M.B.Alt&A.F.Tout eds.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exhibit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2.
[10]M.Borun.Measuring the immeasurable:A pilot study of museum effectiveness.Associ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Centers,Washington,1977.
[11]R.Wolf,B.Tymitz.Do giraffes ever sit?a study of visitor perceptions at the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Smithsonian Institution,Washington,1979.
[12]M.Hood.Staying Away:Why People Choose to Not Visit Museums.Museum News,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Washington D.C.1983,61:4,50-57.
[13]J.Falk,W.Martin&J.Balling.The novel field-trip phenomenon:Adjustment to novel settings interferes with task learning.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1978,15(2):127-134.
[14]S.Bitgood,D.Patterson.The effects of gallery changes on visitor reading and object viewing time.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3,25(6):761-781.
[15]R.Loomis.Museum visitor evaluation:new tool for museum management.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Nashville,1987.
[16]B.Serrell.Paying attention:visitors and museum exhibitions.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Washington,1998.
[17]J.Diamond.The behavior of family groups in science museums.Curator,1986,29:139-154.
[18]J.Koran,M.Koran eds.Using modeling to direct attention in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Curator,1988,31:36-42.
[19]L.D.Dierking,J.H.Falk.Family behavior and learning in informal science settings:a review of the research.Science Education,1994,78:57-72.
[20]A.Lucas.‘Info-tainment’and informal sources for learning sc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1991,13:495-504.
[21]G.Leinhardt,K.Crowley&K.Knutson.Learning conversations in museums.Lawrence Erlbaum,Mahwah,NJ,2002.
[22]P.McManus.It’s the company you keep.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learning-related behavior in a science museu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1987,53:43-50.
[23]L.Rennie.Measure affective outcomes from a visit to a science education centre.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1994,24:261-269.
[24]B.Gammon.Everything we currently know about making visitor-friendly interactive exhibits.Informal Learning Review,1999,39:1-13.
[25]a.C-L.Chen,C-G.Tsai.The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music on the visitor museum experience:A case study of the Laiho Memorial Museum.Taiwan Visitor Studies,2015,18(2):183-195.b.H.Chu.We are not science museums but Ke Ji Guan:A study of Ke Ji Guan in China and their visitors’identity-related motivation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2018.c.C-W.Sheng,M-C.Chen.A study of experience expectations of museum visitors.Tourism Management,2012,33(1):52-60.d.P.P.Shein,J.H.Falk&Y-Y.Li.The role of science identity in science center visits and effects.Science Education,2019,103(6):1478-1492.e.周婧景、王文彬、林咏能:《复合空间的管理策略研究——以长沙博物馆为例》,胡慧林、陈昕编《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2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32—445页。
[26]L.D.Dierking,W.Pollock.Questioning assumptions:An introduction to front-end studies in museums.Washington,D.C: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ers,1998.
[27]关于行为主义,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haviorism;关于建构主义,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tructivism。
[28]前端评估指调查参观者对某个主题或题材的已有知识、态度和兴趣,以帮助展览的设计和信息传播。
[29]Outcome Based Evaluation Basics,[EB/OL][2019-06-15]https://www.imls.gov/grants/outcome-based-evaluation/basics.
[30]a.J.H.Falk,L.D.Dierking.The Museum Experience.Washington,DC:Whalesback Books,1992.b.J.H.Falk,L.D.Dierking.Learning from Museums.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0.c.J.H.Falk,L.D.Dierking.The museum experience revisited.Left Coast Press,Walnut Creek,CA,2014.d.J.H.Falk,L.D.Dierking.Learning from Museums,2nd Editio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19.
[31]a.S.Bitgood,D.Patterson&A.Benefield.Under-standing your visitors:Te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visitor behavior.Jacksonville,AL:Psychology Institute.1986.b.同[16]。
[32]V.Kirchberg,M.Tröndle.The museum experience:Mapping the experience of fine-art.Curator,2015,58(2):169-193.
[33]同[30]a、[30]c。
[34]在自由选择式学习语境下,“学习”被宽泛地定义为一切行为、兴趣、理解、技能、知识或态度的改变。参见[30]d。
[35]N.O.Renner.Multisensory sensemaking:Children’s exploratory behavior has organizing structure at micro-and macro-scal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Boston,Massachusetts,July 21,2011.
[36]a.T.Humphrey,J.P.Gutwell eds.Fostering active prolonged engagement:The art of creating APE exhibits.San Francisco:The Exploratorium,2005.b.J.Gutwell,S.Allen.Group inquiry at science museum exhibits:Getting visitors to ask juicy questions.San Francisco.The Exploratorium,2010.
[37]J.H.Falk,L.D.Dierking.School field trips:Assessing their long-term impact.Curator,1997,40(3):211-218.
[38]J.Greene,B.Kisida&D.Bowen.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Field Trips.Education Next,2014,14:78-86.
[39]a.D.Anderson,H.Shimizu.Personal implications of specific long-term memories on social events:Retrospective and current memory of older Japanese adults’experiences of visiting world expositions.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sychonomic Science,2015,33(2):167-175.b.J.H.Falk,L.D.Dierking.The effect of visitation frequency on long-term recollections.In S.Bitgood Ed.Proceedings of the 3rd Annual Visitor Studies Conference.Jacksonville,AL:Center for Social Design,1990:94-104.
[40]D.Anderson,M.Storksdieck&M.Spock.Long-term impacts of museum experiences.In J.Falk,L.Dierking&S.Foutz eds.In Principle,In Practice,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6:197-215.
[41]a.S.Bitgood,D.Patterson.Principles of exhibit design.Visitor Behavior,1987:2,4-6.b.B.Serrell.Making exhibit labels:A step-by-step guide.Nashville,TN: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3.
[42]J.Blundon.A‘Linguist-In-Residence’…what’s that about?Transcript of a presentation made to the Assembl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DB/OL][2019-07-11]https://www.academia.edu/11839171/Language_under_the_microscope_a_linguist-in-residence_at_the_Metropolitan_Museum_of_Art Retrieved.
[43]T.Dancstep,L.Sindorf.Exhibit Design for Girls’Engagement,A Publication of the Exploratorium,[DB/OL][2019-07-11]https://www.exploratorium.edu/sites/default/files/pdfs/EDGE_GuideToDesignAttributes_v16.pdf.
[44]关于社会文化理论,参见https://simple.wikipedia.org/wiki/Sociocultural_theory。
[45]a.M.Adams.Family learning in interactive galleries:Longitudinal case studies,[EB/OL][2002-05-02]http://familiesinartmuseums.org/research.caseStudy.html.b.T.Astor-Jack,K.K.Whaley eds.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ies of socially-mediated learning.In J.H.Falk,L.D.Dierking&S.Foutz eds.In Principle,In Practice: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s.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7:217-228.
[46]a.同[45]b。b.C.Eberbach,K.Crowley.From seeing to observing:How parents and children learn to see science in a botanical garden.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2017,26(4):608-642.c.K.Ellenbogen,J.Luke&L.Dierking.Family learning in museums:A perspective on a decade of research.同[45]b,第17—30页。d.S.Palmquist,K.Crowley.From teachers to testers:How parents talk to novice and expert children in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Science Education,2007,91(5):783-804.e.H.T.Zimmerman,S.Reeve&P.Bell.Familysense-ma-king practices in science center conversations.Science Education,2010,94(3):478-505.
[47]a.M.Callanan,D.R.Siegel.Learning conventions and conventionality through conversation.In D.Matthews ed.Pragmatic Developmentin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Ti-LAR serie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14:121-138.b.J.G.Fender,K.Crowley.How parent explanation changes what children learn from everyday scientific thinking.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7,28:189-210.c.同[21]。
[48]a.J.H.Falk,L.D.Dierking&L.Swanger eds.Correlating science center use with adult science literacy:An international,cross-institutional study.Science Education,2016,100(5):849-876.b.G.Hull,J.G.Greeno.Identity and Agency in Nonschool and School worlds.In Z.Bekerman,N.Burbules&D.Silberman-Keller eds.Learning in places.The informal education reader.New York,Peter Lang,2006:77-98.c.S.A.Pattison,I.Gontan&L.Moreno.Identity negotiation within peer groups during an inform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gram:The central role of leadership-oriented youth.Science Education,2018,102(8):978-1006.d. 同[25]d。
[49]J.J.Luke,J.Stein&L.D.Dierking.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youth:Mapping success with the“Six Cs”.Curator,2007,50(4):417-434.
[50]a.同[36]b。b.S.A.Pattison,S.M.Randol,M.Benne eds.A designbased research study of staff-facilitated family learning at interactive math exhibits.Visitor Studies,2017,20(2):138-164.c.E.Rosenthal,J.Blankman-Hetrick.Conversations Across Time:Family Learning in a Living History Museum.同[21],第305—309页。
[51]E.Merritt.Revisiting Volunteers and Museum Labor.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 Blog,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EB/OL][2019-07-01]https://www.aam-us.org/2019/07/01/revisiting-volunteers-and-museum-labor/
[52]a.D.Edwards.It’s mostly about me:reasons why volunteers contribute their time to museums and art museums.Tourism Review International,2004,9:21-31.b.J.Son,J.Wilson.Generativity and volunteering.Sociological Forum,2011,26(3):644-667.
[53]同[12]。
[54]J.H.Falk.Factors Influencing Leisure Decisions:The Use of Museums by African Americans.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93.
[55]a.同[17]。b.S.Rosenfeld.Informal education in zoos:Naturalistic studies of family group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0.c.L.D.Dierking.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in a free choice learning setting:An examination of attention directing behavior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Florida,Gainesville,FL.[DB/OL][2019-07-01]http://informalscience.org/research/ic-000-000-008-683/Parent-child_interactions_in_a_free_choice_learning_setting,July 11,2019.
[56]a.同[25]b。b.J.H.Falk.Anidentity-center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useum learning.Curator,2006,49(2):151-166.c.J.H.Falk.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Walnut Creek,CA:Left Coast Press,2009.d.S.Phelan,J.Bauer&D.Lewalter.Visit motivations:Development of a short scale for comparisons across sites.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2018,33(1):25-41.e.同[25]c。
[57]A.Pekarik,J.Schrieber,N.Hanemann eds.IPOP:A Theory of Experience Preference.Curator,2014,57:1,5-27.
[58]Morris,Hargreaves,McIntrye.2007 Audience knowledge digest Why people visit museums and galleries,and what can be done to attract them.[DB/OL][2019-07-11]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2021521-1331/http://research.mla.gov.uk/evidence/documents/Audience%20Knowledge%20Digest.pdf.
[59]a.同[56]c。b.J.H.Falk.Born to Choose:Evolution,self and wellbeing.London:Routledge,2018.
[60]S.Todd,R.Lawson.Lifestyle segmentation and museum/gallery visiting behavio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2001,6(3):269-277.
[61]Axiell.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useum industry:Museums Report 2016.Archives Libraries Museums.[DB/OL][2019-06-22]https://www.axiell.com/app/uploads/2019/04/digital-transformation-in-the-musuemindustry.pdf.
[62]a.K.Budge.Objects in focus:Museum visitors and Instagram.Curator,2017,60(1):67-85.b.A.Espinos.Museums on Social Media:Analysing Growth through Case Studies.[EB/OL][2019-07-11]http://mw2016.museumsandtheweb.com/paper/museums on-social-media-analyzing-growth-through-case-studies/c.L.A.Langa.Does Twitter help museums engage with visitors?In iConference 2014 Proceedings:484-495.[DB/OL][2019-07-11]https://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47289/130_ready.pdf.d.J.Lopez-Sintas,E.Alvarez&E.Perez-Rubiales.Art museum visitors:Interaction strategies for sharing experiences.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2014,29(3):241-259.
[63]a.同[61]。b.F.B.Rey,D.Casado-Neira.Participation and technology:perception and public expectations about the use of ICTs in museums.Procedia Technology,2013,9:697-704.c.同[30]d。
[64]K.S.Wilson.Two multimedia design research projects:Palenque and the museum visitor’s project.New York: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1992.
[65]M.K.Othman,K.I.Idris&P.Talwar.An empirical study of visitors’experiences at Kuching Orchid Garden with mobile guide application.Advance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2018,5740520:1-14.
[66]B.Perdue,T.Stoinski&T.Maple.Using technology to educate zoo visitors about conservation.Visitor Studies,2012,15(1):16-27.
[67]S.Babinowich.How do people relate to history in freechoice learning environments.Unpublished Master’s Cap-stone Project.Oregon State University,Corvallis,2012.
[68]a.同[63]a。b.D.Dierking,J.H.Falk.Audience&Accessibility.In S.Thomas,A.Mintz eds.The virtual and the real:Media in the museum.Washington,D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98.
[69]同[63]a。
[70]同[30]d。
[71]L.Tallon,K.Walker.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museum experience:Handheld guides and other devices.Lanham,MD:AltaMiraPress,2018.
[72]同[62]。
[73]a.M.Phipps,S.Rowe&J.Cone.Incorporating handheld computers into a public science center:A design research study.Visitor Studies,2008,11(2):123-138.b.M.Raento,A.Oulasvirta&N.Eagle.Smartphones:An emerging tool for social scientists.Sociological Methods&Research,2009,37(3):426-454.c.H.T.Zimmerman,S.M.Land.Integrating mobile computers into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Preparing Informal Science Educators,Amsterd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169-183.
[74]射频识别(RFID)指使用无线非接触式系统。该系统使用射频电磁场从附着在物体上的标签传输数据,以实现自动识别和跟踪的目的。
[75]a.J.Hohenstein,T.Moussouri.Museum learning:Theory and research as tools for enhancing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19.b.L.Kovavisaruch,V.Sornleardlumvanich eds.Evaluating and Collecting Museum Visitor Behavior via RFID.2012 Proceedings of PICMET'12:Technology Management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EB/OL][2019-06-22]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1344360_Evaluating_and_collecting_museum_visitor_behavior_via_RFID.
[76]a.同[32]。b.Oregon State University.The free-choice learning laboratory at HMSC,[EB/OL][2019-11-30]http://blogs.oregonstate.edu/freechoicelab/tag/cyberlab/
[77]同[31]。
[78]a.J.H.Falk,M.Needham.Measuring the impact of a science center on its community.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1,48(1):1-12.b.J.H.Falk,M.Storksdieck.Science learning in a leisure setting.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0,47(2):194-212.
[79]a.同[21]。b.C.Heath,D.vom Lehn.Intera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new forms of participation in museums,galleries and science centres.In Ross Parry ed.Museums in a Digital Age.Routledge:Milton Park,2009:266-280.c.M.J.Bradburne ed.Museum 2000:Swedish travel exhibits.Stockholm:ICOM Swedish and the Swedish Museum Association,2000.
[80]a.P.Samis.Creating the visitor-centered museum.London:Routledge,2019.b.N.Simon.The Participatory Museum.Santa Cruz:Museum 2.0,2010.c.同[52]b。
[81]译者注:“入口处陈述”直译自英文entrance narrative,指参观者在展览的入口处(即参观展览前)所具有的与展览主题相关的个人经历、记忆和知识储备。
[82]M.Marino,J.Koke.Face to Face:Examining Educational Staff’s Impact on Visitors.ASTC Dimensions.January/February 2003.The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s.
[83]S.A.Pattison,L.D.Dierking.Staff-mediated learning in museums: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Visitor Studies,2013,16(2):117-143.
[84]a.同[78]a。b.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Learning science in informal environments:Places,people and pursuit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9.
[85]a.Afterschool Alliance.Defining youth outcomes for STEM learning in after school,[DB/OL][2019-06-22]http://www.afterschoolalliance.org/STEM_Outcomes_2013.pdf.b.同[39]a。c.同[40]。d.R.N.Bonnette,K.Crowley&C.D.Schunn.Falling in love and staying in love with science:ongoing informal science experiences support fascination for all childre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DOI:10.1080/09500693.2019.1623431.e.同[48]a。f.同[78]a。g.J.Falk,M.Needham.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dult STEM knowledge.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3,50(4):431-452.h.J.H.Falk,M.Storksdieck&L.D.Dierking.Investigating public science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ce of free-choice learning.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7,16(4):455-469.i.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Identifying and Supporting Productive STEM Programs in Out-of-School Settings.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2015.j.同[76]b。k.D.Vandell,E.Reisner&K.Pierce.Outcomes linked to high-quality after school programs:Longitudinal findings from the study of promising practices.Irvin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Policy Studies Association,2007.
[86]a.同[85]a。b.同[48]a。c.J.H.Falk,D.Meier eds.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five scienc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youth’s interest in science.Visitor Studies.d.J.H.Falk,J.Koke eds.Investigating the Cascading,Long-Term Effects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Experiences.Technical Report.Portland,OR:Institute for Learning Innovation.[EB/OL][2019-07-11]https://www.informalscience.org/investigating-cascading-longterm-effects-informal-science-education-experiencesreport.e.同[85]i。f.同[76]b。
[87]a.J.H.Falk,P.Brooks&R.Amin.Investigat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a science center on its community:The California Science Center L.A.S.E.R.Project.In J.Falk ed.Free-Choice Science Education:How We Learn Science Outside of School.New York,NY: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2001:115-132.b.同[85]h。c.同[78]a。
[88]a.同[47]a。b.同[86]d。c.J.H.Falk,M.Storksdieck.Using the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 to understand visitor learning from a science center exhibition.Science Education,2005,89:744-778.
[89]同[86]d。
[90]a.B.Bevan,J.Dillon eds.Making science matter:collaborations between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CAISE).[DB/OL][2019-07-11]http://caise.insci.org/uploads/docs/MakingScienceMatter.pdf.b.J.Falk,L.Dierking.The 95%solution:school is not where most Americans learn most of their science.American Scientist,2010,98:486-491.c.S.Stocklmayer,J.Rennie&J.Gilbert.The roles of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provision of effective science education.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2010,46:1-44.d.同[85]g。
[91]a.同[3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