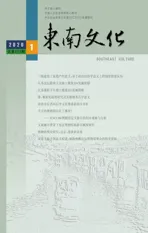考古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废弃过程理论研究及其启示
2020-04-27李彬森陈胜前
李彬森 陈胜前
(1.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考古材料的废弃过程直接关系到考古材料的真实性问题,影响到考古推理的可靠性。废弃过程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从理论、方法再到实践的单独研究领域。废弃过程研究在农业起源、聚落变迁、特殊遗迹性质的判断等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考。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过去的实物遗存来了解古代社会,我们把经过系统调查发掘的物质遗存称为考古材料,它们是进行考古学解释的基础。然而,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较少有学者讨论。其中的废弃过程决定哪些材料会被废弃以及废弃的位置,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物质材料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古人废弃。不同的废弃过程将会直接影响考古材料的构成与空间分布。如果不考虑废弃过程,那么我们所做的考古推理就会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遗址废弃过程研究是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研究方法就是要把遗址形成前后的人为动力与自然动力区分开来,以便更好地了解遗址中人类的行为。而其中废弃过程又是从所谓系统情境(systemic context)到考古学情境(archaeological context)转变过程的关键一环[1],影响着考古材料的“准确性”。
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废弃过程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典实践,分析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考与借鉴。
一、废弃过程理论的形成与基本构架
(一)废弃过程研究发展简史
考古学的废弃过程研究是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中的诸多理论环节之一。早在考古学诞生初期,有关考古材料形成的问题就已出现,当时的人们质疑人类化石、石器以及绝灭动物的化石是否共存。随着越来越多同类考古发现出现,以及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两大方法的确立使这一问题暂时搁置。到二战后放射性测年法解决年代问题后,新考古学对前人研究的反思再次唤起了对考古材料如何形成与废弃问题的关注。
罗伯特·阿舍(Robert Ascher)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与文化堆积的保存状况相关。随着时间流逝,信息也相应流失,只有在如庞贝古城般保存极端完好的遗址中信息才可能较为全面。他将热力学概念中的“熵”应用于考古学中,用“熵”的概念来解释文化堆积[2]。这一观点提醒考古学家需要注意,我们通过科学的发掘所看到的考古材料可能已经“失真”,那么,在此基础上对古代社会信息的提取会受到废弃过程的影响。

表一// 考古材料废弃过程简表
希弗(Michael B.Schiffer)则提出了改造的观点(transformation view)。他的核心概念与阿舍相似,也同样认为考古材料在形成过程的作用下,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扭曲(distorted),但时间并不只影响保存状况,在人类行为影响下,很可能导致新的遗存分布模式。他在《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一书中系统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将考古材料分为文化形成过程和自然形成过程两部分,更加强调考古材料是由行为系统与考古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3]。
亚利桑那大学的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等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了一项长达20多年的图森市(Tuson)垃圾研究项目[4],这项聚焦于当代的研究对考古学,尤其是考古材料的形成与废弃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是方法论上的相关启示,更为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在看待考古材料时应十分谨慎。
近来,一批考古学家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展开了研究实践,研究成果集结为《聚落与区域的废弃:民族考古学和考古学方法》[5]一书,该文集汇集了以民族考古学、考古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使考古材料的废弃过程研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二)关键概念
废弃,英文为abandonment,意为抛弃、放弃。废弃过程这个概念作为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理论的一部分,是由美国考古学家希弗首先提出的。他说:“废弃作为一个过程,其中无论是活动区域,单个结构(房子或其他遗迹),或是整个聚落空间,都从文化系统情境转入到考古情境中。”[6]废弃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从而形成不同形态的考古物质遗存。
时间上的差异方面,在两种“极端”的时间规划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堆积分布(表一)。根据斯蒂文森(Marc G.Stevenson)的研究[7],当一个聚落有计划缓慢地废弃时,可能会出现如下人类行为:居住者会选择停止制作和加工物品的活动,遗址中可能很少发现生产环节的遗迹或遗物;原本居住时进行的清扫活动也会停止,居住面上甚至会富集垃圾。相反,若是无计划的快速废弃,人们通常没有时间整理物品,居住面上还留存有生产、生活的状态,此时会出现大量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器物,即所谓“de facto refuse”的概念,一般译为“事实存在的废弃物”,包括工具、附属设施、建筑和其他物质材料,意指仍然可以使用,但事实上留在了被废弃的活动地点[8]。可见,预期计划程度和是否预期返回是影响废弃堆积最为重要的因素。
空间上的差异可参考拉莫塔(V.M.LaMotta)和希弗的研究,他们曾总结房址居住面器物组合(house floor assemblages)在居住、废弃和废弃后三个阶段的特征[9]。
(1)居住阶段,也就是居址正常使用的阶段。居址内出现的器物种类和器物空间分布与从事的活动类型相关。但是,民族学资料显示,人们在居住时会定期打扫和清理居住面,这两种人类行为会影响遗物的数量与空间分布。其中清理是将垃圾清扫出去,这就会造成居址内原本器物种类的减少,而整理可能会将物品和工具集中放置,也就是破坏原本器物的组合与分布。那么,由此会出现两个重要的概念——原生废弃物堆积(primary refuse deposition)和次生废弃物堆积(secondary refuse deposition)。原生废弃物堆积主要指生产、生活中直接制造的废弃物,包括一些厨余的骨屑、灰烬等不易察觉的细碎物品,通常直接保留在居住面上。次生废弃物堆积主要指生产、生活中间接产生的废弃物,包括体量较大且没有价值的垃圾堆。
原生堆积一般废弃在使用地点,而次生堆积脱离了原工作空间转而废弃在了专门的垃圾堆,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堆积物形成时的人类行为。于考古材料而言,体积特别大和特别小的物品都更可能是原生堆积,前者如厚重而不易搬运的大水缸、石磨盘等,后者如石器修整下的边缘产品等。
(2)废弃阶段的堆积(abandonment stage refuse deposition),当人们准备放弃一处居址时,原本的日常清扫活动可能会停止,居住面就会富集垃圾。在此种情形下的初次和次级废弃物可以称之为废弃阶段的堆积。受人类行为的影响,居住面上可能会出现事实存在的废弃物及物品的打包预置(curation)。这些事实存在的废弃物的堆积取决于是否有计划、缓慢的,还是突然的废弃。对于预期返回的废弃,人们会决策哪些物品留在遗址内,哪些物品随身携带至下一个占居地点。而这些移至其他地点以备使用的物品称之为预置。废弃物与预置行为深受是否有计划性、搬迁模式、距离、是否预期返回以及预期返回后从事的活动类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3)废弃后阶段(Post-abandonment),房址废弃后居住面的所有遗存都将进入到考古埋藏环境中,仍然会受到来自文化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其中的文化过程包括扰乱先前堆积模式,再利用形成新的堆积;废弃的建筑物成为新居民投放垃圾的场所;人与动物的踩踏行为改变遗物的分布;拾荒(scavenging)以及收集(collecting)行为扰乱原居址的器物构成等。
二、民族考古学模型
基于有限的材料考古学难以构建出废弃过程理论,而民族考古学(甚至包括历史与当代的废弃过程)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实际研究中,简单类比的可信度并不高,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型就有所不同了,它是对现象研究的升华,同时可以接受考古材料的检验[10]。因此,宾福德非常重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并亲身参与阿拉斯加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11]。他的开创性工作令废弃过程理论在民族考古学研究中得到充实与发展,同时也使民族考古学为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框架。下文将结合一个美国西南地区的案例来分析废弃过程研究的方式,这个案例对于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早期的遗址非常有借鉴意义。
纳尔逊(Margaret C.Nelson)[12]以拉力(pull)和推力(push)两方面形象地总结了美国西南部古代遗址废弃的原因。其中推力主要指迁出地的不利因素,气候条件的恶化,营养不良、疾病等导致的人口过剩和战争冲突等问题,正是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了人群因生存需要而迁出。拉力则指新迁入地对原有人群的吸引力,这些优势包括自然环境优渥、社会稳定等综合因素。
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位于墨西哥的Rarámuri遗址采用农业—游牧混合经济方式,此种经济形态影响下就需要定期迁徙以适应环境的变迁。该遗址可分为三种居址利用方式:农业居址(Agricultural residence)、主要居址(Main residence)和冬季居址(Winter residence)。分析结果表明,混合的经济方式下产生了不同的废弃方式,如所谓间断式的废弃(Punctuated abandonment),即古人有规律和计划性地将居住地点从一地迁移至别地,那么在两居址间迁徙就变得有计划性且存在预期返回。
三个居址间有相对固定的器物组合,同时还存在移动的物品(图一)[13]。如图中显示,箭头的指向指明了物品流动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固定的遗址家具都不移动,如农业居址与主要居址之间的遗址家具没有互换。而主要居址的大型炊器和容器会向冬季居址移动,收获的粮食也会移至冬季居址以备过冬。适合迁徙的工具和个人物品在三个居址之间都是双向移动的,它们伴随着人群的迁徙而流动。
美国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可以进行直接历史法的比较。而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如何以相应的解释模型与考古材料相对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环境与生存压力,在这种解释模型中,以科技手段探究人群营养健康是切实可行的。例如,我国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据锶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似乎存在几种人群的迁徙[14],如果能从中找到可以结合的部分,将对探讨贾湖遗址的定居与废弃模式大有裨益。
三、废弃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实践
依靠民族考古学构建的模型,以及对当代废弃物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对废弃过程理论与方法的构建及运用日趋成熟。不少研究者对考古学遗址进行分析,例如施兰格(Sarah H.Schlanger)与威尔斯胡森(Richard H.Wilshusen)对美国西南部多洛雷斯地区(Dolores area)在公元600—910年间古普韦布洛印第安人(Ancient Pueblo Peo-ple)废弃房址的研究极具代表性。研究者总结出建筑废弃的四种策略[15],下面进行简要介绍。

图一// 各居址物品组合
策略1:短距离移动/预期返回(short-distance move/return anticipated)。在这种废弃策略中,我们将会在建筑中发现便于翻修和再占居的完整器物。房屋内的设施会被遗弃在使用地点或被移至其他使用地点。若是季节性居所,屋内设施可能会被运输到下一个居住地,但是,完整物品会被处理以防止被拾荒者捡走。如果预期返回失败,这些经刻意储藏的可用物品可能会被拿走。
策略2:长距离移动/预期返回(long-distance move/return anticipated)。在这种废弃策略中,人们将储藏房址内高价值的家具和装备,对出入口和物品进行封存处理。这将会导致居住面上出现一些大型物品,但高价值物品却很少出现。若是季节性的废弃,屋内设施会被更新。此类居址一旦废弃会遭遇拾荒。如果预期返回失败,物品同样会被移除。
策略3:短距离移动/缺乏长期规划或预期不返回(short-distance move/long term of absence or no anticipated return)。在这种废弃策略中,例如像房梁这样的建筑构件会被移至新的居住地重新利用。建筑内的物品在废弃时会被搬空。可能出现两种处置方式:一种是,当整个聚落即将废弃时,建筑物随之废弃,并且没有预期返回的意图;另一种是,聚落未废弃而单个建筑预废弃,这种废弃很可能由劫掠导致。而单个建筑中有作为彻底废弃的火烧行为,则与宗教仪式和埋葬行为相关。单个建筑的废弃却没有火烧行为,则可能是为了用作储藏工具或其他用途。一旦房梁被移除或着火坍塌,物品会有效密封保存在居住面上,从而防止拾荒的发生。
策略4:长距离移动/缺乏长期规划或预期不返回(long-distance move/long term of absence or no anticipated return)。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此类情况。人们可能会将那些较笨重的、低价值物品遗弃而抢先处理那些便携物品。如果屋顶完好无损,说明房屋未坍塌,居住面物品会被捡拾。而如果屋顶坍塌了,相对有价值的物品会得到保存。
以上四种策略主要是针对迁出地与目的地的距离以及预期返回时间长短而构建的理论模型。
首先,迁出前的决策影响居住面遗物的组合与空间分布。在这种决策思维影响下,有意的预置与储藏行为比较显著,我们在分析考古器物组合时需要特别留意有价值物品的缺失。当决定废弃一个建筑时,人们需要考虑物品的去留问题,居住面遗物组合的总体重量(the total weight of the floor assemblage)可以作为考量的突破口。居住面平均重量可以清晰地显示出三种不同的废弃模式,即焚毁的房屋出土物总量最重,其次是再次占居的,最后是完整的房址。被焚毁的建筑拥有更重的堆积物是因为当屋顶坍塌后,不太可能从居住面捡拾完整可用的器物。而再次占居和保存完好的居所内的可用物品会被捡拾,物品随之减少,器物总重量就会减轻,建筑物的功能可能也会随之改变。
其次,遗迹和遗物进入考古埋藏环境中受到沉积后(post-deposition)过程的影响。例如,房址分析中屋顶是否完整是关键性指标,在四种策略的影响下,屋顶的处理方式(roof treatment)主要有三种:屋顶完整的遗弃、屋顶被回收利用、屋顶有意被焚毁。文中分析的多洛雷斯地区废弃的房址通常都经过火烧。屋内居住面上20~40厘米的灰烬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建筑内部的着火情况,这些被焚毁的建筑物内常常有垃圾填土。综合信息表明,焚毁的建筑通常是远距离迁移且没有预期返回的。其他留存有屋顶横梁的建筑物中的木材被重新利用作为其他建筑的一部分,或者被焚烧掉。有些例子中,屋内堆积可以分层,其居住面上层填土中包含灰烬堆积,预示着建筑物在废弃后仍然被居住过。这一研究实例提醒我们在田野发掘和进行考古学研究时尤其需要注意被火烧过的房址,房屋内的结构和堆积受废弃时人类行为的干扰较大。
四、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
我国学者对废弃过程的探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相关译介的产生,研究者结合考古研究中的现象进行思考,并基于废弃模式提出了一些问题;其次,已有研究者开始运用这种理论方法结合中国考古实践进行分析,并取得了相关成果。
1.国内学者的相关理论探索
首先是相关译介与初步探索。这一方面的工作以复旦大学陈淳及殷敏所翻译《北美西南部废弃行为研究》一文为代表[16]。该文提供了一种研究遗址废弃行为的范例,对遗址发掘和聚落形态变迁研究颇具启发性。
徐坚借助希弗行为考古学的视角来看待喀左铜器群的废弃过程。他提出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喀左铜器群规律性埋藏形成的原因,认为可能是古人利用窖穴储备大而重的青铜器,而这种特殊的废弃模式是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影响下周期迁徙时预期返回行为的体现[17]。
另外,张弛在全面回顾了田野考古堆积物的认识之后,采用希弗的文化和自然营力概念展开讨论。在对自然堆积的探讨中,他将自然营力的研究运用到了实际的田野发掘过程中,并在发掘期间观察了驻地当代窖穴废弃成为垃圾坑的过程。这种突破性的分析方法为国内的考古材料废弃过程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8]。
2.国内学者的考古学研究实践
废弃过程理论如何应用到考古材料分析当中是考古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实践以陈胜前和李新伟为代表。
陈胜前运用废弃的文化过程方法探讨了华北含细石叶工艺产品的诸多遗址类型,区分出了是否预期返回与不同功能性遗址等若干遗址废弃模式[19]。同时在探讨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中也运用了废弃过程的理论方法分析材料。例如,对华北地区的遗址家具(site furniture)、磁山遗址的事实上的废弃物(de facto refuse)、北方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实例[20]。在《考古遗址学》一文中,陈胜前将考古材料作为信息的载体进行理解,把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与信息作为媒介的信息论相比较,生动解释了考古材料作为信息源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递减和干扰因素,从比较直观的考古材料到认识论贯穿了考古学研究的整体层面[21]。考古遗址学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可见的遗物分布与形成过程,也关注遗迹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层面。如在旧石器晚期革命的研究中,对人类技术变化的行为意义探索较少,通过不断扩展考古材料,在其与人类行为间架起桥梁,将行为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进一步丰富研究内涵[22]。
将废弃过程作为专门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刘郭韬[23]、卢立群[24]、李彬森[25]。他们分别以白音长汗、查海和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材料,系统运用废弃过程的视角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初创期时的“非稳定定居”现象。如李彬森在分析位于华北北部的北福地遗址时,以希弗事实上的废弃物概念对前人研究中认为的所谓“祭祀场”遗存的分析表明,此类遗存与磁山遗址的“组合物”类似,很可能并不是祭祀,而是一种储藏,刘莉与陈星灿的分析也得出相同观点[26]。李新伟在探讨辽西地区史前文明演进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兴隆洼文化时期居住面的遗存性质,认为这一时期的房址居住面的遗存受到了废弃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其经济结构导致人类行为而产生的[27]。
3.研究实践的启示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学者已逐渐认识到废弃过程方法是研究考古材料不可缺失的一环,并已有相关的理论思考及研究实践。但是,如何依靠民族考古学建立的参考模型与实际发掘的考古材料相对应,并且更好地运用废弃过程分析方法来研究考古材料,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应充分借鉴民族考古学的相关成果。美国西南地区由于有清晰的民族学背景,可以归纳出更多样的废弃模式,因此在解释遗址废弃原因时就显得得心应手。而对于我国的考古材料来说,虽然难以识别出如此多样且细致的废弃模式,但是,突然的废弃和缓慢的废弃在考古材料层面很容易发现。例如,聚落中房址居住面上遗物和遗物组合关系的完整与否是废弃是否突然或有计划性的良好体现。因此,我们应该借鉴民族学模型中所归纳出的废弃模式,对我国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寻找人类行为与物质之间的因果率[28]。
其次,应根据这些关联信息的完整与否来判断居留时间的长短,这一部分需要借助统计分析来看相关性。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考古学情境下的器物及器物组合,如石磨盘和石磨棒是一对器物组合,红烧土和灶是相互关联的遗存。如果这些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器物脱离了原生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判断存在空间上的位移,本文中在介绍废弃过程的理论时,原生废弃物堆积、次生废弃物堆积等概念适用于此部分关联信息的判断。
此外,对遗址废弃过程的整体把握还需要回到当时所处的文化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影响当时人类的行为,而行为因素是除自然因素外塑造考古材料的动因。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仰韶文化已进入农业社会,龙山文化末期进入复杂社会等,这些考古学研究成果是我们去理解单一遗址和整个时期内遗址废弃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键,同样在狩猎采集、农业经济等不同经济构成中人类行为影响下的考古材料呈现形态也不同。其中各个遗址或区域内废弃模式的多样性就需要依遗址生计方式的复原来实现。石器分析是近年来比较好的复原生计方式的方法,主要运用石器痕迹与功能分析、器物组合分析、加工对象分析等得出遗址采用何种经济模式的结论[29]。以上的研究预设与分析方法互为关联,成为一个研究整体框架,最终的研究目的都指向遗址的废弃过程。
综上所述,以废弃过程为视角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显示出这一理论视角的优势及其研究潜力。目前,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人类由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时的重大转变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下文将对未来研究中涉及的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4.思考与展望
长期以来,考古埋藏学研究一直都受到持续关注[30],我国学者从实际工作出发,结合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运用了多种方法,尤其是在判定用火遗迹是否为人工时,遗址的形成问题就十分凸显。然而,遗址的形成是一系列自然与人为作用的结果,除了自然形成因素外,人为因素(也就是人类行为)往往决定了遗址的废弃模式与遗物分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人为因素影响下的遗址废弃过程研究的角度对我国今后的考古研究工作做一番展望。
第一,废弃过程分析将在农业起源及发展时期生计方式变更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西亚地区农业与定居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该地区纳图芬时期由于早期定居能力不强,需要周期性迁居,所以物品废弃模式更接近流动的狩猎采集者,遗址中存在大量储备物,遗址纵向的文化层显示居住时间越长二次废弃物堆积(secondary refuse disposal)越多[31],通过废弃模式分析可以看到当地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的发展过程。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诸多遗址就已经呈现出反复利用的现象,考古材料表现为遗址内废弃物增多,遗址结构复杂化以及呈现反复定居,如河南老奶奶庙、皇帝口所在的嵩山东麓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地点群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功能性遗址所反映的废弃模式差异[32]。农业起源之后,华北地区并未快速实现定居,整个大区域内呈现出不同生计方式组合的状况,废弃过程的初步分析同样显示在农业确定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发展也是阶段性的过程,定居生活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才最终确立[33]。废弃过程研究这一独特的视角越发表现出可行性,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针对已经发掘的考古遗址来说,对一些特殊遗迹及遗存性质的判断可提供更加多样的视角。如本文开头所说,已有相关研究注意到遗址和遗迹的特殊废弃方式问题。此类型的遗迹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自然原因而废弃,如各种地质灾害导致的废弃,我国较为典型的是青海喇家遗址[34];二是由于人为原因而废弃,较为明显的是经过火烧过的遗址或遗迹,如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房址的特殊废弃模式[35]。该遗址中被火烧过房址的物品较多,这些出土物品比较丰富的房址,可能经历过多次利用和反复占居。物品很少或无遗物出土的房址极有可能是被废弃的,屋内的器物被拿走再利用。遗址中出现的这些现象以废弃过程为视角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房址中器物的多寡和组合物变更。类似的还有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哈民忙哈遗址,研究者们通过人骨[36]和生计方式复原[37]等方面来探讨该遗址特殊的废弃模式,似乎都倾向于是由瘟疫导致的特殊人骨对待方式和遗址废弃模式。但是,如果能够留意哈民遗址中经过火烧与未经过火烧、有无人骨房址的废弃过程这一问题的话,可能还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例如,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研究辽宁新乐遗址时,利用一座遭遇火灾的2号房址居住面的组合物分析来复原住房内的生活[38],这种利用相对封闭的考古单位来还原出土情境就可以在具体考古材料解释上更加合理,可在今后研究此类遗址时予以借鉴。
第三,实验考古学对遗迹从建造、使用到废弃的观察都颇具参考价值。孙周勇等通过对陕西寨峁梁遗址房址的建造、使用和废弃的复原认为,房址应废弃在夏、秋之交炎热的时节,古人系突然迁徙,放弃房址前居住面遗物受到了居民选择性废弃[39]。其他研究工作还有山西河曲坪头遗址F1的复原[40],甘肃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41]等。复原实验可以给研究者在分析废弃过程时提供依据和佐证,是很好的参照物。
第四,对未来田野考古发掘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刘绪注意到我们发掘的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通常是低于当时地面的,一些遗迹在高度上的偏差是由于废弃后人类的活动导致的[42]。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受到废弃和废弃后遗迹与遗迹间的平面高度关系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有大批房址的聚落中,可能特别需要注意特殊遗迹的废弃。
五、结语
从目前西方考古学研究来看,在展开研究前关注遗址形成与废弃过程问题已成了一种研究的必要前提,它也成为了解社会组织、居住流动性的形态以及宗教礼仪的重要窗口[43]。不仅是前文所述的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间段的关注,在相关民族考古学[44]、游牧考古学[45]的研究中废弃过程的视角同样是开展研究的重要手段。废弃过程理论的使用范围可以涵盖所有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遗存,因为它们都是废弃的结果。如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考虑废弃过程影响下考古遗存的堆积状况,那么依此进行的考古学推理和解释才能更加有效。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国内考古同仁能够注意到这一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再结合中国的考古学实践,在此基础之上反向创新[46],探索构建中国的考古学之路。
[1]Michael B.Schiffer,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1972(2):156-165.
[2]Robert Ascher,Time’s arrow an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temporary community.Kwang-Chih Chang.In Settlement archaeology.Palo Alto,1968:47-79.
[3]Michael B.Schiffer,Th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University of Utah Press,Salt Lake City,1987.
[4]〔美〕威廉·拉什杰、库伦·墨菲著,周文平、连惠幸译:《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Catherine M.Cameron,Steve A.Tomka.Abandonment of settlements and regions:Ethnoarcha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6]同[3]。
[7]Stevenson,M.G.,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ite abandonment behavior:Evidence from historic mining camps in the southwestern Yuk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2(1):237-265.
[8]同[3]。
[9]V.M.LaMotta,M.B.Schiffer,Formation process of house floor assemblages.from Allison,Penelope Mary,The archaeology of household activities,Oxford:Routledge,1999:19-29.
[10]L.R.Binford.Constructing Frame of Referenc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2001.
[11]a.L.R.Binford.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New York,1978.b.〔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译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2]Margaret C.Nelson,Gregson Schachner.Understanding Abandonments in the North American Southwest.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2,10(2):167-206.
[13]Martha Graham.Settlement org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variability among the Rarámuri.Cathering M.In Cameron and Steve A.Tomka(ed.),Abandonment of settlements and regions:Ethnoarcha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5,Fig3.9.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编著:《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2015年。
[15]Sarah H.Schlanger and Richard H.Wilshusen.Local abandonment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in the North American Southwest.In Cameron and Steve A.Tomka ed.Abandonment of settlements and regions:Ethnoarcha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90-91.
[16]〔美〕马格雷特·纳尔逊、格雷格森·沙克纳著,殷敏译,陈淳校:《北美西南部废弃行为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17]徐坚:《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
[18]张弛:《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中国田野考古中对遗址堆积物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见《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01—819页。
[19]陈胜前:《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文化过程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0]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科学出版社2013年。
[21]陈胜前:《考古遗址学——考古信息的嬗变与传递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22]陈胜前:《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研究范式的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23]刘郭韬:《白音长汗遗址废弃过程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4]卢立群:《查海遗址的废弃过程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5]李彬森:《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废弃过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26]〔澳〕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27]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8]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29]陈胜前、杨宽、李彬森、朱永刚、吉平:《哈民忙哈遗址之石器工具》,《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30]a.曲彤丽、陈宥成:《史前埋藏学的回顾与思考》,《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b.尤玉柱:《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9年。
[31]Hardy-Smith,T.and P.C.Edwards.The garbage crisis in prehistory:artefact discard patterns at the Early Natufian site of Wadi Harnmeh 27 and the origins of household refuse disposal strategies,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4,23(3):253-289.
[32]同[22]。
[33]同[24]。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35]张莉、张卫东、王吉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10期。
[36]朱泓、周亚威、张全超、吉平:《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史前灾难成因的法医人类学证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7]同[28]。
[38]〔日〕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1—210页。
[39]孙周勇等:《论寨峁梁房址的建造、使用和废弃》,《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1期。
[40]张登毅:《河曲坪头遗址F1的试复原》,《文物世界》2012年第2期。
[41]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14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年第5期。
[42]刘绪:《若干田野考古现象分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43]〔英〕科林·伦弗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44]〔美〕尼古拉斯·戴维、卡罗·克拉莫著,郭立新、姚崇新译:《民族考古学实践》,岳麓书社2009年,第258—259页。
[45]〔澳〕罗杰·克里布著,李莎、唐仲明、于澎涛译:《游牧考古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
[46]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的创新问题》,《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