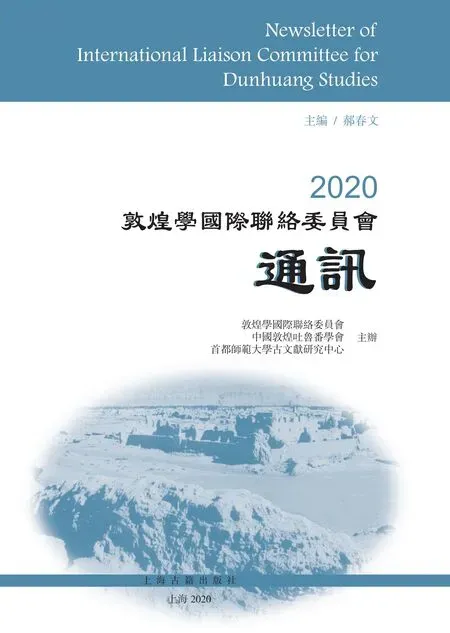P.2555《唐人詩文選集》中陷蕃詩研究綜述
2020-12-01王梓璇蘭州大學
王梓璇(蘭州大學)
P.2555,係一長卷,前殘後缺,正反面抄寫,另有些許殘片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5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將此卷定名爲《詩文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5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正面詩歌: 第336—338頁;背面詩歌: 第342—344頁。。P.2555寫卷中保存了大量唐代佚詩,可補《全唐詩》之闕。P.2555殘卷是一個内容十分豐富的唐人詩文作品的抄卷,共存詩205首,文2篇,其中正面抄有唐人詩歌173首,文2篇;背面抄有詩歌32首,其中保存的72首“陷蕃詩”都是陷蕃詩人所作,這部分詩作是唐人詩集所缺失而爲敦煌詩歌所獨有的,也是敦煌詩歌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包括正面59首和背面13首,前者抄於P.2555正面署名落蕃人毛押衙的《胡笳詞》第19拍之前,後者抄於P.2555殘卷背面署名爲馬雲奇的《懷素師草書歌》之後,夾雜在其他詩文之間。此卷經過國内外學者的整理、校勘和考釋,已取得豐碩成果。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經録》:“P.2555殘詩文集,匯録吐蕃侵佔敦煌時代文件(如爲肅州刺史劉壁臣答南蕃書),及陷蕃者之詩。亦有在敦煌地方通行之詩文,如劉商胡琴十八拍,劉長卿酒賦等。此卷極爲重要。”(2)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録》,收入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267頁。黄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録》:“伯2555號(殘詩文集安雅王昭君詩、孔璋代李邕死表、胡笳十九拍、劉長卿高興歌、孟浩然閏情、岑參江行遇梅花之作肅州刺史劉臣壁答南蕃書,馬雲奇白雲歌,臨王羲之尚書宣示帖等)。”(3)施萍婷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第242頁。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P.2555唐人詩文選集(兩面書寫)按: 匯録吐蕃統治敦煌時代文件(如爲肅州刺史劉壁臣答南蕃書),及陷蕃者之詩。亦有在敦煌地方通行之詩文,如劉商胡笳十八拍、劉長卿酒賦等。此卷極重要。背面有: 詩、月賦、從軍行、江行遇梅花之作(岑參)、冀國夫人歌詞七首、詠拗籠籌、閏情、懷素師草書歌(馬雲奇)、白雲歌、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口號……御制勤政樓下觀燈。”(4)黄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録》,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665頁。本文擬對此卷中72首陷蕃詩的研究情況進行梳理,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 寫卷刊佈與整理
王重民先生最早對此卷進行了整理與研究,遺憾的是,他生前未能最終定稿。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向達先生也曾在巴黎抄録了P.2555寫卷内容,後由閻文儒先生加以考證校勘,以《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校釋》(5)閻文儒《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頁—219頁。爲題,發表了向達先生的録文。1977年,“舒學”在王重民先生原録文的基礎上,又參照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微縮膠卷,整理出了唐代漢族詩人“佚名氏”詩59首,以及馬雲奇詩13首,共72首詩,以《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爲題,首次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上。(6)“舒學”《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文物資料叢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1期,第48—53頁。到1981年,劉修業先生在“舒學”録文的基礎上對72首陷蕃詩又重新進行了整理,發表了《〈全唐詩〉拾遺》一文。(7)王重民輯録,劉修業整理《〈補全唐詩〉拾遺》,《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期,第159—182頁。在這裏需要指出,“舒學”是作者筆名,牽涉到學術界的幾位前輩,以“舒學”署名的文稿不止有一篇,其中《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署名爲“舒學”乃王代文所取,取“初學”的諧音,《光明日報》1983年8月9日載文初《敦煌文學研究的一個成果》一文中曾説:“第一個發現,抄録並從事整理P.2555卷子的是王重民先生,王重民先生去世後,由王堯先生在遺稿基礎上完成了整理工作,並將整理稿題名《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發表於1977年《文物資料叢刊》第一期,署名是舒學。”(8)白化文《“舒學”是誰》,《博覽群書》2010年第3期,第87—89頁。他認爲王堯先生在保存、加工(特别是考釋部分)、推薦此稿方面貢獻極大,他同意文初同志的説法。1982年高嵩先生出版了《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一書,爲72首陷蕃詩作了詳細的整理和注釋,並且對陷蕃詩兩位作者的身份、詩歌的文學價值、詩中出現的地名和陷蕃人的押解路綫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9)高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983年,柴劍虹先生首次披露了P.2555殘卷的全貌,除王重民先生校録的72首詩外,另有“敦煌地方通行之詩文”116首詩和2篇散文作品,將其餘詩文刊佈。(10)柴劍虹《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伯2555)補録》,《文學遺産》1983年第4期,第146—154頁。1991年,熊飛先生又在柴劍虹録文基礎上進行了校勘和補録。(11)熊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2555)補録〉校勘斟補》,《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93—94頁。1995年,張先堂先生發表了《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新校》一文,他借助法藏敦煌文獻縮微膠卷,對P.2555卷的190首詩重新作了校勘,其中包括72首陷蕃詩。(12)張先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新校》,《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5—168頁。最早發表陷蕃詩歌的是陳祚龍先生,也是中國最早發表陷蕃詩歌的人,他在1975年發表了《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13)陳祚龍《敦煌學海探珠》上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05—135頁。與《關於敦煌古鈔某些李唐邊塞詞客之詩歌》(14)陳祚龍《敦煌學海探珠》上册,第99—104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有大批學者出版了有關敦煌詩歌作品的專著,代表人物有徐俊、張錫厚、孫其芳等人,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主要是以寫卷敘録與作品輯校相結合的方式,對敦煌詩歌作品進行比較全面的整理。(15)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686—757頁。孫其芳的《大漠遺歌——敦煌詩歌選評》一書,主要分爲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爲敦煌使吐蕃使詩,第二部分爲其他敦煌詩,這一部分又有其他幾種情況: 一是署名作者的詩;二是佚名作者的詩;三是佚名佚題詩。(16)孫其芳《大漠遺歌——敦煌詩歌選評》,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另外,還包括張錫厚先生主編的《全敦煌詩》。(17)張錫厚《全敦煌詩》第8册,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6年。戴密微在其名著《吐蕃僧諍記》第二章《史料疏議》中引録了P.2555寫卷72首詩的38首詩,並加以闡釋(18)[法] 戴密微著,耿昇譯《吐蕃僧諍記》,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4—435頁。。
二、 研究内容綜述
(一) “陷蕃詩”的作者
有關陷蕃詩作者,學界基本上認爲殘卷正面所寫的59首詩歌與背面的13首詩歌風格迥異,應非一人所作。高國藩先生在《談敦煌唐人詩》中認爲詩歌並非出自一人之手,至少是出自兩個不同經歷的詩人手中。(19)高國藩《談敦煌唐人詩》,《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第94—98頁。熊飛先生贊同高國藩先生的觀點,認爲從72首詩所反映的内容,以及從詩歌所使用的格律形式看,72首作品存在明顯差異,所以72首詩不可能出自同一個人之手。(20)熊飛《P2555殘卷抄録時間等相關問題再探》,《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項楚先生也提出了自己對於陷蕃詩人的三個疑點,較爲謹慎地認爲正面與背面的陷蕃詩是否是同一人所做尚不能肯定。(21)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第224—248頁。
對於陷蕃詩歌作者身份,學者大多根據《春日羈情》《晚秋羈情》《久感縲絏之作》這幾首詩分析,認爲作者是童年出家,弱冠宣法,學通儒、釋,且有一定的名聲,壯年還俗,並做過地方紳士的一位人物。閻文儒先生根據詩歌《夢到沙州奉懷殿下》中的“流沙有幸庭人主”“總緣宿昔承言笑”幾句分析認爲作者是受地方大吏所愛戴的。(22)閻文儒《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219頁。對於陷蕃詩歌作者的境遇,孫其芳先生根據《困中登山》中“戎庭悶且閑”,認爲作者雖被拘禁(即困中)而愁悶,但卻有閑暇時間,常能登山以解愁悶,可見他有一定的自由,只是被軟禁並非被關押。(23)孫其芳《大漠遺歌——敦煌詩歌選評》,第140頁。柴劍虹先生初步考證了陷蕃詩作者的身份,認爲他是“世居安西,後又定居敦煌的漢人”(24)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初探》,《新疆師大學報》1982年第2期,第71—77頁。。湯君先生根據《春日羈情詩》對佚名氏詩人的身世進行了考辨,她認爲柴劍虹先生所考證的陷蕃詩中作者是世居安西,後又定居敦煌的漢人這個身份不准確,認爲詩人是因故土淪陷才流落到敦煌的。(25)湯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作者考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6期,第242—247頁。楊富學、蓋佳擇根據P.2555寫卷背面有多份黏附其上的歸義軍時代的文書與雜寫,認爲:“以上數件文書多作於張氏歸義軍後期淮鼎、承奉時期,被順手拈來黏貼在紙背,足見詩人當與之時代緊鄰,而其從能獲得《書信》《周弘直狀》這種節度使往來的私密文書看,其與幾位節度關係斷不一般,文書的擁有人很可能就是那位曾經多次與金山國殿下出入於歌舞筵席的落藩人。”(26)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2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有關陷蕃詩的作者,高嵩先生認爲陷蕃詩歌72首的作者是甘州張掖郡和沙州敦煌郡的幕府官員,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攻陷張掖敦煌後,把兩地幕府中的一些官員押解至青海湖東側的湟水流域實行監押,他們的詩作大多是在押解途中寫成,能够反映建中元年(780)至建中五年(784)的唐蕃關係。(27)高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文學價值〉》,《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第81—84頁。
對於陷蕃詩作者被俘的時間以及押解時間,湯君先生認爲馬雲奇被俘是在廣德二年(764)夏天涼州失陷以後,開始是沿祁連山脈向甘州方向押解,永泰二年(765)又被押解入吐蕃,在赤嶺關押,她指出,詩人在廣德二年(764)冬出使吐谷渾,可能遊説吐谷渾與吐蕃聯盟未成功,在大曆元年(766)甘州失陷後,被吐谷渾押往臨蕃。(28)湯君《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作者考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第242—247頁。楊富學、蓋佳擇認爲,落蕃詩人出使吐蕃的時間,很有可能是在金山國與回鶻第一次、第二次交戰之間隙。(29)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2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有關陷蕃詩的具體作者,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佚名詩人和馬雲奇、毛押衙、鄧郎將。
1. “佚名詩人”和馬雲奇
主要代表學者有王重民先生和“舒學”。王重民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步整理法藏敦煌文獻時,就將72首陷蕃詩録爲佚名詩人所作的59首和馬雲奇所作的13首,指出:“右詩五十九首,鈔寫在伯二五五五,按其内容和編次,當是一個作者的詩集,可惜作者的姓名不可考了。”(30)王重民遺稿《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第49—52頁。即他認爲59首詩的作者是“佚名詩人”。而對於另外13首詩歌的作者,他認爲:“格調均相似,除第一首外,又皆詠落蕃詩,故可定爲一人作品。第一首下題馬雲奇名,作者殆即馬雲奇。”即他認爲十三首詩的作者爲馬雲奇。“舒學”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中前言提到:“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 一個(姓名不可考)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攻佔敦煌後,在此年初秋被押解離開敦煌……另一個是馬雲奇,大概是公元787年吐蕃攻佔安西後,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31)“舒學”《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文物資料叢刊》1977年第1期,北京: 文物出版社,第48—53頁。湯君先生同意該觀點,在《敦煌唐人詩集作者考辨》中分别考辨了陷蕃詩的兩位詩人: 馬雲奇和佚名氏,認爲馬雲奇系江南西道湖南衡陽人,最後馬雲奇失蹤不是被蕃軍遣回,而很可能是被殺害了;佚名氏的故鄉在今内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一帶,自幼剃度出家,精通佛理,但亦不放棄儒學,後還俗問政。(32)湯君《敦煌唐人詩集作者考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第242—247頁。閻文儒先生對13首詩歌的作者進行考辨後他認爲13首詩或都是馬雲奇所作,因爲殘詩集二(P.2555殘卷背面詩歌十三首)中,第一首是“懷素詩草書歌”,署名馬雲奇,第二首詩歌是“白雲歌”,他認爲白雲歌風格與懷素詩草書歌極其相似,並在白雲歌小序中自注是:“落殊俗隨蕃望之,感此而作”,所以13首詩可能都爲同一作者馬雲奇,又從《白雲歌》中的一句“即悲出塞須出塞,應亦有時還帝鄉”分析認爲馬雲奇可能是當時到河西的官吏。(33)閻文儒《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8頁。王志鵬在《敦煌寫卷P.2555白雲歌再探》認爲P.2555背面的12首詩與正面的59首陷蕃詩,並非同一作者,馬雲奇也只是《懷素師草書歌》的作者,而不是陷蕃詩的作者,他從《白雲歌》所表達的思想内容及寫作手法方面分析,側面説明《白雲歌》的詩人是一位具有較高的佛學修養者,是一位儒、佛、道三者兼通的佚名僧人(34)王志鵬《敦煌寫卷P.2555白雲歌再探》,《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第81—87頁。。
2. 毛押衙
主要代表學者有柴劍虹先生和潘重規先生。柴劍虹先生在《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馬雲奇詩”辨》(35)柴劍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馬雲奇詩辨”》,《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第53—58頁。中,認爲馬雲奇的《懷素師草書歌》與其後的12首詩歌在抄寫風格方面有所不同,但與正面59首佚名詩歌的抄寫風格很相似,所以推測除《懷素詩草書歌》外的12首詩與正面59首詩歌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柴先生注意到,緊接前59首詩歌抄録在劉商《胡笳十八拍》之後是第十九拍,署名“毛押衙”,這首詩歌從内容格調來看,與59首詩歌連貫一氣,應當爲一人所作,所以他推測這71首詩歌的作者爲落蕃人“毛押衙”。潘重規先生對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進行了深入研究,證明馬雲奇不是陷蕃詩的作者,他從筆跡入手,推斷“毛押衙”爲72首詩的作者(36)潘重規《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第1—20頁。。其他學者如徐俊、項楚等雖然同意正面59首詩歌與背面12首詩歌因筆跡不同、格式不同,推斷不是一人所作,但是並不同意作者或是抄寫者即爲落蕃人毛押衙。徐俊先生從敦煌所存詩卷的整體狀況和本卷與其他詩卷的情況看,認爲13首詩歌爲同一人所作詩的情況很小。(37)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第689—690頁。項楚先生在《敦煌詩歌導論》中認爲陷蕃詩歌正面59首和背面12首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作,前59首陷蕃詩的筆跡與落蕃人毛押衙所寫的第十九拍的筆跡相同,也與背面陷蕃詩白雲歌的筆跡相同,所以這個作者爲毛押衙的可能性較高,且他認爲馬雲奇只是《懷素師草書歌》的作者,而不是陷蕃詩的作者。(38)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第224—248頁。
3. 鄧郎將
主要代表學者是邵文實先生。邵文實認爲正面與背面詩不是一人所作,她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從詩作反映的内容來看,所寫的對象有所不同,正面59首詩中屢屢出現“敦煌”這一地名,而背面12首詩中無一提及,倒是將甘州指爲自己的暮居之地;第二,從詩中作者的押解路綫來看,正面59首詩作者的押解路綫寫的非常清楚,敦煌——馬圈——墨離海——赤嶺——白水古戍——臨蕃,而背面12首詩中所敘述的行跡並不是那麽清楚,作者根據背面12首詩中的《送游大德府甘州真言口號》和《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言口號》,判斷後者詩歌中提到的“主君”是甘州的“將軍”,那麽他的出發地當是甘州而不是敦煌,又根據《九日同諸公殊俗之作》這首詩歌判斷作者的方位是在青海,若詩人此後被押往安西,則是從青海出發西北上了,那詩人所述的行跡與正面59首詩中的行跡恰恰相反,所以正面59首詩與背面12首詩的作者應該不是一個人;第三,59首詩與12首詩所述作者的家鄉並不在同一個地方;第四,根據59首詩與12首詩所推測,作者的被俘原因也不相同,根據59首詩中對的《夢到沙州奉懷殿下》《春日羈情》《久感縲絏之作》,諸篇認爲作者是奉使入蕃時被拘的,根據12首詩歌中的《秋葉》認爲背面詩歌的作者是作爲戰俘被拘的;第五,創作的風格也有很大的差異,背面詩歌没有正面詩歌表現出感傷和抱怨之情。所以邵文實先生認爲P.2555號正面59首詩與背面12首詩的作者應該不是一個人。對於詩歌的具體作者,她認爲抄寫者是一個知道“毛押衙”的人,因爲作者本人是不會稱自己的官名。邵文實先生又將背面《白雲歌》小序中的“予”代稱爲12首詩的作者,背面“予”所寫的詩與正面59首詩有一問一答,一唱一和,且“予”詩有《贈鄧郎將四弟》,所以她認爲正面59首詩歌的作者可能是“予”稱爲“鄧郎將四弟”的人,P.2555殘卷中的72首“陷蕃詩”中至少有三個作者,一是《胡茄十九拍》的作者毛衙押,一是正面59首詩的作者鄧郎將,一是《白雲歌》及其後來11首詩歌的作者是“予”。除了考辨了P.2555殘卷72首陷蕃詩有作者,她還論述分析了因個人經歷不同、性格不同的三個詩人表達出了不同的思想感情和筆調風格。(39)邵文實《吐蕃佔領時期敦煌没蕃詩人及其作品》,《東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第80—85頁。
(二) “陷蕃詩”中地理及其路綫的研究
有關於“陷蕃詩”中的地理及其路綫,學者們已經有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閻文儒先生在《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中,偏重於歷史、地理以及陷蕃時間的考證,在詩歌的内容和意義方面只是略説了一些。閻文儒先生分析這些陷蕃詩,雖然是文學作品,但實際上是一種紀行詩。從今日敦煌入南山,過山至哈拉湖,再東行到鄯州,西六十里至臨蕃,他還通過詩歌分析了作者一路上經歷的季節和花費的時間,他離開敦煌是在初秋,作者在墨離海過了一年,後到達臨蕃又在臨蕃過了一年,由詩歌《題故人所居》:“與君昔離别,星歲爲三周。”可見他逢到友人已是在第三年了。
高嵩先生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的“《殘卷》作者押解路綫圖説”總結了佚名氏和馬雲奇兩個人的押解路綫,認爲佚名氏的押解路綫是從敦煌郡城出發,西行而南,經過今當金山口,即“凶門”,向西南繞蘇幹湖,循“奔疾道”,至墨離海,佚名氏在墨離海上某川地過冬,至來年夏季方才離開,過西同向南,到“把險林”,由“把險林”經過巴隆、香日德、都蘭、茶卡,至青海湖西南蕃庭,自“蕃庭”向東南行,過赤嶺(今日月山)北折至白水古戍,再由白水古戍沿陵谷東北而行,最後到達湟水北岸臨蕃城。馬雲奇的押解路綫是從甘州張掖出發到達淡河,又到達大鬥拔谷(今扁都口),然後從大鬥拔谷到達了青海北某個近海的山區,作者認爲這一綫的傳統通道是: 扁都口——俄博——祁連——冰溝——剛察,最後到達了臨蕃。(40)高崇《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6—111頁。項楚先生認爲59首詩歌記敘了作者從敦煌出發,經過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直到臨蕃,前23首詩歌是途中紀行詩,後36首詩是在臨蕃所作。(41)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 巴蜀書社,2001年,第248頁。陷蕃詩作爲紀行詩,其中在詩題與詩歌中大量出現一些地理名詞,按詩歌抄録順序梳理,主要有以下這些: 馬圈,陽關,墨離海、青海、敦煌、沙州、赤嶺、白水、臨蕃等,詩歌中出現的這些地理名詞,大致可以爲我們勾畫出陷蕃詩人被押解的路綫,實際上這條道路就是溝通敦煌與青海的“奔疾道”,也叫做“把疾路”。陳國燦先生認爲:“南口烽以南是吐谷渾活動的地域,故使用並不頻繁,而青海地區的吐蕃、吐谷渾則常從此道進入敦煌。”(42)陳國燦《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7—515頁。通過詩歌呈現的落蕃詩人所行的地理路綫,對於考證研究唐代交通道路及唐代河西沙州地區與青海地區往來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三) 有關陷蕃詩的寫作時間
1. 陷蕃詩是作於吐蕃佔領敦煌前
柴劍虹先生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初探》中,認爲五十九首佚名詩並非寫於吐蕃佔領敦煌之後。他認爲,佚名詩基本上是按時間順序寫的,而且前七首詩並没有透露出敦煌淪陷和詩人被俘的消息,作者認爲佚名作者所寫的《夢到沙州奉懷殿下》證明了當時沙州敦煌並未淪陷;大曆元年(766)五月涼州陷於吐蕃後,河西節度使才徙至沙州,因此親王坐鎮敦煌應在大曆元年之後,作者經過對《册府元龜》的考證,承審受封爲敦煌王,只有受封爲“敦煌王”後,他才可稱爲殿下,指出“佚名詩當作在至德或大曆元年之後,建中敦煌淪陷之前”。而且還指出馬雲奇詩也並非寫於787年吐蕃攻佔安西以後,因爲從詩歌的内容來看,並不都是他被吐蕃拘禁時所作的詩,其中的第一首詩是《懷素師草書歌》,從這首詩歌的詩意來看寫於懷素三十歲,懷素卒於貞元元年,安西淪陷時他早已去世,所以馬雲奇所寫的這首詩不可能寫在吐蕃攻安西之後,他認爲馬雲奇詩與佚名氏詩寫作年代大致相同,即是寫在758—781年吐蕃逐漸侵吞了河隴地區,但是沙州、西州尚爲唐軍堅守之時。(43)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卷殘(伯2555)初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71—77頁。熊飛先生認爲“從殘卷中已知作者的情況看,殘卷抄録作品所反映的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的歷史情況,大多作品創作於玄、肅、代三朝”,他又根據相關材料考定殘卷背面《懷素師草書歌》寫於大曆四年(769)春,根據詩歌《夢到沙州奉懷殿下》中的“昨來魂夢傍陽關,省到敦煌奉玉顔”認爲在佚名詩人的眼裏,敦煌尚在唐人手中,所以詩歌可能作於建中二年(781)沙州淪陷之前;根據詩歌《登山奉懷知己》中“陣雲衡北塞,煞氣暝南荒”,認爲若當時沙州陷蕃,那麽河隴地區便已在吐蕃人手中,詩歌所描繪的風物就不合當時形式了;他認爲“《冬日書情》爲七言律詩,極合律,幾無一字越格者,此又是天寶前難以見到的,故此詩及前後數詩仍應寫於天寶中”(44)熊飛《P.2555殘卷抄録時間等相關問題再探》,《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63—73頁。。高國藩先生從詩歌描繪的風物來推測,不認爲詩寫於建中二年(781),他認爲“舒學”所説的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攻佔敦煌,這個時間過於具體化,且原稿裏没有建中二年的記載,他認爲根據殘卷,對詩歌所作的時代背景只能做大致的推斷,所以高國藩先生認爲,陷蕃詩應當不是作於吐蕃攻佔敦煌後。(45)高國藩《談敦煌唐人詩》,《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第94—98頁。顧浙秦先生認爲,“從其五十九首詩作可以看出,他(陷蕃詩歌的作者)是敦煌即將陷落之際,在敦煌郡幕府殿下的懇請和遣派之下,入蕃軍交涉的,結果‘猜嫌被網羅’被疑作爲奸細而遭縲絏,一路押至臨蕃羈用”(46)顧浙秦《敦煌詩集殘卷涉蕃唐詩綜論》,《西藏研究》2014年第3期,第73—82頁。。
2. 陷蕃詩是作於吐蕃佔領河隴後
陳祚龍先生在《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中認爲,背面12首詩作於吐蕃佔領河隴諸州後,他認爲,“自從李唐玄宗天寶安、史之亂後,相繼陷於吐蕃,直到懿宗咸通年中,次第全經光復期間的作品”(47)陳祚龍《敦煌學海探珠》上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34頁。。舒學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中指出:“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姓名不可考,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攻佔敦煌後,在此年初秋被押解離開敦煌,經過一年零一二月的時間,由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到達臨蕃;另一個是馬雲奇,大概是公元787年吐蕃攻佔安西後,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他們的這些詩,按時間先後編排,記録了作者沿途的見聞和感慨。”(48)“舒學”《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文物資料叢刊》1997年第1期,北京: 文物出版社,第48—53頁。閻文儒先生認爲:“作者陷蕃當在建中初閻朝等以敦煌投降的時候。是年初秋押解離開了敦煌,大概由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到達了臨蕃,在臨蕃又被囚禁。所經過的這些地方,都是吐蕃的佔領區。”(49)閻文儒《敦煌兩個陷蕃人殘詩集校釋》,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0頁。邵文實先生在《敦煌邊塞文學研究》這本書“吐蕃佔領時期没蕃文人及其作品”這部分中認爲P.2555號的72首敦煌没蕃人詩歌是作於河西節度使政權覆滅以後,敦煌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淪於吐蕃之下時期,他認爲“在這一時期,經濟上是蕭條期,政治上是沉淪期,而文化上是變異期。”且他用“没蕃文人”這一稱呼來稱這一時期文學作品的作者,因爲他認爲這或多或少的與吐蕃統治有關聯,也反映了吐蕃統治下的漢人心態。(50)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頁。
3. 陷蕃詩是作於張承奉金山國時期
孫其芳先生在《敦煌使吐蕃使及其詩作探微》中,根據59首陷蕃詩中的其中一首《夢到沙州奉懷殿下》一詩的詩題中出現的“殿下”一詞,確定了詩作寫成的年代在西漢金山國時期。她認爲,“殿下”是對太子的尊稱,也可用於稱諸侯王,但按唐制,卻只能用於稱呼皇后和太子,金山國自用此制,則這個“殿下”便是金山國的太子。而且詩中又有“流沙有境庭人主,惟恨無才遇尚賒”,説明了當時敦煌有“人主”統治小朝廷,這個小朝廷非金山國莫屬了。所以她認爲“陷蕃詩”應當寫於西漢金山國時期,詩的作者是張承奉的西漢金山國使者。(51)孫其芳《敦煌使吐蕃使及其詩作探微》,《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陳國燦先生在《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一文中認爲佚名氏詩的作者是金山國的官員,於910年冬被派往吐蕃求援,在臨蕃城被羈押,所以陷蕃詩可能爲金山國時期作品。(52)陳國燦《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詩歷史背景新探》,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2頁。楊富學、蓋佳擇先生同意陳國燦先生的觀點,《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一文中認爲,P.2555寫卷之最終形成年代應在歸義軍時期,根據寫卷背後黏附的歸義軍時期文書與雜寫,認爲數件文書多作於張氏歸義軍後期淮鼎、承奉時期,被順手黏貼在紙背,他們通過辨證詩歌中出現的“退渾”“唐家”“鄉國”“殿下”,卷背的《白雲歌》帶有的濃厚的佛道色彩,以及詩作所反映的河湟廢墟化,認爲詩歌當作於金山國統治時期。(53)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二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四) 陷蕃詩的文學性和藝術特色
有關72首陷蕃詩歌的文學性和表現的文學藝術特色,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頗豐。主要集中於分析其72首“陷蕃詩”的文學價值,主旨結構,詩人表達的思想情感,以及探究“敦煌詩”與唐代“邊塞詩”之間的關係。
柴劍虹先生在《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初探》中,從詩歌的藝術特色分析認爲貫穿於整個佚名詩的是悲愁和淒涼的心情,他從“陷蕃詩”出發還初步探索了“敦煌詩”與一些内地文人所寫邊塞詩的聯繫。(54)柴劍虹《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初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71—77頁。馬驍、馬蘭州在《敦煌寫卷P.2555以“落蕃漢人”爲題材的60首詩作文本分析》中基於陷蕃詩作品本身,從唐代邊塞詩歌的發展的背景出發,對於敦煌P.2555以“落蕃漢人”爲題材的60首詩歌從文本角度作了單純文學意義上的分析,並對其文學價值作了評估,分析了60首詩作的主旨和結構、審美情感,對60首詩作進行了歷史定位,認爲非盛唐、晚唐以及貞元元和之作。(55)馬驍、馬蘭州《敦煌寫卷P.2555以“落蕃漢人”爲題材的60首作文本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第34—38頁。王志鵬先生在《敦煌寫卷P.2555白雲歌再探》中對於背面12首陷蕃詩(包括《白雲歌》)的作者和《白雲歌》的思想内容作了探討;(56)王志鵬《敦煌寫卷P.2555白雲歌再探》,《敦煌研究》2004年第6期,第81—87頁。高國藩先生在《談敦煌唐人詩》中,分析了詩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認爲詩歌反映了當時詩人思念家鄉的哀歌和内心的反抗。(57)高國藩《談敦煌唐人詩》,《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第94—98頁。邵文實先生在《吐蕃佔領時期敦煌没蕃詩人及其作品》中,認爲陷蕃詩作都受到了中原邊塞詩歌的影響,而且他們有與中原詩人不同的經歷,所以他們的詩歌又有自己的特色。邵文實還考辨P.2555是由三人所寫,且在三人詩歌價值方面做出了論述。其中特别强調了鄧郎將的詩歌價值,“用一個開始意氣風發,而後沉淪孤況的落蕃者的眼光,注視了時事的變遷。”(58)邵文實《吐蕃佔領時期敦煌没蕃詩人及其作品》,《東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第80—85頁。孫其芳先生《大漠遺歌——敦煌詩歌選評》在詩歌的評析中,她通過詩中描繪的景物分析了每首詩歌詩人所表達的羈愁、鄉思、懷念友人的思想感情,以及分析詩人的寫作方法和文學特色。(59)孫其芳《大漠遺歌——敦煌詩歌選評》,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顧浙秦先生在《敦煌詩集殘卷涉蕃唐詩綜論》中主要分析了陷蕃詩歌的文學特色,他認爲,涉蕃詩抒發了落蕃後的孤獨傷感和思鄉懷舊,亦飽含有憤懣之情,認爲涉蕃詩作描繪的異域風情凸顯作者被羈後身處異域的淒涼,表達對邊地戰争的反對和譴責方面陷蕃詩在思想境界上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他還具體舉例分析了詩歌的文學藝術特色。(60)顧浙秦《敦煌詩集殘卷涉蕃唐詩綜論》,《西藏研究》2014年6月第3期,第73—82頁。胡大浚、王志鵬的《敦煌邊塞詩歌校注》也對“陷蕃詩”的文學性和表現的藝術特色方面作了分析。(61)王志鵬《敦煌邊塞詩歌校注》,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 正面59首陷蕃詩寫作時間再探
筆者在閲讀詩歌及結合史料後對於陷蕃詩歌的創作年代也有了自己的看法,認爲正面59首陷蕃詩應當不會作於吐蕃攻陷敦煌之前,其年代至少在唐文宗(809—840)之後。
首先,陷蕃詩中的第一首詩歌爲《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其中詩題中的“退渾”即吐谷渾。這一時期的“退渾國”可能作爲吐蕃的屬國而存在,所以在詩題中稱之爲“退渾國”。從《資治通鑑》記載:“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曆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鎮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62)[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二,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7695頁。可以得知“吐谷渾”是由“退渾”音訛得到,而且由“吐谷渾”音訛到“退渾”的時間至少在文宗以後,所以正面59首詩歌的寫作時間大概在晚唐時期。而柴劍虹先生所認爲的佚名詩作於至德或大曆元年之後、建中敦煌淪陷之前;熊飛先生所認爲的殘卷抄録的作品創作於玄、肅、代三朝;高國藩先生認爲的陷蕃詩歌作者是在敦煌即將陷落之際,在敦煌郡幕府殿下的懇請和派遣下,入蕃軍交涉。這些認爲陷蕃詩歌作與肅代時期的觀點自然不能成立,59首陷蕃詩應不是作於吐蕃攻陷敦煌之前。
其次,在663年吐蕃滅吐谷渾到8世紀,吐谷渾一直是藩屬於吐蕃而存在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國家。高宗龍朔三年(663),“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群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63)[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八四,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5301頁。吐蕃吞並吐谷渾據其地後,除了諾曷缽與妻唐弘化公主引殘部徙居内地依附唐朝外,龍朔三年後,留居青海故地的吐谷渾部族便處於吐蕃的統治和奴役之下,這一時期的吐谷渾是吐蕃的藩屬國。楊銘先生根據敦煌石室發現的藏文手卷《吐谷渾(阿柴)紀年》(vol.69,fol.84)分析認爲,663年吐蕃滅亡吐谷渾之後,吐蕃所立之吐谷渾王,是與吐蕃王室聯姻,且自稱“甥”的一支,作爲吐蕃小邦王子而存在,這個吐蕃小邦王子就是吐蕃扶植的吐谷渾可汗,即“莫賀吐渾可汗”。(64)楊銘《吐蕃統治敦煌西域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30頁。根據《新唐書·吐蕃傳》中所記:“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65)[宋] 歐陽修《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6076頁。這表明雙方在咸亨元年已經成爲了甥舅國,吐蕃佔領其地。在這一時期,吐蕃控制下的吐谷渾國更多像一個歷史或地理名詞而非政治實體。(66)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2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吐谷渾這一時期作爲吐蕃的臣屬國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吐谷渾作爲吐蕃的藩屬國,常常被征税。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獻P.t.1288《大事紀年》與吐蕃簡牘以及其他藏文文獻資料中記載有吐谷渾部完全臣屬吐蕃,楊富學、蓋佳擇已經在《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中有很詳盡的討論,這裏不再贅述。(67)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2018年。所以在吐谷渾國小王在統治自己國家方方面面没有實際的權力,所以吐谷渾在8世紀遠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獨立的國家,而是在吐蕃的控制之下的。吐谷渾作爲吐蕃的藩屬國還表現在他們共同聯合侵擾唐朝,《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寇陷涇州。十月,寇汾州,又陷奉天縣。遣中書令郭子儀西禦。吐蕃以吐谷渾、党項羌之衆二十餘萬,自龍光度而東。”吐谷渾不但與吐蕃共同作戰,而且還爲吐蕃提供兵源。(68)[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5237頁。
敦煌法藏藏文文獻P.t.1288《大事紀年》記載:
及至狗年(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
冬,[贊普] 牙帳駐於劄瑪之翁布園。於“島兒”集會議盟。徵集吐谷渾之青壯兵丁。(69)《王堯藏學文集》卷一《吐蕃本敦煌歷史文書吐蕃制度文化研究》,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第155頁。
再根據《資治通鑑》記載:“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青海爲吐谷渾部落的屬地,吐蕃畜牧青海,表明吐谷渾可能還爲吐蕃提供軍糧。(70)[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四《唐紀》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7224頁。吐谷渾作爲一個國家直到張氏歸義軍時期仍然存在,這一點在P.2962《張議潮變文》中可得到證實,但是在歸義軍時期,吐谷渾附屬與吐蕃的國家性質恐怕已經有所改變,其實力也不容小覷,在P.2962《張議潮變文》開頭記載:“諸川吐蕃兵馬還來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來報僕射:‘吐渾王集諸川蕃賊欲來侵淩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齊集合。’僕射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鏨凶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才經信宿,西至西同側近,便擬交鋒。其賊不敢拒敵。即乃奔走。僕射遂號令三軍,便須追逐。行經一千里已來,直到退渾國内,方始趁趃。”(71)王重名、向達等編校《敦煌變文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14頁。“敦煌北一千里鎮伊州城有納職縣,其時回鶻及吐渾居住在彼,頻來抄截伊州,俘虜人物,侵奪畜牧,曾無暫安。”(72)王重名、向達等編校《敦煌變文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14頁。從這一段可以表明,在歸義軍時期,吐谷渾仍作爲一個國家而存在這一點毋庸置疑,雖然變文是文學講唱作品,有一定誇張性,但從這段變文中提到吐谷渾王集合吐蕃會集出征、侵淩抄掠,以及從變文中所描述的吐谷渾侵略伊州的情況來看,吐谷渾的實力在歸義軍時期並不薄弱,吕建福先生認爲,嗢末起義後,退渾的力量强大,也不見得没有反過來依附者。(73)吕建福《唐末詩文中的吐谷渾》,《中國土族》2004年第3期,第47頁。
從《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中的兩句“西行過馬圈,北望近陽關”記録的退渾國的方位來看,在沙洲的西面,在P.2962《張議潮變文》中記載的退渾國的方位一致,所以在《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中這首詩題中的“退渾國”可能就是張議潮南征的吐谷渾,所以説明詩歌可能作於張議潮剛剛收復敦煌時期。更重要的是根據前人學者對於陷蕃詩歌中地理及其路綫做過的研究(74)有關於陷蕃詩歌中涉及地理路綫的研究成果,前文已有所述。,認爲詩歌作者所行進的路綫是循“奔疾道”而行,即由敦煌進入退渾國,後至墨離海,到達青海,又經過赤嶺、白水最終到達臨蕃,這條道路與《張議潮變文》中張議潮通過南山道行進1 000多里追擊吐谷渾的道路相一致,變文中將此道稱之爲“把疾路”,是吐蕃進入沙州與青海地區往來的重要一道。
所以筆者認爲吐蕃從667年滅亡了吐谷渾後,吐谷渾分裂爲兩部,但青海一支一直作爲吐蕃的藩屬國而存在,從吐蕃向吐谷渾徵集大軍並共同對抗唐王朝可看出,直到中晚唐時期,吐谷渾國家仍然存在,但附屬吐蕃的國家性質可能已有所改變,這一時期吐谷渾在軍事力量增强,作爲“退渾國”而立據於西同之地,所以在張議潮收復沙州後不久,落蕃詩人從敦煌郡出發,可能是作爲勸説吐谷渾的歸義軍政權使節入退渾國,但受到吐蕃的猜疑而被縲絏至臨蕃。所以正面59首陷蕃詩歌所作時間,應當不會在吐蕃攻陷敦煌之前,可能作於張議潮收復敦煌、南征吐谷渾時期。
四、 P.2555殘卷中72首陷蕃詩研究述評
P.2555殘卷中的72首陷蕃詩雖不能與同時代唐代中原詩歌進行相提並論,但從史學角度出發,這些陷蕃詩可以對正史起到印證與補充作用,對於研究唐蕃民族關係、吐蕃在敦煌西域的統治、吐蕃統治時期的疆界等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以及從陷蕃詩人的親身經歷看出吐蕃對於陷蕃漢人如何統治,正如陳祚龍先生所述: 假若我們致力研究李唐沙州本部及其與吐蕃的文化關係,那麽,我敢説,它們可能就更得算爲“第一手”“第一流”,最寶貴、最重要的參考資料(75)陳祚龍《敦煌學海探珠》上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09頁。。所以72首陷蕃詩的文獻價值要遠遠大於文學價值。通過以上綜述,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可以看出目前對於P.2555殘卷中的72首陷蕃詩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
1. 就殘卷中詩歌的校録方面,目前學術界對敦煌詩歌的輯佚、校録工作仍在進行,但不同的學者對於P.2555殘卷中72首陷蕃詩歌的個别字的校録都不同,所以對於陷蕃詩歌的校録還需要不斷完善,在校録詩歌方面,應該結合詩歌的整體意境和字形而校録,比如在殘卷正面的《夢到沙州奉懷殿下》中的第三句:“流沙有幸逢人主,惟恨無才遇尚賒”中的“逢”,(76)此句依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所録。王重民先生録作“庭”,項楚先生認爲:“庭”當“匡”,蓋“匡”字先誤作“廷”,又誤作“庭”也,但是筆者認同徐俊先生的録文,因爲前一句的“逢”字與下一句中“遇”字含義相近且對仗。再比如正面詩歌中《夜度赤嶺懷諸知己》中的第7句“獨嗟時不利,詩筆唯然操”中的“唯”,王重民先生校作“雖”,閻文儒先生校作“誰”,徐俊先生校作“唯”,根據下一句詩“更憶綢繆者,何當慰我曹”的含義: 思念與我情誼殷切的友人,何時我們又能相互安慰,那麽結合上一句的含義,大致可能是: 只有自己一個人感歎時局的不順,又有誰能與我一同作詩。“誰”字更能反映出詩人思念友人的情感。
2. 就研究内容和方向而言,對於72首陷蕃詩歌的研究在詩歌文學價值方面研究成果較多,但對於72首陷蕃詩歌在史料價值方面挖掘得不够深入。國内學術界對於P.2555陷蕃詩歌在某一方面的專著較少,大部分是在關於敦煌詩歌的某一部分中闢出一章節進行連帶敘述,例如: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等,而且對於72首陷蕃詩歌的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考辨陷蕃詩歌的作者等方面,對於佚名詩人、馬雲奇及鄧郎將等人從個别分析中得出他們的生平資料,研究成果豐富,但對毛姓押衙的生平考證,因材料的缺乏目前尚未考證,以及對於P.2555殘卷正面59首詩歌和背面13首詩歌之間的聯繫以及對於72首陷蕃詩歌與中原詩人所作的邊塞詩歌的研究有待於再深入。而近幾年的研究成果,又主要集中在陷蕃組詩的個别詩歌作品的研究,多是單篇文章的研究,缺乏系統性的研究,而且若是就詩歌本身來研究詩歌不結合其他史料及敦煌文書,所得到的結論會有片面性,比如在對陷蕃詩歌作者及作者的身份、詩歌反映的歷史背景以及創作年代,學界相關著作雖已經有了充分的論述,但是有關陷蕃詩歌的創作年代的定位仍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在這裏結合詩歌與敦煌文書相關史料來看,正面59首陷蕃詩歌作於敦煌淪陷吐蕃時期可能性不大。
所以,接下來在對P.2555殘卷中陷蕃詩的研究首先應當區分清楚詩作的抄寫年代與創作年代,有關這一點目前學界還未曾有過關注,需要結合P.2555卷中的其他文書來分析詩作的抄寫年代,只有對陷蕃詩的創作背景與時間有了明確的定位,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文獻價值。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還需要關注詩作的抄寫者與創作者是否爲一人,以及正面與背面詩歌是否爲一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