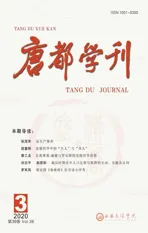秦汉时期关中人口迁移与族群的互动、交融及认同
2020-12-01刘志平赵若彤
刘志平, 赵若彤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西安 710069)
本文所言“关中”是指汧陇以东,至于黄河西岸,秦岭以北的泾渭流域,即三辅地区,亦即“秦川”。秦汉四百四十余年间,关中的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历史特征。从族群(1)“族群”是一个灵活而具有伸缩性的概念,既可指一个“民族”,也可指一个“民族”之下的有区域差异性并具历史传承意义的各次级人群。虽然“‘族群’这一词语具有了比‘民族’更加宽泛的含义。但是,这种宽泛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限于人类群体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族类化’范畴,而非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出现且日益增多并称为‘族’的社会文化群体。”参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互动、交融及认同的角度考察秦汉时期关中的人口迁移,有助于推进秦汉区域史、人口史、民族史的研究。
一、关中人口迁移与“秦人”认同的扩展、隐没及“汉人”认同的出现
虽然“战国中期到秦代”,“真正统一的‘秦人’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在‘秦人’内部还存在着客观的族群差异和‘裂隙’。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故秦人’即原住民与关东之民之间,以及秦境内的‘秦人’与‘蛮夷’之间”[1]366,但秦朝大规模地将关东人口迁徙至关中,无疑会对“故秦人”与“关东之民”的互动、交融产生积极的推促作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 “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2]239。关于此次移民,葛剑雄指出:“以每户5口计,共有60万人。豪富主要集中在关东,所以关东是主要的移民来源。”[3]64同时认为“这次移民完成以后,关东移民已经大大超过了咸阳的土著人口”[3]64。可见,超过关中本土“秦人”数量的关东移民的迁入,无疑对关中“秦人”与“关东之民”的互动与交融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事实也表明,虽然在整个秦代,关中“秦人”与关东“非秦人”的族群区分仍很明显(2)参见刘志平《先秦秦汉“秦人”称谓与“秦人”认同研究》,2017年第四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参会论文,于上海。,但秦始皇这次所迁移的大量关东“非秦人”无疑很快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关中“秦人”。大概因为在整个秦代,秦朝政府对关东旧六国之民一直是采取歧视性的人口政策(3)参见韩国学者尹在硕《秦朝的“非秦人”认识与占领地支配》,2015年第三届简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于广西桂林。,而这些关东豪富一旦成为关中“秦人”,其地位要得到很大提高,所以这些关东豪富对成为“秦人”应没有反感,甚至还会有优越感。
在秦代,另一次较大规模向关中移民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正所谓“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2]256。这次移民共8万家,约40万人。“此次徙民当自东边沿海迁至关中较为可靠”[4]。这是关东民再次徙入关中,对这些徙入关中的关东民还有“复不事十岁”的优待。这次徙民关中,对关中“秦人”与“关东之民”的互动与交融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以上两次徙入关中的关东之民成为后来楚人刘邦、项羽率领关东旧六国诸侯之民(包含楚人、齐人、燕人、赵人、魏人、韩人)攻入关中后所面对的“秦人”,“秦人”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而关东旧六国诸侯之民与关中“秦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又带领数万关东之民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南入汉中,所谓“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2]367。而这也是“山东人”和汉中之“秦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几个月之后,刘邦又率领这支包含“山东人”和汉中“秦人”的军队北上平定了关中三秦之地[2]368-369。此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与项羽展开了争夺。关中再次成为“山东人”和关中“秦人”的互动与交融之地。也正是在此时,产生了“汉人”这一称谓,虽然其为“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是‘汉’这一新诸侯王政权名号统摄下的包含‘秦人’、‘楚人’、‘燕人’、‘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等在内的人群集合体,还不是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汉人’称谓”[5],但在“汉人”之名义下,“秦人”与“山东人”的族群分界渐渐模糊。
综上,秦朝两次大规模向关中移民,对关中“秦人”与“关东之民”的互动与交融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秦人”于是含纳了越来越多的“关东之民”。秦末反秦起义及楚汉相争时期,刘邦率领的“关东之民”与“秦人”又有了进一步的互动与交融。与此同时,“秦帝国”灭亡,“汉王”刘邦逐渐取得了政治优势。在此背景下,“汉人”称谓首次出现,“秦人”称谓逐渐隐没。
二、关中人口迁移与“汉人”认同的维持、扩展和巩固
刘邦建立汉帝国,起初打算定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刘邦“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刘邦都洛阳[2]2043。刘邦后来采纳了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定都关中,这再次给“山东人”与关中“秦人”的交融、互动提供了契机。以此为基点,“‘秦人’称谓的主导性在汉代更是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汉人’或‘汉民’称谓的凸显,这是与关西之‘秦’成为‘汉’直辖的郡县相对应的”[5]。当然,“在汉初,由于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汉人’(‘汉民’)在当时观念和现实中的显著存在,‘汉人’(‘汉民’)作为真正整体意义上的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族群称谓还没有明晰的确定”,而“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5]。
在此过程中,关东之民不断徙入关中,是促成渐具广泛性、整体性的族属和文化含义的“汉人”称谓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据史书记载,“汉朝建立后,基本沿袭了秦代的移民政策。从汉高祖九年(前198)开始一直到成帝鸿嘉二年(前19)的近180 年间,相继向关中移民10余次,其对象大多来自于关东。”[4]在西汉,“与迁入的数量和次数相比,从关中迁出的人口要少得多。”[3]116总的说来,“西汉一代从关东迁入关中人口累计近三十万人,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后裔已有约122万,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3]121当然,在广义的族群意义上,这是华夏的内部互动。但因“秦人”曾经对“夏”概念进行了狭隘界定,形成了将关东华夏排除在外的狭隘的“秦(夏)”认同,而这一人口政策在汉初又得到了惯性继承——关东“诸侯人”被排除在“汉人”之外,故囊括关东华夏的整体意义上的华夏概念长期隐没在历史舞台背后,直到汉武帝时代,才走上历史舞台,形成了族群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三者之间处于相对一致的稳固状态(这种稳固状态又带有开放包容性)的“汉人(华夏)”认同(4)参见刘志平《先秦秦汉“秦人”称谓与“秦人”认同研究》,第四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参会论文,上海,2017年8月。。关东人大量徙入关中,不仅加深了关东人和关中人的区域性融合,而且对囊括关东华夏的整体意义上的“汉人(华夏)”认同的产生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中正因大量关东人的徙入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性人群风貌,正所谓“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6]1642-1643。先前“好稼穑,务本业”的“先王遗风”[6]1642发生了改变。不过,“大量齐鲁儒士的西迁,使关中地区成为了秦汉时期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4]。不仅如此,“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居统治集团上层”,更表明了汉武帝时代“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7]55。关中汉人也因此具有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在关中三辅地区,又有少数族群的存在,如活跃于长安的“胡巫”与“越巫”、西汉王朝正规军中的“胡骑”与“越骑”(5)参见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两汉的“越巫”》《汉王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收入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331、332—347、348—356、357—369页。。这些少数族群应是“归降、被俘、被征发及移居的人员”[3]113。他们与关中三辅地区的汉人无疑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不过,他们在关中汉人脑海里的异族形象似乎长久挥之不去,而这又强化了他们的自我族群认同。降汉的匈奴人金日磾在取得汉武帝信任而“入侍左右”时,被汉人称为“胡儿”[6]2960。而当汉武帝“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时,金日磾仍明确说自己是“外国人”,甘愿做霍光的副手,以避免“使匈奴轻汉”[6]2962。这足以说明当时汉人的“匈奴人就是外国人”这一观念确实影响到了归附汉朝的匈奴人本身。甚至到了金日磾弟弟金伦的曾孙金涉、金参、金饶时,其异族性似乎依然被汉人想起,故他们的职任一度都与异族有关,如金涉“领三辅胡越骑”,金参出使匈奴,被拜为“匈奴中郎将”,金饶被拜为“越骑校尉”[6]2964。
总之,西汉关东人大量徙入关中,不仅加深了关东人和关中人的区域性融合,使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性人群风貌,而且对囊括关东华夏的整体意义上的“汉人(华夏)”认同的产生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人(华夏)”认同也由此得到了巩固。在关中三辅地区“汉人(华夏)”与少数族群的互动中,“汉人(华夏)”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关中人口迁移与异族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
两汉之际,关中战乱频仍,人口伤亡很大,另有大量关中人离开关中。据《后汉书·隗嚣列传》记载:“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8]521关中汉人与“民以板为室屋”“名将多出”“民俗质木,不耻寇盗”[6]1644的陇右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互动。投奔陇右隗嚣的三辅士大夫中,就有杜林、杜成、范逡、孟冀等,而且是“将细弱”而徙[8]935,即举家迁徙。“通儒”杜林正是因为有了客居陇右的经历,故当后来光武帝刘秀“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时,对答甚佳,得到刘秀的赏赐[8]936。而扶风安陵人班彪在“三辅大乱”之际,先从陇右隗嚣,后又“避地河西”,依附窦融[8]1323-1324,对陇右和河西的风土人情、族群实态都有一定的了解,故其后来向刘秀详细汇报了凉州的族群状况,提出的民族政策也被刘秀采纳[8]2878。还有扶风茂陵人孔奋因“遭王莽乱”“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其治下的“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其受到姑臧吏民及羌胡的真诚拥戴和热情颂扬[8]1098-1099。这可看作关中汉人与河西汉人及羌胡友好互动的典型史例。不仅如此,孔奋后又与陇右武都吏民及氐人有良好的互动[8]1099。
东汉定都洛阳,“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关中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原在关中的一部分宗室、贵族、在朝廷任职的人员以及他们的附属人口必定会东迁洛阳”[3]122-123。如汉章帝时,京兆长陵人第五伦上疏称“卫尉(马)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马)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8]1398。可见三辅官绅移居洛阳的不在少数,关中人与关外人的互动有了新的动向,即趋向新的政治中心——洛阳地区。关中往年因人口繁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的繁华盛景不复存在,一度出现“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8]1688的衰败景象。
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及东汉政府的边地收缩政略(6)东汉“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2页。所谓“三绝”之理由,光武帝是“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汉章帝是“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汉安帝是“以其险远,难相应赴”。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09—2911页。而“三通”中的“第二通”,主要是凭借班超的个人能力与作用,东汉政府对他的实际支持比较有限,班超是“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参见《后汉书》卷47《班超列传》,第1582页。“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参见《后汉书》卷47《班超列传》,第1584页。而“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2页。这些都是东汉政府边地收缩政略的典型表现。,关中一度成为东汉政府控御异族扰乱的缓冲地带。如针对汉安帝永初凉州羌患,庞参提出的将“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功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8]1687的建议被东汉政府采纳,庞参被拜为“谒者”,专门负责“三辅诸军屯”事宜[8]1687。面对这次羌患,庞参明确说道:“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8]1688可见,为应对陇右羌患,关中三辅士民成为重要的凭依力量。当庞参、邓骘等人针对这次羌患提出彻底“弃凉州”之建议时,虞诩表示反对,理由是:“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8]1866此建议被东汉政府采纳,而三辅虽然没有成为“塞”,但其作为东汉政府控御异族扰乱的缓冲地带被定格了下来,这从西北边郡多次内徙关中就可明显看出(7)汉安帝永初羌患导致安定郡治所徙至右扶风美阳县、北地郡治所徙至左冯翊池阳县、上郡治所徙至左冯翊衙县,而汉顺帝永和羌患导致之前复故地的安定郡治所与北地郡治所再次内徙关中三辅地区。。
在上述背景下,东汉时期关中在人口迁移与族群的互动、交融及认同方面呈现出这样的显著特点:少数族群大量内徙关中,与关中汉人的互动逐渐得到加强。如建武十一年(35),“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8]2878-2879羌人不仅被迁徙至陇右,还被迁徙至关中西部,羌汉互动的地域自此从陇右扩展至关中。又如永平元年(58),在大破烧当种羌滇吾后,对降羌进行了大规模内徙,总共有七千人被迁徙至三辅地区[8]2880。“三辅的范围包括整个关中盆地,这意味着羌人又向东迁移了一大步”[3]234。可见,羌汉在关中的互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还如永嘉元年(145),左冯翊梁并以恩信招降离湳、狐奴等种羌五万余户[8]2897。这进一步增加了关中的羌人数量。而“在东汉末的战乱中,关中平原的人口大量死亡或外迁,由于羌人本来一般聚居在渭北高原或盆地的边缘,损失远比汉人为小。所以在曹操统一北方时,羌人在关中和西北人口中的比例已经大大上升,成为人数仅次于汉人的第二大民族。”[3]236
此外,氐人也大量内徙关中。建安年间,夏侯渊“督朱灵平隃糜、汧氐”[9]270。隃糜、汧二县在关中西部(8)此二县本属右扶风,汉献帝中平六年(189)后,别属汉安郡(汉兴郡)。,说明关中已有氐人徙入。“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9]858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两支氐人共有二万余落,人口接近十万,假设死亡逃亡占一半,尚存四五万人。扶风、美阳地处关中盆地腹地,据雍州的行政中心很近,将曾经参预反叛的氐人安置在那里可便于控制;而广魏郡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县东北,离雍州的中心较远,故安置了未参预反抗的氐人。”[3]239-240平均来算,被迁徙到关中的氐人有两万多口。还如曹操曾令张既到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9]472-473。以种落聚居的武都氐人不仅被迁徙到陇右的核心地区,还被迁徙到关中。被迁徙的氐人“估计有20多万口”[10]98,平均来算,被迁徙到扶风的氐人应有10多万口。这些语言、风俗与汉人有异的氐人,于是与汉人有了更多的互动,正所谓“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9]858-859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羌、氐、胡等异族内徙关中的情形延续到魏晋以后。正始元年(240),郭淮“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9]735。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11]2549。这使得关中的异族人口越来越多,正如江统所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1]1533。从而使得以关中为核心区域的北方异族在与华夏的互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使北方的华夏化进程具有了由异族主导的新特点。
纵观两汉之际,关中由于战乱频仍,大量关中人离开关中,关中汉人与陇右、河西汉人及羌、胡、氐等异族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互动。东汉政治中心的东移及东汉政府的边地收缩政略,使关中一度成为东汉政府控御异族扰乱的缓冲地带。在此背景下,羌、氐、胡等异族大量内徙关中,这一情形延续到魏晋以后,从而使得以关中为核心区域的北方异族在与华夏的互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秦及西汉时期,大量关东人徙入关中,不仅使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性人群风貌,而且最终促成并巩固了含纳关东华夏在内的整体性的“汉人(华夏)”认同,取代了秦及汉初狭隘的“秦人”或“汉人”认同。“汉人(华夏)”曾一度主导了以关中为核心区域的整个北方异族与华夏互动的历史进程。两汉之际,关中战乱频仍,人口伤亡很大,另有大量关中人离开关中。而到东汉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及东汉政府的边地收缩政略,关中一度成为东汉政府控御异族扰乱的缓冲地带。在此背景下,东汉政府对异族进行了大规模内徙,导致关中异族人口越来越多,异族在与关中汉人的互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羌、氐、胡等异族内徙关中的情形延续到魏晋以后,最终造成以关中为基地建立的异族政权不断涌现,这成为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北方异族政权不断涌现的一个典型表现。这样,秦汉时期以北方关中和河洛地区为主要基地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华夏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体华夏势力南移,大大推进了南方的华夏化进程,而北方则开启了异族主导下的新的华夏化进程。这一新的华夏化进程的最终成果即以关中为基地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华夏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