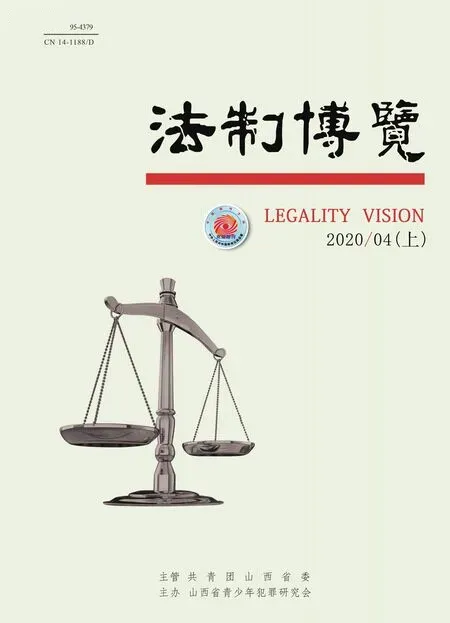论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问题
2020-11-30黄昭
黄 昭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目的
(一)对诉讼机制规范
我国虽然早已通过改革的方式废除了自前苏联承袭的刑事诉讼原则和办案模式,但是对于重客观证据而不要求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办案思维仍然扎根于司法系统之中,传统的办案思路认为只有以绝对证据的指控,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而在实践中却很难达到完整证据的搜集,更难以形成绝对证据的优势。所以在现有的诉讼体制中,着重应当改变的就是这样陈旧的办案思路,对以往僵化的司法诉讼机制进行改革与创新,达到人为调校的最优化效果。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引入,一方面可以防止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片面地重视客观证据,而忽略了主观上能够发现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在客观证据没有绝对优势的证明能力时,控方也可以对合理怀疑作出合乎法理与情理的答疑,以及进行符合事实的客观推论,从而有效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原有的苛刻的证据标准,同时也保障了刑事诉讼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使得诉讼机制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二)对被告人人权保障
在现代的刑事诉讼原则中,无罪推定原则是达成共识的基本法理,因此被告人不需要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一旦被告人被一系列的证据指控为相当具有可能性的犯案人,而被告人却没有任何证据为自己洗脱嫌疑的时候,则会面临相当不利的地位,甚至会被认为有罪。而如果通过排除合理怀疑机制,在犯案可能性极大的论证中,由于控方也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就不能完成经由常理推断被告人有罪的论证结果。由此可知,排除合理怀疑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了避免通过间接证据,或者有罪可能性极大的控诉而产生的冤假错案,从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三)对有罪判决的监督
按照刑事诉讼原则以及自由心证制度的要求,有罪判决的作出,是审判者在了解案情后,居中听取控辩双方的理解,以及对证据的审查,最后达到坚信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一个过程。而排除合理怀疑,就是审判者坚信被告人有罪的体现。所以,排除合理怀疑而达到有罪判决的作出,即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证,也是法理所体现的最终要求。
同时,排除合理怀疑,也是法理兼具情理的体现。由于有罪判决的最终作出是由审判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法则,凭借良心与常理推断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其源于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排除合理怀疑,即是对被告人所犯法律后果在道德上予以否定或肯定。对于审判者而言,有罪判决的作出是一种双重确定性认定的表现,即对证据上的确定与道德上的确定,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提出,便可以充分验证这两者的确定性,从而使审判者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二、排除合理怀疑适用的实务困境
(一)排除合理怀疑在诉讼中的适用不明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明文规定,表述为“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是否能对单一的证据提出合理怀疑,以及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是否影响其证明力,这些问题都没有详细规定,使得审判者适用起来有所困惑。就连判例法国家代表——英国司法界也承认对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感到厌恶,认为它太容易使陪审团在定罪时不知所措”。[1]
在一些证据证明力不强,证据链较为松散的刑事案件中,某些定罪证据本身就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意义,如果认可了此类证据具备证明力,则相当于直接认可了这些证据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指向变为了控方所指控的单一指向,因此,合理怀疑适用的界定不清,使得控辩双方围绕合理怀疑来提出不同意见时容易产生拖沓和滞后,在质证阶段得不到效益发挥的最大化,减损了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二)合理怀疑在诉讼中的“不予回应”
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案件中,存在之前审理过程中没有明确回应的合理怀疑,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成了改判的依据和理由。许多一审程序中,控方往往无视辩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或者不认为辩方所提出的怀疑事项具有充分、合理的依据,从而否认其具有影响事实认定的作用力。如今,大量的基层案件并不一定具有充绝对的证据优势,由于可能影响审判的流畅运行,审判人员在面对合理怀疑回应时就会产生消极的应对心理。
(三)合理怀疑在诉讼中的“不予承认”
由于受到我国刑事司法技术的限制,侦查机关在许多的案件得不到十分有利的关键性证据,而随着刑事诉讼法律的完善,有专门知识的人和专家证人、专家鉴定人在司法鉴定和证据证明力上的作用也愈发强大,从而使得辩方在一些科学含量高、技术争议大的证据或事实推论上有了能与控方相抗衡的实力。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操作问题,使得传统的办案手段、方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而对于新出现的关键性证据博弈,控方往往应对不足,或者难以用充分的科学依据得出排他性的结论。对此,控方的应对方式往往是机械重复自身已经掌握的相关证据,自说自话的强调自己论证的证据链条。尽管此类应对方式对于保障个案的实质公正不一定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实务中,诉讼程序中如果缺乏对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进行充分的说理释疑,往往会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大众的热烈争议,对国家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说服力产生不利后果,显然也不利于法治社会的长远发展。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建议
(一)针对证据和事实的双重怀疑
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证据的排除认定主要是非法证据排除,而随着法制化的进步,直接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变得相当困难,隐性的非法证据在庭审中难以排除,审判结果就可能出现错误。实务中,一方面是排除非法证据的功能不足;另一方面是除了非法证据以外还存在其他单一证明力不强或者存疑的证据。在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综合全案,排除合理怀疑”,是建立在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要求之后的。因此,中国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判断规则的定位,与英美法和日本法以其为证明标准的主要表达方式存在区别。[2]因此,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应当追加对于证据本身的提出合理怀疑的权力,使得在证据和由证据构成的事实两个维度对于判决中的排他性结果起到最大限度的还原。
(二)确立必须回应的相关保障制度
对于最为普遍的合理怀疑应对模式,不予回应存在于大量的一审案件以及部分二审案件之中,在以往的办案套路中,控方在庭审之前的准备主要是在对自身证据链的固化和补强,以此形成完整的证明思路,达到证明被告有罪的效果,一般不会对可能存在疑点进行答疑或者解释、思考。因此在庭审之中突遇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控方的应对技巧往往是强调所掌握证据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以此无视或者否认合理怀疑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从辩论技巧的角度来看,片面强调自身论点的有效性,从来都不是对疑点提出的有力还击,也并没有从正面消除可能存在的疑虑。因此,在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之下,控方应当正确认识到合理怀疑的存在,并且应当为排除合理怀疑负有相关释疑的证明责任。正因为排除合理怀疑是控方在控诉论证过程的最后环节,所以控方更应该正面应对并用相关的证据或推论排除合理怀疑,从而形成对被告有罪论证的闭环,达到与客观证据链相互印证的证明效果。
(三)合法证据、瑕疵证据的合理性考量
目前我国的刑事办案流程中,对于搜集证据的合法程序存在许多规制盲区,在搜集的证据本身真实的情况下,程序瑕疵往往是可以补强的。而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程序瑕疵的证据,也可以产生合理怀疑。而不局限于“综合全案”的前提要求。因此,在这种合理怀疑规则的框架下,办案人员显然需要更加重视证据的合法来源程序,提升办案的法制意识,从而避免可能产生的排除合理怀疑,而影响到证明作用。
而对于合法搜集的证据的本身,也应当赋予排除合理怀疑的权利,即在排除非法证据以后,具有证明力的合法证据也有可能存在偶然性与特殊性。客观的证据是不能改变的,且往往不会直接明确的指向待证事实,很多都需要主观的推测与论证,以及审判者最后的认定,保留对客观证据的合理怀疑,是对公正事实的保障与监督,也是文明法治社会的正确司法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