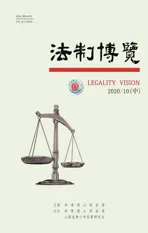刑事司法中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思考*
2020-11-30席珺
席 珺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被害人谅解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比例相当高,除了存在被害人谅解主体不确定、适用的阶段不确定、适用案件范围不明确等问题,笔者通过查阅无讼,发现在个别被害人谅解的案件中存在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情形①,被告人李某某赔偿被害人张某2损失2万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后被害人声称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人的行为不予谅解。上诉人(即被告人李某某)上诉理由称:民事部分已赔偿,并取得谅解,被害人反悔说谅解书是在其不清醒时其父让其签的字,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没有证据证实其是在不清醒时签的,原判量刑重,请求二审法院对该刑事谅解书及赔偿协议予以认定,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笔者以此案为例,分析实务中被害人谅解反悔的原因、对被害人谅解的自愿性审查以及被害人反悔后的具体操作展开简要分析。
一、被害人反悔的原因
被害人谅解必须基于自愿,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司法实务中,加害人为得到从轻量刑,通过对被害人恐吓、威胁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出具谅解书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案被害人称谅解书是在其不清醒时其父让其签的字,但没有向法庭提供有力证据,只有庭审中出示的证人李某1的询问笔录提到,加害人逼着李某1的父亲到被害人家里,跪在被害人家人面前,说如果不签字谅解的话,加害人李某某就会打李某1。
若本案被害人确实遭受来自加害人方的威胁逼迫出具谅解书,那么被害人谅解的过程就违背了自愿原则,对被害人形成二次伤害,有违该制度的初衷。然而要想说服法官认定谅解受到胁迫,是在非自愿情形下做出的,被害人需要提供有力证据佐证,否则,法官会推定被害人谅解的合法性。
二、对被害人谅解自愿性审查的必要性
实践中,受办案压力、司法工作人员配备不足、节约司法资源等客观因素制约,当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谅解书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大概率地推断被害人是出于自愿而作出的,此时对被害人谅解仅做形式审查。如果相关机关不对被害人谅解的自愿性进行核实,不仅会助长加害人及其家属为了获取谅解书而不择手段的风气,同时会让公众产生被害人谅解就是“花钱买刑”的错误认识,容易对法律的公平正义产生质疑。
具体而言,应当区分不同阶段对被害人谅解进行实质审查。
第一,侦查阶段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检察机关应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责[1],对于侦查机关提交的书面资料进行审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被害人的询问,了解被害人作出谅解时的客观情况,以此判断被害人作出谅解是否出于自愿,意思表示真实与否。
第二,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协议,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应区别是在检察院主持下达成的谅解还是被害人与加害人私下达成的谅解。若是在检察院主持下达成谅解,检察工作人员应告知被害人如下内容:谅解应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出具谅解书的意义。充分询问被害人是否自愿后由双方就赔偿数额、谅解的内容展开协商,通过参与被害人和加害人协商的过程,检察工作人员观察被害人的表情、聆听被害人的表述,据此可判断出被害人谅解是否受到威逼胁迫。检察院将此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留存,提起公诉时一并提交法院。
对于侦查卷中的被害人谅解书,检察机关不能推定被害人是在自愿基础上作出的谅解,要积极与被害人及其家属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保证谅解书是他们的真实意思。[2]
第三,审判阶段被告人向法庭提交被害人谅解,法官应询问被害人意见,当庭质证,不能只通过纸面材料就认定被害人的谅解一定是自愿的,进而加快审理,作出判决。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同样享有监督权,若发现审判阶段提交被害人谅解的,应督促法院就被害人谅解的自愿性进行实质审查,以防出现被害人反悔的情形。
三、本案中,法院对被害人谅解的反悔处理之分析
本案中,针对被害人谅解后的反悔,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请求法院对该刑事谅解书予以认定。依此请求,二审法院应就刑事谅解书的内容、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而本案判决中未体现法院对于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该请求的处理,只在“本院认为”中表述“案发后,上诉人李某某家属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通过判决书的表述,可推定法院认可了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同时认为可酌情从轻处罚,至于被害人谅解是否出于自愿、被害人对谅解反悔以及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提出由法院对刑事谅解书予以认定的请求均未涉及。
法院如此判决的问题有二:第一,对于上诉人的请求未做处理。即使法院出于现行法律缺乏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操作规范而难以对本案的被害人谅解予以认定[3],但仍应在判决书中阐明不予认定的理由,如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就像民事案件中,原告起诉的事由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法院在裁决书中需就此阐明理由,而非绕开焦点、置之不理。第二,本案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的上诉理由称,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原判量刑重,请求从轻处罚。法院裁判说理部分,承认了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表明可以从轻处罚。这么来看,法院认可从轻量刑是因为赔偿,而非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本案中,加害人非法拘禁被害人后与同案犯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致被害人“身体体表损伤为轻伤一级、左手损伤为轻伤二级”,加害人理应为自己伤害被害人的行为负责,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因为加害人赔偿了被害人就理所应当获得从轻量刑,从轻的关键应是被害人是否原谅了加害人的犯罪行为。因此,判决书中对上诉人(即加害人李某某)请求认定刑事谅解书不予说明,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被害人谅解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通常处理方式。
四、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具体操作
处理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操作,应区分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完善刑事诉讼相关规定。首先要肯定的是被害人谅解加害人的权利,那么谅解后反悔也是被害人行使权利的一种体现。
第一,侦查阶段中被害人谅解后反悔,侦查机关应与被害人及其家属沟通,弄清被害人反悔的真正理由,倘若因为谅解违背自愿,那么谅解是无效的,当然可以反悔。如果被害人反悔是由于加害人只赔钱,没有真正忏悔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而反悔,此时侦查机关可从中调停,促成被害人谅解的实现。
第二,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反悔,检察机关同样应与被害人及其家属沟通,必要时积极介入,帮助被害人与加害人传递意见,促成被害人谅解的达成。
第三,案件进入审判阶段,被害人反悔的,对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讲,不能因为工作量增加,急于结案,一刀切的认定适用或不适用被害人谅解,反而应通过当庭质证,允许控辩被害人三方就被害人反悔发表各自意见,法官综合三方意见在判决书中应说明是否将被害人谅解作为从轻量刑的依据并阐明理由。
五、结语
被害人谅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操作差异较大,尤其在缺乏被害人谅解后反悔的具体操作规范时,相关机关多数采取回避态度,但是置之不理,问题仍存在,只有尽快规范被害人谅解的操作程序,才能使该制度发挥推进和谐社会进程的作用。
注释:
①案号(2018)晋08刑终1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