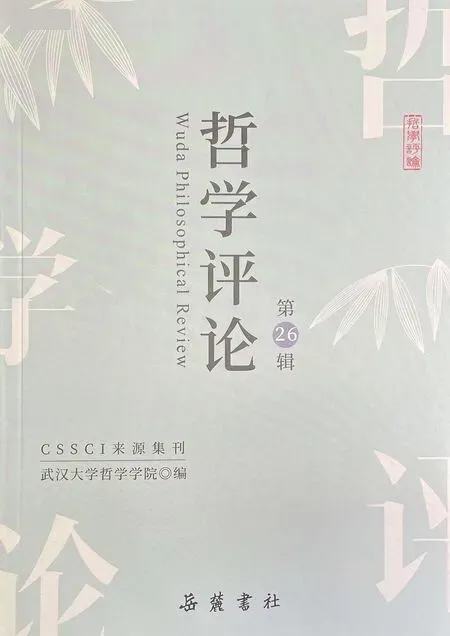认知归因视域下的运气概念及其哲学启示
2020-11-30黄俊维
黄俊维
运气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说明和理解某些事件的一个常见概念。偶尔买了一张彩票却中了大奖,通常被认为是行了好运;而各种天灾人祸的发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霉运。可见,“运气”常用于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分析行动成败的重要归因因素。
在哲学上,运气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早于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经分析运气、德性与个人幸福的关系,并认为运气是影响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1]Aristole. Nicomachean Ethics, R. Crisp(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18.;而在当代的哲学研究中也常常能见到分析和讨论各种由运气引起的哲学问题。例如,伦理学家普遍认为,运气不应该在一个道德评估中被考虑进去,但对很多有道德意义的行为的正确评估却会受到运气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所谓“道德运气”难题。[1]T. Nagel,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449—456.这一难题引申到关于自由与责任的讨论中,则会产生一个更为严重的悖论,从而侵蚀甚至瓦解自由与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得以确立的基础。类似地,认识论中也存在“认知运气问题”,即一个合理的知识理论应该把与知识不相容的运气排除在外。
在早期的相关讨论中,“运气”往往作为一种未定义的概念来使用,而鲜有关于运气概念的深入分析。这样的情况所带来的弊端十分明显:由于“运气”缺乏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概念,这使得在我们谈论“道德运气”“认知运气”时容易引起误解和混乱。因此,大约从 20 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哲学家开始重视对运气概念的分析,他们相继在以往关于运气的零散刻画中提取有启发性的观点,并且尝试提供一个关于运气本质的阐述。一般地,把运气理解成偶然性因素,或者把运气理解成不可控制的因素,是两类关于何谓运气的主要观点。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运气概念的刻画和使用仍然存在极大的分歧。
由于运气这一概念在使用上与人们对事件的归因具有紧密的联系,故此,本文尝试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来梳理“运气”概念在认知归因中是如何被使用的。从认知归因的视域上看,运气可以理解为基于不同的归因动机和目的而得到的某种归因因素或归因模式,它们可分别被称为“事件运气”与“行动者运气”,而哲学讨论中的两类主流的运气概念——偶然观和控制观——则刚好对应此两类运气。这样,“运气”一词实际上指代了两个并不一样的概念,而这一区分可以厘清众多哲学争论中究竟是在哪个意义下谈及“运气”,并有助于分析和消解部分由运气所引起的哲学难题。
一、运气理论:偶然观与控制观
对运气的其中一种主流理解是把它视为偶然性因素,即如果事件出现是碰巧的、不确定的、事前无法预知的,就认为是运气使然。这种运气观十分符合日常生活中使用运气一词的时候想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买彩票中大奖或者劫后余生都是一种运气,即认为这仅仅出于一种偶然、是不太容易发生的并且不可预期的,也无法用个人技能或者环境等因素所解释。这样一种关于运气的理解称为运气的偶然观。
运气的偶然观:一个事件的出现是一种运气,当且仅当这个事件的出现是偶然的。
如何理解运气概念中的“偶然”,存在两个较为重要的分支。其中一个是通过概率来表达运气概念中的偶然性,即当我们说某个事件基于运气而发生,就是指其发生的概率很小。这样,运气事件就是小概率事件,并且运气程度可以通过概率演算的方式来量化。[1]N. Rescher, Luck: the Brilliant Randomnes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p.31—3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运气中的偶然性不能用概率来刻画,而应该基于模态稳健性的角度来考虑,即事件发生存在运气,在于它不具有模态稳健性,也就是很容易不发生。[2]D. Pritchard, Epistemic Lu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8—133.
运气的偶然观存在不少批评,一些学者指出,偶然性对于运气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存在一些事件,例如即兴行动,尽管带有明显的偶然成分,但也难以认为是运气所致;而在另一些情景中,即使某个事件的发生是受人操纵的,或“冥冥中早已注定”,但依然可以被认为包含莫大的运气。[3]J. Lackey, “What Luck Is Not”,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2) , 2008, pp.255—267.
除了基于偶然性的解读,运气一词有时候也用于表达一种无可奈何、无法施加影响、只能听天由命的意思,即把运气视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因素。在道德运气的相关研究中,基本上就是在这意义下使用“运气”这个概念。例如,道德运气问题的提出者之一内格尔(Thomas Nagel)对道德运气的刻画如下:
“当一个行动的重要方面取决于行动者所不能控制的因素,但是它们却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时,它可以被称为道德运气。”[1]T. Nagel,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50.
可见,内格尔正是从“行动者对事件的控制”这个角度来刻画运气的。在往后的哲学争论中,有很多哲学家沿用内格尔这种关于运气的看法,形成“运气的(缺乏)控制观”。
运气的控制观:一个事件对于主体而言是运气出现的,当且仅当这个事件的出现不在主体的控制之中。
尽管这种对运气的刻画抓住了我们关于运气概念的一个重要直觉,但它也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例如,对于日出日落这种稳定发生的自然事件,尽管谁也无法控制,但也没什么运气可言。[2]A. Latus, “Constitutive Luck”, Metaphilosophy, 34(4) , 2003, pp.460—475.诚然,事件存在运气的确意味着缺乏控制,而事件缺乏控制却并不一定就是运气所致。可见,“控制”似乎是运气的一个必要因素,但并不足以充分地刻画何谓运气。
运气的偶然观和控制观是两类关于运气概念的主流观点,但它们各自都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和一系列的反例。有些学者尝试对这两个观点进行综合,或结合心理学中关于运气认知的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关于运气的某种综合理论。例如,要求同时满足偶然性和控制条件的“合取观”[3]E. Coffman, “Thinking about Luck”, Synthese, 158(3) , 2007, pp.385—398.、认为只需要满足其中之一的“析取观”[4]N. Levy, Hard Luck: How Luck Undermines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35.以及综合考虑常人认知习惯的“范型理论”[5]黄俊维、朱菁:《运气的当代哲学研究》,《哲学动态》2014年第7 期,第93—100页。等等。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何谓运气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更常用的是基于控制观的运气概念,而在认识论当中则是偶然观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状反映出,不同的运气观也许只是分别刻画了两个使用同一名称但内涵并不一致的概念,而并非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下文尝试通过引入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研究,寻找运气一词在概念和具体使用上如何对应于常人的认知归因,并由此区分出作为归因因素的、符合偶然观所刻画的“事件运气”,以及作为归因模式的、符合控制观所刻画的“行动者运气”。
二、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的研究始于海德(Fritz Heider)尝试从民俗心理学(naive psychology)的角度解释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出一个事件或行为背后的原因。[1]F.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p.1.经过数十年不断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关于个体如何阐释事件或行为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并广泛应用于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
海德认为,在大众的常识当中行动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体内部的原因,如天赋、技能、性格、情绪、态度等;另一个是外部的环境因素,如天气、外部压力等。归因理论的另一位奠基者韦纳(Bernard Weiner)则把海德关于大众归因的“个体—环境”二元对立纳入其归因理论之中,并称为“因素源(locus of causality)”维度,用于衡量因素究竟来自个体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此外,韦纳指出,即使因素源明确,如认为事件的出现主要是个体内部因素导致的,归因者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区分两类不同的因素。其中一种是天赋、技能等相对稳定的、在多次行动或在不同时期之下都不会产生显著变化的因素;另一类是努力、情绪等不稳定的因素,会在不同的行动或不同时期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同样地,对于外部条件亦是如此。以射手射箭为例,一些外部因素如箭靶的距离是相对稳定的,而在射箭的一刹那是否出现一阵强力的怪风则是不稳定的因素。故此,在“因素源”以外,“稳定性(stability)”也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归因维度。韦纳的归因理论提供了一个二维的、包含四类归因因素的分类系统[2]B. Weiner, I. H. Frieze, A. Kukla, L. Reed, S. Rest and R. M. Rosenbaum,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E. E. Jones, D. E. Kanouse, H. H. Kelley, R. E. Nisbett, S. Valins, and B. Weiner(Eds.) ,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2, pp.95—120.:
1.内在的、稳定的因素:天赋、技能、性格。
2.内在的、不稳定的因素:努力、情绪。
3.外在的、稳定的因素:环境、任务难度。
4.外在的、不稳定的因素:运气、偶然。
这个二维的归因理论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对归因因素的分类框架,它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对事情的归因倾向。例如,当一个技巧娴熟的射手射箭命中靶心时,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基于他射箭技能而产生的结果;如果一个对射箭一窍不通的人同样命中靶心,人们则会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归因理论的一个重要性在于,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些事件进行归因,在于需要理解、预测和改变世界:对事件的归因分析,可以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对未来相似事件是否发生的预期,以及形成在将来促成某类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行动方针。例如,一名球迷在观看球赛时,如果把某支球队获胜归因于球队的强劲实力(内在的、稳定的因素),那么这名球迷将会预期该球队在下一次比赛中仍然会获胜,也倾向于押注这支球队会取得不俗的成绩甚至夺得冠军。相反,如果把球队的获胜归因于对方守门员在比赛结束前的一个意外失误(外在的、不稳定因素),那么这名球迷并不会预期该球队能够在下一次比赛中顺利获胜,也不会下注在这支球队身上。
以上这种归因动机是要理解事件间的因果联系,对相似事件的发生与否及条件做出预期,并调整行动以提高自身的效益(认知的或实践的)。下面把这种归因动机及其所产生的归因倾向和归因模式统称为“基于事件的归因”,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事件进行因果分析,并希望通过理解事件和各种潜在因素的因果联系而获得知识并提高归因者的预测能力和实践效果。
然而,除了基于事件的归因,也存在另一个不以提高预测能力和实践效果为目的的归因活动。例如,家长会关心孩子某次考试成绩骤然下降并进行归因分析,如果家长最终发现原因在于孩子最近学习不用功(内在的、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很可能会进行斥责与教育,并加强对学习的管束;如果家长最终发现原因在于这次考试难度极大(外在的、稳定的因素),孩子的成绩排名其实并没有下降,那么自然不会去责怪孩子。
以上这种归因聚焦于行动者与其行动后果的因果关系,如行动者能否控制事件的出现、是行动者的什么因素产生了影响、行动者能否自主改变这种因素等等,并常常以此作为根据对行动者做出价值判断。下面把这种归因动机所产生的归因倾向和归因模式统称为“基于行动者的归因”。人们常常进行的各种关于他人是否获得成就、是否具有某种动机、是否应该对事件负有责任等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行动者的归因而做出的。同样地,人们在对自身行动后果的反思在很多时候也是基于行动者的归因,并且往往会对今后行动的期望、情绪、努力程度等产生很大的影响。[1]B. Weiner,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2(4) , 1985, pp.548—57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过程,也不代表归因者只会在具体的一次归因认知中选择其中一种。区分两类归因活动是要指出,由于存在不同的归因动机和目的,归因者会产生不同的归因倾向和形成不同的归因模式,这两类归因活动是其中两个典型。事实上,诸如“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就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归因而引起的一种认知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区分两类归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何谓运气,以及为什么存在两种不同的运气观。
三、事件运气与行动者运气
在经典的归因理论中,“运气”与“偶然”两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指的是一种外在的、不稳定的归因因素。并且,在相关的实验研究材料中常常是用基于概率或者不确定性的表达来指代运气。也就是说,大部分心理学家在归因理论的研究中默认采用了运气的偶然观,如果把事件的发生归于运气,即认为它的出现并非由稳定的环境因素所决定,行动者自身的影响也不重要。
同时,“偶然”这个因素在理解和预测事件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事件的出现主要归因于能力(内在的、稳定的),那自然可以预期事件在将来也会再次发生;如果归因于环境(外在的、稳定的),那么也可以预期在相似的环境下也能再次发生,但在不同的环境下则不能做出预测;如果归因于努力或态度(内在的、不稳定的),则可以预期行动者能够通过改变自身来影响事件是否出现。可是,如果归因于偶然(外在的、不稳定的),就意味着当前的事件的出现对未来事件不具有预测能力,毕竟没有稳定的环境因素或个体能力可以保证该事件的出现,而行动者也无法通过改变自身施加任何影响。
可见,偶然性这种外在的、不稳定的因素,是“基于事件的归因”中的一个重要的归因因素,因为把事件的出现归因于偶然,则意味着当下的信息不足以获得关于该事件的相关知识,也无法凭此对事件是否会再次出现进行预测。这样,运气的偶然观是以理解和预测事件这类认知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运气观,即把基于事件的归因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称为运气。而运气的存在意味着知识的缺乏,也意味着一种认知的风险。在这种解读下,“运气”是基于事件的归因中的一个归因因素,是事件本身的一个属性,以下把这种运气称为“事件运气”。
然而,同样的逻辑无法运用于运气的控制观之上。这是因为,把运气理解为缺乏控制显然无法与“理解和预测事件”很好地对应上。诚然,如果行动者能控制事件是否发生,固然可以很好地对类似事件的发生做出预测(因为他自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件是否出现),但即使行动者缺乏控制,事件也可以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日出日落”这个情境便是如此,并没有人能够控制天体运动,但我们依然认为明天的太阳会如常升起。这个常用于质疑“运气的控制观”的反例,实际上是表明“缺乏控制”在基于事件的归因中并不重要,它必须进一步划归到具体的某些归因因素,如稳定的环境或者偶然性当中,才能够做出有意义的理解和预测。
由此可见,从“行动者对事件的控制”这个角度去理解运气的方式无法在基于事件的归因中找到合适的理论位置。不过,这并非表明运气的控制观及其背后的理论直觉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在基于行动者的归因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基于行动者的归因是要理解行动者与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得到关于事件何以发生的因果解释。因此,从其动机而言,基于行动者的归因会以“与行动者是否相关”区分出两类归因因素,这也是早期归因理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以因素源为维度的因素分类的依据之一。毕竟,如果因素是在个人之外的,那么事件的发生就应该与行动者关系不大,反之行动者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地,各种内在因素也存在不同的属性,从而影响归因认知以及归因者的价值判断。例如,一个学生成绩很差,把它归因于糟糕的天赋或者归因于无心向学,其意义大相径庭。从老师或家长的角度看,如果归因于天赋,那么应该做出教学难度和任务的调整以适应学生本人;如果归因于无心向学,则更可能需要较强的教育管理或者进行心理咨询。从学生自己的角度,如果把坏成绩归因于天资不足,那么他可能会降低将来获得好成绩的期望,甚至自暴自弃;如果是归因于自己无心向学,那么未来可能会发奋图强,争取获得好成绩。
可见,基于行动者的归因敏感于因素源的区分,并进一步敏感于各种内在因素的区分,而不敏感于外在因素究竟还具有怎样的不同属性,如稳定的环境,或者仅仅是偶然。在这种对内在因素区分当中,如果仅采用二维理论中的“稳定性”维度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的归因倾向,例如心境、疲劳程度、努力三者都可以归类为内在的、不稳定因素,但其中“努力”与另外两者不一样,它是一个可以通过自主控制的因素。同样地,内在的、稳定的因素也存在这一种区分,例如懒惰和耐受力常常作为人格特质而被归为稳定的因素,但也同时被认为是可以由行动者所控制的,相对地,天赋则不是一个可控的因素。
因此,在后期的归因理论研究中,往往会再引入一个“可控性”(controllability)维度。显然地,如果一个内在因素是可控的,无论它是否稳定,归因者会更倾向于行动者对事件的出现负有责任,也更倾向于行动者应该根据事件的性质尽力地促成或阻止它,反之则没有这种态度的倾向。可见,基于行动者的归因敏感于一类归因模式,即促成事件出现的主要因素是否处于内在的、可控的维度下,而不关心具体究竟是由哪一个或者哪一类因素导致的。
这样,基于行动者的归因实际上可以很好地对应于运气的控制观。如果促成事件出现的主要因素并非处于内在的、可控的维度下,我们就说事件的出现对行动者而言是一种运气,可称之为“行动者运气”。
行动者运气并不是一个归因因素,而是行动者和事件之间的一个关系属性,并用于表达一个归因模式——事件并非行动者所能控制,它的发生不取决于内在的、可控的因素。基于行动者的归因则可以理解为一种鉴别事件和行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行动者运气”的认知活动。
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运气”一词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下被使用的,并可以对应于以下两个概念:
事件运气:事件的出现是偶然的。它是事件的属性,是解释和预测事件何以发生时所关注的一种归因因素。
行动者运气:行动者对事件的出现缺乏控制。它是行动者和事件的关系属性,是刻画行动者和事件关系的一种归因模式。
过往大部分关于运气概念的讨论中,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杂使用而不加区分,因而阻碍了对何谓运气以及运气相关的哲学讨论。例如,对运气偶然观的批评往往就是在行动者运气的概念下进行的。同样地,对运气控制观的指责则常常援引事件运气的情境作为反例。然而,从以上分析可知,即便偶然观和控制观在具体表达上存在缺陷,也不应该归责于它们无法满足另一个观点背后的理论直觉,因为它们是分别刻画了两个使用同一名称但内涵与外延并不一致的概念,而不是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理解。
下面以“自由意志的运气论证”和“认知运气问题”为例,展示以上的“运气”概念分析所能带来的哲学启示。
四、启示一:自由意志的运气论证
一般认为,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是相伴相生的: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自由的,那么他便需要对其行动后果负有道德责任;此外,也就意味着该行动处于非决定论世界之下。以上呈现的就是“意志自由论(1ibertarianism)”,是人们的理解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一个常见观点。然而,梅勒(Alfred R. Mele)指出,对运气的分析很可能会威胁到意志自由论。[1]A. Mele, Free Will and Lu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9.他的观点可以简单重构为如下的“运气论证”:
P1:行动者要对自由行动负有道德责任。
P2:存在一些自由行动的出现是运气所致的。
P3:如果一个行动的出现是运气所致的,那么行动者不对其负有道德责任。
C:存在一些行动,行动者既需要又不需要负有道德责任。
其中P1 是意志自由论的其中一个立场,即道德责任以自由意志为前提。P2 是非决定论立场的推论,因为如果行动是自由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些自由行动,在出现之前不可能从历史事件和自然定律当中得到预测,在这个意义上行动的出现就是一种运气。P3 要表达的是“应该蕴涵能够(ought imples can)”,即行动者只应该为本人所能控制的事情负责这一伦理学原则。如果承认三个前提,梅勒指出,则会得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不考虑其他更为细致的分析,运气论证在关于运气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它把事件运气和行动者运气当成是同一回事:P2 中指出自由行动是“在出现之前不可能从历史事件和自然定律当中得到预测”,这显然是一种事件运气的表达,但其背后的理由是该行动受自由意志所掌控,这恰好拒斥了行动者运气的存在;而P3 中的运气则明显是行动者运气。这样,如果对P2 和P3 中的“运气”作进一步阐释,那么这两个前提不可能同时成立,也就无法得到其结论。运气论证之所以看上去是合理的,是因为在自由意志和非决定论世界的论述中采用“事件运气”的意义来使用运气一词,但在关于道德责任问题上却换成了“行动者运气”。从基于认知归因的运气概念分析可得,这是两个内涵、外延和使用习惯也不尽相同的概念,不应该混为一谈。
事实上,运气论证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一般来说,科学家可以用化学的概念、术语和理论来分析生物学问题,但不会用生物学来分析化学,这是因为化学是生物学的底层理论。类似地,哲学论证也需要用“基础的”“底层的”概念来分析上层概念,而不能反过来。然而,运气论证的攻击对象是形而上学范畴的“自由意志”和“意志自由论”,而用于分析它的“运气”却是综合了形而上学(控制)、概率论(偶然性)、认知科学(归因)等概念资源而得到的下位概念,在论证规范上不能对自由意志形成概念上的约束。由此,我们对运气的理解,才应该敏感于包括自由意志在内的形而上学概念。例如,若承认运气论证的逻辑是合理的,应当反思的是论证中的运气概念是否有误,或者它们是否内涵一致。这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推论,例如P2 中指代偶然性的“运气”和P3 中指代缺乏控制的“运气”不应该是同一类东西(否则自由意志就出问题了),这就跟上述基于认知归因的运气概念分析殊途同归了。
五、启示二:认知运气问题
自盖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面世以后,运气在知识理论研究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一个主流的认识论共识是:对知识本性的理解应当充分体现出知识与运气关系,并为知识概念提供一个(或一组)合理的反运气条件。不少学者如扎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等指出,这是近几十年来学界对盖梯尔问题的分析所带来的认识论洞见[1]L. Zagzebski, “The Inescapability of Gettier Problem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4(174) , 1994, pp.65—73.,目前一般称为“认知运气问题”。
但是,与知识不相容的“认知运气”究竟属于事件运气还是行动者运气?这个问题显然十分关键,但在早期的认识论争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要害。例如,昂格尔(Peter Unger)在盖梯尔问题出现后不久,便敏锐地意识到运气对理解知识具有极为重要作用,认为知识“不能仅仅由于运气为真”。[2]P. Unger, “An Analysis of Factu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8, 65(6) , pp.157—170.但是,昂格尔笔下的运气常常与“意外”一词混用,既可以指代获得真信念的偶然性,也可以指代信念为真并不在认知主体的控制之下。这样,究竟与知识不相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在概念上依然十分模糊。
约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认识论学者尝试对运气本性进行分析,并以此推进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事实上,两个不同的运气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可归属于两类不同的认识论进路:
1.导真性(truth-conduciveness)进路:知识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可靠的或是模态稳健的。这一进路强调知识形成机制的非偶然性,认为与知识不相容的是事件运气。其中常见的就是过程可靠主义和反运气认识论。
2.知识的荣膺观(the deserving credit view of knowledge):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是因为认知能力而为真的信念。这一进路强调认知能力对真信念的贡献,认为与知识不相容的是行动者运气。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德性认识论。
大部分知识理论对认知运气的处理方案都可以基于以上框架来理解。不同理论的支持者往往会指出对方关于认知运气的理解有误,或构造反例来表明对方无法排除“真正的运气”。但是,这种争论方式似乎前景黯淡:如果承认“运气”具有两个哲学蕴含明显不同的概念,它们的相互指责就是无效的。毕竟,排除事件运气的条件当然无法排除行动者运气,反之亦然。
从认知归因的视域下的运气概念出发,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其一,对认知运气问题的有效推进,不应追求对“认知运气”的概念形成共识。因为不同进路所关注的运气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个共识是无法达成的。
其二,“运气”在使用上是模糊的、混杂的而且充满认知偏差,对运气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解释和个人经验,它不应作为支撑更精确的概念(例如“知识”)的基础术语。
其三,从两类运气概念的共性出发,可以发现,知识的无运气论题其实是为知识概念引入一种敏感于信念归因的条件。这个与传统知识概念强调辩护(justification)基础是截然不同的。进一步说,是对知识本性的理解从知识宣称(或作信念辩护)转移到知识获取与维持(或作信念形成)上。
最后,从知识获取与维持的角度上看,排除运气要追求的其实是排除信念为假的风险,从而保证对知识的采信是安全的。这样,认知运气问题的本质其实是“认知风险问题”,两大进路的差异无非在于,导真性进路主张从隔离风险源(外部的、不稳定因素)的角度来维护信念安全,荣膺观则主张合格的知识需要基于内部掌控(内部的、可控的模式)来控制风险。
六、结语
本文论证存在两类不同的“运气”,并不是指运气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方式或理解角度,而是有两个内涵和外延均不一样的“概念”共用了“运气”一词。过往众多涉及运气的哲学讨论中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澄清能产生一些有益的哲学启示。例如,在自由意志的运气论证中,对意志自由论的攻击源于把事件运气和行动者运气视为同一类东西,它实际上并不构成关于自由意志和意志自由论的威胁。在认知运气问题上,不同运气观的支持者不应追求对运气概念形成一致意见,而应该进一步深入讨论不同的运气观实际上对知识提供了何种规范。这个思路的结果很可能是:认知运气本身并不重要,如何保证知识获取和维持的安全才是要害所在。
在认知归因的视域下看,“运气”一词可以分别指代作为归因因素的“事件运气”或作为归因模式的“行动者运气”。这表明,运气的偶然观和运气的控制观其实并非刻画同一个概念,两个观点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刻画了不同的东西。因此,在涉及运气的哲学争论中,明确“运气”的具体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两个概念在分析和论证中的混淆,也能削弱不同“运气观”之争对具体哲学问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