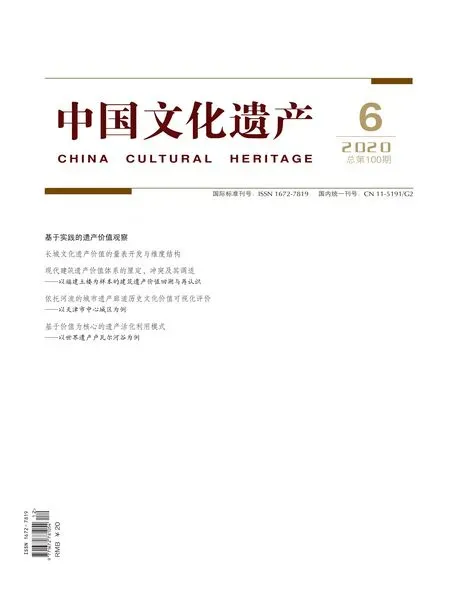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中国实践
2020-11-30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
魏 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引言
简单地说,水下文化遗产是指部分或者全部位于现代海洋或者内陆水体中,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且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在人类濒水生活和掌握航行技能的久远历史中,因人类活动或自然变迁而形成的水下文化遗产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然而,受人类自身水下活动能力的限制,除偶然的发现外,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些珍贵水下文化遗产所知甚少。1940年代之后,随着水肺潜水装备以及声呐等遥感探测技术的发明和普及,水底世界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大量的水下文物和水底遗址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何保护和管理这些水下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而水下文化遗产及其相关保护、管理理念的出现更是只有短短数十年的时间。现有资料显示,水下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从“文化财产”向“文化遗产”转变和从“考古遗址”向“水下文物”转变两个过程交互影响的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物古迹保护的意识在欧美地区迅速增强,一些国家制订了专门的法律法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陆续制定了多个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或宪章①例如1954年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海牙公约)》、1964年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等。。在这些文件中,“文化财产”是界定文物古迹的标准表述,其内涵无一例外都是较为宽泛的,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文物所在环境甚至保管这些文物的场所都被囊括进来。虽然早在《海牙公约》的文本中已使用了“文化遗产”一词,不过它与“文化财产”之间的关系及界限并不明确。1970年代,“文化财产”一词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学者们认为这一术语中含蓄地强调了文化物品的经济属性,进而提议用中性并具有传承含义的“文化遗产”一词进行替代。1972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明确将“文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的国际性文件[1]。同时,水下文物也从考古遗址中逐渐分离出来,保护“区域”或“海洋”中的“考古和历史文物”②例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第149条、第303条之表述。开始成为考古学和海洋法学关注的问题。人们认识到,对水底世界开发活动的增强一方面加深了对各类水下遗迹、遗物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它们被人为破坏的危险。在文化遗产概念已成共识的情况下,把水下遗迹和遗物独立于陆上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1980年代之后,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国际文件陆续出台,如1985年欧洲理事会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欧洲公约》(草案)、1994年国际法协会(ILA)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草案)和199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国际宪章》等。虽然这些文件的制订者是区域国际组织甚至非政府组织,文件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后来都成为制订《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蓝本。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以下简称《水下公约》)。《水下公约》不仅为缔约国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最低标准,而且明确了保护公共利益、原址保护、禁止商业性开发、国际合作和尊重国际法现状等基本原则。截至2019年4月,已有61个国家批准并成为《水下公约》的缔约国。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超过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和漫长的大陆海岸线。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华夏先民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了海洋探索活动。《汉书·地理志》中更是明确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时连接华南和东南亚、南亚港口的海上贸易路线。隋唐以降,随着造船和航运技术的日益成熟,海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已将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北岸、西岸的国家、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繁荣的海洋和内陆水域人类活动在我国现有海洋及内陆水体中留存下了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虽然我国目前不是《水下公约》的缔约国,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与《水下公约》所倡导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在遵循共性的同时,文物行政部门和遗产保护工作者也不断探索创新,总结出不少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特征及具体国情相适应的保护和管理方法[2]。
一、发展历程
1980年代,由于欧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不断加强,国际上水下文物的商业打捞和盗掘活动向加勒比海、南中国海等海域转移,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劫掠。为应对南中国海海域文化遗产面临的不法破坏,我国文物行政部门当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其一是通过立法手段规范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广泛使用的“文化遗产”概念,对我国也产生了影响。虽然我国文物行政部门直到2019年仍习惯用“水下文物”来指称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人类水下文化遗产,但两者的差别细微,如2009年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就明确指出“水下文物,是指遗存于下列水域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水下条例》)正式颁布,而在此之前我国的文物法律法规中,只有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条例》中简单涉及内水、领海中文物的国家所有权和发现不报的罚则。虽然《水下条例》正文只有13条,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文件,内容涵盖保护和管理的几乎所有方面,特别是在管辖权、所有权制度方面的规定与欧美国家制定的同类保护制度相比也毫不落后[3]。实践证明,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护,对于推进水下遗产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二是开始组建水下考古机构和培训水下考古人员④1987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负责统筹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同年底,我国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此后20余年间,该研究室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统筹协调全国的水下考古和水下文物保护项目。参见: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这一时期,国家文物行政部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派出考古人员赴荷兰、日本等地学习水下考古,并邀请澳大利亚专家来国内联合举办培训班,引入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水下考古理论、技术和方法。二十年间逐渐在沿海省份建立起数支水下考古和文物保护的专业队伍⑤1989—2018年间,国家文物局先后委托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8期水下考古培训班,加上广东省2005年举办的省级水下考古培训班,全国共培养了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百余名。。目前,我国沿海省份基本都已建成各自的水下考古或水下遗产保护机构,多数具有独立进行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勘探、登录和保护的能力。国家层面上,2009年成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了全国范围内水下文化遗产的组织协调、交流培训和规划实施等工作[4],2012年,获中编办批准更名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原有职能基础上又赋予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审核、装备技术研发管理、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新任务[5]。该中心成立后,机构和功能迅速完善,并先后建立了宁波、青岛、武汉、福建和南海等五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地方基地。
总体上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以1987年和2009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87年之前,虽有水下文化遗产的零星发现,但由于机构队伍缺乏、设备技术空白以及缺乏法律保障等原因,属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空白期;1987年至2008年,各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逐步建立,专业队伍和人员不断成长,专门法规和文件开始制定颁布,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期;2009年,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进入发展期。近十年来,除机构、人才队伍、装备和法律规定持续完善外,还在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理念、技术、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方法。
二、中国实践
《水下公约》是当前国际上最获广泛认可的有关水下文化遗产的多边法律文件。该公约将原址保护作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首选原则,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首选原则”并不等于“唯一选择”[6]。《水下公约》同样鼓励各国“根据各自的能力,运用各自能用的最佳的可行手段”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我国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水下文化遗产的现存状况和保护手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应根据“不同类型遗产所具有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遗产所出现的危害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适用性保护方法、技术以及管理措施”[7]。
(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类型主要包括沉船遗址、城址与聚落、其他水下古代遗迹等。根据这些文化遗产的不同特性和构成特点,保护模式也应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沉船遗址多根据其保存情况和遗产价值,选择采用考古发掘或者原址保护的方式;对于体积巨大的城址、聚落等,保存状况不佳或者受自然和人为因素潜在破坏风险低的古遗存,基本都会采用原址保护的做法。
1.原址保护
由于水下文化遗产类型多、数量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针对性的保护模式和保护技术,原址保护是其中最常见的保护模式。欧洲国家曾在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技术方面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例如采用“沙袋、聚丙烯网、特效人工溶液、沙质沉积物、路障、人造水草和地质纤维覆盖物”等[8]。这些保护技术各有优势和不足,具体采用何种技术应基于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在最佳保护的原则下进行选择。白鹤梁遗址的保护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利用的代表性项目。该遗址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中的一条江心石梁,其上保留有唐朝广德元年(763年)以来的165段历代文字题刻和72个枯水年份水位记录。为避免这处重要水下文化遗产因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而被永久淹没,文物部门提出了“原址建馆、原环境保护、原状态展示”的保护思路,并为其专门建设了一座水下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现在,观众可从岸上陈列馆经交通廊道进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并透过观察窗直接观赏水文题刻[9]。白鹤梁遗址的保护项目是对“原址保护”理念的创造性发展,不仅完成了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有效整体保护,同时实现了可持续利用,让观众即使不掌握任何潜水技术也能近距离欣赏这处位于水下38米的文化遗产。当然,这种保护展示方式投入巨大,需要文物保护专家审慎评估究竟哪些水下文化遗产值得如此去做。21世纪的实践中,我国的文物机构也进行了其他的尝试。发现于广东三点金海域的“南澳I号”是一条明代木质沉船,考古机构在以考古方式提取了全部船载物后,采用了以钢管焊接的金属保护罩覆盖并原址保存的做法[10]。为防止原址保护的水下文化遗产遭受非法劫掠或者人为破坏,还对“南澳I号”和福建漳州“半洋礁一号”两艘沉船遗址实行了安全监控。前者采用了岸基的雷达监控技术;后者则运用了3G无线海上监控系统,实现文物部门与部队、边防武警的联防联动[11]。当然,水下文化遗产及其保存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并没有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保护方式。例如文物工作者采用牺牲阳极保护法来防止“南澳I号”沉船保护金属框架的锈蚀,2012—2016年间的潜水调查回访表明,沉船船体受到有效保护,金属框架也没有出现锈蚀和片状剥落现象。然而,当同样的方法运用于甲午沉舰“致远舰”和“经远舰”保护时,效果却并不理想[12]。
2.迁移保护
“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项目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迁移保护。“南海I号”是发现于广东海域的一条南宋时期沉船,船体和船货保存较好。沉船距离陆地较远,存在被盗捞的巨大风险,而且沉船所在海域海况复杂、水体能见度为零,常规的水下发掘方法无法科学地获取考古信息。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决定采用整体打捞方案:也就是将沉船及其周围泥沙按原状固定在一个预制的钢结构沉箱内,然后将沉箱打捞出水并拉移到专为沉船设计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进行后期发掘和保护。迁移保护方法在陆地文化遗产,特别是古建筑、古墓葬等的保护中并不少见。国际上对于沉船等水下文化遗产进行迁移保护也不乏实例,亚洲商船新安沉船、华光礁一号沉船是通过水下考古方式打捞船货并在水下拆卸船体,然后在博物馆中进行修复保护;欧洲战舰瓦萨号、玛丽罗斯号则是在提取船上物品后,采用钢缆或者金属框架将船体打捞出水。但是世界范围内迄今还没有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能像“南海I号”项目这样采用“边发掘、边展示、边保护”的策略,不仅能在完全可控的人工环境中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细考古作业,出水文物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观众还能亲眼看到考古人员的现场发掘。该项目在完成考古与保护工作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水下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展示。“南海I号”沉船的这种模式虽然对水下遗产的存在环境、使用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投入有较高要求,不过对于受破坏风险较高的重要水下文化遗产而言,无疑是值得考虑的可行方式。目前,上海崇明岛附近发现的“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正在进行以类似方式整体迁移保护的可行性研究。
3.考古发掘
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也是我国文物机构较多采用的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具有较高历史、艺术或者科学价值,然而又不具备原址保护条件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从1991年起,我国文物行政部门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的沉船发掘项目,包括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13]、浙江宁波渔山岛“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14]、福建连江“白礁I号”宋元沉船、平潭“碗礁I号”清代沉船、“大练岛I号”元代沉船[15]、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16]、海南西沙“华光礁I号”宋代沉船等。水下沉船遗址经过考古发掘,提取船载文物后,对于船体的保护方式会视保存情况及未来保存展示条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南澳I号”沉船那样进行原址保护;二是如“小白礁一号”“华光礁I号”沉船那样在水下对船体分解后提取到陆上文物保护和展示机构进行保护、修复。
水下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特定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进行针对性的评估和研究。也就是说,首先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考古调查或勘探,然后根据考古和历史资料对其进行重要性、易损性和稳定性评估,并结合其现存环境、安保压力、资金投入以及后期保存保护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
(二)水下文化遗产的管理方法
按照文物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国实行不可移动文物的登录和分级保护管理制度,水下文化遗产的管理实践亦在此框架下开展。
1.水下文化遗产登录与分级保护制度建设
虽然《水下条例》第5条规定了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全国或者省级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然而,囿于水下考古机构和队伍建设不足、水下文化遗产家底不清、价值评估缺失等方面的限制,其后近10多年时间里该条款在我国并未真正落实。2006年海南省的北礁沉船遗址成为最早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水下文化遗产。1990年代后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牵头在福建、广东的沿海及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了有计划的水下文物调查,获取了一批水下遗址及文物点线索。在2007—2011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水下文物资源调查被首次纳入普查目标,除东部沿海省份外,一些内陆省份也把内河、内湖、运河和水库等水域纳入调查范围,全国共登录并公布了100余处水下文化遗产点。在此期间,一些省份陆续将重要的水下文化遗产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海南省于2009年公布的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就列入了华光礁沉船遗址、南沙洲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玉琢礁沉船遗址、浪花礁沉船遗址等水下文化遗产;2011年浙江省公布的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也有千岛湖的狮城水下古城。
此外,建立水下文物保护区也从规定变成了实践。2012年,海南省提出在西沙群岛海域划定北礁、华光礁、玉琢礁、永乐礁四个文物保护区,并与公安部门合作构建海上监管平台的工作设想。2015年,广东省成为国内首个设立水下文物保护区的省份,公布了第一批2处水下文物保护区,即“南海I号”水下文物保护区和“南澳I号”水下文物保护区⑥两处水下文物保护区分别覆盖以南海I号和南澳I号沉船遗址为中心,半径500米和800米的圆形区域。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并公布第八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一批广东省水下文物保护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2015]343号)[EB/OL].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4/post_144512.html#7.[17]。与欧美国家实行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实践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初步,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如澳大利亚在21世纪初已登录5000多处受保护的沉船遗址,并划定了13个联邦保护区和9个州保护区。这些保护区的位置被标注在海图上,一般覆盖了以遗址为中心的半径500米的范围[18]。
2.法律体系建设
《水下条例》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首部专门法规,自1989年颁布后对于指导和规范全国水下考古和遗产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国务院只在2011年对该条例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的个别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保护理念的更新,迫切需要开展《水下条例》内容的进一步优化完善和修订。2011至2016年,国务院连续6年将该条例的修订列为“需要积极研究论证的项目”。2019年,国务院又将其纳入“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2018和2019年,国家文物局和司法部还分别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1989年的《水下条例》相比,本次修订草案增加了禁止商业打捞、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程、水下文物保护执法和利用等新内容。不过,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其在定义、管辖权、部分类型的水下文化遗产法律地位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尚有改进空间[20]。除国家层面外,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加快了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地方立法建设,如2008年颁布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中有两条专门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2009年颁布的《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三章“水下文物的保护”的5条规定,对辖区内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责任、方式和处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明确。此外,海南省、福建省福州市也曾启动过地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立法的相关前期工作。
3.国家主导的水下文化遗产管理体系建设
《水下公约》第22条明确了各国政府在水下文化遗产管理方面的主体责任,提出“设立主管机构”负责“水下文化遗产目录的编制、保存和更新工作,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保存、展出和管理,并开展有关的科研和教育活动”。虽然我国尚未加入该公约,但已设立了不同层级的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和专门机构,而且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国家主导、地方支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水下文化遗产管理体系[19]。“国家主导”不只表现为中央政府给予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政策、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也表现在国家级水下遗产保护机构组织全国水下考古工作、建立地方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研发和制造考古船等大型专用装备等方面;“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具有多层次、多部门、分散性的特点[21]。海洋执法和海域管理涉及不同的部门,水下文化保护和管理也必然关乎相关部门的相互协调配合。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和积极性,避免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责权不明确、部门诉求冲突等被动局面。2011至2012年间,国家、地方的文物部门和海洋管理部门通过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方式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专项联合行动,在部门协调配合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以广东为例,文物部门和海洋管理部门的合作不仅包括了联合执法、打击文物犯罪、对管辖海域内的9片水下文化遗产分布密集区进行重点巡查,还涵盖了加强专业研究、人才培训和海洋文化领域合作等方面内容。
三、几点建议
虽然30年来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能在技术、方法上有所创新突破,并逐渐摸索出不少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陆上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相比,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根据当前保护和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文物行政部门未来可尝试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基础工作力度,包括尽快建立水下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登录与价值评估体系,完善水下文化遗产立法和制度建设,大力推进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和保护区制度建设,以及加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人才队伍建设等。虽然我国已经开展了数次水下文化遗产的专项调查,但发现和登陆的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仍然相当有限。与澳大利亚、法国等水下遗产登录数量已超过5000处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工作仍有明显差距。在我国,即使水下文化遗产登录数量最多的海南省,也不过百余处遗址,这种状况与我国广阔的内陆水体和管辖海域面积以及历史上通过河流、海洋进行的频繁涉水活动很不匹配。在已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划定为水下文物保护区的数量比例极低。限于机构、经费、专业人员和重视程度不足等原因,不少水下文化遗产甚至连最基本的保护都做不到。各级文物部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时,可考虑主动纳入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人才和队伍建设、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专项调查、建立健全水下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等内容,进一步强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强基础、补短板、亮特色”等工作。国家的主导性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特色,在此基础上可按照分级管理和行政事权划分的相关规定,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鼓励地方根据自身特色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尝试。
二是继续创新保护管理方法,包括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提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水平。比如通过设立水下文化遗产公园、建设水下文化遗产径和水下遗址博物馆、开展虚拟展示等方式推动水下文化遗产教育展示模式更新,通过遥感和互联网技术促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监控体系的建立,尝试进行水下文化遗产的认养和义务监察员,以及制订科学的保护模式和保护效果评价政策等。美国佛罗里达州从1980年代开始,为辖区内的水下沉船和其他历史遗址划定了11处水下考古保存区,并开辟出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水下公园[22]。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潜水进入水下公园,也可登录专门网站进行虚拟参观。欧洲的意大利、克罗地亚、法国等也有相似的实践,这些做法都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虽然我国的相关行政部门也曾提出过建设“海洋历史文化遗址公园”或者“水下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议,但截至当前尚无任何开展此类工作的计划和行动。希望正在征求意见的《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完成修订并公布实施后,文物行政部门能尽快将相关内容落到实处。
三是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包括招募志愿者参与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发掘工作并逐步完善对这些志愿者的培训机制;加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开放部分水下文化遗产供公众了解和近距离接触;建立奖励制度,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政府主动报告在生产、科研和休闲活动中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线索,对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同时,通过将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与博物馆展示、数字化展示、公共空间展示相结合的方式[23],提升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认知,让水下文化遗产在公众心中变成“我们的遗产”,让文物保护真正变成公众的一种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