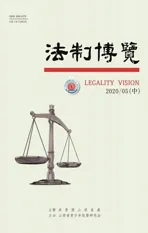中西刑法思想史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探索
2020-11-30
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一、中西共犯体系的不同起源
在共犯制度发展中,将共同犯罪区分为正犯和共犯的真实存因在于区分实行犯和非实行犯。欧洲大陆的共犯理论也深受中世纪欧洲大陆将世俗政权重心放在有无实施犯罪行为和造成的犯罪结果之上的影响,在刑罚中实行行为人甚重于未实行行为人。然而对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加以区分方法,则应归于意大利中世纪法学注释罗马法的成果。德国和日本的正犯、共犯理论最初追随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但经过不断的实践可以窥察出,有时候教唆犯、帮助犯的行为往往更加具有社会危害性,以致后来对犯罪问题探讨一般根据行为的实质,对于构成要件起到主要作用的称为正犯,其他辅助性的称为共犯,逐渐走向正犯“主犯化”。
以《德国刑法典》为例,从正犯、共犯区分制共犯体系上来讲,共犯也就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到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根据犯罪情况的不同,在量刑的过程中,一般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刑罚相较于正犯较轻;在《意大利刑法典》中,实行单一制共犯体系,对正犯共犯并不加以区分,只要实施共同犯罪,即统一按照正犯的刑罚量刑。探索大陆法系共犯体制的历史进程,单一制共犯体系则实为抒解在区分制共犯模式中量刑不均衡之纷繁。
中国对共同犯罪的定义主要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两种,从客观方面来讲,共同犯罪的行为包括: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中国的刑法从主要形态上,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以及教唆犯。逻辑上来看,这四种形态并非一类,前三种是在共同犯罪中以犯罪程度的不同进行区分,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作用分类法。而最后一种却是按照参与人类型进行区分的,也就是分工分类法。
依据不同逻辑的划分标准,引发了中国学者关于共犯体系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共犯体系是单一制共犯体系,在量刑时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考虑;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的共犯体系是“双层次区分制”,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根据参与程度和参与人类型进行分类量刑,在争论的背后,实则是对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分类方法的争论。“正犯”在我国清朝时期的律例中就已出现,在民国时期《暂行新刑律》以及之后的国民党政府刑法中一直沿用。我国对于正犯的定义是实行犯,与1975 年的德国刑法典中的定义相同,但对主犯的定义略有差异,主犯在英文中表示为“principal offender”,即现场实施犯罪不法侵害人,德国及日本定义与之相同,但差异于我国传统意义上主犯的含义。从立法历史上看,我国将正犯表示为实行犯,但是实行犯却是作为主犯的一种形式。
二、中世纪西欧大陆封建制度下刑罚权和中国的刑罚权
在德国,中世纪期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各封建领主掌握着绝对的司法权,在罗马帝国境内,帝国、区域领主、城市以及乡村间都有各种法庭;在法国,封建领主在各类案件中享有绝对的行使管辖权,虽16 世纪后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甚至建立了巴黎高等法院,但由于受中世纪晚期法国王室法院贪污现象及世袭制度的影响,国家司法权虽由国王掌握,也仅昙花一现;在南欧,王室争斗使地方割据愈演愈烈,导致后期封建贵族对封臣具有审判的绝对权。当时欧洲的统治模式径直导致司法权的分散,无统一的法律标准,各个封建法庭只能依据罗马法和当地的习惯法为根据。
欧洲中世纪,罗马教会和世俗政权统治着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肉体和思想,罗马教会关心犯罪意志,世俗政权看重犯罪行为和结果。而当时并无任何一位君主的才略权势能将刑罚权统一,所以费尔巴哈在法律内容的统一上竭心尽力,将刑罚权所指向的行为确定化、类型化,明确规定刑法分则行为为类型化行为,罪刑法定原则才得以确认。但刑法分则类型化行为是针对单独犯罪制定的,所以对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为减少法官在定罪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每个参与共同犯罪的人定性上须找一个区分重罚和轻罚的标准,亦为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而在罪刑法定原则上,非实行行为不具备构成要件,所以其不应被认定为犯罪。此处即产生了一个悖论,同样的非实行行为,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所受到的刑罚较轻,在司法实践中此原则却往往不能够将量刑均衡,走到了量刑悖论上。
中国自秦代实行帝制伊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和颁布了统一的法典,此举措也对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律例影响颇大。故从中国的历史渊源上来看,中国统一政权建立的时期较早,刑罚权集中,而且我国已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发展出完备的中央司法制度,统一法律与中央司法权使罪刑法定原则没有生长余地。在案件管辖权上,不同等级的官员依据级别断定案件,死刑案件需送至中央刑部进行决断。死刑案件在明清时代的程序又更为复杂,从督抚到刑部再到三法司,最后由皇帝批准。完备的中央监察制度的确立,杜绝了司法擅断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比附援引”有效的确保皇权不逾矩地运行,对封建统治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稳定也有所保障。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罪刑均衡核心为“探求罪刑间对应关系”,其存在历朝历代的律例之中,亦贯穿于司法实践至今。罪刑均衡原则在中国共犯体系中的形成与西方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并无牵连,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主要根源以人民所公认的恶行来确定合适的刑罚。中国历朝历代的律法中,都着重表现刑罚与犯罪为等价,此原则保障了帝制中刑事制度的稳定发展。而罪刑均衡原则思想基础是儒家传统里“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的中庸思想,其融会于共犯体系,根据共同犯罪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将其分为首犯,从犯,也就是首犯的处罚重于从犯。有学者提出,首犯从犯罪刑相适应无区分制的逻辑堪称缜密,揭露了事物本质,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从犯比主犯从轻处罚,与罪刑相适应思想吻合。
三、罪刑均衡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
在司法实践中在体现罪刑均衡之际也应合理的预防犯罪,设计罪刑梯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以典型例子说明,在中国,假如有人在抢劫的时候杀了人,其罪刑就会比只实施抢劫的不法侵害人罪刑重。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孟德斯鸠在论述罪刑均衡时笑谈道,“中国抢劫者不常杀人,俄罗斯抢劫者经常杀人”。我国现今的刑法贯彻的徒刑是从北魏时期开始将徒刑作为五刑之一的理念,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对于死刑体现了区分精神,根据分为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为依据。但是对于刑期跨度较大的有期徒刑,我国却未将罪刑均衡较好贯彻,因为计算死缓、无期徒刑实际服刑期限可得出其相对于有期徒刑较短。虽然刑法理论界调整了死缓及无期徒刑,但是却忽视了有期徒刑的改革。对于上述问题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借鉴唐朝律例的有关徒刑的规定,在有期徒刑六个月到15 年的幅度内划分若干刑格来匹配适用具体罪名。
对于当代的借鉴,首先要做的是承认共同犯罪,大陆法系国家在特殊犯罪类型中往往不承认共同犯罪,认为共犯属于犯罪形态,是实行犯的共犯,承认共同犯罪为独立犯罪类型即意味着对团体责任的承认。再者,以我国刑法逻辑划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两者并不属于同一范畴,而胁从犯与我国当时处于解放战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形势政策紧密相关。现今具有完备的罪刑梯度和罪过层次,将共同犯罪中对首犯、从犯加以区分,无妨于对共同犯罪问题的解决。目前,刑法学界对于教唆犯、胁从犯作为独立的共同犯罪种类争议较大,对教唆犯的保留也使得中国共犯体系的逻辑非常混乱,所以两者均有取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