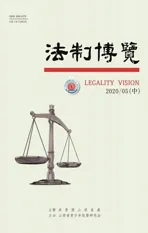浅析唐律中的私人财产权利
2020-11-3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399
“权利”一词古已有之,但是古今词义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古代汉语中,“权利”主要是指权势和货财,且大体上是消极或贬义的。近代随着西学东进,“权利”一词进入法律领域,并逐渐固定为英语中“right”一词的对应词。“权利”的含义相应的变成权能和利益,且逐渐摆脱了消极贬义,被赋予了公平、正义、理性、利益等丰富的价值蕴含。
人们之所以赋予“权利”一词以新的含义,正是因为汉语中原本没有能够与“right”含义相契合的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实践了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并没有现行法律中非常重要的“权利”概念,也更谈不上“权利”观念了。下文为方便论述,统一借用现今的“权利”概念来进行表述。但是中华法系虽然没有“权利”概念,却有非常发达的规范权利的法律和制度。①
就拿私人财产权利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确定财产归属之私权观念。孟子将恒产和恒心联系在一起,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认为真正的仁人、明君应该让百姓保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财产。[1]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定赏分财必有法”的思想。“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2]他认为只有权属清晰了才能避免犯罪,如一只归属不明确的兔子,绝大部分人都会追逐;但是如果归属明确,哪怕盗贼也不敢去偷去抢。
所以中国立法者历来重视对私人财产归属的规范。《唐律疏议》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性法典,在中华法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王朝一部最完整的法律典籍,唐以降的立法也多以其为蓝本。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立法者们,对私人财产制度作了详细的规范,这些规定与现今的规定相比在权利主体、内容、种类、分配、实现程度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这诸多差异中,权利主体和实现方式的差异是最鲜明的。
一、主体不同
唐律中的财产权利是以家庭所有制来实现的。《礼记》中有“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3]《唐律疏议·户婚》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4]只要有直系长辈在世,子孙分家或析产的判处徒刑3 年。
《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的刑罚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其中徒刑有5 个等级,从一年到三年,每半年一个等级。“上罪三年而捨,中最二年二捨,下罪一年而捨。”[5]由此可见子孙在直系长辈在世的时候分家产的属于重罪。
直系长辈在世,子孙别籍、异财,不仅是重罪,而且是“十恶大罪”。不孝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重大罪名之一。《尚书》认为,不孝是万恶之首,“元恶大憝,矧唯不孝不友”。[6]唐律认为分割家产和另立户口,实际上已经没有尽孝之意,名分及亲情都由此沉沦,情义及节操都由此丧失,以制度和礼法衡量,属于罪大不能宽容。别籍和异财,两种行为只要犯其一,都以十恶论罪。[7]父母过世后,也不能在父母的服丧期内另立户、分家产,“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8]
直系长辈在世,子孙不仅不能分家产,而且也不能私自动用家产。“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9]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财产虽然是家庭内部共有,但是统摄于家长。
现今宪法赋予公民的财产权,是完全体现个人意志的财产权利。家庭中子女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置。而且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法律也作了周全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 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 条亦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财产。”
子女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在涛涛告奶奶的案例中得到充分体现。2017 年初,年仅11 岁的小男孩涛涛将78 岁的奶奶施老太告上法庭。过去每逢春节、生日,长辈们都会给涛涛压岁钱,母亲朱女士将涛涛的压岁钱如数存进一张涛涛名下的银行卡里。2014 年7 月份,涛涛父母协议离婚了,涛涛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施老太分多次将涛涛卡里的钱全取走,共计4 万5 千多元。朱女士多次向施老太讨要这些钱,未果。无奈之下,她带着11 岁的涛涛把78 岁的奶奶告上了法庭。法院认为赠与的行为自钱款存入涛涛的账户时就已经完成,施老太未经涛涛同意擅自取走存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涛涛的奶奶向其返还压岁钱及生日礼金共计4 万5 千余元,且二审法院支持了原审判决,本案目前已经生效。
简而言之,唐律中财产权的主体是家庭,而现今中国法律中的财产权则是具体到每个个体的人的。假如涛涛生活在唐朝,涛涛的奶奶完全可以处置涛涛的钱财。如果涛涛因此状告奶奶反而是犯了十恶大罪之不孝罪,即使所告属实也要被处以徒刑两年或徒刑两年以上刑罚。[10]
二、实现方式不同
唐律承认私人财产权,而且保护私人财产权。《唐律疏议·厩库》规定:“诸财物应入官、私而不入、不应入官、私而入者,坐赃论。”“凡是公私论竞,割断财物,应入官乃入私,应入私乃入官,应入甲乃入乙,应入私乃入公廨,各计所不应入而入,坐赃论。”[11]这里,“官”主要指国有;“私”则是百姓所有,并且具体到甲、乙、丙等私人对象代表。[12]
古代财产权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唐代实行均田制,禁止土地买卖,只承认农民对土地拥有部分所有权,在立法时将北魏的“均田令”编入《户令》之中。②名义上土地国有,国家将土地均分给自耕农,受田农民向国家缴纳租佣调,国家依法对地主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保护,对违法者依《唐律》实行惩治。《唐律》规定了“占田过限”、“盗耕种及强耕种公私田”、“妄认及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及盗葬于人田”等罪名,尤其是为防止在职凭借官势侵夺百姓田地,专门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13]而且在职官员侵夺百姓田地,如果官员解职后案发,仍然适用本罪。
对于土地以外的财产,唐律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保护范围广泛。无论强取、窃取、动用受寄财物,甚至“得遗阑物满五日不送官”,都要以“坐赃论”,受到刑律制裁。[14]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唐律疏议》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注意平等对待。《唐律疏议·厩库》中“故杀官私马牛”、“畜产毁食官私物登时杀伤”以及“放官私畜产损食官私物”等都是平等对待公私财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对“官物”予以重点保护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贯传统。[15]比如唐律中“得遗阑物满五日不送官”这一罪名,遗阑物为私物的比官物罪减二等论处。[16]
抛开法律层面的这些规定,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财产首先是作为特权在社会上进行行政“特权”配置而不是法律“私权”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在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只有拥有权力的人才能依靠强权来决定财富的分配。政治权力尽管自身不能创造任何社会物质财富,决定社会物质财产的具体流向。政治权力的分配过程就是财产分配的过程。这种财产分配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行政的手段固定财产归属。[18]
古代中国公权力的绝对至上,导致虽然有较为完备的保护百姓财产的法律体系,但是百姓的财产极容易受到侵犯。尽管历代也曾存在不少禁止侵害私人财产的法律规定,但这些法律主要是为了惩处民间发生的财产侵犯行为,对于各级权力机构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则极少有现实的制度性约束。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旧制中籍录并没收犯人所有家口和财产的“籍没”制度。在传统社会中,籍没私财往往不是依据原有的法律规定,而是审判者临时专断的结果。被籍没的对象从私人财产扩大至青壮男女。历代王朝籍没私财任意剥夺私人生存的物质基础,打破了私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稳定状态,而世袭贵族的存在更是无从谈起。[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 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公民财产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其中,刑法专门设置了侵犯财产罪,对严重侵犯公民财产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在民法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物权、债权到知识产权的全方面公民财产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宪法虽然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对公私财产侵犯行为都是一视同仁的对待。而且为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财产的法律救济制度,公民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财产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拆迁法规也对政府征收公民房屋做出了严格限制,规定征收公民房屋必须限于为公共利益需要而且必须给予充分补偿。
概言之,现今中国以法律手段来固定公民的财产权,而古代中国以行政手段固定百姓的财产权。这两种固定财产的方式特征非常明显,前者有众意性、平等性、规范性、公示性、长期性、可靠性,后者有随意性、隐蔽性、不确定性、不公平性和不平等性。[20]
三、总结
造成这两种本质差异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阶级社会里,法律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而统治地位则是统治阶级最大的利益。
唐朝虽然在经济、文化、政治、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封建社会的性质,其制定的法律只能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最终目的的。制定于“刑罚由服从家庭伦理原则开始向服从国家根本利益转变”[21]时代的《唐律疏议》充分体现了“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妥协和统一。一方面“家政统摄于家长”,家长不仅掌握着“家庭之组织管理权、家庭经济管理权、对子孙卑幼的专制权等”[22],而且掌握着对子孙的生杀大权。祖父母、父母故意杀害子孙的只处以徒刑二年或两年半。如果是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的教诫和命令在先,祖父母、父母依法执行处罚,致子孙死亡的,无罪。反过来,子孙哪怕是骂父母、祖父母,都要处以绞刑。另一方面皇权至上,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危害皇权的犯罪都是祸及整个家族的大罪,“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哪怕是口说要造反的话,内心没有真正实行的打算,而且又无行为后果的,也要处流刑二千里。[2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家族掌握财产权,财产权的实现受制于皇权以及让位于官物也就都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国体决定了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法律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个体,不因身份、地位等外在的不同,而被法律区别对待。因此财产权也必然是具体到个人的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私人财产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不同的立法出发点决定了唐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者在“法的本位”上的本质区别。中华大地上施行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是典型的义务本位。它把社会秩序作为法的最高价值和本位价值,依靠对社会个体成员赋加义务,限制其基本行为的自由,实现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状态的渐变。[24]《唐律疏议》开宗明义,立法的原因是百姓中有些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满了恶念,如果不加以刑罚,大则扰乱天下,小则违背等级秩序。因此国家不能松懈了刑罚,家庭不能荒废了惩罚。[25]现今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决定了社会主义法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
不同的法律性质造就了完全不同的对待诉讼的态度。唐律里有所谓“以刑止刑,以杀止杀”[26],法的体系也是诸法合一,以刑为主,甚至“法”、“刑”同义。因而,对官吏来说,法就意味着定罪判刑;对老百姓来说,法就意味着认罪服刑。[27]因此传统中国才会追求“无讼”。而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里,一方面人人都是法律权利的主体,在感觉到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人人都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国家也鼓励百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纷争,为公民诉讼创造便利条件。因此中国也一改流传几千的“无讼”传统,法院立案量和结案量逐年攀升。
注释:
①有学者将权利分为“观念权利”和“实在权利”,认为中华法系虽然没有“权利”概念,但是有丰富的关于“权利”的法律和制度,如彭诚信在《“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的缺失——从文化根源的比较视角论私权的产生基础》(刊登于《环球法律评论》2004 年03 期)一文中就有详细的分析.
②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土地私有化的加强,唐王朝逐步放宽对买卖土地的限制,允许农民因供葬而出卖永业田,因从宽乡迁居狭乡而出卖口分田.实际上已承认了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