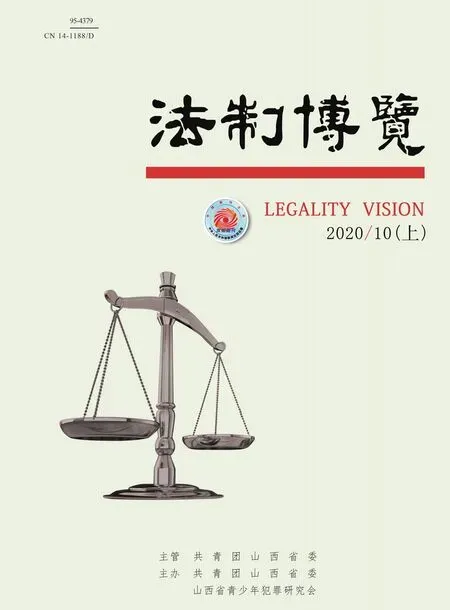《唐律疏议》视角下我国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探析
2020-11-30黄浩
黄 浩
四川省内江监狱,四川 内江 641000
一、引言
中国古代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周礼· 秋官· 司刺》的“三赦”之法,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当时的法律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精神智力不健全的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到了汉代,《汉书·惠帝记》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不得使用肉刑。到了唐代,在统治者的治理下,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唐代法律更堪称为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因此,在现代老龄化社会中,以《唐律疏议》为蓝本探究中国古代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亦可对当代社会建立和完善老年人从宽处罚制度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二、镜像与现实:《唐律疏议》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基本内容
(一)唐律中有关老年人犯罪年龄阶段的细致划分
从现代刑法学的意义上来讲,所谓老年人犯罪,主要是指达到一定年龄标准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唐代的老年人犯罪以七十岁为起点,《唐律疏议》中又将老年人的从宽处罚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了细致的划分,大体上分为九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上未达到九十岁的、七十岁以上未满八十岁这三个阶段。
(二)唐律对老年人犯罪刑罚减免的有关规定
《唐律疏议》在刑罚体例上基本继承了隋代《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在刑罚主要种类上沿袭了前代“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制度,对老年人犯罪的刑罚减免也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缴纳银钱减免刑罚。唐代以前,老年人犯罪减免处罚的方式主要有主刑减等和不适用附加刑。[1]到了唐代可以铜赎罪,《唐律疏议》规定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犯流罪以下的,可以通过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物品来达到减免刑罚的目的。二是特权阶层的老年人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对于特权阶层犯罪减免刑罚方面沿袭了前代的“八议”和“官当”制度,并有所细化发展,最终形成“议、请、减、赎、当”的减免制度。其中:“八议”指符合“亲、故、贤、能、官、贵、勤、宾”等八种情形的老年人犯死罪者可以通过上请的方式请求皇帝裁决免死;“请”是指特权阶层(皇室宗亲、“八议”)范围内的老年人犯死罪者由其家人上请皇帝裁决,流罪以下例减为徒三年;七品以上官员和九品以上官员,犯流罪以下的分别例减为徒三年或者向官府缴纳银钱收赎。三是特定罪罚,余罪免刑。《唐律疏议》规定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犯杀人罪时,官府不允许直接宣判,而是要上请皇帝裁决;犯偷盗、抢劫财物、故意伤人的“用铜赎罪”,其余犯罪,“余皆勿论”。这里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已经因死罪被“例减”为加役流、会赦流、反逆缘坐流等罪行的不得再行减免。《唐律疏议》卷四:“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流… 此等三流,特重常法,故不许收赎。”[2]四是免除处罚的年龄限制。《唐律疏议》在刑罚执行幅度上总体比前代宽缓,它规定了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对一切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虽然,这种规定对人均寿命比较低的中国古代来讲显得有些“天方夜谭”,但其蕴含的“刑罚宽缓化”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进程,是人类法制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五是刑事诉讼中限制对老年人的刑讯。《唐律疏议· 断狱》规定:“若年七十以上,并不合拷训,违者以故失论。”[2]唐代继承了汉代以来的“颂系”制度,考虑到老年人的受刑能力,唐律限制了对老年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刑具,并不得对上述人员刑讯逼供;六是案发前主动自首的减轻处罚。《唐律疏议· 名例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2]唐律对老年人犯罪后第一时间自首交代罪行的,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按照类推原则比照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犯罪减轻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七是刑罚执行方面的特别优待。唐代对于年满七十岁的老人“不加杖责”;在执行财产刑方面,对于犯罪的老年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放免不征”。另外,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男夫年八十,妇人年六十并免。”[2]这就是说,达到一定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男子八十岁以上、女子六十岁以上)的犯谋反、谋大逆等罪行的,可以免除死刑,减为加役流进行处罚。
(三)唐律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特别处理
唐代律法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特别处理,主要体现在跨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和被教唆犯罪时的从宽处罚方面。
一是区分犯罪时和审判时的年龄状态。《唐律疏议》规定:“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此。”[2]通过对以上法律条文分析,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方面,在犯罪时未满七十岁,在事发时或者在审判时达到七十岁的标准,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可以按照“收赎”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如果在判决后的刑罚执行期间,因年龄状况达到符合减轻处罚标准的,对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也按照符合减轻处罚的年龄标准来处理:“平均一斤铜可以折抵刑期十八天,如果剩余劳役天数不足十八天的,则是释放回家”。[3]二是对教唆老年人犯罪方面。唐代统治者认为,老年人年老智昏,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因此对教唆老年人犯罪的,按照“有人教令,独坐教令者”的方式只处罚教唆犯。这样的“从宽处罚”立法原则对今天来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现行刑法只对被教唆的老年人规定了“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定罪处罚”凡此种种,有处罚过高之嫌。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有唐一代,特别是唐初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的历史教训,在立法时就将“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儒家“恤老”思想贯穿其中,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更是吸取隋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教训,用刑较隋代以来更加宽缓持平,这对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战略与考量: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犯罪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在现代老年人口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老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处于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及妇女保护的需要,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罚条款。但与此相反的却是,作为同样是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从宽处罚机制却相对缺失。直到《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增加了有关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才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上老年人犯罪宽宥制度的正式建立。
从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来看,老年人犯罪的因素主要来源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在生理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生理指标逐渐下降,同时大脑的认知功能逐渐退化,对事物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在心理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导致对新事物耐受力的下降,从而对应激反应有较差的耐受性,促使犯罪行为的产生”。[4]
笔者认为:就当前老年人犯罪的成因来讲,除了理论界提出的现有观点外,还可以将老年人犯罪的成因大体归纳为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其中,外源性因素包括:社会地位变化与犯罪、家庭结构变化与犯罪、经济困难诱发的犯罪和文化生活匮乏与犯罪;内源性因素包括: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以及心理的变化导致的对事物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减弱。因此,依照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老年人在身体机能上与未成年人、残疾人一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逆转的欠缺,刑法有必要对其从宽处罚。
四、传承与发展:《唐律疏议》对建立我国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机制的启示
当代刑法学界著名教授张明楷先生认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5]一方面,随着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使得其在刑法上的责任能力也有所减弱。另一方面,老年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的可能性也比一般成年人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犯罪的老年人适用与成年人相同的刑罚处罚原则很明显有违“刑事责任能力”原则。因此,以《唐律疏议》为视角探究中国古代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可以对当代社会建立和完善老年人从宽处罚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降低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基线
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年龄基线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刑法中关于老年人在达到75岁后才适用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有过高之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纵观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许多国家将60岁或者65岁定为从宽处罚的年龄基线。著名学者赵秉志教授也认为:“应当将老年人从宽处罚或者免死的年龄设定为年满70周岁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6]对此,笔者也赞同赵秉志教授的观点。一方面,基于历史原因,自唐代以来就有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从宽处罚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将老年人宽宥处罚的年龄基线定为70岁也是基于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需要,因为刑法在充分保障受害者权益的同时,也应当保障犯罪人的人权。
(二)区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人脑所支配的辨认控制能力也随之减弱,使得其在刑法上的责任能力也有所减弱。我国刑法总则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体机能还不成熟。那么,同样是作为认知能力和辨认控制能力欠缺的老年人,也应当参照未成年人的标准细化区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刑事责任,以期科学的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探索建立取消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新机制
我国历来主张对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采取谨慎态度,《刑法修正案(八)》也明确了有关老年人年满75岁不适用死刑的年龄标准。但是,其“但书”又存在例外规定。笔者认为:刑法并非是报应性的对犯罪的人单纯的进行惩罚,而是通过处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考虑到社会控制的效果,在不久的将来,立法界可以逐步删除刑法总则中“但书”的规定,逐步放宽对老年人禁用死刑的标准。
(四)扩大对老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途径
根据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身体特点,笔者认为:对犯罪情节较轻的老年人可以参照《唐律疏议》中“以铜赎罪”的有关规定,用罚金“代替”收监执行刑罚。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负担,符合刑法谦抑原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老年人更好的回归社会,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与此同时,应当比照未成年人放宽对老年犯减刑标准,并且建立科学的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评价体系,以此来降低行刑成本,实现最大效益。
(五)探索建立老年犯监管改造新模式
近年来,老年犯数量的不断增长,已成为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的一大难题。因此,探索建立老年犯监管改造的新模式无疑对增加老年犯的教育转化率,维护监狱底线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应当探索设立老年犯集中关押改造模式。如在一省参照未成年犯管教所模式设置一定数量的老年犯集中关押点,以便于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改造,避免与其他罪犯关押在一起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其次,深入推进特色改造工作。不断深化对老年犯的个别教育,打造有特色的文化品牌项目建设;再次,创新劳动改造管理。如根据老年犯的劳动岗位能力,引进适合老年犯的劳务加工项目,使其在劳动改造中掌握一技之长;此外,有研究表明色彩学在老年犯的矫正过程中能够起到明显的作用。因此监狱应当在建筑色彩上适当增加暖色调的色彩,以此来稳定老年犯的情绪、增强舒适感、提升改造质量。最后,要聚焦老年犯的再社会化,帮助他们摆脱因长期在监狱服刑产生的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为其刑满释放后顺利回归社会培养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五、结语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建立健全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机制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与今天的刑法相比,《唐律疏议》中老年人从宽处罚制度更多的是维护有唐一代封建统治的需要。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法律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它的出台不仅受制于立法者的认知水平,还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在其身上更是被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烙印。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无法苛求古人在立法时存在的不足;相反,我们更应当思考的是现代法治事业中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薄弱,然后试图打开薄弱链条上的关键环节,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绵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