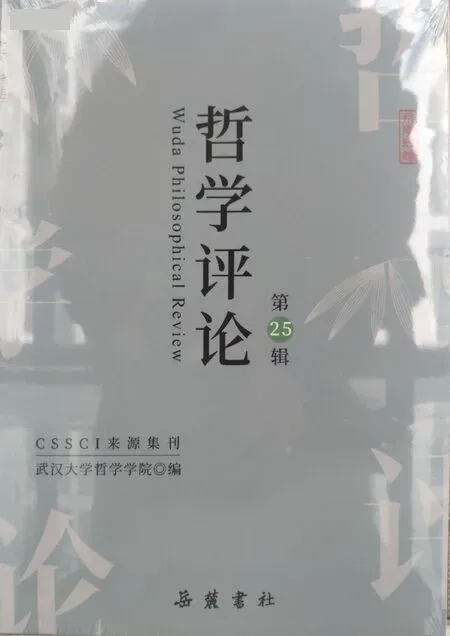平等价值、自我所有与道德动机
2020-11-29徐峰
徐 峰
分配正义是当代道德与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近几十年间涌现出诸多经典作品,然而其中不少是立基于“理想情境”得出的,看上去缺少对现实人性的恰当关注。[1]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8 页。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性会不会,和多大程度上将影响人们选择正义原则,是值得深究的话题。葛四友教授的新著《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正是围绕该问题开展创新性的突破。在他看来,包括罗尔斯(John Rawls)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在内的主流义务论,在人性动机和道德直觉的讨论中,并不如后果论有说服力和辩护力。由此,他以有限的利他主义为基础,通过批评罗尔斯等人的理论,尝试证成一种后果主义的正义观念。本文将回应葛四友对罗尔斯的部分批评,表明这些批评是有问题的,如果要从后果论的角度证成新的正义观念,则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罗尔斯。这些回应构成本文的第2 至4 节,在第1 节,笔者将引介葛四友书中一个极其有益的区分,澄清当前关于平等价值之纷争的实质。
一、如何理解平等的价值
在当代分配正义的讨论中,为什么要追求平等,通常有两种回答。第一种回答是,平等自身就是好的,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值得追求。另一种回答是,平等有助于实现其他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比如快乐,幸福或人类繁荣等,由此平等具有工具价值,值得追求。这两种回答都有不少拥趸,彼此也互相攻讦,时至今日这些论争仍然热闹不凡。在此,笔者先简要描述这些论争的概貌,继而借鉴葛四友在书中做出的一个有益的区分,因为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目前平等价值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一般来说,运气平等主义者(luck egalitarian)坚持第一种回答。在他们看来,平等是一种至上的美德,具有内在价值。这一点是运气平等主义者进行论证不可动摇的预设和起点。他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有些东西超出了人们的控制,例如人们的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和个人禀赋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随机和任意分配的因素,从道德的观点看,人们不应当凭借这些任意因素为自己谋利。换句话说,由这些任意因素带来的任何有利或不利的后果,都不是人们应得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理应抵消肇始于原生运气(brute luck)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社会中也有一些东西看起来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例如我们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做出自主选择,也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多收入。运气平等主义认为,一个正义的制度也要体现出对个人自主选择的尊重,即个人应当对自主选择的后果负责。按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说法,运气平等主义的口号是“钝于禀赋,敏于抱负”(endowment-insensitive, ambition-sensitive)。[1]Ronald Dworkin. “What is equality?Part 2: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81. 10(4) . pp. 283-345.
但是,运气平等主义这种自认为不可动摇的预设从理论提出伊始就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批评说,人们总是错误地依据平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偶然联系,或者错误地认为物品的效用遵循边际递减法则,对财富收入的平等分配能够最大化它们的效用总和,从而想当然地认为平等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法兰克福认为,经济平等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空洞的形式学说,对平等的追求是拜物教的表现。作为平等主义的替代物,他提出一种充足主义(sufficientarianism)的观点,指出道德上真正重要之事不在于比较人们之间是否平等,而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只要处境不利的人达到充足门槛,那么不平等就不再是一种恶,我们对不平等的道德憎恶只是对不充足的憎恶的回响。[2]Harry Frankfurt. “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 , Ethics, 1987, 98(1) , pp. 21-43.充足主义的观点简明扼要,便于操作,它对于制定和推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等公共政策有着深远影响,所以受到很多学者的追随和推崇。[3]参见Roger Crisp. Equality, Priority, and Compassion. Ethics. 2003.113(4) . pp. 745-763; Paula Casal. “Why Sufficiency Is Not Enough” . Ethics. 2007.117(2) . pp. 296-326;Liam Shields. Just enough: Sufficiency as a Demand of Justi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等。
帕菲特(Derek Parfit)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运气平等主义提出挑战。他说,如果人们坚持平等具有内在价值,就相当于坚持如下主张: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的处境更差,这就是坏的。[4]Derek Parfit. “Equality or Priority?” in Matthew Clayton, Andrew Williams (eds.) . The Ideal of Equ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 81-125.根据该主张,运气平等主义者要求消除不平等,甚至不惜将富人的财富向下拉平到与穷人相当的水平,同时辩称在平等的维度上这样做是一件好事。帕菲特批评说,支持向下拉平的做法显然很荒唐,声称一种事态是否变好必须要看它能否有利于个人,也即影响个人的观点(person-affectingview),向下拉平使得富人变差,却没有让穷人的福祉变好,那向下拉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一件好事,因此“平等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不可靠。帕菲特据此提出一种“优先主义”(prioritarianism)的观点:当一些人越差的时候,给他们以利益就越重要。[1]Derek Parfit. “Equality or Priority?” in Matthew Clayton, Andrew Williams (eds.) . The Ideal of Equ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 81-125.与运气平等主义强调人际比较不同,优先主义只关心人们的绝对福利水平。优先更不利者,但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处于较低的绝对福利水平,以及福祉的效用会随着人们处境逐渐变好而边际递减,这不关乎与其他人的比较。
客观地说,充足主义和优先主义的批评有合理之处,他们通过厘清平等、充足和优先等概念间的关系,告诉我们要警惕平等本应承载的道德分量,不可将分配正义中的所有道德考量全部压在平等身上,否则会造成平等概念的“崩塌”。但是这不意味着运气平等主义理论就此失败了,或者说平等不该具有内在价值。不少运气平等主义者已经反驳过那些批评,[2]参 见Kok-Chor Tan. “A Defense of Luck Egalitarian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8.105(11) . pp.665-690; Slomi Segall. “What’s so Egalitarian about Luck Egalitarianism”. Ratio. 2015. 28(3) . pp. 349-368 等 .本文无意考察这些反驳,而是借鉴葛四友作出的一个新颖且有益的区分,即他对分配正义中“初定”(prima facie)和“初步”(pro tanto)的区分,来澄清围绕平等的内在价值的误解。
按照葛四友的解释,初定合理性是在概率意义上讲的,如果直觉具有初定合理性,这种直觉越强,其为真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如果相反证据足够强,那么初定合理性的概率无论多高,都可以降低到零,也就是说这种初定合理性是可以取消的。而初步合理性主要在权重的意义上讲的,如果某件事具有初步合理性,那么做这件事就是有一定权重的道德理由,权重越大,就越应当做。这表明,如果相反的理由的权重足够大,那么初步合理性无论具有多大权重,都是可以被压倒的。但是它不可能被取消,被压倒的权重仍然存在。[3]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 页。
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平等价值争论的实质。很明显,法兰克福和帕菲特等批评者是从初定的意义上考察平等的价值,他们认为追求平等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会耽误我们追求更重要的事,例如对优先或者充足的关注。也就是说,当我们分析人们的处境时,很多时候乍看之下是在关心平等,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让人们脱离糟糕的处境本身,而不是和他人的处境之平等的比较。用批评者话说,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饥饿之人的饥饿,有需要者的需要和病患的痛苦”[1]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40.。此时,平等在乍看之下所具有的合理性亦将随之消逝。
运气平等主义者却是站在初步的意义上来考察平等。对他们来说,平等重不重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即使在向下拉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坚持说这样做至少体现出平等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运气平等主义者会一口咬定必须时刻都向下拉平。因为可能有其他的理由可以压倒追求平等的理由,比如对效用总量的关注,所以平等即使被压倒,也不意味着它就此消失,不再具有任何道德分量。如新近的平等主义者特姆金(Larry Temkin)所言,任何理性的平等主义者一定是多元主义者,平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但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具有独立的规范性力量。[2]Larry Temkin. Egalitarianism Defended. Ethics. 2003. 103(4) . pp. 764-782.所以,即使运气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也不影响他们在综合考虑之下,选择某种支持不平等的方案。
因此,在方法论上澄清初定的和初步的不同意涵,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运气平等主义、充足主义和优先主义之间的争论。平等主义的批评者看起来混淆了平等在概率意义上的合理性与权重意义上的合理性之差别,因而他们提出的“向下拉平”等反驳也相应地丧失了批判力度。平等主义者也依然可以坚持说平等是重要的,具有内在价值,虽然有时候可以被其他价值所压倒,从而倾向于支持某种不平等的分配原则。
二、罗尔斯论自我所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尔斯不会被卷入到关于平等到底具有内在价值还是工具价值的论争中,因为他认为,平等虽是一种重要的道德理想,但经济不平等也是可欲的,只要这种不平等能够让所有人受益,尤其有利于社会合作体系中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是故,帕菲特也承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能免于“向下拉平反驳”的挑战,性质上属于“道义论平等主义”(deontic egalitarianism),不是他竭力批驳的“目的论平等主义”(telic egalitarianism)。[1]Derek Parfit. “Equality or Priority?” in Matthew Clayton, Andrew Williams (eds.) . The Ideal of Equ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pp. 81-125.笔者认为,不限于此,如果我们澄清对罗尔斯的某些误解,实则会发现他的理论可以抵挡很多似是而非的攻击。
让我们首先考察葛四友对罗尔斯自我所有权的批评。葛四友多次提醒人们,罗尔斯接受天赋是共同资产,不承认所谓的自我所有权。“这里不仅仅是把天赋与才能看作共同资产,实际上同时对于其分配也是有规定的,那就是预设了‘不应得’理解。……在反对罗尔斯理论的人眼里,关于天赋与才能的这种说明成了罗尔斯理论的软肋。”[2]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 页。如果罗尔斯真的不承认自我所有权,那将与我们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相冲突,因为人们一般认为自己的智力、劳动能力都是属于自己的,除非自愿,别人没有理由要求我们为他们做什么。
然而,该批评是有问题的。罗尔斯一直强调,天赋和才能的分配作为一种共同资产,人们共享这种分配的利益。换言之,是天赋和才能的分配,而不是天赋和才能自身,被看作是共同资产。天赋和才能理所应当地属于每个人所有,这是无异议的。当然,任何一种天赋与才能之所以脱颖而出,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设想一个根本不知道篮球为何物的社会,一个叫作库里的人能够在10 米外将圆球扔进悬挂的空心圈中,这肯定是一种才能,却不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才能,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可能捕鱼多或者爬得高才更有市场。所以,根据罗尔斯的说法,人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与才能,而且这种“自然资质的分布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人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正义。这是自然的事实。正义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3]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8 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提出了“反应得”的主张:从道德的观点上,天赋的分配是任意的和偶然的,人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和社会天赋中所占的位置,凭借这些任意和偶然因素的谋利是不应得的。
虽然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处处彰显自我所有权的至高无上相比,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的强调明显式微和模糊很多,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此否定了自我所有权,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罗尔斯是承认自我所有权的。诺齐克坚称的自我所有权是一种“彻底”(full)的、坚不可摧的权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得侵犯,而且拥有自我所有权就等于拥有财产权,任何对财产权的侵犯是对个人的奴役,甚至对劳动所得征税也等于是强迫劳动。[1]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 页。罗尔斯的自我所有权并没有那么“彻底”,这首先表现在他不要求无条件地保护私有财产。以第一个正义原则中的自由清单为例。罗尔斯说人们平等地拥有“政治上的自由与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人的自由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以依照法治的概念不受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7 页。然后,他紧接着说,拥有某些财产(如生产资料)的权利和自由被排除出基本清单,不受第一原则的保护。这表明对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不是“根本的”和“不可让渡的”,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根据平等或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许此时罗尔斯想到的是,他的正义理论必须具有开放性,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能够与他的正义原则相兼容。
罗尔斯的自我所有权不那么“彻底”还表现在他与运气平等主义者的理论分野中。虽然他们分享着同一个命题:人们不应得凭借任意分配的天赋得来的利益,是谓“钝于禀赋”。但是运气平等主义者在“钝于禀赋”的基础上还重视“敏于抱负”的重要性,要求个人对自主选择的结果负责。但就这点而言,罗尔斯多少显得进退两难。他察觉到很多东西都会对个体的自主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和社群文化等。所以,他说使我们努力培养自己能力的优越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环境”。[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9 页。那么,个体是不是不需要承担选择带来的任何后果?罗尔斯也不这么认为。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罗尔斯只是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说“全部依赖于”,这看起来多少是给人们的自主选择留下空间。
如果留意罗尔斯在其他地方的表述,也能找到不少证据证明他认同人们自主选择的可能。比如他在描述良序社会时,指出其中必须有刑法、警察、法庭和监狱等机构,这就假定了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人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 页。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对善的公平》中,罗尔斯又强调人们有掌握和修正其需要和欲望的能力,因而要对自身的偏好和自己为之献身的东西负责。[3]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上册),陈肖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20—321 页。
因此,到底如何判定自主选择与后果责任的关系时,罗尔斯表现得很纠结。他不像运气平等主义者那样奉“敏于抱负”的信条为圭臬,而是指出很多“抱负”或“选择”是由环境所决定,但是又不愿承认所有的经济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内心纠结的后果使得罗尔斯最后不得不暂且放弃考虑该问题,在后期作品《政治自由主义》中,讨论“闲暇时间”是否应当列入基本善的范畴时,他暗示道,自主选择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很棘手,差别原则的实施必须暂且去掉这些麻烦情况。[4]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93 页。
可以看到,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的论述非常模糊,他既不是葛四友指认的那样完全拒绝自我所有权,却也不像诺齐克那样坚持“彻底”的自我所有权,而是在其间摇摆不定。笔者已经指出,这种摇摆还体现在罗尔斯与运气平等主义者对待自主选择与后果责任的不同态度上。
三、差别原则背后的道德动机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表明,如果某种获得额外基本善的道德动机能带来更多的社会福祉,且这些福祉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话,那么这种道德动机就是正当的。对此,科恩(G.A.Cohen)给出了严厉的批评。科恩认为,人们在建构社会制度时宣称自己是平等主义者,却又在个人行动时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了动机悖论:个人的动机内在不一致。[1]G.A.Cohen.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他用增加税收的例子予以说明:
(1)如果经济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它是有证成的。(大的规范性前提)
(2)当税率是40%的时候,(A)能干者生产的比在60%的税率下要多,(B)结果最不利者在物质上反而得益更多。(小的事实性前提)
(3)结论:税率不应该从40%上升到60%。
科恩的意思是,如果能干者宣称自己是平等主义者,那就应该发挥自己最大的劳动潜力,表现得跟税率40%的时候一样多的潜力(甚至更高),同时为了正义,又支持税率上升到60%。唯有此,才是平等主义的要旨,否则“如果你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2]G.A.Cohen.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8-130.
葛四友认同科恩对罗尔斯的批评。他用更加清晰简洁的语言予以阐释,“不平等之所以有利于最不利者,是因为如果不给予激励的话,能干者就会罢工。而能干者之所以会罢工,是因为能干者不具有平等主义态度”。[3]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0 页。因此,“‘除非改善他人,否则不想要更多’与‘最大化的自利动机’是不相容的”。[4]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2 页。如果科恩与葛四友的批评成立,差别原则背后人们的道德动机就有问题,两个正义原则也相应地称不上是正义的,至多是临时性的社会管理规则。但是,在笔者看来,对道德动机的批评可能有失公允,在罗尔斯那里可以找寻到理论资源予以回应。
我们从罗尔斯理论中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内容谈起,即他对何为人的观念的理解。包括葛四友在内的一些批评者认为,无知之幕背后的立约人是原子化的个体,“选择者是空荡荡的个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实际上就会瓦解个人尊严的基础”。[1]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9 页。但是此类批评的错误在于,在罗尔斯的社会中,立约人有着很多共同的目的和承诺,这是罗尔斯理论的特色之一,也往往是被误解的地方。
(1)我们要谨记,罗尔斯的论述对象是一种良序社会,在其中,公民具有一种他所说的“正义感”,这能够激发他们按照正义的原则行事。换言之,在良序社会中,人们对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动机保持真诚,不可以欺骗。如果只是希望从公共的钱袋里获取额外的补贴,那就没有依照正义感行事。如罗尔斯所言,人们的善是受约束的,“人的情感和友谊,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合作,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美的对象的塑造和观照,所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价值,不仅在我们的合理计划中是突出的,……与欺骗和教唆他人堕落的欲望形成对照,在对人的善的描述中做不正义的事被排除了”。[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35—336 页。
(2)罗尔斯明确表示,他的观点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属于“私有社会”的内容。对于“私有社会”,他的界定如下:
“它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无论他们是个人还是社团,都具有他们的私人目的,这些目的或相互冲突,或彼此独立,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赞美。第二,制度本身被看得没有任何价值,和制度有关的活动不被看作一种善,如果被看作什么的话,也是被看作一种负担。所以,每个人仅仅把社会安排当作实现他的私人目标的手段。没有人考虑他人的善,或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善;毋宁说,每个人都偏爱于选择使他得到最大的财富份额的最有效的方案。”[3]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2 页。
根据罗尔斯的看法,良序社会与私有社会的区别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罗尔斯的构想中,公民们具有某种形式的共有目的和最终目的。在良序社会中,正义是公民们彼此给予并相互获取的,他们从事这些行为时又被广泛地支持。也正是在“给予—获取”的过程中,公民们通过对社会制度和他人行为的认可来体认到他们的最终目的。
其次,罗尔斯构想的良序社会是某种形式的社会联合。他援引威廉·洪堡的观点作为支撑,“正是通过基于社会成员的内在需要和能力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所有其他人的丰富的共同资源”。[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4 页,注1。这好比每个人都是管弦乐队中的成员,都根据一种默契在各自选定的乐器上发挥技艺,以便在共同演奏中实现所有人的能力。将良序社会描述为某种社会联合,罗尔斯是要表达出每个人的善都是人类完整活动的因子,这个活动是大家都赞成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我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别人的成就,同时我也将他人的成就视作自己的成就。
最后,差别原则指导的良序社会例示着罗尔斯所说的互惠性(reciprocity),而不仅仅是“互利”(mutual advantage)。这里讲的互惠可以类比于家庭内部的关系。罗尔斯说,“一个家庭的成员通常只希望能在促进家庭其他人的利益时获利。那么按照差别原则行动正好也产生这一结果。那些处境较好者愿意只在一种促进较不利者利益的结构中占有他们的较大利益”。[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1 页。对罗尔斯这个类比的正确理解是,在良序社会中,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和天赋,但是离开社会制度背景,很多被认为有价值的才能并不具备真正的价值,所以,人们具有的不同才能应该为共同目的来服务。
(3)葛四友担心,既然罗尔斯把自尊视为一种重要的基本善,可是“动机悖论”却会瓦解人的尊严,因为能干者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要求更多的经济回报。[3]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9 页。笔者认为,这个担心也是不必要的。首先如上文所述,在彰显社会联合和互惠的良序社会中,我们能够体认到自己的人格和行动受到他人的赞扬和肯定,这时候社会制度被安排得能够维持每个公民的自尊。不仅如此,罗尔斯还说,在良序社会中,自尊的基础会日益扩展到别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比如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在非经济活动中获得满足感。简言之,只要人们能够感到他们自身的价值,认识到值得努力去实现他们的生活计划,也能够带着自信推进自己的目标,他就是有自尊的。
如果上述三个方面的回应成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差别原则背后的道德动机的批评有失公允。站在罗尔斯的立场看,他不会落入葛四友所批评的动机困境的窠臼之中。
四、重思作为公平的正义
通过指出罗尔斯的理论暗含三种自相抵牾的人性设定,葛四友尝试重构罗尔斯的理论,同时也呈现出他自己的分配正义立场:以人道为基础,以公平为要求,二者缺一不可。接下来,笔者将分析葛四友对罗尔斯理论的重构,指出这种重构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并没有表现出比罗尔斯原先的理论有更大的吸引力。
葛四友认为,如果接受他对罗尔斯的批评,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选择的原则是类似的三个正义原则,但会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第一个原则是基本需要原则,不考虑人们的具体贡献,要求人们作为一个集体承担一种责任,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即人们基本的衣、食、住、行能够得到满足,享有基本的教育权和医疗权。第二个原则是罗尔斯谈到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初衷是抵消社会偶然性对人们的影响,让拥有同样天赋的人,发展出同样的能力,做出同样的贡献。第三个原则是罗尔斯谈到的平等自由原则,包括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1]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7—188 页。葛四友指出,这三个原则遵守词典式序列,第一个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人道的义务,第二和第三个原则主要体现公平的要求。
笔者认为,葛四友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作为人道义务的理解是准确的。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包括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生存、基础的教育和基本的医疗等——无论如何都是最底线的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公共权力将丧失合法性。葛四友也敏锐地解读出罗尔斯的理论中已经预设基本需要原则作为正义第一原则。他的依据是罗尔斯的自然义务概念。罗尔斯认为自然义务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的内容一般来说并不是由这些社会安排的规则确定的。这样我们就负有一种勿残忍的自然义务,一种帮助他人的义务,而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这些行为”。[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1 页。除了自然义务外,罗尔斯实际上还在不少地方谈及实现正义必须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促成社会的最低保障。
在《正义论》中述及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时,罗尔斯说转让部门的活动必须要把基本需要考虑进来,并赋予基本需要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强烈反对由竞争者来决定总收入的分配,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需要的权利和一种适当的生活标准。”[2]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8 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描述达成重叠共识之步骤时强调,“给所有公民的基本需求提供最起码的满足也是宪法根本的一项内容”。[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42 页。又如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回应有限功利原则时说,“差别原则规定了一种源于互惠性理念的社会最低保障。这起码满足了过一种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基本需要,或者还会更多一些”。[4]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2 页。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罗尔斯意识到满足基本需要,或者提供社会最低保障,是讨论分配问题的前提。在这点上,笔者与葛四友的观点并无二致。我们都同意,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没有完整地素描出作为公平的正义之全貌,这里不妨认为还存在一个基本需要原则,且词典式优先于后来的两个正义原则。但是,对于葛四友重构的第二个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又要优先于第三个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笔者并不同意,接下来我们转向对自由优先性的考察。
葛四友注意到罗尔斯的“一般性正义观念”说法,“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5]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2 页。换言之,在某些环境中,两个正义原则允许在基本自由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进行交换。此时,自由不再具有优先性。但是罗尔斯说,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是这种“一般的正义观念”的具体实例,尽管后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也只会发生在某些很特殊的情况中,例如在紧急状态中,有时可以根据一些人的较大利益超过其他人的损失来容忍奴隶制。[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 页。或许葛四友会回应说,由于罗尔斯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之区分没有多少解释力,自由的绝对优先性因此也不具有直观合理性。但是考虑到罗尔斯的理论中隐含的基本需要原则,即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绝对优先,加上和平等的自由原则的共同作用,对于人们理性地形成和修正善观念来说就不会构成很大的问题,或者具有可接受的、有限的影响。退一步讲,当基本需要原则得到满足后,人们经过理性慎思,可能不会认为当所有人都处于一定门槛之上时,自由价值之间的差别仍然很重要。因为虽然不同的自由价值(金钱等)能够带来更多的物质层面的善,但这对于促进公民理性地形成和修正善观念的能力影响甚微。尤其要注意形成和修正善观念的能力,而不是金钱,才是罗尔斯说的人们的“最高阶利益”。
平等的自由原则必须具有优先性,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具有“零和”的特征。虽然都属于人人欲求的社会基本善,但是权力在性质上与收入、财富之类还是有很大不同。一些人的权力影响更大,势必会导致另一些人的权力影响式微。财富与收入则不同,一些人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可能引起另一些人的增加。所以,原初状态中的公民们更乐于接受政治自由及其价值的平等分配,至于收入和财富,则允许不平等的方式分配,只要能使最不利者的处境变好。所以,笔者认为,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置于“平等的自由原则”之前是不合理的。
最后要指出,在葛四友所重构的三个原则中,没有了差别原则的身影。可能的原因是,他认为差别原则在应用时会遭遇动机困境,因为收入差别作为激励变得无济于事。上一节笔者已经证明,罗尔斯并不会陷入动机困境之中,他的理论能够免于这些批评。此外,差别原则之不可或缺有个重要原因。葛四友的重构目标是:(1)有同样的天赋的人有条件发展出同样的能力;(2)有同样的能力的人有机会做出同样的贡献;(3)做出同样的贡献的人能够获得同样的收入。[1]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8 页。这里的讨论是有同样天赋的人拥有类似的未来期望,但是具有不同天赋的人该怎么办?葛四友似乎没有给出答案,不过他的表述倒流露出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和自信。例如他支持收入累进税和财产使用税,以此人为地减少自然垄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没有那么容易致富。除非我们应该为人们提供轻易致富的机会,或者说人们应得轻易致富的机会”。[2]葛四友:《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4 页。不过,此类表述看上去仍然可以认为是在支持“类差别原则”的要求。
本节的论述表明,葛四友对罗尔斯的理论重构并不成功。一旦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理论,即基本需要原则作为绝对优先原则,再融合两个正义原则,同样能够很好地实现葛四友所追求的分配正义目标:人道与公平。
五、结 论
至此,如果笔者的论证无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罗尔斯可以较好地应对来自后果论的挑战,他有更好的理论资源和空间为己辩护。当然这不是说,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完美无缺。比如,罗尔斯的支持者们需要认真对待自我所有权,和由此引申的产权民主问题,也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基本需要原则如何作为绝对优先原则。所以,本文旨在为罗尔斯的理论作出有限的捍卫。另一方面,葛四友的《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一书展现出的理论抱负与问题意识,值得学术同仁进一步地参与、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