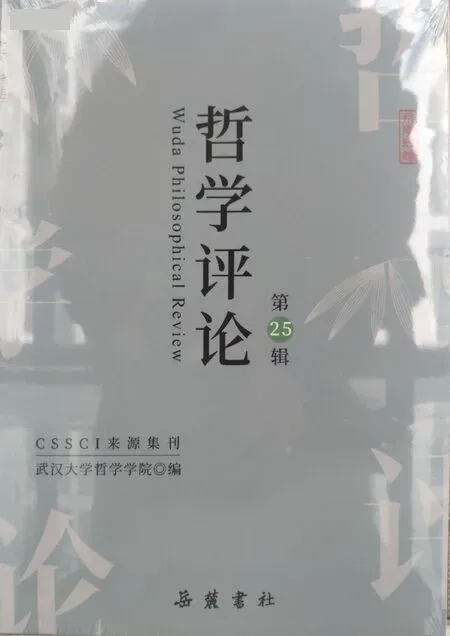康德“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中的“直觉的知性”
2020-11-29邢长江
邢长江
众所周知,现象与物自体、直观与思维、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严苛区别是康德哲学的一个经典特征。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正是尤其不同意这种区别,所以才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康德的先验哲学,使其中的两歧得以互相沟通。
不过,回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第77节中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似乎自己提到了沟通和超越这两歧之可能性(“经验与理性的那些最高原则的结合”,AA399)。比如,在这里,他提出,人类具有一种特殊的判断力,即“直觉的知性”(intuitiver Verstand),而它又同时包含了他在自己早先已然区别开来两歧:一方面,它与一般的、“推论的”(diskursiv)知性不同,因为它是“直觉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理智的活动,因为它是“知性”。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Glaubenund Wissen)中,就认为康德通过“直觉的知性”,在“自然目的”概念中,表达了概念与实在之间的统一性,从而展现了整个德国观念论运动的主要意图。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黑格尔像歌德、席勒、费希特和谢林一样,给予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极高的评价。[1]Hegel, Theorie Werk Ausgabe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p.325. (以下简称TWA II)
但是读者不禁会质疑,为何康德要在《判断力批判》的这个关键的部分谈到“直觉的知性”?既然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以二元区分为基础的,那么“直觉的知性”的说法是否仍旧属于康德先验哲学?诺佐(Angelica Nuzzo)就站在捍卫先验哲学的独特性的角度,明确地指出,“直觉的知性”与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所憧憬的统一试图有根本的差异:“如果把第76—77 节看作是后康德哲学的跳板的话,那么这些人就完全脱离了文本语境,且在‘直觉的知性’这个问题上过度发挥了。”[2]Angelica Nuzzo,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76-77: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the Limits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Kant Yearbook, ed. Dietermar H. Heideman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144.
《判断力批判》中“直觉的知性”的观念是不是预示了德国观念论者所谓“绝对统一”的可能性?这又如何理解这个观念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基本特征之间的矛盾?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说,在“直觉的知性”上,我们可以多少读出一些康德哲学与整个德国观念论哲学的核心关切。而如果正如诺佐所说,康德本人和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对先验哲学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那么“直觉的知性”确实足以成为深入研究两者的一个引子和问题线索。
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线索出发来展开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探讨。为了避免使这个本已宽泛的探讨流于空疏,或脱离康德论述的原意,本文将紧紧围绕“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文本脉络,把问题限制到分析“直觉的知性”在其中所扮演的必要角色,以此达到对康德本人意图的最大同情。
一、“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基本框架
虽然人们熟悉《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直觉的知性”的谈论,但是事实上,早在硕士论文之中,康德就已经对“直觉的知性”有详细的说明。[1]Christopher B. Garnett, Jr., “Kant’s Theory of Intuitus Intellectuals in th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of 1770”,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46, No. 4 (Jul., 1937) : 424-432.而正如康德自己指出的那样,这个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提及。[2]Kant, Gesammelte Werke, ed, königlich preußische (später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vol. V, S. 405. (以下简称AA V)这些都说明了,“直觉的知性”是康德在长时间关注的一个概念,并非他在写作《判断力批判》时突发奇想的产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关于“直觉的知性”的论述与康德别处对它的谈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无疑来自它所处的特定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判断力批判》(特别是其中的“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整体论述思路决定了,“直觉的知性”必须要在其间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角色。
我们可以从“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基本框架入手来理解这一点。在《判断力批判》中,“直觉的知性”首次出现在“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结论部分。无疑,之前的整个“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探讨都围绕着目的论判断力所存在的二律背反展开。康德指出,之所以会有二律背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目的论构想大体上都是依据“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这两种互相区别的判断力而做出的。这两种形式的判断力的运作机制之间明显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谓规定性判断力意为:确定的原则已经先行被给予出来,而通过这种判断力的规定,我们把具体的事物归摄于其下,因此这种判断力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随着前提具有确定性从而具有了实在性。“规定性判断力独自并不具有关于客体的概念的原则;它不是什么自律;因为它仅仅在作为原则而被给予的法则或者概念之下进行归摄。”[1]AA V 385.与之相对应地,反思性判断力则没有确定的原则被先行地给予出来。我们不能有一个客观实在的前提得以依靠,以至于我们不能援引它而得出确定的结论。它只能从主体出发来对原则做一种主观的反思(“然而,反思性判断力却应当在一个尚未被给予的,因而事实上只是对于对象进行反思的一条原则的法则下进行归摄,对于这些对象,我们在客观上完全缺乏一个法则,或者缺乏一个客体概念,来充当出现的种种情况的原则。”)[2]AA V 385.通过反思性判断力,我们确实能够对一个原则和目的形成理解,但是这个原则和目的并非是一个客观实在的原则,而是我们自身主观设想出来的主观原则。这种反思性判断力得出的主观原则能够使我们对自然的经验事物的认识依循一个统一的尺度而具有章法。
因为主体能够凭借的经验和知性这两个准则本身并不相同,所以由这二者出发进行的判断也就会互相抵牾。比如,从经验出发,我们运用规定性判断力思考目的,所得出的结论是:“物质性事物及其形式的一切产生都必须被评判为依照单纯机械法则才是可能的。”[3]AA V 387.在这个时候,自然界中的目的是唯一的目的,且它是一个“构成性原则”,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都从属于这一原则之下,在机械的自然框架和因果链条中扮演一个角色。但是从知性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则是:单纯的机械法则不是唯一的,“它们的评判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因果性法则,亦即终极因的法则”。[4]AA V 387.在经验的自然之外存在着一个作为“终极因”的目的,它是一个“范导性原则”。它确实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目的,但是它并不是自然世界中直接地驱使事物服从于它的“铁律”,而是万事万物最终指向它的超越者。换而言之,两种不同的目的论判断力所得出的目的论图景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人们通常对目的论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理解:一种是把目的完全等同于经验的自然界中的机械原则的目的论,一种是把目的看作是超越于自然界的机械的经验原则之上的终极因的目的论。
我们可以同时用机械因果性法则与终极因法则来进行目的论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又是相反的。这就是反思判断力的二律背反的问题[1]AA V 386.。之所以会出现二律背反的问题,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区分清楚目的论判断力的两种形式,以至于混淆了规定性判断力的建构性原则和反思性判断力的范导性原则。在第72 节“关于自然合目的性的诸体系”中,康德给我们梳理了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关于目的论的理论体系。以往的哲学家要么完全否认目的的超越性,而只是纯粹从经验的机械论的角度来理解自然,要么承认目的论的超越性,但只是从一个形而上学的理念论的角度来理解目的和原则。不管这些观点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异,这些目的论的体系无非都只是单纯从或“规定性”或“范导性”的一侧去理解目的论的体系,所以只不过仍旧在延续已有的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只能是幻相和独断论。
康德认为,只要我们不混淆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那么这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在第74 节中,他指出,之所以以往的目的论体系都只能是独断论,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通过经验认识自然目的,也不能通过理性的手段对它进行证明。归根到底,自然的目的不是一个构成性的原则,而只能是一个在主观的反思中获得范导的原则。它虽然具有“自然必然性”和“客观必然性”,但是它同时又是偶然的,因为它不能直接地作为理性的对象而被把握。而如果我们强行用规定性判断力对范导性的自然目的做出断定,那么只不过是仍旧在用自己的、未加审查和讨论的主观设想强加到自然之上,然后宣称自然正是依据这种“目的”而运行。当然,每个人的主观设想不同,所以对自然目的做出完全不同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之间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相反地,如果我们用反思性判断力来对待自然目的,那么就给予了后者以恰当的尊重,其结果只能是,不同的人就会对超越的自然目的得出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理解。[2]AA V 391.
为了澄清传统独断论的混淆,康德给出了一种“批判的”的、关于自然目的性的“先验哲学”。这里的“批判性”何在?一方面,康德批判机械论的自然观,并且承认具有超越于机械的自然世界之上的超越目的。他认同这种目的具有“客观实在性”,并且认为理解这种实在性需要超越机械因果性思维之上的理智的运用(“为了有权甚至提出最大胆的假说,至少人们假定为根据的东西的可能性必须是确定的,而且人们必须能够保证这个根据的概念有客观实在性”[1]AA V 394.)。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像传统的形而上学那样(康德在这里把斯宾诺莎主义作为靶子),单纯通过理智来演证这种目的的客观实在性。我们如果依照理念论的方式设想目的论,把一切世间存在者都统一在绝对主体之上,那么就不能体现目的论本身所意味的因果关系,目的论与本体论也就没有根本的区别(“即使人们承认这个主体有这样一种为了世间存在者而实存的方式,但那种本体论的统一性毕竟由此还并不马上就是目的统一性,而且绝对没有使得人们可以理解目的统一性”)[2]AA V 394-395.。自然目的只能在人对目的进行反思过程中被显明。所以,从批判的先验哲学的角度来看,要真正理解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就必须要突破单纯的经验或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性处理方式,以此避免把目的独断地看作是一种经验实在或者观念实在的构成性原则。
博雅平台也是一个好的在线教学平台,它通过互联网的使用,将课程与在线相结合。博雅平台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学习平台,它包含的学科比较多,能够很好地满足各种学科的学习[6]。它支持在线授课,在线交流学习,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学业评估。这种教学方法对我们的学习有很大的好处,也有了很多的可选择的学习方法。博雅平台的使用使学习更方便,更多元化。
在康德看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的合目的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任何一种固定的框架。在第77 节中,进一步地从批判的先验哲学的角度来对人类与自然目的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说明。一方面,自然目的作为理念,虽然归根到底只是对我们的判断力进行调节,但是因为它是在自然界这一语境之中的,所以它总是“看起来”是一条构成性的原则。另一方面,自然目的毕竟并不现实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限制,人更不能由此认识到自然的目的。对于自然的目的,我们只能进行主观的反思。它事实上绝非是一条构成性原则,而只能是间接地对人的行为起调节作用的范导性原则。
正是因为自然的目的本身的内涵是足够复杂和丰富的,所以它只能以一种不陷入任何一歧的“批判的”方式被理解。关键在于超出对立的攻讦,并且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自然的目的。因此,康德指出,我们需要在这两种形式的目的论公式“之外设定”“在经验与理性的那些最高原则的结合(Vereinigung)”[1]AA V 4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谈到了看似跨越两歧的所谓“直觉的知性”。
二、“直觉的知性”的内涵
“直觉的知性”出现在第77 节“人类知性的那种使一个自然目的的概念对我们成为可能的特点”中。康德指出,乍看之下,“直觉的知性”似乎可以被当作是目的论判断力的代名词。因为它与后者一样,都是人类理解自然目的的一种能力。它之所以是“知性”,是因为它似乎符合一般认识能力的特征,即它面对着自然界,以被动接受的方式认识到客观的自然的先行规定。
但是,“直觉的知性”又与认识领域中的一般的人类知性不同。这首先是因为它们二者具有不同的运用机能。直觉的知性本身并没有给予经验的对象,更不对任何客观的经验对象进行形式建构。它只能是反思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它并不能从先行给予的、确定的对象和原则之中直接推出任何现成的东西。通过“直觉的知性”,我们确实能够对自然目的有所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目的绝不被当作现成的经验事物。相反地,它是体现出超越于知性之上的理性的特征。因为它的运作机制是“由下至上”地进行主观的回溯(“上述理念并不是对于知性来说的,而是对判断力来说的一条理性原则,因而只是知性一般而言在可能的经验对象上的运用;确切地说是在这样的地方,在此判断力不能是规定性的,而只能是反思性的,因而对象虽然是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但就连按照理念对它确定地【更不用说完全适合地】作出判断也根本不能,而是只能对它作出反思”[2]AA V 405.)。通过“直觉的知性”式的理性反思,我们得以理解一个超越于自然的机械世界之上的目的,这个目的作为基础为一切一般的知性思维提供范导(“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就必须有不同于人类知性的另一种可能知性的理念作为基础”)[1]AA V 405.。
“直觉的知性”与一般人类的知性之间区别还体现在,在它的视域之下,具体事物(“多”)与作为共相的自然目的(“一”)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样态:用康德的话说,体现了由“特殊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共同构成的世界图景。[2]AA V 406.当我们用一般的知性来进行目的论判断的时候,作为“一”的、整体的、自然目的首先存在,作为“多”的具体事物通过规定性的判断力而被整体目的所规定(“从分析的普遍的东西【从概念】进展到特殊的东西”[3]AA V 407.)。在这种知性所建构的机械论自然观的目的论图景之中,具体事物和整体目的都内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关系链条之中。任何自然之中的具体事物都因为这种链条关系而被归于抽象的整体目的之中,被后者分析推论出来(“我们的知性是一种概念的能力,亦即一种推论的能力,对于它来说,能够在自然中被给予它并且被置于它的概念之下的特殊的东西,会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不一样,这当然必定是偶然的”[4]AA V 406.)。而与之相对应地,在“直觉的知性”所理解的目的论图景中,“特殊的东西”则不是从“普遍的东西”中派生出来,自然目的也并不依照从“一”到“多”的线性过程而发展出来。康德说,直觉的知性“由于不像我们的知性那样是推论的,而是直觉的,所以就从综合的普遍的东西(一个整体作为这样一个整体的直观)进展到特殊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整体进展到各个部分”[5]AA V 407.。
那么到底什么是“从综合的普遍的东西进展到特殊的东西”“从整体进展到各个部分”?康德所谓的“综合的普遍的东西”是指“一个整体作为这样一个整体的直观”[6]AA V 407.,也就是说,至上的、作为整体目的的“一”从一开始就被在其与具体事物的“多”共在的整体关联关系中被一齐给予出来。整体的自然目的(“一”)一开始就因为这种与具体特殊事物(“多”)共在的整体关联关系而获得意义,所以它虽然是包含万有的整体,却依赖于其中的各个部分。自然界中的具体特殊的事物虽然居于整体目的之下,却因其存在而内在地构成目的论的整体。作为整体的自然目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与一切具体事物相互联结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且外在地让后者归于某个单一的、抽象的概念之中。[1]AA V 407-408.
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知性只是致力于某种概念的抽象:它总是要依据某个特征把不同的事物都归于一个普遍的名词之下。所以通过这种概念的抽象,知性虽然确实可以表达某种共同的、“一”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如若可能,无疑必须要以消解和牺牲“多”的丰富内涵的“抽象”活动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总括了万有的普遍的抽象概念本身也会变得内容贫乏,更谈不上完成真正意义上、尊重个别事物之价值的“统一”和共同体。这也是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者批判所谓“知性思维”的重要原因之一。[2]舒远招:《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第21 页。而我们看到,明显康德自己已然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目的论的境域中,他认为不同于一般知性的“直觉的知性”能够不加抽象地就把一切个别事物容纳到目的论的整体结构之中。在这个整体结构之中,个别的“多”一方面固然是从属于最高的“一”的原则,但是它又完整地肯定了个体的意义,因为“多”和“一”共同且先在地包含在一个目的论的共融和整体关系之中。
正是因为作为包含着“多”与“一”的、整体的自然目的一开始就处在与“多”共融、互相依赖的整体关系之中,所以“多”和“一”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必然的。杂多的自然事物必然以绝对的自然目的为旨归,因为这种关系已然预先设定在一个有机体之中了。与之相比较之下,一般的推论的知性所描绘的“一”“多”关系总是以自然界的纷繁复杂的杂多事物作为背景,这些事物作为实体归根到底是互不相同甚至互相排斥的。知性只不过是把它们笼统地归于一个抽象的共相之下,由共相推出。在其间,并不具备预先给定的内在勾连统合的关系,所以仍旧是一种外在的、偶然的关系:到底是整体的目的之下能够推论出怎样的具体事物,完全事先不可得知。康德认为,知性所描绘的自然的实在的整体并不真正地具有“有机性”,而“只能被视为各个部分相互竞争的运动力量的结果”[1]AA V 407.。即使一般的知性宣称事物之间依循一个自然的目的,这种目的论在他看来也是偶然的和矫揉造作的。只有在事先对整体、综合和有机的目的可能性的关联系统有一个全面的概观,自然目的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的统摄才真正地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人如何能够预先得出这种关联系统的全面概观呢?一方面,这种整体关系是一开始就被给出了,而不是先有一个整体目的(普遍共相),进而从它之中推论得出具体事物。所以依照常理而言,这种全面概观不可能是知性能够胜任的,“想象杂多联结中的这样一种统一性对于任何知性都是不可能的(亦即自相矛盾的)”[2]AA V 408.。它只能出于直觉。也就是说,它只能通过未经间接推论的方式直接地被人所接受下来。当然,另一方面,康德指出,它与一般的感性直观不同,它并不完全地是一种被动地接受对象感官刺激的能力,而是自发地设想一个理智的自然目的的理念,所以它又是一种超越于感性之上的“知性”。正是因为这种得出目的论的全面概观的能力既出于直觉而又是一种理智的知性能力,所以综合两方面而言之,康德把它称为所谓的“直觉的知性”的能力:“因为,毕竟直观也属于认识,而且直观的完全自发性的能力是一种与感性有区别的、完全独立于感性的认识能力,因而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知性,以至于人们也可以设想一种直觉的知性(否定地说,就是只作为非推论的知性)。”[3]AA V 406.
对于康德来说,“直觉的知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似乎完全突破了硕士论文到《纯粹理性批判》一再强调的直观与思维、感性与知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极端区隔。一方面,它虽然是“直觉”性质的,但是它因为其理智的特征而具有一种知性的能力。另一方面,它虽然是知性,但是它绝非一种经验认识领域内的建构性的知性,因为它所给出的“产品”绝非一个机械自然观中的因果关系,而是超越于其上的“原型”理念。用康德的话说,它是一种与推论的知性(“作为摹本的理智”【intellectus ectypus】)不同的“作为原型的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它并不具体地与自然界内部的实体打交道,塑造出一种现成的知识和形象,而是预先地给出一种“一”与“多”内在交融的有机目的论的可能图景。杜辛(Klaus Düsing)由此指出,康德的“直觉的知性”直接地呈现出的目的论图景中,整体是作为个体的整体,个体是整体性的个体,整体的目的和具体事物不再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概念,而是在一种既直观又思维的创造性活动中互相成就。[1]Klaus Düsing, “ Ästhetische Einbildungskraft und Intuitiver Verstand: Kants Lehre und Hegels spekulativ-idealistische Umdeutung”, Hegel-Sudien, Vol. 21 (1986) : 105.或如诺佐所说,在这里“具体的东西不再是归于普遍的东西(‘分析的普遍者’)之下,而是包含在其中(‘综合的普遍者’)”。[2]Angelica Nuzzo,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76-77: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the Limits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 Kant Yearbook, ed. Dietermar H. Heideman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166.很明显,康德的目的论构想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描绘出这种有机的整体关系和图景。而从“直觉的知性”在其中所扮演积极角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直觉的知性”是整个目的论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三、“直觉的知性”与先验哲学的基本前提
无论如何,“直觉的知性”还是因为其重要性吸引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在这些学者之中,黑格尔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比如,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中对康德的“直觉的知性”做出的两个主要的判断就很有深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康德式的直观形式与思维形式根本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作为特别孤立的能力而互不相关,因为“直觉的知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他看来,康德通过“直觉的知性”与先验想象力交相辉映,把视角推升到了理念的绝对必然的境界之上,完成了可能性与现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3]TWA II 3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已经意识甚至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而并不像通常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局限于二元的分离(“康德式直观形式与思维形式根本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作为特别孤立的能力而互不相干”)[1]TWA II 305.。
不过,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即使如此,康德的“直觉的知性”虽然致力于会通感性与知性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它摆脱不了是一种“观察的方式”(Betrachtungart)[2]TWA II 326.。如果不摆脱这种观察的方式,不摆脱主体性的反思的立场,则真正的统一、直觉知性的有机统一就绝不可能。因为这种超越于主体性反思立场的终极统一已然超出了人的能力:
尽管康德并不认为它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观察的方式,但是他仍旧坚守这种促使绝对分裂发生的观察的方式;而对此的认识也就变得是随意、绝对有限且主观,他称之为人类的认识能力;而他宣称,理性认识,因为它是有机体,所以作为理性的实在性,是比自然更高的原则,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是超验的。[3]TWA II 326.
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一主观的和人的立场出发的“统一”当然有深刻的警觉。他明确地认识到,“康德局限于主观的范围来设定主客观的统一是极其困难的”。[4]舒远招:《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第20 页。与之相对应地,黑格尔自己的客观观念论的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立场超拔出来,从自在的绝对精神的角度来呈现康德在“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中希望呈现的终极统一的自然目的。黑格尔对康德“直觉的知性”的学说既有肯定又有批判,体现了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贯态度。
除了黑格尔对康德的“直觉的知性”的学说有相当积极的评价之外,当今的学术界对这个学说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派的代表是著名的黑格尔专家杜辛。杜辛在《审美想象力与直觉的知性:康德的学说和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论式重释》中,不仅追随黑格尔对康德的称赞,强调了康德的“直觉的知性”与黑格尔本人形而上学的联系,而且还进一步地通过揭示这个概念所意味的“一”“多”之间的源始统一的关系和“具体的共相”的内涵,指出康德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在他看来,康德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那样,都描绘了一种原初统一为核心的“原型的理智”“神性的努斯”(göttliche Nous)[1]Klaus Düsing, “Ästhetische Einbildungskraft und Intuitiver Verstand: Kants Lehre und Hegels spekulativ-idealistische Umdeutung”, Hegel-Sudien, Vol. 21 (1986) : 104, 106.。杜辛认为,通过“直觉的知性”,康德从本体论的角度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源始统一提供了基础,而杜辛认为,这种思想正是后来的黑格尔所采纳的。
另一派的代表是诺佐。在《判断力批判》的第76—77 节《反思判断力和先验哲学的界限》一文中,他从“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整体结构出发,指出“直觉的知性”这种说法其实内生自康德本人的先验哲学构想,是后者的有机构成。所以它体现了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些本质特征:它同时包含了二歧,而不是用一歧统合另一歧。这种本质特征与后来德国观念论的思想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康德的“直觉的知性”仍旧是一种“批判的”视角下的反思判断力,所以它归根到底始终是“人”的视角下的知性,它与后来德国观念论的“理性”与“精神”完全不同:“我已经论证过,在第76、77 节中,康德呈现了他的先验哲学的巅峰环节。在这里,人的思维或者更进一步说,通过第三批判获得其具体原则的探索的判断的能力最终反思了自身,并且对最为合适的主观特性和条件有所意识。就此而言,黑格尔的解读——即认为康德超越了先验哲学的界限——看起来就被否定了。”[2]Angelica Nuzzo,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76-77: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the Limits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Kant Yearbook, ed. Dietermar H. Heideman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 171.“直觉的知性”是反思判断的功能,人通过这种功能使得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显现。就此而言,“直觉的知性”体现了康德先验哲学的本质特征。它是完整的,不需要任何的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做任何修正和扩展。
事实上,持平而论,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者之所以会重视“直觉的知性”确实具有道理,因为在二元论为主轴的康德先验观念论中,“直觉的知性”确实是一个异数。在第76 节中,康德曾经鲜明地指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分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因为这种区分深刻地根植于先验观念论所描绘的人类知性的本性。人类知性的本性就在于它不能直接从对象中获取知识的内容,而正是因为人的知性不能直观,所以在直接的对现实事物的直观之外,还需要超出现实经验世界之外的知性进行的可能的建构。自然也就会出现现实的世界和可能的世界之间的分隔。[1]AA V 402.但是因为“直觉的知性”沟通了直观和知性这两端,知性和直观两者之间也就不再是互相隔绝的,所以就从根本上使得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得到了统合。就此而言,《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人类的知性的基本定性在此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而“直觉的知性”已然突破了第76 节中康德所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单纯区分。
不仅如此,康德的“直觉的知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目的论乃至于整个形而上学的图景。他认识到,目的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看自然目的和自然界中的一般存在物之间的目的论关系,那么会发现其核心是“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见识不凡之处就在于,他不是简单地把这种关系当中的一个抽象地归于另一个,他在此处所说的“一”“多”关系也已经不是纯粹抽象的共相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他要指出,两者之所以能够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目的论的链条,是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从属于一个意义关联系统。通过这个意义关联系统,两端都具有了对方的内涵和意义。而理解这一先行的意义关联系统正是目的论判断力的关键所在。从这个层面上,康德指出,要理解这一源始的意义关联系统,需要的是一种既非一般抽象的知性思维而又非经验的感性的认识能力。他名之为“直觉的知性”。毫无疑问,康德的这种不惜突破自我的洞见事实上启发了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甚至新康德主义者。如果舍夫(Walter Cerf)说的没错,即为了实现世界的统一,早期的谢林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都在尝试一种并非感性直观的、“理智的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2]Walter Cer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Intu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Essays”, Faith & Knowledge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xii.那么他们与康德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谢林的同一哲学那里看到非常类似于康德“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的整体结构:它由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共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全之下,而谢林更进一步指出,这个有机的整全是真理的标志。[1][德]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石泉、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 页。
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眼中康德通过“直觉的知性”体现出来的所谓理性统一的问题意识虽然具有承前启后的哲学史意义,但是它事实上又与后来德国观念论者的问题意识有根本不同。黑格尔并没有说错,康德的问题意识根植于一个“观察”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康德揭示了,人具有“直觉的知性”这种理解自然目的的主观能力。事实上透过对“直觉的知性”描述,我们看到,康德在处理目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最重视的是人如何理解这一内涵丰富的自然目的,问题背景始终是人面对自然目的时呈现出来的情境。再者,正如诺佐所说,康德“直觉的知性”所意味的统一虽然是一种先行综合的直观,但是它仍旧是在机械论与超越论、现实性和可能性这二元冲突之上给出的。他之所以要提出“直觉的知性”,为的是在这种冲突之上进行弥合和协调。而这显然与后来德国观念论者所说的终极统一的精神和理性本身自在自为地展现自身的绝对真理这一视角完全不同。众所周知,谢林的整全是客观、绝对的无意识的上帝(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在自然界(“被动的自然”【natura naturata】)之中显现的自身,而黑格尔所谓的终极统一所指的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的外化。所以就此而言,他们的基本观点已经与个体理解超越目的这一情境式的考虑不同。事实上,不得不说,从整体思维方式和问题取向的角度看,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已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而“直觉的知性”即使呈现了先验观念论对系统统一的追求,也仍旧必然和后来的德国观念论所谈的绝对统一根本不同。
四、结 语
虽然,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会因为康德“直觉的知性”的反思立场和“观察视角”而把它判定为“主观的”,进而对此加以否定,但是从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角度来看,自我反思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反思的结果是主观的,更不意味着“直觉的知性”所意味着的先行呈现出来的系统统一的整全视野是主观的。不得不说,康德的“直觉的知性”确实体现出了批判哲学不被一般学者所知的形而上学动机:先验哲学并不止于两个世界的分立,而是要指出,这种分立事实上基于一个更为超越、且更为深刻的内在统一的基础。就此而言,“目的论判断力辩证论”中的“直觉的知性”就有必要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但是很明显,康德并没有真正地对“直觉的知性”的思想做更加详细的叙述,以至于它虽然在“目的论判断力”甚至整个先验哲学中扮演了终极统合的角色,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对这种特殊的综合统一能力的运作过程和成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它最多只能作为一个“整全概观”的印象模糊地出现,我们不能再对其做更多的实在性的追问。也许这也正是康德先验哲学本身的格局所决定的:它毕竟不能像后来的德国观念论者那样,对本原的、自在自为地化生万物的绝对统一的实体做直截的描述和呈现。“直觉的知性”也许只能是康德先验哲学中的一个奇特的谜题,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与后来哲学发展的不同本质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