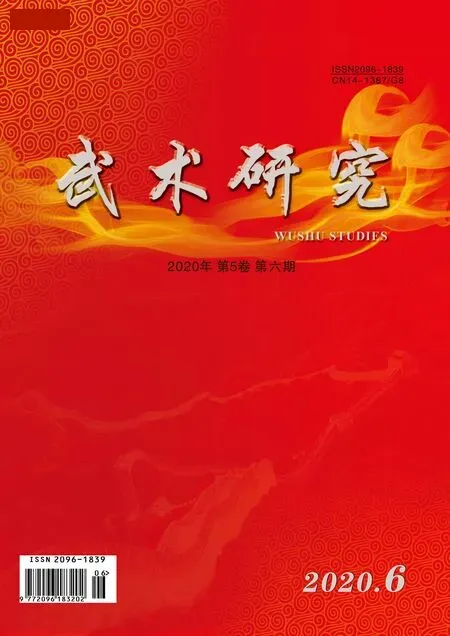儒家身体观对武术精神文化的影响研究
2020-11-24冯仁娇
冯仁娇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遂宁 629000
古代人在没有体育意识的情况下,身体观就是从事体育活动的理论依据。身体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儒家对身体的认识首先是承认身体的重要性,所以才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论断。但儒家对于身体的认识不仅停留在生理上的躯体,更看中身体在心灵的主导下所表现出的社会化的德性,儒家对身体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哲学性。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项技击技术和健身方法,还是一种身体艺术,是中国文化的“全息影像”。本研究关注的是这种身体艺术在儒家身体观的影像下表现出怎样的精神文化特点,以窥探古代人们看待武术活动的文化心态。
1 儒家身体观——“践行”的身体哲学
儒家对身体的重要性、完整性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不同历史时期权力和文化的影响,儒家身体观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如:先秦时期,在“六艺”教育体系中,孔子提倡通过礼、乐、射、御等身体活动达到教育目的,侧重于通过身体的形态、身体的思维、身体与环境的关系表现道德秩序、伦理纲常和政治倾向;晋至唐时期,儒家思想在与佛、释、道的冲击与融合中,更加注重身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礼仪对于身体的束缚有所减轻,追求精、气、神健全的身体,身体被看做一种隐喻,是社会道德规范、政治权利的载体;唐以后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仍然强调通过身体活动实现“修身”的自我完善的目的。通过禅定、坐忘、静坐等活动形式,达到豁然贯通的精神境界,追求身体从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实体达到无身的理想生命状态。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儒家与其他文化学说、宗教流派冲击与融合中,对身体的认识也不断的变化,但其内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儒家的身体观可概括为主张身心相合的“践行”身体哲学,形成了作为政治权利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以及作为隐喻的身体。[1]身体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工具,被权力和知识赋予各自时代的“目的”和“意义”,[2]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超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治平之论,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
2 儒家身体观对武术精神文化的影响
体育文化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物质文化维度、制度文化维度和精神文化维度,其中精神文化是内核。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影响和支配着任何一个文化领域,儒家身体观也影响着习武者对武术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通过武术运动表现出的艺术文化。
2.1 躬身践履的德艺修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重行”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对于道理、知识的体验与把握在于实践,而实践的基础在于身体。武术非常重视习武者的“悟性”,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讲的就是以口传心授的传统武术对精思笃行的重视,是对儒家“践行”身体哲学的具体表现。师父的个人经验体会来自于“时时操练、朝朝运化”的结果,手把手的教导远甚于经验之谈,拆招、喂招都是在模拟实践中提高技击技术。拳谚“拳练千遍,其义自见”,是达到着熟、懂劲、阶及神明的必经之路,要掌握娴熟的技艺必须将师父的经验教导经过身体的反复习练,才能转化成自己的功夫。作为一种身体艺术,最真切、最可靠的个人技艺是在实践中体验得来的,需要个体经年累月的躬身践履。通过实践塑造出的不仅是娴熟的技艺,还有习武者的道德人格,从纷繁复杂的拜师礼、象征着五湖四海为一家的抱拳礼开始,到习武锻炼中磨砺出的意志品质,形成了一整套武德修养的行为实践程序。尊师重道、门规戒律都在习武者日习而不察的日常行为中内化为习武者的价值认同和生命态度,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
2.2 承担社会责任的侠义精神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讲究“克己复礼”“爱人”,遵循忠恕之道、中庸之道以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修身,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齐、治、平是修身的主体推衍,[3]也是修身的目的。武术悠久的历史文化源于其不囿于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活动,而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进入到更为广阔的场域,表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习武者忍受三膘三瘦的形体变化,经历三伏三九的刻苦磨砺,希翼在技艺上有所建树,不仅仅是追求一种技击技术和养身方法,而是因为武术可以实现理想抱负、匡扶正义,是修身的方式和途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当各方面矛盾平缓时,它辅助朝政,“治四海如磐石之安”;当社会矛盾激烈,则又荡敌护国,“替天行道”。[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民间武术虽然与军事武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与否。民族危难之际,习武者以“恢复中国为志”,突出民族大义,给予了无数习武者力量与责任感。
2.3 武学境界的整体意识
儒家对于身体完整性的重视也表现在武术运动的协调性上。田径被认为是运动之母,其中各个项目也要求运动员的上肢与下肢协调配合,但主要是在于脚或手,而武术则强调牵一发而能动全身的整体协调性,其中包括内脏活动、呼吸吐纳以及精神气质。西方的拳击、击剑、摔跤等项目在技击对抗中强调勇猛快捷、直拳直脚,而传统武术则讲究纵横往来、圆转变化,套路表演更是重视全身上下协调、龙腾虎跃、起伏跌宕的节奏变化。儒家认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反对“一己之力”“匹夫之勇”,不讲“怪力乱神”,形成了武术倡导以“四两拨千斤”的整劲和巧劲的技击特点。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外在物质力量,高超的武技需要不断的钻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道德修养的提高,也贯穿于整个习武生涯中。外在的物质力量和内在的侠义精神,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了传统武术中特有的最高武学境界,驱动着习武者穷尽毕生精力去接近、去实现,诠释了儒家身心一体的整体身体观。
2.4 “范我驱驰”的竞争意识
王良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善御之人,曾两次为赵简子的宠臣嬖奚驾车狩猎,因按规矩驾车一无所获而遭受非议,又因不安规矩驾车收获颇丰而获得赏识,王良以“不贯与小人乘”为由“请辞”,后世对王良择善而居的个人品质大加赞赏。这个记载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范我驱驰”的故事反应了儒家看待身体的“中庸之道”,教化人们身体活动应有节制,强调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在众多武侠文学和当代的影视作品中就能看到,竞争的双方,一方总是占有绝对优势,与人出手大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逼不得已。切磋时应点到为止,赢得漂亮,还要让对方输得体面,方能显示出这一方德才兼备、德艺双修的谦谦君子形象。如果在竞争中险胜了对方,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即使赢了也不光彩。在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下,推崇“君子之争”,体育活动、娱乐活动要符合礼制,身体活动更像是个人社会化的自我修行方式。
3 结语
儒家身体观对于武术精神文化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传统武术重视实践使得武术技艺的深度得以挖掘,但是忽视经验的总结与整理也使得武术缺乏理论的指导,荒诞经验之谈大行其道,以致现代武术的发展难以向科学理性迈进;中庸、礼让的倡导下,武术作为体育项目的竞争性、娱乐性遭到了遏制,缺少“制度思维”使得武术在现代体育项目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传统身体活动项目成为蘸满礼仪的文化活动,在发挥体育的德性教化和身体训练双重功用方面,同样具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5]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最积极进取,最主动作为的一部分,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的文化基因。受其影响,武术精神的博大弘深远远超过了武术本身。武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孤立的技击技巧和健身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6]只有在整体上充分把握武术的特点,才能继承和发扬武术的优良传统,促进武术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