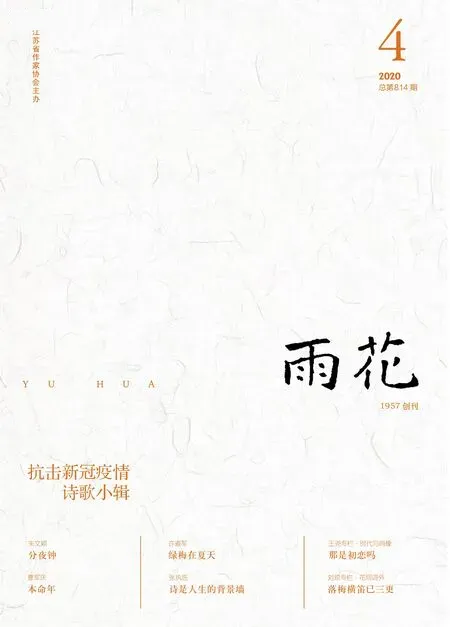那是初恋吗
2020-11-22王尧
王 尧
冬妮娅,那个遥远国度的少女,留在了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阅读记忆中。
和许多人的感受一样,冬妮娅几乎让我失魂落魄,我甚至觉得我第一次“失恋”是保尔与冬妮娅两个人分手的时刻。冬妮娅哭了,她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我一直记得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我让自己代替了保尔,我看着冬妮娅远去的背影,我也哭了。这一年,我读初二。在这之后,我读到了《卓娅与舒拉》和高尔基的几本小说。卓娅在另一个方向上打动了我,她的气质和我向往的崇高、英雄气概吻合了。
多少年以后,我去俄罗斯访问,终于去了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我在那里看到了巨大墓碑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在向这位少年时代心中的英雄致敬时,我也凭吊了那个叫冬妮娅的女孩。少年时代,在我心中与冬妮娅和平相处的还有另一个苏联女孩卓娅。我找到了她的墓地,卓娅裸露着只有一只乳房的胸脯——她的另一只乳房被德军割掉了。卓娅像天使。她哥哥舒拉安息在她的对面,墓碑上的舒拉是位帅气的小伙子。卓娅、舒拉、冬妮娅和保尔,是我少年时在书本中最熟悉的苏联朋友。
我年少时在报纸和广播里听说的那个王明和赫鲁晓夫,也葬在新圣女公墓。另一个书本上的朋友是高尔基——我读高尔基时,还不能能完全读懂他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他的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边上。在新圣女公墓,我见到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果戈里,还有柴可夫斯基。我们又驱车去了托尔斯泰的庄园,他的苹果树上还长着苹果。在读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高尔基时,我还不知道有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人与我的少年无关,如果他们曾经在我的少年生活中出现,我不知道今天的我是不是另一番面貌。
在一个禁锢的年代,我对异性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我的阅读。我读到了《苦菜花》中的母亲,读到了《林海雪原》中的白茹,读到了《红旗谱》中的春兰,读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银环,还有《三家巷》中的区桃和文婷。我很奇怪,我们村上的一位青年从哪里找来的这些书。这位老兄抽烟,我没有办法给他送烟,谈好的条件是我用一盒香烟屁股,跟他借一本小说。如果大队开会,或者放电影,那便是我收获最多的时候,在会议或电影散场后,我捡起地上的香烟屁股。我在小说中认识的女性,几乎都与革命有关。我后来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看到少剑波深情地拉起白茹的手时,还是很不习惯,这个动作把我阅读中关于他们俩朦朦胧胧的美好打碎了。
我感到好奇和诧异的情节,往往是在我有限的生活经验之外的那些。有一天,当那个穿着裙子的上海姑娘在大桥上出现时,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惊艳”了。这个女生并不漂亮,但她的花裙子像一阵风刮过。那一年,正是五月的大水过后,所有的麦子都泡在水里,一直到夏天,整个村子里都散发着霉味。这个穿裙子的姑娘到桥上乘凉时,还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她用的雪花膏和我们这边不一样。在这个姑娘离开之后,村上穿裙子的人多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教室里也坐着穿裙子的女同学。
那个叫小朵的女生到我们初二班插班时,是穿着凉鞋过来的。我们男生女生穿凉鞋的很少,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都是穿木拖鞋,平时我们都穿布鞋子。小朵的爸爸到我们这边的邮电所工作了,她跟着过来。我和她并没有交往,有一天她发现她坐的是不久前死去的同学的座位,在放学时突然大哭起来。我是班长,就请示班主任同意,跟她换了位置。她问我,你不怕死人?我说,一起长大的,他不会吓我的。这个同学是肺结核不治去世的,他在课堂上咳嗽时,我们也没有人想到要戴口罩。那时我们也没有口罩,个别有手帕的女生,最多在他咳嗽时用手帕捂着嘴巴。男生很少有用手帕的,偶尔流鼻涕时,就用袖子的内侧擦一下。衣服反正不是很干净,鼻涕的痕迹只有在洗衣服时才会被发现。小朵觉得应该送一块手帕给我,一次放学的路上,她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新手帕给我。我吓得加快步伐往前走了,但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这个插班的女生是有点漂亮。我在一篇未刊稿中,记录和虚构了我对她的印象:其实我并不能说出她哪里漂亮,你甚至说不出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什么样,但你对她的长相无可非议。一年后,这个插班的女生又到另一个地方的班级插班了。她给我写来了一封信,我记不得内容了。我给她回信了,也记不得内容了。再后来,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忙着准备考高中,我们以温暖的方式结束了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感情。再过了几个月,我拿到升学考试的作文题目:读书务农,无上光荣。
我到镇上读高中,开学第二天,就和镇上的一个女生发生冲突了。记得我们的“交锋”是这样开始的,我的话尚未说好,她就跟在后面学舌:女同学也是半边天嘛。我从乡下来,还说着土话,镇上的同学基本上说着他们认为是普通话的普通话。在她学我说话后,我朝她瞪了一眼。当时,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学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讨论班主任老师在班会上的讲话。我被指定为班长,正在小组会上发言,发表如何度过高中两年的想法。虽然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担任班长,但上高中后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仍感到意外。我们高一(2)班城镇同学特别多,他们对我这个来自乡下的男生当班长也很惊讶。因此我对别人的反应非常敏感。我瞪了眼睛后,她又朝我笑笑。我也只能保持风度,没有再吭声。多少年以后,同学叙旧,说到这位女同学,我想起她的笑,真的是笑得很甜。
她坐在我前排,但彼此并不多话。她估计我对她有些不满,便找机会与我和解。一次下课,教室里剩下几个同学,她回过头来对我说:班长,我以前好像见过你,在你姑妈家什么地方。我印象中,也感觉在姑妈家门见过她,和那时比,她只是轮廓大了,是个姑娘了。姑妈在镇上,但和她家不是邻居。镇就那么大,也许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友好地说,可能吧。我接下来就不言语了。
我发现她很能够团结其他女同学,男同学也愿意和她说话。那时,我还不知道用“校花”这个词,现在想想,她确实是个校花。她落落大方的举止,在全年级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她又娇气。好像老是捏着手帕,到了劳动课上,手帕就不离手了。抬大粪时,一只手靠肩顶着扁担,一只手用手帕捂着鼻子,粪桶一放下,她就逃之夭夭。我想批评她,看她的模样又好笑,就不说什么。心想,天下没有喜欢闻臭味的人。
那时的学校一片政治氛围,各类政治活动特别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出专栏,过了几天又是讨论会。当时班级排演文艺节目,我记得是说唱表演,叫“新事要用火车拖”,歌唱新生事物。她参加演出了,形象不错,演得一般,而我原来以为她是个文娱人才。看来她的特长是体育,在操场上英姿飒爽,铁饼拿了名次,短跑也不错。当时她已经是校篮球队队员,我去看过一场她们的比赛。不久听说她在谈恋爱,很快又听说是别人在追她,她本人并不同意。我非常奇怪我会在意她的事情。一次下课,她看我在那儿发呆,问,你在想什么?我说,不知道。她像知道似的朝我笑笑。
我觉得心里烦躁。又有同学说,坐在你前面的那位同学在谈恋爱。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是班长就得管。就在那几周,学校发现一些同学在偷偷传看手抄本《一个少女的心》,班上不少同学看了。有个同学问我看不看,我问写的是什么,同学说,写一个少女发育的故事。我赶紧拒绝了。在团支部会上,看的同学都作了检讨。其中一位说,要向某某人学习,给她看,她拒绝了。班主任和校团委老师表扬了她。散会后,她对我说,你不要总是把我当坏人。这一年招收空军飞行员,政治审查时,凡是看过《一个少女的心》的同学都没有通过政审。学校政教组组长到我们班上讲话了,他说,现在就看黄色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做了飞行员,能不能禁得起国民党女特务的诱惑呢?我们面面相觑。老师又说,你们都要吸取深刻的教训。
因为闹地震,我们班级一半同学回到乡下上课,我也回到村上了。一个星期天,我乘船到镇上有事,船经过油米厂码头时,她正好在码头上汰衣服,她捧起脸盆时,我们彼此看到了对方,犹豫片刻,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喊了对方的名字。船已行远,我回头发现,她还在码头上看我们的船远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女同学目送我的眼光。
粉碎“四人帮”时,我们已是高二上学期。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很多,语文老师拿了一篇《解放日报》上批狄克(张春桥的化名)的文章给同学们看,问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读了以后举手回答,指出文章有几处语法上的问题。语文老师说非常正确。隔天,她悄悄给我写了封信,说很佩服我,并要我为她随信附上的作文提些修改意见。她的字像小学生写的一样,没有她人漂亮。过了几天,我按照她约定的时间和地方,在校园的一角,把修改后的作文交给她。她已在那儿等我。考虑到影响,我转身就走。她说,就不能说几句话吗?我们都开始考虑高中毕业后的前途,她问我的打算。我告诉她,听说要恢复高考,我想上大学;如果不考,就去当兵。她说她可能要插队,又说到时我们再联系吧。她和我开始变成了“我们”。就在这个星期天,我回到村上,在电影场上突然发现她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在一起看电影。换片时,杨同学把我喊到她们那边去坐了。我忐忑不安,听得出她的呼吸声,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在银幕上。
临毕业前夕,要好的同学之间流行到各家串门,同村的同学把她邀请到我们村上。我们家是兄弟仨,妈妈看到有女同学来特别高兴。她临走时对我妈妈说这儿不错,妈妈说你就做我的干女儿吧。她停了会儿,说好的,走时恋恋不舍。毕业离校的前一天,镇上一个男同学请我们几个吃饭,她也去了,还喝了酒,大家闹得很凶。男同学的爸爸过来,说了一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就散了,在同学家门口,她向西,我向东。
毕业时她还没有定下到哪儿插队,说定下来再告诉我。过了些日子,得知她要到离我们镇很远的一个在海边的国营农场去。我惊讶得不得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她可以插队在本公社某个大队,但农场是国营性质,可能对她以后的出路有好处。我和一批同学赶到镇上为她送行,她站在大会堂的台上,戴着大红花。她看到我们几个了,朝我们挥手。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来信,还随信附了让我回信的邮票。我在回信中对等地用了一个字来称呼她。我记得是母亲养秋蚕时,她从农场回来探亲,特地赶到我家看我。我在另外一个村子做代课老师,接到电话,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回家。她被海风吹得黑黑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的神态好像期待我能够拉一下她的手,但我如同木瓜一样僵硬地站着。等出了庄前的大桥,我和她挥手告别时,我才醒悟过来。
我们频繁地通信。她后来说,那些信件是在她最困难的日子里最好的慰藉,如同当年坐在我的前排读书一样。我相信这是真的。在我落榜的第二年,她从农场回来,我们好像就没有再见过。那年春节,她托人给我带来一盒自己家做的炒米糖,后来就没有再联系。我知道这是她和我告别的礼物。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时,她到村上来送我了。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话说,我说不出把她送到桥口时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对此事最失望的可能就是在九泉之下的外公了,他离开人世时可能还认定这位姑娘是他的外孙媳妇。许多年以后,妈妈告诉我,她来送我时,在她面前哭了。
中学毕业二十年时,一位同学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回去,我说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就说起班上同学的近况,又说高中时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现在如何如何。我印象里最漂亮的女同学就是她。同学说不是她,他说出了另一个女同学的名字。我想,也许没有“最漂亮”这个概念,每个男生记得的大概都是自认为漂亮的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