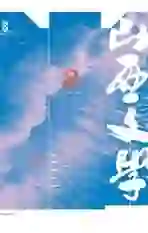大湖
2020-11-19蒋冬梅
鱼把头站在冰面上,一千年前也这样站,一百年前也这样站。他是查干的一只鱼鹰,心里装着整个大湖。
有人看见夏季湖面曾搅起的巨浪,传说一条从未见过的大鱼和鱼叉对峙过。
人人都在期盼着大鱼,可今年冬捕的重头戏,师傅决意不来了。
刚入冬,师傅就带着另一队人马,跑内蒙了。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鱼把头说:“查干,就交给你啦!”这让把头想起,大鸟把小鸟喂养大,就离开了那片树林。
寒冷把天地和大湖冻在了一起,策马狂奔的队伍像刀剑割开北风,车马从切口里闯了进去,马的影子跑在冰里。马匹背对着光亮,把头也背对着光亮,哈气升腾起来,像窜出的火苗。赶在太阳升起之前,人马齐备、大战在即。马嘶,狗吠,号角声里,把头像一个将,统领着一切。
把头趴在冰面上,寻找冰层里珍珠一样的气泡。他看不见鱼,但鱼的呼吸会暴露自己。
“鱼知水性,人知鱼性!你喘气儿鱼也喘气儿!”鱼把头想起了很多年前,师傅趴在冰面上,寻找大鱼吐出的气泡。寒冷冻不僵男人的血性,师傅的脸冻得皴裂流血了,他让把头朝他脸上喷一口烧酒,再使劲朝大湖喊一嗓子,就又朝冰面趴下了。
今年的冰层从未有过的奇异,鱼呼吸的气泡都被冰层深深地锁住了,透过冰面看到的尽是形状怪异的花纹。这些异象让人们对大鱼的出现,更加想入非非。
供桌,敖包,鼓声,铃音,口口相传的经文在叩问,一千年前这样叩问,一百年前也这样叩问。
风吹得非常烈,把头的心有些乱了,可他不能让人看出他的乱!
师傅带着把头上冰很多年了,每当冬捕遇到情况时,有师傅在,把头的心就落了底。“公家把这个事儿交给咱,咱就得担得起!”年年冬捕,师傅都说这句话。
冬捕前的那些天,师傅天天带着把头到冰面上探冰。查干渔场多少口子人呢,一半的日子要指靠着冬捕。一场冬捕在哪儿凿开冰洞,就像打井找水眼一样重要。他记得冬捕前的很多天,嗜酒的师傅從来滴酒不沾,直等到选定冰眼,凿出湖水的那一刻,师傅才拿出酒壶,狠狠地灌起来,他抓着酒壶的手,都在剧烈地抖动。
这一刻,把头的手也在抖动着。
冰面上是有山丘和低谷的。把头辨识着那些矮小的山丘,一脉水波拱起一座山丘,山丘下将喷发鱼的讯息。从前他拿不准水眼的位置时,师傅总是说:“你一定得信自己,一半经验,一半信,才能找到鱼!”把头终于选定了一处冰层,坚定地砸下鱼铲,在冰花的绽放里,叩问大湖的安静,钻木取火般凿开一眼泉,黑色的湖水涌出,像新鲜的血。
凿出的冰洞一字排开,四匹马拉着绞盘,拖动大网向湖中布阵。水冻成透明的玉,数尺之下能看见网在游,把头跟着网,像追着一只鸟。大鸟张开翅膀,自由舒放,仿佛要揽过整个大湖。网入大湖纵横成田,鱼像秧苗布立其间,每个网眼只有四寸大,拦住大湖也放过大湖。
人、马匹、狗在冰上踢踏,纷乱着破晓的早晨。几十号人在冰封的大湖上耕耘,索取在夏秋肥美起来的大鱼。太阳照在人头顶的时候,该起网了,鱼儿带着热气,被网裹挟着出水。把头抱着第一条出水的鱼,在镜头面前笑着。人们欢呼雀跃,将把头抬起,抛向空中。但把头知道,更多的人在翘首等待传说中的大鱼。
把头拎着一瓶烧锅酒钻进帐篷,像师傅那样,两手颤抖着拧开酒瓶,狠狠地灌了下去。刚才在镜头前的笑容,渐渐褪去,他没有把握捕到那条大鱼。
外面的锣鼓声,人声,歌舞声,一浪盖过一浪。把头知道,那些热闹不是自己的。他寂寞地坐在师傅坐过的位置,咧开嘴,用牙齿又咬开一瓶酒的盖子。
他想起有一次,同样没有像人们盼望的那样,捕到更多的大鱼。那时把头还年轻,有些垂头丧气的,师傅递过来的酒他也没心思喝。
师傅独自喝了几口,突然给他讲起了从前的事:“十六岁那年,听人说黑龙江有大鱼,我们就从白洋淀往那奔。没想到半道上,火车让洪水拦下了,我们就在查干湖下了车。谁承想,一下车就在这停了一辈子!人都说一场洪水把我拦下了,其实是大湖把我拦下了。”
把头叹了口气:“人人都稀罕大鱼,你捕了一辈子鱼,可谁知道大鱼在哪呢!”
“你记着,人,活不过湖!大鱼,一直都在湖里!”
那一刻,两人立在查干的湖心,像大鱼游弋在无边的湖水。
【作者简介】蒋冬梅,从事法律职业。作品散见《小说月刊》 《短篇小说》《天池小小说》等报刊,并入选各类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