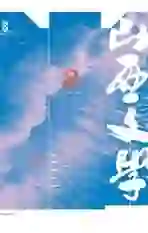一只大白鹅
2020-11-19黄亚琴
苏先生是一个不及格的四川人,他吃不了辣。
漫长的下午里,我正坐在自己小小的文具店里,用薄薄的刀片在一支铅笔上小心地削出蝴蝶翅膀般的轻翼。屋外的轻风不时地跑过来晃晃我的绿色透明门帘,这样过了许久,一个留着胡茬的中年男人挑开门帘单露进脸来,悄然问了一句:“请问朝阳小学怎么走?”我抬起一根指头朝右指了指。“谢谢,多有打扰!”他盯着我削出来的薄薄脆弱的铅笔屑,面有愧色地说了句。我冲他微微笑了笑。
后来,那个蹙着两道眉的问路先生常带上他儿子来我的文具店买一些小东西。他儿子站在我的被区分成不同价位的货架前总是难以一时下决定,他也不急,站在一旁微笑着慢慢等。顺便转眼打量我琳琅满目的商品。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他笑呵呵地自言自语道。
有一次,他儿子选了个1.5元的笔,他给了2元钱,我翻来翻去找不到零钱。他说,就这样吧,以后弄个二维码,现在满大街都是了,方便多了。说着拉上儿子的手就走了。我便记住了他们,总等着下回把钱还回去。
再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渐渐熟悉起来。
熟悉之后的某一天,望着挂在屋檐上断不了的水珠子,他说,看见我削得轻薄的就要断掉的铅笔屑,心里总悬着件事,逼他再过来看看。“那样心细的人,总该会让人放心。”他不知所以地跟了一句。
苏先生其实是很笨的,他直到第四次来才在别人的提醒下知道了我的缺陷。他面露愧色地对我说,“哎呀,对不起呀,我不知道是这样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也是个四川人。不介意地对他笑笑。他却慌慌地拉着儿子的手匆匆离开了。我以为他不再来了。
没想到那周五,他又举着一把伞躲进了我的小门店里。彼时,外面的雨下得正大,我正用削得细细的铅笔在我卖的田字格上小心地写下一个个汉字。
他像一团柔软庞大的云朵闯了进来——他的伞是白底,细看,还有朵朵淡蓝的花。收起伞,随手立在门口,顺着伞滑下的雨水洇湿了一小块台阶,这块湿像是走向夏天的圆太阳,一点点扩大着,看得人心里忽地生出些暖来。他把一张温热的脸凑过来看我写字,说了句,“呀,真好看!”好像,我已经跟他很熟。也好像,他已经忘了我是个哑巴。我报他一个久久的笑。
盯了一眼墙上的表,离他儿子下学还有二十多分钟,他来得有些早了。可那天以后,只要来接儿子的时间充裕些,他基本都把这些零碎时间打发在我这里。
我则坐在玻璃柜台后面,用各种表情来回应他多变的谈话。
后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听得懂吧?”我白他一眼,把脸扭向别处。不屑回复他的质疑。
正是这些放学前后的断续的碎片时间里,我们之间慢慢熟稔起来。
他倒聪明,安排得很妥当,儿子冲出校门直接来我的店里。如果他还没来,他儿子会在我的门前稍稍等一等。出于礼貌和对苏先生的好奇,我常常趁小朋友涌进来正忙乱的空当里走过去塞给他儿子一把瓜子或者一些小零食。那小孩腼腆又礼貌,刚开始总不肯进门来。
说也奇怪,每天到我这里买文具的小孩很多,可我从来没有因为哪个孩子而想起自己的孩子。当我第一次看到苏先生的儿子立在我门前朝远处张望的小小背影,就想到了我那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所以,我总是忍不住多关心他一下。比如摸摸他的头,把他从寒冷的外面拉进屋里。大概有半年多的相处,他才不再低着头和我讲话。他害羞得不像个男生。熟了以后,我用手语示意他。也许他懂了,嘿嘿地对我傻笑。
他一开口就叫我“胡阿姨”,我正给他翻弄卷进衣服里的红领巾,瞬间惊了一下!第一次怀疑自己判断错了别人的话。
我想了好几天。后来想起来是自己在写字的小本子上标了名字的。想了一回,我就暗笑苏先生的认真。
我总怀疑苏先生喜欢和我说很多话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个只会笑的哑巴。不过,我也乐意看他说。反正,我还因此从他身上赚了一些钱——他不时在我的小店里买点东西。到底是在他身上赚得多还是在他儿子身上赔得多,我从来没细算过。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赚得多,因为不管是卖还是送,我都是开心的。
一直以为苏先生是个爱说话的人。他什么都肯说,比如有一次,我指着他儿子写在课本上的名字:苏忆川。当时刚开学,他买了我的书皮,包好后直接往上写了名字。我只是想告诉他川字写得不规范,不是由三个竖组成,他爸爸却给我解释起了他的名字。哦,我是四川人,在这里上的大学又和他妈妈结婚留在了这里。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他的籍贯和姓氏。暗自慨叹,竟然没从他的口型和语调里辨认出“川味”来,也不知道是自己的“技能”退化了,还是苏先生的普通话太过标准。第二天他来了,趁着他不着急的空当,我在纸上写下巴中,指指自己,他则兴冲冲地说他是攀枝花人。回他笑的那一刻,我稍稍遗憾自己和他的老家离得有些远。不然我们可以分享更多共同的话题。
他再来时,我就把托人捎来的老家的小零食拿出来分享给他。在我执意塞给他这些味道大致相同的食物后,他竟然因为辣而流了满头汗。我心里轻轻笑了一下,想这苏先生是不是地道的四川人,竟然怕辣。
北方的冬天總是冷,比如南方的水,心肠总是软的,在北方却是冰冷的硬。手不想往出掏,脸上像贴了冰,我的高跟鞋踩在结实的冰上像针遇到了铁。可我喜欢这样的干脆冷酷,往往穿了高跟鞋走在坚冷厚实的冰上,硬硬地扎下去,觉得自有一种痛快。
就是那样的一个下午,苏先生提了一袋梨跺着脚进来了。他的嘴唇干裂着,像个地形复杂的地图。
“还是你这暖,”说着他把梨丢在柜台上,拿手伸到煤球炉子上烤。
这么冷的天,要梨干啥?我瞥了一眼看上去凉飕飕的梨继续盯着电视。
“冻严了,哪也是冰,要人命哪。这会儿要在老家裹个毯子都能捂出汗哩。”他絮絮叨叨地谈了一些,清了清嗓子,起身摸起一个梨啃起来。明显是不想活了。我过去直接从他手中把梨夺走。他瞪圆的两只眼睛跟着我的手把梨削了皮,切成小块,又滚在了热气腾腾的开水里。捧着泡在碗中的梨,蹲到炉子前,看着他滑稽的样子,笑着给递过去一个勺子。他嘿嘿笑了一下,不好意思的样子。
“真是个贤妻良母啊。”
苏先生的比喻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我白了他一眼。外面放学的队伍已经壮大起来,可是天太冷,家长不允许孩子再来我的店里消磨时间。正张望着,忆川闯了进来,我搓搓他冻得通红的小手举到苏先生眼前,怪他也不给孩子戴个手套。
苏先生又只是笑笑。嘴角两边荡起几重波浪,白白的牙齿像是刚刚降落的雪,让人怨恨不起他来。
忆川看见冒着热气的梨了。我给他一个勺子,又挖了一勺蜂蜜添进去,他就挤到爸爸旁边开始埋头捞梨吃。
“真不公平呀!”
苏先生看我给忆川添了蜂蜜觑着我笑着说。
我摸了摸忆川的头,让他慢点吃,他的头发已被冻得冰冷坚硬。
“爸,你啥时候也能像胡阿姨一样对我这样体贴?”
这孩子,别看每天在外人面前安安静静地,心眼明亮着呢。我捏捏他的小耳朵。
“啊呀啊呀,这又不是八戒的耳朵,肉一点也不多,不好吃的。”他故意逗我。
“别老说胡阿姨好,说也没用,快吃你的。”
我拿起柜台上的小本子卷起一个筒来敲了一下苏先生的头。
他故意捂起头,斜眼对着他儿说,看见了吧,胡阿姨也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忆川则笑得稀里哗啦。
忆川的头发很旺,可脸总看上去晦暗。冬天的风一刮,人更显得苍白瘦削。我总对着苏先生叹气,让他看别人家养得白白嫩嫩的孩子。苏先生不当回事,却反过来责怪他挑食。
“你做的难吃死了。”
两个人又开始了拌嘴。
我走到中间,瞪一眼苏先生,他知错似的嘿嘿笑着把话题绕开。
苏先生似乎像我一样很怕这北方冬天的寒冷。那两天又刮北风。接近中午,苏先生裹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挤进了我的小店里。
“呦,哪里来的大白天鹅。”
我笑着努嘴望他,心里说着这句嘲笑的话。
“呵呵,南方飞来的大白鹅!”
我怔了一下。觉得这苏先生也真是可爱至极。走到炉子边,把下面的风门开开好让火更旺一些。
也许我们同是外乡人,加之又是半个老乡的缘故吧,我总感觉和苏先生之间好像有条看不见的结实的线把我们拉扯起来,时远时近却也牢固稳定。
北方的冬至兴吃羊肉胡萝卜馅饺子。日子近了,路边卖羊肉的多了起来。我也跟着房东学着调好羊肉馅包了一些饺子。冬至那天,我把煮好晾凉的饺子装进快餐盒里,塞了满满两盒让忆川提走了。
下午放学的时候,忆川又跑来向我告状。
“阿姨,你给我的饺子都让我爸抢着吃了,全吃光了,晚上都没得吃了。下回我就在你这吃吧?”
忆川边说边舞动着小手。
“写作业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积极呢。”
苏先生抢白。
我给忆川装了两个烤红薯让他带回去。
当晚把剩下的羊肉馅全包完后冻起来,明天中午正好可以让他们带回去煮了吃,这样想着,安心睡觉。
其实苏先生给我的东西也不少。
糖炒栗子,热猪蹄,熟牛肉,猪耳朵,石头饼,街头的炸油糕……他常买了这些东西往我这里带。我不太喜欢肉,可他每次执意放下,后来我的冰箱里总能找到他带来的食物。仿佛他的生活也是被这些七零八碎的街边小吃补充完整。忆川的瘦弱也就不难解释了。
也许苏先生是想减轻我的生活负担吧。不管怎样,我也在努力想办法报答。而这样的回报往往在忆川身上。
比如这次去进货,我专门给忆川选了个柔软宽大的书包。他的那个乌龟壳一样的书包已经不时兴了,会遭同学们笑话。
背上书包。忆川站在那里说:“手套,口罩,书包,有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就是这世界上比有亲妈还幸福的人了。耶!”
苏先生敲了一下他两根组成v的手指。
“我给你买那么多东西就不幸福了?”
“阿姨,你看我爸。”忆川噘起嘴向我告状。
我笑着刮刮他的小鼻子。
这样挺好的。我们三个人的友谊那样轻又那样暖,像是冷冷江河中同挤在一条船上的三个难友,互相明白各自的隐忧,难以抵挡的依赖是自不必说的。不知为何,我忽然会有这样的感觉。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往前推进。冬天完了是春天,春天完了是夏天。忆川一点点长高起来,脸上的笑也多了。人多的时候,他还能帮我算账收钱,替我回答顾客的问题。除了做买卖,我还会抽出时间做很多的美食,给忆川带走或者看着他在我的店里消灭掉。
我看你还是给胡阿姨当儿子算了。苏先生总这样说他。
好呀,好呀。
忆川也总是不客气地回他。
我则搂住忆川的肩头望着苏先生“告诫”他:没问题!我看这样挺好。
苏先生就哑着嘴不說话了。
那天的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正是中午放学时分,门前小小的巷子像煮开的沸水。小文具店里挤满了孩子,他们指指点点挑挑拣拣地买东西,我一边收钱,一边帮他们装物品。正踮脚探着靠墙货架上的贴纸时,我瞥见外面两个人在打架。隔着层层叠叠的人,我看不见里面打架的人。正纳闷着,从中间飞出来一顶帽子,那是一顶我很熟悉的帽子——苏先生说他有鼻炎,离不了。我扔下手里的东西撒腿就往外跑。
苏先生已被一个胖大的男人按到了地下用拳头捶,他快速抓挠的手指像多脚的蜘蛛,只是被死死压住使不上劲,我出了一身汗,着急着要进去帮忙,柔弱温和的苏先生怎受得了这个。可我单薄的身体一次次被围观的人群弹回来,我张大嘴巴歇斯底里。我所有的努力都被嘈杂的人群淹没了。
那个胖男人最终被拉开,嘴里骂骂咧咧着:谁让你孩没妈了,就要说咋啦,有本事就找个……
慌乱中,一脸血的苏先生被救护车抬走了。我着急地捧起几个小孩的脸,以为是忆川,可最终一无所获。
那个下午像是被拉长了,坐下起立看钟表点点滴滴地走着就是过不完。我一直在等苏先生的消息,或者哪怕放学的忆川。什么都没等到。屋外的亮光被一点点收走,不知何时,巷子里的灯也渐渐熄灭,我才不情愿地回到小小的出租屋里。
原来忆川只由苏先生管着。即使早猜到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可还是忍不住对忆川又多了一层可怜。
为何这世上的月亮,总是缺的时候多,圆的时刻少?我烦恼地想着。
第二天,我心里仍悬着苏先生的伤情和忆川的着落。半上午,苏先生发来短信:忆川这几天就先麻烦你了。我回他,放心。是的,我都忘了他曾经向我要过电话号码的。我的手机一般只用来看时间,谁会给一个哑巴打电话?他曾想送我一个智能手机,告诉我可以用里面的“微信”收付款或收发信息,我知道那个手机得上千块,就拒绝了。
第二天中午,忆川来到我的店里。他受惊吓也不小,我看见过一会儿他会不自觉地轻轻哆嗦一下。我给他煮面条,熬水果汤喝。晚上带他回了我的住处。他乖乖地跟着我,一步步都按我的指挥来。
就是吃完饭写了作业后,他害羞着不让我给洗澡。他自己在洗澡间冲了很久,出来后人就放松多了,明显活跃起来。不停地摸着我给他准备的宽大的睡衣,那是我穿过的,上面有可爱的小熊。他坐在塑料凳子上,我拿吹风机给他吹头发,他洗过的头发软软的,像三四月初升的小草。在我给他拨弄头发的时候,他忽然亮着眼睛抬起头,盯着镜子里的我说:“我也觉得你像我妈妈。”手里的吹风机差点摔到地上。
忆川在我的身旁睡了安稳的一夜。我像是重新找回了做母亲的感觉,一夜里无数次醒来看看他,吻吻他,给他盖盖被子。那一夜,我不仅失眠,还赔上了一些眼泪。这些都是久违的事情了。
第二天早上,忆川的胃口大开,两个煎鸡蛋,一根煮玉米,一碗豆浆都被他送进了肚里,小孩子果然不存事,我笑着想。给他背上书包,又往他手里塞了个小纸条:中午放学去看你爸爸。他望着我点点头。然后,他很乐意地被我拽着小手送到学校。和他相跟着走在赶往学校的大军里,我看见他一改往日跟着他爸爸总垂着头的丧气样子,无比骄傲地大步向前。而我的幸福就像阳光刚刚撬开一朵花的睡梦。我们两个人一定是这些匆匆人流里最渴望时光能够再慢一点儿的人了!
为着去医院探望苏先生,我回家换了两次衣服。总算决定了穿那个深蓝色绣着一只花蝴蝶的长裙子,外面罩了一件黑色风衣。中午接上忆川提上保温盒便挤公交去了市医院。
苏先生的脸上缠着绷带,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我坐在床边给忆川削苹果,他躺在那里输液,说的话不多。
要送忆川上学时,他拉了拉我的衣角,说了句,下午买卖不忙就过来吧。很祈求的样子。我点了点头。
北方的秋天一点也不客气,凛冽的空气逼着每一扇窗戶都关着。阳光从病房明亮的窗户上进来,抚慰着屋里需要温暖的人。我把背留给阳光晒着,手里正织着毛线,那种柔软的灰色毛线。
送完忆川,因为不着急赶时间,我就步行来医院了,在来医院的路边上买的。
苏先生盯了一会我织毛线,阳光暖着他的脸,又轻轻睡过去一阵。
在他睡着的空当里,屋里的阳光发生了小小的转移,一大片白白的墙被阳光擦亮,像是等待涂上彩色画似的。我的脖子有些发酸,抬起头撞见这堵亮亮的墙。应该画一个女人,她穿着红色的裙子正在厨房忙碌,小猫蹲在一旁看她做鱼,还要画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他俩正坐在餐桌前盯着她看。餐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两只白天鹅在夕阳下飞过……
是苏先生一阵轻轻的咳嗽唤醒了正发呆的我。喂他喝了一次热水,递去橘子他推开了。
冷不丁地,他冒出一句:“讲讲你吧。”我毫无防备。
埋下头,又接着织了几针。我从包里掏出随身带的笔纸,写下一些话:六岁被我继父一巴掌打成聋哑。十八岁在我妈的安排下嫁给钉鞋的瘸子阿拥,二十岁善良的阿拥死于车祸。二十二岁被安排嫁给青白,他打骂人,二十六岁时,孩子丢掉,后来我就逃出来。
他看完纸条后很久没说话。我就接着织毛线。感受着阳光像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着我们之间的空气。
本来以为来日方长,还可以对苏先生说很多话。可是我的预料错了。所以很多秘密还是没能让苏先生知晓。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听力的我并不清楚。只是从我又开始听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收获的都是痛苦。我的第二个丈夫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对我从早到晚用尽了污秽的语言,它们像密密的毒针害得我甚至想重新把耳朵堵起来。那个时候,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的眼球瞪得生疼,我大张着嘴,我要说话,我要骂他,我要还给他同样邪恶肮脏的语言,可我的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我只能发出难听的不受自己控制的啊啊啊啊的声音,我绝望透了,这种啊啊啊一遍遍刺激着我。也许正是受不了这种无能的折磨,我义无反顾地出逃。
当时只是决定,离我的家乡越远越好,于是就很偶然地落脚到这个北方小城里。
但我不知道自己竟然还保存着语言的能力。当我发现自己还有这个能力时,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天,我喊出的是:别打了,别打了。
后来,在苏先生消失掉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想,假如我是一个和别人交流无碍的正常人,我和苏先生之间又将会是怎样的关系?仍仅仅是朋友?我像个不甘心的赌徒,从一副牌中抽出一张又一张不同的数字和表情赋予它奇特而神秘的意义,我守住门前的行人,期待任何一次意外的发生。
“哎,这地方是没法待了。”苏先生明明在医院对我说过这句话的。我怎么能没当一回事呢?不然的话——会怎样?我也不太清楚!
我一遍遍懊恼着。
也常常会做一些怪诞的梦。比如我和一只白天鹅坐在一起嗑瓜子。比如忆川喜欢的哆啦A梦文具盒给卖光了忘了给他留一个而焦急。奇奇怪怪地总能让我回想好几天。
不知何时起,我的心竟像一汪水一样又有了三月里清风涟漪的波动。曾以为那些年积攒的仇恨和伤痛会一直把它冰封在晦暗的角落,秘不示人又深不可测。
梦中的怨恨和挣扎渐渐离我远去。却是时常在梦中去见一些久远的人。有阿拥。在遇到他以前,我是个深陷在安静冷漠世界里的一块铁,坚硬且无知无识地活着,无声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他竟不顾我是个呆滞的哑巴,开始对着我的眼睛和我不停地说话,教我做饭,教我把脸洗干净又给我买来镜子。慢慢地,不仅能摸准他的每种口型,在我细心地观察下,任何人只要一张口我就能猜出他是在表达什么意思。每日里,阿拥开着他的小电动三轮车,载着我和一堆破烂家什走村串街地去给人钉鞋,他逢人就介绍我,这是我的媳妇呀!眼光里满是骄傲,我为着他的那种骄傲让自己变得更加地合乎他的心意起来,我像他一样对着陌生的人笑,从他们多变的口型上回应他们的夸赞或戏谑。遇到他们表扬我了,就大方地回报一个充满谢意的笑。看见有人一说再见,就先帮他把东西递过去。蛮机灵嘛,你的媳妇。纵使他们夸我像在夸一只猴子,阿拥还要开心很久。阿拥把挣来的钱给我花,我就去买裙子,头上的发饰,学着街上的女人把自己也敞亮地显出去。人们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就比阿拥多了。但我总是紧紧地依着阿拥,以为可以一辈子和他快乐地钉鞋。
还有我那可爱的儿子,他的面容在梦里还是模糊。但我看到他不停地笑着叫妈妈,妈妈,好像在告诉我,他很好。
我不再恨着谁了。却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也应该去拥抱点儿什么。
也有刮风下雨落雪的时候。有时会走出屋来在门前站一站,看着小巷里一溜屋檐嗒嗒地落下无数水珠,然后不由自主地伸起脖子向前面望望。
什么也望不到。
风有时候会来晃我的门帘,恍惚间,我似乎看见有个人像一只温暖的大白鹅探着脖子伸进我的铺子里。我就随时准备好静静地回答他的提问。
真奇怪,再美丽的日子一旦过去了就像是玻璃碎掉般,无论你抱紧多少玻璃渣子,就是无法把它拼凑成往日的模样。我又不知不觉地在一次次拼凑过往的日子里挨了很久。
这一年临近中秋的时候,超市里打折的宣传册铺天盖地地卷进来。我受不住鲈鱼将要便宜的诱惑。在中秋假期第一晚,穿上新淘来的红色长裙,擦了点口红去了超市。每次外出对我都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我会买来丰富的食物和廉价但鲜艳的衣服,我会拥挤在热闹的人群里现出自己脸上难抑的激动和笑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只有这点欢乐了。
拥挤的货架前,我正对比着两款护手霜的价格——这个秋天来得有些迅猛,秋雨已连绵了三场。一个高个子的姑娘忽然越到我面前喊了一声阿姨。她比我高半头,我疑惑地打量她,圆圆的脸透着娇嫩的红,双眼黑白分明,青春的气息格外浓烈,是那忽眨忽眨略带羞涩的眼神提醒了我。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有个小女孩把一只粉色自动笔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她像抚摸一只小兔子一样轻轻地摩挲着它,可是她最后又把它放回1.5元区的位置,从口袋掏出1元交到我手里拿了一只普通的1元区的笔。我看见她的眼神实在可怜,把那只1.5元的笔便宜给了她。后来她路过我的店常对着我笑,从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一直到六年级的小姑娘。小学毕业后就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如今,她最少也是高中生了,歲月真是跑得快,只有我还想赖在老地方慢慢地踏着步。
忆起这些,我很开心地“哎”了一声!她显然吃了一惊,瞪圆了眼直勾勾盯着我不眨了。是的,哑巴阿姨开口说话了!
我逃了回来,责备自己没有抑制住冲动。是的,那一刻,我太想张开嘴回答一声了,我就那么自然地忘记自己不会说话。我倒在自己小小的床上,直到枕巾被泪水浸成湿漉漉的,圆圆的月亮正淌进柔和的光,像儿时母亲的手抚摸着我,我在这湿漉漉里沉沉睡去。
其实对着镜子练习说话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不敢在人前展现。这一次开口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觉得心间又腾起热浪,这热浪逼迫着我向前走。
处理完货物,退掉房子。我很果断地离开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五年很快。我从一个角落换到另一个角落,从一份工作换成另一份工作,从牙牙学语般的嗫嚅到与人畅谈无阻……五年,不是风一吹就过了,是很多风吹过,依然有一些坚如磐石的坚守刻在心上。它指引着我的行踪,飘飘摇摇地绕着一个城市转圈圈。
在攀枝花的这个聋哑学校里,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校长,他们说我勤苦耐劳踏实可靠。我自然知道这里不缺比我勤苦的人,可是只有我知道,孩子们想要的,只是一点点温暖和安全感。他们陷入在无人能懂的恐惧和无助里,有时候大量的讲解和安慰还不如一个深深的拥抱。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我多想反身去抱抱那个可怜的自己。现在,抱着他们就像是抱着昨天的我——渴望着完整,却正好差一个温暖的怀抱。我相信我的拥抱会赐予他们冲破黑暗的力量。也是在此,我仿佛找到了那个丢失已久的我。
我用自己的伤温暖着这些折断了翅膀的孩子们。我爱他们,一如爱自己那刻在伤疤里不可舍弃的痛。是的,就留在这里吧,不要走了。在孩子们幸福的笑脸中,我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
攀枝花的秋天不如北方的浓烈。那天,我正在和孩子们跳《画眉鸟》,轻轻转完一个圈,我看见一个戴帽子的穿着白色风衣的人正跨着包推着一个单车从我们后院篱笆墙外的小路上走过,头顶的树叶稀稀地在风中晃着。他仰头向着天空,样子像多年前见过的一个人。
我的手像画眉鸟的翅膀轻轻落下,那个走路慢悠悠的背影瞬间打开了很多回忆。我推开门跑出去,身上穿着单薄的舞蹈服出现在明媚的阳光里,站在微黄而柔软的青草地上喊了一句:苏先生!
他转过来,看见我,笑了。他显然有些诧异,但更多的是眼中涌来的喜气,深厚绵长。我们一起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他有些老了,帽子下面露出的鬓角有些泛白,额上的皱纹也让他的淳厚显得更温暖。
“结婚了?”他一开口竟是这样的问题。
难道他忘了我是个哑巴了吗?忘了最好,我在心里又惊,又喜地笑了一下。
“你呢?”这一次,我终于毫无遮拦迫不及待地问回去。
“一直没找下忆川喜欢的,就没结。”他的笑鼓动了更多的皱纹。
“你等着。”说完我就转身跑回去,要去给他取一个多年前准备的礼物。
这么多年了,苏先生又像一只白天鹅一样扑棱棱飞到了我的眼前。那个柔软的大白天鹅,他还缺一顶灰色帽子。
它明明一直躺在行李箱里的,我专门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包着。可此刻在我要送出去的时候,它竟然不翼而飞了。去了哪里呢?
【作者简介】黄亚琴,生于1990年。现供职于汾阳某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