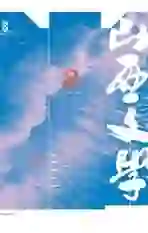寻找诗意的栖居
2020-11-19张凡张银蓉
张凡 张银蓉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上,周晓枫的散文创作可谓独树一帜。通过温婉尔雅、富有表现张力的文本,她向世人传递着一种隐秘而令人神往的自然神性与了然于心的禅意。尤其她那基于边走边看边记的自得其趣和对大自然无与伦比的“在场”倾听和敏锐的感受力,将花、鸟、虫、鱼的一举一动描摹得自然、生动、贴切,却又不落窠臼。很大程度上,周曉枫那极具力量感的文字、置于潮流与主流之外的鲜明个性,都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了她对大自然所赋予人的一切的美好与独特以及对现实社会和生活日常的一种深切关怀和关注。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的散文集《河山》,可以说是周晓枫近年来致力于抒写自然山川与风物、再现人与景与情交融于一体、同时表达个人思考及自然感知的一部力作。在散文集《河山》中,周晓枫以轻柔娴静的笔触,以游记这种比较自由的文体形式来表达了对大好“河山”的真爱之情和对大自然中一草一木的别样倾心。某种意义上,写作之美不止于文字表面,更在于写作者精心描绘之自然山水以及深居其间的人与情。周晓枫在散文集《河山》中将情感寄托于山、林、河、海、园、城中,其间的文字之形与大自然之神气融为一体,有力地呈现出基于自然之上无限的生命力以及无比真诚、率性而作的畅达人生。周晓枫曾认为,“真,包含着真实、真诚、真相、真理等等,这是散文的基础和远方;即使虚构,也不能扭曲和篡改这样的原则。所以我要以此为题,强调散文虚构的目的,正是为了靠近真实。”[1]不难发现,周晓枫笔下的自然山川充满一种诗意之美、意境之真、文化之韵,无论雪峰之上的残根,亦或湘湖的跨湖桥遗址,甚或博尔塔拉的水,凡此种种,均被她赋予了一种近似神性的存在。细读散文集《河山》里的一篇篇美文,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作家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极富真切感的探知欲与独特理解。作家不露声色地寄寓内心深情,上善若水,充满对自然原生之景的热爱与敬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理解,而这些早已内化为作家以景写情、借景抒情的表达旨趣和介入逻辑。
1.自然神性
充满喧嚣的现代城市生活虽在很大程度上掳走了人们沉下心来感知“寂静”的耐性与敏锐,却在另一种层面上促进人们去思考如何在一片嘈杂中寻求“静下来”的可能和情不自禁。比较而言,自然之道在于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性和天然性,其足以阻挡、遮蔽都市日常里的喧闹、杂乱和纷纷扰扰,以原初的自然之形来抚慰现代都市人那饱受煎熬的内心与敏感脆弱的神经。在作家周晓枫的笔下,以山川风物来呈自然之形,于无声之美景与真情流露带给人们以一种足以净化灵魂的诗意、细腻与温婉。很大程度上,周晓枫的散文以真切的自我感知为表达旨趣,传递出一种沁人心脾、返璞归真式的人类情怀。“周晓枫的散文向读者展开了丰富的身体感觉中的世界。这种感觉来自于个人的体验、记忆,是开放身体感官所获得的关于自我、类群以及其他生命景象的观察、感受和想象的心灵烙印。”[2]她的文字看上去在写山林、写河海、写原野,而事实上却透过其笔下一个个自然风物的浮面来再现个人内心对外在世界、自然万物最直接的情绪和最真切的感触。作家周晓枫受邀走访多地,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之际,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创作素材,一次次被眼前无限美好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她那深藏于心的乐幽喜静之偏好也不时地被激起,荡漾于心的更是无限诗意和温情。一般而言,身外之物于她,可比为过眼云烟,而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却被作家尽收眼底,并被作家赋予了静谧又崇高的自然神性,而这便是作家周晓枫钟情万物的写作之道。
阅读作家周晓枫的文字,人们不难发现,她对自然生灵的书写皆是安静的、隐秘的。正如其散文集《巨鲸歌唱》中的《弄蛇人的笛声》和《独唱》所展现的——均在无声的世界里,感受大自然的隐秘力量,同时在有声的世界里,找寻无声的珍贵与难得。而在散文集《河山》中,作家以山、林、河、海、原、城为叙写主题,刻画了万千自然的形与貌。自然之静美,美在天然去雕饰,亦美在无声世界里那份巍峨和深沉。当作家从车窗里第一次瞥见四姑娘山主峰时,一下子被震撼到了,“我停顿数秒之后才惊呼,是因为瞬间遭受重击,我所目睹的神迹令我无法说话。很厚的云层围裹,一座巍峨雪峰,恰从云层中间的晴朗里显露出来,有如悬浮。”[3](《雪峰之下》)源于对海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在短短数天的庄河之行中,作家醉心于长达两百八十五公里的海岸线,尤其那幽旷、神秘而又深沉无比的大海,令人遐想万千、心潮澎湃,“无论是在神秘的海王九岛,还是人迹寥寥的黑岛,我看到的是那么优美的大海,那么沉静的大海,那么孤旷的大海,那么狂寂的大海……我看到它永不驯服的野力。”[4](《庄河观海》)相较于让人情绪低迷的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和无序,相较于只为谋生或虚荣心胁迫下的繁忙的日常,作家更青睐宜兴竹海中那份自得逍遥,“在竹林里走了几千米,身上有了薄汗,我们就在旁边的亭廊里坐下,饮茶。清风徐来,阳光照耀着竹节之间迸发的新芽。难得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慢生活,自在随心……甘美的茶,禅意一样渗透我们的身体。”尤其当身处宜兴的“竹海灵境”之时,更愿意于寂静之竹海深处放飞自我,让压抑已久的内心获得一种由衷的释放,“就想这么坐着,陷入竹与茶的清香之中,陷入幻想……即使乌米饭一样的夜色即将到来。越过交错的竹梢,远端是暮色中的庙宇,钟声悠长。”[5](《宜兴竹海》)对成天被刺鼻的尾气味、喧嚣嘈杂包围着的城里人而言,越是贴近清新越能沁人心脾、越是浑然天成越能激越人心,更何况有如作家这般心怀“田园梦”、对外界风物处处敏感、时时在意的人。无论山峰、还是大海、竹林,作家笔力所及之处都被赋予一种神性、一种禅意,它们于无比“寂静”之中尽显大自然种种神迹的无比威仪与无限生机,这中间孕育着于自然之声中陶冶性情、净化心灵的自然力量。于此身外,那尘世间所有的繁杂与纷扰,也都在此刻销声匿迹,也都在此时烟消云散。惟有真切感知到自然之真正寂静与悠然,方可暗中生发出一种对抗俗世纷扰的强大内在,从而使得自我与外界真正得以相得益彰、互为映照。周晓枫之写作,力求将细腻与敏锐融于对自然的悉心感知中去,于寂静中内化于心,继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向万千读者再现自然之声的永恒神性和无穷之隐秘力量。
某种程度上,喧嚣和寂静可以说是生命体的“一体两面”,其既有客观层面的“物”的意义,也有主观层面上的“精神”指向。如前所述,作家周晓枫以纯粹而真诚的生命体验去拥抱自然、接纳万物的同时,也以自然万物的纯净与幽邃来陶冶红尘中被世俗生活沾染的现代人的心灵。从周晓枫散文的字里行间,依稀可见一种于寂靜之处生发的关乎生命活力的“喧嚣”,而这种“喧嚣”亦是深处于寂静之中、并由此层层升腾的无限生命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于无声之处迸发无比灿烂的生命之光,或许“这就是自由之味吧?天真烂漫,保持着本性。”[6](《界》)“天真无邪”的大自然作为周晓枫个人情感抒发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为她寻找生活日常中的诗意提供了基础的要素和表达的可能。沉重的山脉,柔软的云层,温情的猴子,孕育苍凉巍峨的雪峰,栖霞童话般的苹果园,还有湄潭持恒的炒茶工艺等等,这些散落在周晓枫散文世界的人间日常,寄托着作家对于寂静处大好“河山”的无比真情和深沉感恋,而它们对习惯于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就是远离尘嚣的“诗和远方”——另一种自在生活的探寻与发现。批评家项静曾认为,“周晓枫把日常抒情和散文和蔼可亲的部分,分割在散文的不同章节之中,避免过度集中引起的不适和虚假感,又能够串联进自己的新语法中,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们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7]处于自然本真状态下的山山水水,不论表面的跌宕起伏还是内在的激流涌动,其必然带来的无尽改变,都将影响到作家对于眼前世界的态度和观察的视角。“一切都是安静的,无论生死。”阅读《雪峰之下》一文,可见作家对原始状态下的大自然和那些处于静态中极富野性美和生命韧性的生命体充满敬畏,她笔下的生命个体,不论何时、处在什么状态下,都高昂着不屈的头颅,“那个向着高处、向着云端的梯架倒了,即使死去,它似乎还保留着不屈的树魂。”“更多的树顽强存活。有些树的方向,几乎是在地上攀爬,它们的根被生生从地里撕扯出来,露出动脉似的根和毛细血管般的须。然而,被闪电劈砍,它们生长;被马匹的门齿啃咬,它们生长;被水泡、被虫蚀、被冰雪封锁,它们依然生长。”[8](《雪峰之下》)悄无声息的生命世界,看似寂静缓慢,却孕育着自然生命的无限律动,其间尽显一种坚毅、顽强、向上的生命活力。
2.茶意如禅
众所周知,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往今来,爱茶悟道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他们从日常的喝茶到极富层次感的品茗,可以说是享有尽有,五彩斑斓。从最初的回甘体验到较高层次的茶事审美,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通透与彻悟,均在不同层面上彰显了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无可比拟的显著地位。同样对茶情有独钟的作家周晓枫,在散文创作中习惯将对茶的观察置于平凡的生活日常中,将自身对茶的认知从科普、从见闻中撷取出来,一方面书写品茗和炒茶的闲情逸致,又从文化层面去考究茶所蕴含的丰富意趣和曼妙神韵,以茶之清香来浸透每一个爱茶人的神经与遐思,恰似如“瘾”随形,在轻歌曼舞之间,如沐春风,透彻心扉。“茶,深具植物的美德,是嘉木界的大青衣。四季皆宜,暑日的茶让人清凉,冬天的茶暖也沁人心脾——翩翩的茶,在剔透的玻璃杯里轻歌曼舞。如此深得天地滋养,如何能不漾动人心?喝一口湄潭翠芽,肠胃里荡漾着复活的春天。”[9](《慢舞的茶》)在一次又一次的相约而往、尽兴而回的游历途中,作家周晓枫把视野内大自然中的每一物象都几近视作自己身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茶”尤为凸显。甘甜与清苦,茶味如是,人生亦如是,细品一盏茶犹如回味一段岁月、一件往事。作家眼中的“茶”有近于神迹之处,拥有“万能的再生”之力量。“活着的茶,在冷水浇着,根系沉默的一切;死了的茶,在滚汤沏着,重新活过,在袅袅升腾的丰沛水汽里,还你故乡的云雾缭绕。”[10](《人在草木间》)不论“活着的茶”还是“死了的茶”都具有“从伤害中汲取成长力量”之傲然内质,作家以此来反观人之生与死,还借以表达漂泊异乡的游子深藏于心的那一缕缕乡愁和离情别绪。
“茶,看似羸弱,却隐藏柔韧而惊人的力量。站在这株古茶树旁边,我观察它厚实的叶片、陈旧的花瓣。我安静,和朋友偶尔交流,也尽量低语……我不由自主的态度里,仿佛包括对时间和沧桑的尊重。”[11](《人在草木间》)作家于近处观察一株饱经风霜的古茶树,它只身荒野,自由而任性,汲天地之精华,萃日月之灵气;同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万古以来的凡间烟火和人世传奇。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然古茶树千年之悠悠,方显岁月的稍纵即逝和人生一世的短暂与微不足道。从古至今,文人好酒亦爱茶,而文人墨客相聚品茗论道更是一道让人无比神往的人文风景。散文集《河山》集中了作家近些年三十三篇散文,总体来说虽无几处显茶,然却处处有茶,作家把对茶的情有独钟和偏好隐匿于字里行间,于每一处景中,于每一份情中。“一盏茶里,汇集金木水火土……我们人生的五行,尽在其味,尽在不言之中。茶作,是人与植物的灵魂交流,就这样日月天地,就这样草木山水。”[12](《人在草木间》)可见茶系天、地、人,方寸一念间。一方面,平时整日穿梭于高楼大厦间的人们难有一份闲适;更何况,烦乱无序、焦虑压抑的都市生活早已压得人们无法自由呼吸,继而造成很多人无比向往和渴望一份宁静以及随之用以思考的独特的“寂静”。周晓枫也在不断追寻远离城市与喧嚣的那个“高处”——让自己可以安静地去思考的别致的空间。茶意如禅,悟道于心,在作家看来,炒茶犹如写作,彼此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炒茶场景,让我联想起写作。尽管生活提供的素材层出不穷,也需要以敏感的心、灵巧的手、持恒的耐性才能收取,如同采茶。即使你有幸坐拥茶园,也不意味着坐享其成。对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类似于炒茶的处理过程——脱去过度抒情的水分,使之紧实,提取其中储藏的香气。伟大的写作者看似寻常,同样的文字、结构和主题,经过他们的手所炒制,就像复活的茶那样,完成出色而乱真的还原,并且在韵味和情怀上弥散持久的香气。”[13](《慢舞的茶》)炒茶之于茶农,莫过于写作之于写作者,拥有禀赋和耐性并不能完全成就有志于此的人,惟有长期以往的日积月累和对有心生活的拿捏有度,才能完成“近似的完美”之上等佳作。
如前所述,长期被一种烦乱、无序、快节奏生活包围着的人们,对慢节奏的生活有种近于心切的渴望与倾心。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他们更神往于寻得一片宁静之所,借以安放难得安静的个人心绪、并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找到诗意的落脚地。进一步地说,大多数作家都试图在繁乱忙碌之庸常生活中作出一种努力——凭借文字来营造或建构略显个人色彩的“梦里桃源”——虽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而对作家周晓枫来说,她心中的“梦里桃源”或许更切近于位居云贵高处的湄潭和其间的万亩茶海,“湄潭适合种茶或植字的人,适合美好的劳动,也适合安逸的隐居。桃花源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恰好,湄潭有一条桃花江。”[14](《慢舞的茶》)作家更愿置身于此种有如仙境之地,如茶农一般每日躬于采摘,既可克服庸常生活中“四体不勤”之怠惰,也可在浓淡相宜之山水乡村享受那份难得之闲情逸致。
值得一提的是,深谙中国茶文化的作家周晓枫,以彰显中国传统之深韵的茶之道来表达她那深蕴于胸的茶情、茶意与禅境,继而为那些被杂乱无序、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搅得焦虑不安、疲于奔命的人们送去来自大自然的最为澄澈的关怀和慰藉。更为关键的是,作家周晓枫以自然之序归置茶之自然本性,尽自己所能维持自有茶意在她笔下的味感与质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越发凸显其“独一份”的散文创作之意境之美和神思之涌。
3.传统之思
相比人们司空见惯的现代散文书写模式,周晓枫的散文创作可谓有别于传统散文写作。作为比较注重个人风格写作的周晓枫,她在散文创作中“强调个性,强调与众不同的异质性、独创性,强调独立判断和智慧。”阅读她的作品,“无论是题材的广博、结构的繁复,还是语言的力道,较传统的东西,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15]而这些,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力促作家周晓枫在延展“新散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上做出了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成了造就她散文写作独特性以及个人风格的关键要素。更进一步地说,周晓枫尤为擅长在写作中呈现出“一贯的盛大、华丽、意象繁多而哲理深刻的笔致”[16],而这是她被多数评论家点赞和肯定之处,因此更加深了作家自己坚持这种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也成就了她散文写作的一大特征。批评家项静在论述周晓枫创作时曾指出,“周晓枫很少发表短小随意的写作,每一篇都带着工匠手工劳作的痕迹和专业写作者的自觉意识,步步为营,靠着理性的设计和语言的力量扎实前行,绝不是一时一地灵感、心绪和臆想引发的灿烂火星和美丽霞光。”[17]换句话说,周晓枫始终以一颗匠心来精心打磨和雕琢自己的作品,力求工整有节,而非一时兴起或昙花一现式的即兴而为;与此同时,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轻柔观照、并打量着自然万物,用心发现、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当然,我们阅读她的散文,可以真切地感知到她的文字带有一种深沉的力度,其文字背后的浑厚力量根源于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化于周晓枫而言,仿若高楼之基,正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她的文字与情怀满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和人类的关怀,继而以自然之力丰富、延展传统文化之韵。
汪曾祺在《蒲桥集》自序中曾指出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极为丰富;他还指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诗、戏剧和小说受外国影响巨大,惟有散文乃是本土的,因而写散文的人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而这样的“学思践行”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周晓枫来说,在其散文写作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她在文中对自然万物细腻而富于深情的刻画与描绘,离不开她对万物生灵的用心观察与感同身受。不言而喻,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作家周晓枫的每一个落笔之处都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子,而这得益于作家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资源不自觉地吸收与运用。在《蔚县剪纸》一文中,作家从以往对自然山水的独特观照中跳脱出来,以说书人的一方醒木拍响了传统艺术之门,于是作家把笔触落在极富民间意味的古老的传统手工艺——蔚县剪纸的前世今生。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当代人更习惯以高效的技术手段来追求新的体验或迎合市场,致使传统“手艺活”面临商业化的强烈冲击和所谓的“大浪淘沙”,然而仍有像陈越新这般精通并执着于传统剪纸的能工巧匠。他致力于这种常人眼中费时费力的“手艺活”早已超脱普通人的“为稻粱谋”与世俗的名与利,更多的是追求卓越的匠心和悟道于此的慧心。“真正的敬畏传统,是尊重与理解之后的责任担当——不是浇注水泥来巩固它的造型,而是灌溉清泉,让它开枝散叶。对传统的捍卫与对创新的渴望,使陈越新这位笃信者的脚印成为一条方向清晰的开垦道路。”[18](《蔚县剪纸》)究其本质而言,“传承”的要义既要精耕于传统,更要高于传统,“我们不能只靠传统产生的利息过活,需要注入新资本和新活力。”[19](《蔚县剪纸》)正如民间艺术家陈越新整套的具有现代美感和审美风格的剪纸力作《一百单八将》——不仅是他甘愿下“笨功夫”的精心制作,更是千挑万选的呕心沥血之作。
在周晓枫眼中,陈越新的匠心之作《一百单八将》既是个有形的态度,更是个无声的宣言,彰显的是一代手工艺人传承文化、守望传统的用心、信心、恒心和静心。“没有俗物障目,没有俗声入耳,艺术世界的隐秘光线照彻进来,他才能目睹万物生动,听到低语悦耳。大约唯有寂寞与怡然的宁静中,才会有天籁降临。”[20](《蔚县剪纸》)陈越新钟情于平生所爱的“手艺活”,醉心于与众不同的剪纸人生,这样的民间艺术传承人以一方剪纸为世界,带着手艺人的无比虔诚和独特审美,为世代相传的剪纸艺术增添“天然的补给”。虽说蔚县剪纸不过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但作家笔下剪纸艺人日常的执着和精益求精,却为世人打开了传统守望者匠心之作的真正内在。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传统的笃信和守成,并非政策“保護”下的条条框框,需要依靠的是独具匠心的传统手艺人——拥有大智慧和赤子之心的文化传承人。“艺术家有若小神,他创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彼岸世界,让我们信任、沉迷且向往。”“美,来自限制之下的放纵,以及教养之后的不羁。”[21](《蔚县剪纸》)这些尽显作家周晓枫真诚率性的文字与表达,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传统之美的隐秘力量,更使人们对造就艺术之最高境界终于“收放自如”有了共情——大千世界的人人事事,真可谓功与勤勉,精于匠心。而传统之思,之于周晓枫,是她字里行间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哲思和彻悟;之于我们,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守望传统之光,发掘文学与艺术的诗意遐想和可能。
结语
新世纪以来,尤其在“新散文”的创作版图上,周晓枫以其带有哲思和富有内蕴的文字占据重要的一极。“新散文将充满个性、自由且有锐利发现的感知引导至思想、心灵和梦想,精神的奇迹在散文中崛起。新散文作家周晓枫在访谈中拒绝了被贴上先锋写作的标签。她表示新散文努力突破旧有规则的束缚,而试图达到新的自由和新的真实。”[22]不难发现,作家周晓枫也是新散文创作群体中极具个性的独特灵魂,她积极入世却又能超然,始终保持一种出世的情怀。而一向以乐于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和边界的作家周晓枫,在散文集《河山》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介入祖国山山水水,因景生情,借景抒怀,把散落于大江南北的自然神迹以优美的文字呈现在万千读者眼前,继而勾连起心怀“田园梦”的现代城市人向往远离尘嚣和嘈杂的山林与自然。面对生生不息的万千风物,作家又以无比倾心之姿来观照它们。不论山林、河海,还是原与城,在作家笔下又多是无声的、静谧的、巍峨的和充满生机的,它们看似静静矗立于人世间,却默默孕育着无与伦比的生命的力。黎坪之秋、橘花之盟、沧桑之舟、春日阆中、贺开的古茶山、呼伦贝尔的雪……丰富且纯情,柔软且坚硬,作家均以特殊的话语形式再现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天然之态。某种意义上,作家周晓枫之近作《河山》犹如一部极具神韵的山河之书,通过与自然山河的相濡以沫和情投意合,得以悠然俯仰于天地间,因而在不经意间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散文传统平添了几分安静、禅意和境界之妙。
参考文献:
[1] 周晓枫:《虚构的目的,是为了靠近真实》,《文艺报》2019年4月12日第002版。
[2] 丁晓原:《周晓枫:穿行于感觉与冥想的曲径》,《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第53页。
[3]、[4]、[5]、[6]、[8]、[9]、[10]、[11]、[12]、[13]、[14]、[18]、[19]、 [20]、[21]周晓枫:《河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第139页、第65-67页、第116页、第3-4页、第53页、第33页、第33页、第34页、第54页、第55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4页、第211页。
[7]、[17] 项静:《“缺席的散文”和一个散文家的档案——周晓枫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第67页、第66页。
[15] 东篱:《周晓枫散文中的几个关键词》,《名作欣赏》2005年第1期,第62页。
[16] 周晓枫:《如果没有候鸟的心怀高远,我们容易成为过早匍匐在地的人》,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1130/c405057-29677467.html,2017年11月30日。
[22] 刘云春:《论周晓枫散文的审美特质》,《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第138页。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区域文化视野下新疆兵团文学研究”(2018M643773);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新疆兵团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传播研究”(19YJA850016);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地域文化視野下新疆当代文学专题研究”(RCSX201743)。
【作者简介】 张凡,1982年生,安徽舒城人,文学博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银蓉,1997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