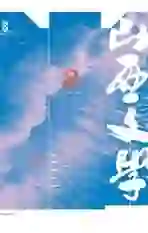安身
2020-11-19李瑞华
辛姐叫辛爱爱,大家都叫她辛爱或者辛姐,她在家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姐,下面一个弟。她在家里的地位,是受宠爱又受厌恶的,父母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才好,到她二十九岁上,姐姐辛花花的女儿都三岁了,弟弟也处了个对象,她还是没有着落,继续在县城做保姆。父母都不敢说她,她嘴太厉害,生气时嘴巴尤其不饶人,父母觉得亏欠着她,都忍着,只盼她能在县城里好好找个婆家,嫁出去了事。
当时,辛姐正在我家做保姆,刚干两个月。早上八点来,中午在我这里吃饭,晚上做好饭后去县城她姐辛花花那里吃晚饭和住。她干活利索,夸张点讲,每天,我在地板上和墙面任何反光的地方看看自己就能出门,到处亮晶晶能做镜子来用。做起饭来,花样也多,她说姐姐和弟弟早早出去读书,去县城工作,只有她在农村待着,天天在地里和家里干活,她伸出手来给我看,说作家你看看劳动人民的手。那手不长不厚,据她说是没福气的手。她手关节比一般女人大,结着一个一个硬茧,几乎没有任何女性特征,我摸摸它们,说,怎么还有点划拉人。她冷笑一声说,你那是什么手,娇贵得跟没皮一样,让我这粗不啦几的爪子碰到,还能不扎?
我已经习惯她的说话方式,也不计较,只说你也不容易啊。
她在我这里做到四个月时,一次晚上临走,我拿了自己的几件衣服给她,她自己又要往楼下拿垃圾,于是我说送她下去,她却怎么都不肯,她一向直爽,这回看她吞吞吐吐,倒很新鲜。我让她把垃圾先放下,她也不同意,说,今天垃圾一定要扔,这是工作。我拗不过她,看她半抱半拖往下走,心说你可以明天再拿衣服啊。但这话我没敢说。
等她从楼梯消失,我去关窗帘,准备完成一个约稿,无意中看到楼下的辛姐,正和一个男人站在一起。男人身量不高,也看不清脸,两个人一起到垃圾箱扔掉垃圾,又把两包衣服分别放到两辆自行车上,并行走了。
看到这个情景,我特别高兴,想必辛姐是恋爱了。希望对方不要嫌弃辛姐才好。
隔天,辛姐来后,我问昨天和她在一起的是谁,辛姐脸红了,不过她一向直爽,快人快语。说是别人介绍的对象,在县城里有房子。
人是干什么的?我问。
跟著别人干装修。辛姐说。
也算一门手艺啊,不错。我说。
人家是知识分子家庭,爸是退休数学老师。辛姐颇有点自豪的样子。
我有点好笑,辛姐自己没读过书,对知识分子家庭的仰望是她的弱点,我不敢说知识分子家庭也没什么了不起,怕她多想,点点头说好啊,有文化好。
说完这句,我又觉得不对,辛姐呵呵笑,说你们知识分子说话就是爱绕弯弯,明明你们自己觉得高人一等,还常常说热爱劳动人民,劳动人民高尚。看看,露馅了吧?
她心情好,干活的时候哼着歌,我只好让她闭嘴,说要写作,不许唱歌。她吐吐舌头,像个小女孩一样地笑。这时,她嘴上的那道疤痕丑陋得随着笑容扭曲着,让我禁不住转过头去,心里暗骂自己矫情。
辛姐个子有一米六多点,大眼睛,乌黑的头发,鹅蛋脸,本来该是美女,可惜生下来就是唇腭裂,家里人没钱给她做手术,直等到十几岁上才遇到一次义诊,把手术给做了。手术做得晚,伤疤也明显,侧鼻塌陷,鼻孔过大,唇线不明显,她这是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好给耽误的,本来早年间是可以通过多次手术整形恢复的。但即使现在,她也没有这笔闲钱啊。
恋爱起来后,辛姐也不耽误干活,有一天,我从书房出来,到客厅拿水喝,她正坐在餐桌上择韭菜,准备包饺子。我站在那里问她进展如何,她不直接回答,倒反问起我来,说妹子,我这是长得有毛病,没人要,才耽误到现在,你这细皮嫩肉水灵灵的,咋二十七了都不结婚?
我说我是独身主义。
她想了想,说,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我说,怎么不一样?
她说,你不结婚也没人管,你爸妈还给套房子,让你天天写文章。我不结婚,爸妈在村里都抬不起头。唉,还是你命好啊。
她又看看手中正在择的韭菜,再叹一声,说,还能雇个我,在这里给你包饺子吃。又说,你可不知道住我姐家有多憋屈,姐夫对我好吧,姐不高兴。姐对我好吧,外甥女不高兴,外甥女对我好吧,姐姐姐夫都不高兴,说有了小姨淡化了对父母的感情。我真是太难做人了。
我笑起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于是问她说,你不是为了父母才谈恋爱的吧?又劝她说,你可想好,这可是大事。
她放下手中的韭菜,盯着窗户外面蓝色天空,爽朗说,他对我挺好的。
我说,哪天带上来,让我瞧瞧。
她说,带就带,只要你不嫌他长得寒碜。
说过这话的第二天早上,她还真把对象带上来了,是个瘦瘦的,长相其实也不丑的小伙子。之前我已了解到他叫王格,比辛姐大两岁,三十一了,不过看过之后,觉得比三十一还要老相一点。我急急忙忙给他倒水,拿水果,心里直犯嘀咕,担心辛姐就此辞工。说实话,一时半会,还真不好找这么勤快爽利的人。
王格说话很客气,很仗义,说听爱爱说我是好人,有啥事需要他办的,尽管开口。我只有点头的份,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需要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瘦弱男人来帮忙。他还执意想请我中午吃饭,说感谢我照顾爱爱,我急忙拒绝,说有稿子要写,走不开,同时担心他要进书房看我的稿子。我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他喝了几口水,真要起身往里走,说拜读一下我的文章,辛姐及时阻止他的过分关怀和热情,说书房不让别人进去的。王格这才坐下,嘴里还嘟囔说以后就不是外人了嘛。
他坐了一会,说还要去给一家装修,就告辞了。辛姐送他下楼。我的窥探欲又发作,在窗户上往下看,看到楼下两个人还抱在一起告别,我赶紧缩回头,心里偷笑,这小伙子,和辛姐还是蛮般配的,虽然人普通点,不过,辛姐也是有毛病的,两个人,估计能成。
辛姐回来,问我咋样,我说不错。这话是真的,其实,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身上有种假矜持,惺惺作态,这个王格,倒像是仗义侠客,根本没有酸腐气,可能跟他的职业有关吧。
我没敢把这些话说给辛姐,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不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她肯定不高兴。反正,这小伙子给我第一印象不错是真的。
辛姐辞工结婚,是在一年之后,婚礼我恰好去外地,只捎了一份礼过去。婚后,她和王格父母同住在一起,大概在她结婚半年后,我顺路去过一次,才知道她口中王格的房子,只是一个两室一厅的二层单元楼。这么小的房子,让辛姐收拾得妥妥帖帖,但是,我难以想象他们是怎么住的,辛姐好强,和公婆住一起,能合得来吗?
去的时候,辛姐公婆不在,说是去医院体检了。我看到老人的房间里,果然有个大书架,堆着不少书,我对书感兴趣,问辛姐可不可以去看看。辛姐还不改自己说话刻薄的口气,说,随便翻,这些东西,可没你的娇贵,也能碰也能摸。
我打开玻璃柜门,随手拿出一本,是高等数学,又拿起一本,还是一本跟数学有关的书。我是最怕数学的,等发现书柜里几乎全是数学之类的相关书籍时,有点胆怯。关上门,看到旁边的书桌上,还摆着一摞一摞的纸,又翻了翻,看到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演算草稿,有点晕了。
这都什么呀?我问辛姐。
辛姐鼻子里哼了一声,骂道,奶奶的,什么破知识分子,就是个顽固的老家伙,说是要算出个什么新的数学公式来,算了一辈子了,还没算出来。家里啥都不管,吃饱饭就算数,要不是有这么点退休工资,早就饿死了。
我说,你不是还有王格吗?他赚的钱,你好好计划。
本来是开导的话,谁知道她听了,更是气愤,拉我到客厅,一屁股坐下说,我可是上大当倒大霉了,什么赚钱呀,跟他老子一样,也要研究出一种世界上最好的什么油漆配方,说自己配置,可以节约成本。赚点钱,全投进去做实验了,吃喝都有问题,结婚后我才知道他在外头欠了五十几万的债,这个破房子,已经顶给债主了,下个月就得搬家。
我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那你们以后住哪儿?
辛姐说,死老头子说了,她和老伴自己租房子住,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又说,能有什么办法?
我想起有个朋友,是个单位一把手,他们单位有个一楼偏西面的房间,只有一室,说是给臨时工准备的,一直没招人,还空着。就问辛姐愿不愿意去那里住,辛姐说,这时候了还挑啥,就是狗窝我也愿意。
我不理她的气话,给朋友打电话,朋友说,住可以,不过得每天帮着把单位院子打扫打扫,水电免费,看行不。我把这话说给辛姐,她高兴地说,当然行,我还怕干活吗?
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当即就带辛姐去见朋友,拿了那间房的钥匙。那是个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靠东有个小窗户,里面放着一些杂物,还有一张床。辛姐感激得要请我吃饭,我说,你走了,我家里都没人收拾,你也不用请我吃饭,有时间,十天半个月的,帮我大扫除一次就行。辛姐说,那还不简单?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行。
我把家里钥匙给辛姐一个,她果然如我所愿,在忙完搬家后,基本一周能来一次,帮着收拾一次家,一般都是在周六。这样,我又和辛姐时常见面了。
辛姐对我这个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充满羡慕,她从来不掩饰这个,总说这辈子能有这么套房子,什么都值了。我说你是先要房子还是先要孩子,她拿着抹布的手停下来,直言说,我也不瞒着你,我流了两次了。
怎么回事?我盯着她问。
不知道,三个月内,准流。
医生怎么说?
也没说出个道道来,就说再怀个看看。
她脸色蜡黄,搬家和流产想必让她元气大伤。我有点愧疚,说,你多在家休息,我这里,以后你可以少来几次。
她眼睛一瞪,直脾气又上来了,说那可不行,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连这点活都不帮你干,那还叫个人吗?
我其实周六是不写作的,完全可以自己做家务,而这个时候解释,显然不是最好的时机,我返回书房打开电脑,胡乱敲字,辛姐已经悄悄帮我关上了书房门。
没想到,辛姐在我帮她找的这个小屋子里,一住就是六年。两年后,朋友调离了那个单位,万幸的是,新上任的领导我也认识,并且,由于辛姐把院子收拾得干净,单位众人都为她说好话,新领导又把她留下了,这是好事,否则,她还得再搬家。辛姐在这期间,又怀了四次孕,都没保住。有一次,已经怀到六个月上了,又流产了。医生已经判定她是习惯性流产,建议她不要再怀孕。
我这里,辛姐还是时断时续的来,怀孕了,休息一阵子,流产恢复后,她又接着来,我劝她不用再过来,她说,你做的是文化事,不该做这些粗活,我有时间,就来。因为她坚持,再加上有时一个月两个月她才来一次,我就不再推脱了。她来后,把家里全部擦一遍,把衣柜里的衣服分类叠好,给我省了不少心。说实话,我是顶不爱干这些事的,每次她来,我都十分欢迎。有一年,我忽然想起辛姐的年龄,问她多少岁了,她说三十八了。又说,妹子,你也都三十多了呢,早知道结婚这么难活,我还不如学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呢。
说到这里,她又伤感起来,扫地的动作也慢下来。我知道,她一定想起自己不能生孩子的事,也不好劝解什么,她自己倒给自己宽起心来,说,命里没有娃儿,再想也没有。我准备寻一个去。
领养一个,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辛姐说,生不如养,养的还不是一样亲?
我没生过孩子,自知没有发言权。她继续说,哎,我这也是肠子给肚子宽心,自己不能生,有啥办法?
我问,王格那边,同意吗?
辛姐说,他敢不同意?要不是他把房子抵债,我能气成这样?我这不能生孩子的病,就是活活让他给气的。
她呼吸都粗起来,继续说,我家的事,事事我说了算。孩子是没指望了,这辈子,就是累死,也要给自己买套房子,让那些笑话我的亲戚们睁大狗眼看看,我辛爱爱命不好,可也不是个认命的?货!
又过了一个月,辛姐来时,带了个瘦巴巴的丫头来,一岁多的样子,穿着不合身的粉裙子。辛姐说是娘家邻村一户人家给的,这家两个丫头了,本来要生儿子,不料又生了个女儿,就五千块钱给她了。那孩子眼睛大大的,和辛姐还有点像,我跟辛姐这么一说,她乐得咧开嘴嚷起来,别人都这么说,这丫头活该是我的。哈哈,这就是命啊。
她这会,也不说不认命的事了,我笑起来,看着辛姐高兴,也跟着高兴,拿着一个橡皮狗给那孩子玩。不知道这闺女怎么称呼,问辛姐,她说,起了个名,叫房房。我说,是芳香的芳,她大力摇头,说不是不是,是房子的房,房房。
房房,这是个女孩名字吗?辛姐对房子的执念,真是深刻啊。
接下去,有两个月,辛姐都没来。快过年时,大概是去年腊月二十四早上吧,她带了几个卷卷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进厨房,打开电饼铛热给我吃,家里什么地方她都熟悉,熟门熟路,就跟她自个家一样。我坐下来吃东西时,她拿着抹布开始收拾起来,看她气色不错,就知道她有好事,这个人,啥都在脸上写着。果然,她主动开口,说王格已经放弃对油漆配方的研制,再也不用往里投钱,并且,还认识了一个老板,是老乡,带着他到处干活,钱比以前赚多了。
这几年,我没见过王格,每次问起辛姐,她都不耐烦地说死了,或者说,躲债去了。吓得我后来也不敢多提。没想到,这个人终于放弃自己的执念,原本,他是想节约成本,不过,研究这么多年,没有名堂,倒投进去不少,能够放下,就是转机,这下,辛姐的房子,该有指望了吧。
我吃了两个卷卷,是豆芽鸡蛋猪肉木耳做的馅料,非常好吃,随口对辛姐说,你咋不开个早餐店,你这手艺,可比街上店里做的好多了。
辛姐正半蹲着擦沙发一角,听我这么说,一拍腿,说,哎呀,这主意不错啊。该开个店,虽然得早起,可来钱快啊。又问我,你知道哪里有门店?
我让她先别干活,索性和她一起研究起开店位置,又是百度开店知识又是想县城布局,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在主街道右手边,大菜市场口,是最好的选择,人流量多,位置非常好。辛姐高兴得就要回去张罗,我一把拉住她,说,你咋这么快性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给你问个人,确定一下那里合适不合适。
辛姐听话地坐下来,等我联系。我先给一个外地经商的朋友打电话,问了开店的选址窍门和注意事项,开了免提给辛姐听,她认真听着,一个字都不敢落下。我又给住建局的同学打电话,问她市场附近有没有合适的门店,同学说刚好有一家原来打饼子的店,店面不小,生意火爆,近来那家两口子要回安徽老家,所以门店空出来了,因为临街,现在,好多人都眼红盯着。同学开玩笑说,怎么,你这大作家,要下海?我回说你看我像做生意的料吗?同学说,那你问这个干啥?我急忙说,你要认识人,可操心想办法找人,给我留着,是,是我姐要开店。
辛姐在旁边热切地看着我。眼里的感激都快流到地上了。
同学说,好,你这么高冷的人都主动开口了,我还能不给你想办法吗?对了,是你什么姐啊,这么热心?
亲姐。我回答说。
你还有亲姐?你不是只有个弟弟吗?同学揭我的老底。
说亲姐就是亲姐,我耍起无赖来。同学说好好,就亲姐,也是我亲姐,行了吧?
挂断电话,辛姐已经眼泪汪汪了。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她哭,心里也不好受起来,想想她遭遇的各种事情,也真够不顺当的。活个人,咋这么难!
我以为辛姐要说什么感激的話来,谁知,她说,唉,我可欠你情欠得还不起了。一辈子都得给你当牛做马。
她一把把我的手拉到手里摩挲,表达感激,她手还是一贯的扎人,硬茧一处处硌着我的皮肤,我的心无端酸了起来。
说着容易,但真正干起来,已是来年三月份,辛姐公婆不肯帮着带孩子,一是要做数学研究,二来嫌这也不是亲孙女。辛姐在早点店放了玩具和童车,童车上拴根绳子,把小孩子放到里面去。小店开起来后,辛姐再也顾不上来给我料理家事,于是三天两头叫我过去拿吃的回去。炸油条,给我炸一大包,包子,是肉馅素馅分开各一包,她说我不爱出门,可以冻到冰箱里,一周吃完,下周再来拿,我知道她的脾气,要是不去拿,她肯定是非要想办法给我送过来的,于是每周我都尽量去那么一次,在她店里那六张桌子的其中一张坐下来,喝碗馄饨或者是老豆腐,陪她的女儿房房玩一会,再提着她早就给我包好的食物,悠悠回家去。
一晃半年过去。她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人多的时候,六张小方桌都会满满的,早上大家都赶时间,人流量大,每张桌子边的四个蓝色板凳上,有人起身出去,有人又填充进来。王格每天早上也来帮忙,做些收钱端饭抹桌子之类的活,付现金的大都是老人,年轻人一般都是支付宝微信,倒也省事。辛姐忙中有序,常常一边跟我搭话,一边在厨房烙葱花饼,一边还吩咐王格给客人端一碗黄澄澄的米汤出去。整个市场,只有她这一家早点店,加上样数多,味道好,人特别多。辛姐悄悄跟我说,钱赚得飞快。看着她忙碌不停的手和每次见面都肿肿的眼睛,我问她每天几点起,她说半夜三点起,发面,熬粥,做准备,中午前收摊做饭,饭后睡一觉,上班前起来给住的单位院子打扫卫生,给孩子洗衣服,做饭,忙家务。
太累了,我由衷心疼她的辛劳。
累啥?辛姐开心说,累也值。她两只手忙着炸油条,点头示意我靠近点,我凑过去,她悄悄说,已经在别人手里买来一块地基,准备自己盖房子了。
真的?我手里捏着的半根油条差点掉在地上。又高兴又意外。
真的。辛姐点头,咧嘴仰头笑起来。她对自己的缺陷,一向感到自卑,又经常因为性格使然,忘了这点。这会儿是得意忘形,也忘了捂嘴,也腾不出手来捂嘴,就这么不管不顾笑起来。
又带孩子,又开店,又要给单位每天打扫收拾,又要盖房子,我真是担心辛姐吃不住,这么多活,对于这个中年女人,可不是小事。她以前年轻点,眼睛大,脸蛋鼓囊囊,还有可爱的地方。现在,两颊陷下去,眼睛也经常布满血丝,真像个五十岁的人。她自己也经常对我说,自己老得快,有时她看看我,说看你这脸,认识你都多少年了,还是这个嫩样。
我开导说,你有老公有孩子,现在,就快有房子了,还羡慕我这个光棍干啥?
她哈哈笑,说女的也有光棍啊?
我说对啊,我是女光棍,以后老了,你捎带管管我。
她爽快一笑,说那必须的。
又说,那时不知道我在哪块地头上埋着,还得你给我烧香呢。
我一时无语,人生无意义的感受长久以来一直深植脑海,此刻,更是一片茫然。
夏天到了,我开始忙起来,县里新来一位县委书记,要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我受聘每周给县上撰写创卫中的人物和集体先进事迹。同时,要给省市媒体写专题文章,宣传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县城的巨大变化,因为忙,去辛姐那里倒比以往多,主要是去吃早饭,辛姐不收我的钱,我只好想办法悄悄扫她门口贴的二维码,知道她日子苦,我实在不忍心让她损失一点点。
我自觉做的是件对本地有益处的工作。的确,县城干净整洁起来,垃圾不乱扔,行人闯红灯的都少了,墙上和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小广告,也让志愿者们清理完了。县电视台和网站每天宣传这件事,县城满是浓浓的创卫氛围。连乡镇和农村,都动员起来了,城里村里都增加了健身器材,新买的几辆垃圾车放着祝你平安的曲子,每天下午六点钟,在县城各处定点收集垃圾,人们大袋小桶,从家里走出来,把垃圾拿到垃圾车上去。晚上,再也没有那些油烟乱冒的露天夜市,新搭起的一个定点蓝色大棚,足足有三百余平米,所有县城各处打游击的夜市都集中到这里,不许零散经营,门店牌匾重新整齐划一,一样的字体一样的大小,确保整齐,门店外面一律不许放任何杂物。
那段时间,到处冲突不断,事件频发。有一家门店老板把自己店里的笤帚拖把簸箕放到门外,不服从管理,让住建局的同志强行没收。还有个卖西瓜的商贩,拉着自家西瓜在市场口外面叫卖,住建局的人过去劝他把三轮车开走,他就是不听,工作人员要强行扣车,这个人拿出西瓜刀就要砍人。我当时正在附近,刚采访完住建局局长的工作事迹,局长赶去开一个会,所以这一情景他没看到,全程被我看到。住建局工作人员被追得满街窜,群众在旁边注目看戏,有一个刚买好西瓜的人不走,在三轮车上找到了一把小点的西瓜刀,把自己买的西瓜分而食之,递给围观的人吃,热闹极了。当然,最后邪不压正,在派出所同志配合下,该商贩被带走,车也被扣留。围观人群渐渐散去后,我一抬头,看到辛姐正在门口张望,估计是早看到我了,对我招招手,让我过去。
我这才发现,小吃店门口,也早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以前老豆腐馄饨汤锅,都在门口支着,现在,全不见了。跟她走到店里,发现厨房也没有,她这才解释说,因为管得紧,最近凉菜都不能在外面摆了,还把豆腐馄饨都撤掉了,油条因为有油烟,也不敢炸了。时间已近中午,辛姐慢腾腾地开始收摊,她的女儿房房在地上坐着,玩着一张皱巴巴的餐巾纸,她也不去理会。
快没生意了。辛姐说。
这么闹下去,生意没法做了。辛姐去抹桌子,接着跟我抱怨。
我拿起把扫帚,帮她扫地,问怎么王格没来。辛姐说,最近店里吃的样数少,客人也少了,她一个人能应付来。
我把垃圾扫到簸箕里,想到以前门外有个垃圾桶,刚要出去,辛姐却说,你干啥去?垃圾桶在厨房。
我这才醒悟,门外现在是不准放任何杂物的,垃圾桶当然不能放到门外,可是,放到厨房,也不是個事儿,客人进来,看看这环境,会怎么想?
辛姐叹息说,门口的牌子,本来是年后新换的,这不,非要求换个合乎规格的,还让去定点的店里去,还价都不行,花了八百五。
这么贵?
是啊,根本不让人还价。辛姐无奈地说。
你的房子,开始盖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辛姐。
开始了开始了。辛姐听到说房子,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不过她又说,现在创卫,说是不让动工建设,现在停着工呢,主体都起来了。快了,快了。
她又说,现在收入少了,停停工也好,这盖房子,处处都是要钱的。
听到这里,我有点心虚,没想到,这次县上创建卫生县城工作,给辛姐带来这么多影响,而我,还骄傲地参与其中,觉得自己做的完全是一件美好的事业。
唉,我也说不清楚,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好事,省市领导先后来县里参观过战果,对县委书记的工作十分满意,县上环境大为改观,领导讲话说,也许能吸引到前来投资的客商呢。虽然目前还没吸引到谁,不过,总归是有希望的,谁能想到,这件大好事,给辛姐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带来这么大的困扰呢。
正说话间,几个穿住建局制服的男女进来,三男两女,为首的我看着眼熟,想起是一个姓张的科长,以前找他要过资料。对方显然更熟悉我,客气地点头说,李作家,你怎么在这里,是还没吃早饭吧?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过他并不关心,转向辛姐说你就是辛爱爱吧,辛姐把手在围裙上擦擦,说对,我是。她警觉地看着这几个人,如临大敌。张科长说,我来给你说一下,这里要拆迁了,你这两天赶紧收拾东西搬走。我大惊,问怎么回事,张科长说为配合县上创建卫生县城,这个市场要整体修整,根据规划,市场最前面这个门面,因为临街,不符合美观要求。张科长指了指门口说,李作家你看看,如果说市场一个长方形,那么这家门店就像是长方形的一个边长长了一截。他比比画画,辛姐在旁边急了,说,我不搬,我不搬你能怎么着?
张科长说这间门店是要拆除的,你说了可不算。
辛姐还想说理,张科长跟我说了句还有别的事,就出去了。令我意外的是,辛姐快速往门边紧走几步,一把扯住张科长左边上衣的衣服袖子,大声喊起来,说你不能走,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让我马上搬到哪儿去?这装修和搬迁的损失谁赔?我马上到哪里找门面去?。
张科长面不改色,作为住建局的中层干部,估计这些事他见多了,给你一周时间,到时候不搬,后果自负。
说完,匆匆而去。
我过去扶住辛姐,她咬牙切齿,说,妹子,你说,我该咋办?你认识他们领导不?去找他说说行不行?
我不忍心拒绝她,可是也知道找领导没有用,这是县上定的,不是住建局一家单位说了算。这次拆除和重建的地方不是辛姐这一家,书记下了死命令,并且有理有据,谁敢违抗?
这时,我电话响了,是宣传部催采访稿,我不得不告辞,辛姐站起来送我,说你先忙,我再想想办法。
我匆匆离开了,第二天,因为核实一些数据,去住建局见局长。局长说有个女的因为所租门店要拆除到政府里闹,影响极坏,被派出所带走了,我问是谁,局长说,开早餐店的。
采访结束,我又写了差不多一周的稿子,才稍微有了点时间。给辛姐打电话,没人接,又跑到市场上看,门店已经被拆掉了,只有一片废墟,我走过去,看到地上一角有一块写着字的东西,拿起来看,是个残缺的房字,那不正是辛姐花八百五新换的牌匾上的房字吗?房房早点四个字,像一个气泡般,暂时毁灭了。
辛姐有好久没联系我,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埋怨我没有能帮助她,随着发稿增多,找我写稿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报酬也算可以,我于是又陷入新的忙碌中去。这样,到县上创卫成功结束时,我已经是三个月没有见过辛姐了。
一个周六,我望着许久没打理的衣橱,想着把厚的衣服拿出来,把夏天衣服收拾起来。这对我是一项大工程,这时,我听到有人正在外面用钥匙开门,我心里一喜,是辛姐,来得太是时候了。但随即,又觉得自己脸皮太厚,这么久没有联系她,还只想着让她帮忙干活,真是太自私。
辛姐已经推门进来,她神采奕奕,眼睛明亮,仍然是那个很有精神的辛姐。我问她这么久干吗去了,她说自己最近交到好运,忙着迎接。我放下手中正在叠的一件白衬衫,连忙问怎么回事。她高兴地说,那次去政府里闹了闹,被派出所带去,她当时说不闹了,回去把店里的东西都搬回家后,第二天又去找了政府,趁着他们没提防,又大闹一场。
我说,政府楼十几层,还有保安,你能进去?
那哪能进去?辛姐撇嘴说,我只能在政府楼下闹,连一楼大门都进不去。
她说,反正我说了,不给个说法,我就天天来闹。后来是住建局的人从政府楼下面用小车接走的我,给我退了房租钱,虽然没给我找下合适门面,但是给王格找了好多活,反正到处都要建设,他带人去干活,赚了不少。
我问,人家能及时给你结账吗?
辛姐说,对上班的人,公家有办法,对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公家可没办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又不用提拔,又不怕开除党籍,敢不结账,我就跟他们闹。
看看我有点担忧和意外的神色,辛姐说,你别怕,我也不是做过分事,该给我的东西,正常给就行。
辛姐说完,推开还在发愣的我,说快靠边站,这些活,我三下两下就干完了,你干呀,三天都弄不完。
我感激地看着她,正如她所说,她干活真是一把好手,衣服叠放整齐,归置有序,我根本插不上手。我问她小女儿谁看,她说送幼儿园了。我说,那么小,人家收?辛姐说,公立的不收,私立的收了。早上送晚上接,房子那边又开始干活,顾不上管她。
太好了,我真心为她高兴。
多会能完呀?到时候我去看看。我说。
她说,创卫检查组走了才开始重新动工,还有点活,这几天加紧干,因为快入冬了,冬天不方便干,要抓紧提前多干点,来年春天肯定全部完工。
到时候你来,她兴致勃勃,一说房子,她就有劲头。
四月,辛姐的房子落成,我按照辛姐电话指引,走到她新家附近,却又被一个紧急电话召走,没见她面,直到次日上午才又去。路上,遇到分管住建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达和住建局的局长副局长一干人,正在辛姐家房子附近指点江山,我过去打了个招呼,住建局局长问我怎么在这里,我说一个朋友搬家了,过来转转。又笑说现在县城已经改天换地旧貌换新颜,你们这又是要干啥,局长哈哈一笑,说大作家这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吗?我说岂敢岂敢,他转为一本正经豪迈地说,这片要拆了。我说哪里?哪片?局长说就你脚下这里,他一挥手,指着前面一排房子,说,这些都要拆,我说拆了干吗用?局长说,建学校,这个是大事,县里要把目前的两个中学合成一个,把优质教学资源集中到一起,争取让来年教学质量提升,中考成绩提上去。
这时,李达书记已经走远了一些,局长赶紧和我告辞,急急跟过去,我站在原地发呆,腿都有点发软,嗓子发干。辛姐迎面走过来,说,妹子,你咋到家门口还愣着不进来?我不甘心地问,就是这里吗?她说,对呀,两步就到。
说话间,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着,进了一个巷子,我心里一凉,这里,就在刚才局长说要拆的范围。
房子不算大,有个小院,种着各色的花儿,我认识其中有仙人掌和吊兰,院子里还垒起了一块水泥菜地,辛姐说已经买好小葱韭菜菠菜种子,要自己种菜吃。进门后,屋子清洁利落,沙发垫子都铺得没有一个折痕,地上,桌上一尘不染,卧室里铺着崭新的床单。不过,家里电视机冰箱等电器却是旧的,辛姐说,将就着用吧。
我在客厅坐下,说,你收拾这么干净,哪个敢坐啊,这不是要撵人吗?辛姐又咧嘴笑起来,畅快得很,因为舒心,连模样都变好看不少,给我递茶后,说撵别人也不能撵你呀。
我问起原来住的那个小屋,辛姐说,正要跟你说呢。已经跟人家单位退了,领导很好,说反正没用,我住着也行。可我不能占人家的地方,自己有了房子还贪图公家的东西,那可不行。
我心里暗暗替辛姐着急,小屋退了,现在这届领导是最讲究雷厉风行,一旦要拆房,辛姐可往哪里搬,又能获赔几个钱啊?
辛姐非要留我吃饭,说要给我包韭菜馅饺子,我找个借口,坐一会就告辞了,趁着她去给水杯添水,想把给她暖房的五百块钱放在沙发垫子底下,没想到她看到了,非要让我拿回去,直到我跟她变了脸,才不好意思收下。说,妹子,你帮我这么多,可不该再给我放钱,人到了,姐就高兴了。
辛姐和我一起出来,说去接孩子,她的小女孩房房已经上大班了,王格天天在外头揽活干,要把以前研究油漆配方和盖房子的钱还了,所以常不在家。
我试探着问,你公公婆婆呢?
回老家了。辛姐没好气地说。
以后不来了?
还来做什么?她口气还是愤愤地。
不过,她存不住话,又说,搬了家,倒是打電话让他们来住的,人家说年龄大了,以后就在那边老死,不跑了。
谁打的电话?我问。
老王打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辛姐叫起王格老王,我们走在外面,有认识她的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媳妇,叫她姨。我一吐舌头,说,这么大人叫你姨,你有那么老吗?
咋不老?辛姐两只手把自己脸拍得啪啪响,我一把拉住她的两个手,批评她说,你怎么使这么大劲?我都听到响声了。辛姐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手和脸都老了,皮肤厚,哪里会疼。
她的手握住我的手,硬硬的茧仿佛真的比先前更厚,我心里再一酸,挣开她的手,扭头走了。
我不敢回头看她的新家,不敢看大门和大门口那红艳艳的对联。不知什么时候,眼泪早已顺着脸颊落下。
半个月后的一个大早上,我去政府办事,正看到一个妇女带着个小女孩,正突破两个保安的围追堵截,往政府楼里面冲。因为还早,并没有几个围观的人。四个人撕扯成一团,我看到妇女和孩子的正脸,正是辛姐和女儿房房,辛姐没有看到我,此刻,她头发乱做一团,嘴里高声叫喊着什么,正和一个胖保安推搡,小小的房房拉扯着另一个保安的胳膊,正用力咬下去,随着啊的一声惨叫,辛姐和房房已经取得最佳战机,飞一样先后冲进大门,跑进楼里去,瞬间,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
【作者简介】李瑞华,山西古县人。山西文学院第六届签约作家。有小说、诗歌、散文散见于《中华文学选刊》《山西文学》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