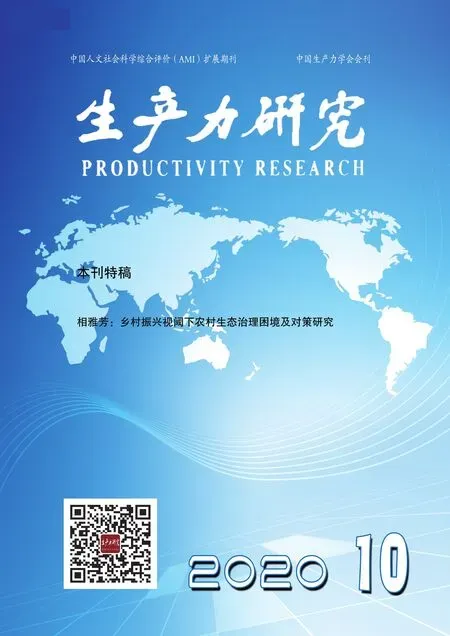国内失地农民的地方感、身份认同与发展能力转型研究
2020-11-19
(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作为城镇、工业化的伴生群体,失地农民规模数量不断上升,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CNKI中关于“失地农民”的研究最早始于2002 年,其研究数量趋势与城市化数量研究趋势基本吻合,在2003—2007 年研究数量上升最快。而利用“失地农民”“生计”作为主题及关键词检索时发现近十年关于此内容的研究与2000—2010 年相比更趋向于从失地农民自身出发,着重考虑其生计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自2015 年以来,关于失地农民心理状况的学术关注度升速较快,如2016 年关于失地农民适应性研究中文文献环比增长率为150%,关于失地农民心理状况学术关注度环比上升300%,由此可见,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正逐渐由宏观向微观转变。基于对上述已有文献研究趋势的思考,认为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在于使其产生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资本和政府一次性安置补偿金的能力,为此则须使失地农民适当减少其原有的土地依赖,明晰其身份的最终去向。故选取“地方感-身份认同-发展能力转型”作为整理国内现有文献的思路。
一、失地农民的地方感——精神的慰藉或物质的束缚
“地方感”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通常用来反映人与空间的种种物质和精神联系(杨振山等,2019)[1]。由于乡土中国是“耕种的农民”的社区(王雅林,2015)[2],对于农民而言“乡”与“土”既承载着物质空间的积累,也包含着精神空间的支撑,并与其产生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感就自然成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特有的情感连接纽带。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规模不断扩大,长期植根于农民心中的“地方感”可能会发生动摇。但考虑到社会是一个“异质共存”的组织体系,具体表现为既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人群,又处于同一个社会“屋檐”下的“共同性”生活,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中,需要重新研判这样的“地方感”究竟是精神的慰藉亦或是物质的束缚。

表1 2000—2020 年国内失地农民文献主题及数量
我国对“地方感”的研究起步较晚,1974 年段义孚提出“恋地情节”这一表述[3],用来表达个体在自然环境中的情感感知。目前,着眼于旅游学视角的地方感研究在国内关注度较高,有部分研究通过分析“主客”之间的地方感差异(吕龙等,2019;邱慧等,2012)[4-5],从而提升旅游地对游客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孟令敏等,2018;唐顺英和周尚意,2013)[6-7]。
有研究通过对比失地农民与未失地农民在满意度、根植性、土地依存、归属感和社交认同五个方面的差异确定失地农民的土地依赖和地方依赖情感,结果表明,未失地农民的土地依赖和地方依恋均强于失地农民,并且失地农民归属感整体较弱,且存在学历、年龄、收入方面的差异(薛东前等,2019)[8],正是因为生活环境的迁移影响居民对地方的记忆与情感,而地方依恋和社区认同的丧失,可能会对年轻人产生负面影响(孔翔等,2015)[9]。与此同时在现阶段,城中村移民地方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上(朱竑等,2016)[10],这就说明虽然“家”的空间发生迁移,但经济资本才是“家”的营建所必须的物质本底(尹铎等,2019)[11]。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逐渐扩大“地方感”研究的范围,但是关于失地农民地方感的研究鲜有报道,从现有文献看,农民在离开土地后的地方感会日益衰退,且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结合我国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背景,城镇化行为大多建立在相互协商之上,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协商后保持积极心态迁移进城的失地农民群体渴望融入甚至扎根于城市(顾朝林和李阿琳,2013)[12]。可见,地方感可能会在失地农民心中主动或被动消减,失地农民在自身生计资本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寻求新的生计策略。基于此,绘制如图1 所示的韦恩图,对于尚未完全失地或年龄较大的失地农民,地方感是一种文化脉络的传承和内心的寄托,且会产生代际传递,故对于中年群体而言,既承载着老一辈群体的传统文化,也有着迫切希望融入新群体下的地方感,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来满足生存需要,但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仅留存少有的传统“地方感”,而新的环境更富有新引力,因此,此前产生的地方感可能会成为物质空间的羁绊从而被淡忘。
二、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城里的乡民或农民的终结
身份认同通常是指个体在社会中通过与别人的差别确立和认证自身[13],因此,这样的认同不仅源于自身,还延伸于整体社会环境,即一个完整的认同活动既包括内化环节也包括外化环节(陈新汉,2014)[14]。纵观已有文献,身份认同的关注对象主要为处在身份转变或环境变迁过程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如新生代农民工(张淑华和范洋洋,2018;张明斗,2015)[15-16]或农民工随迁子女(罗竖元,2014;栗治强和王毅杰,2014)[17-18]等。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失地农民群体间产生分化,地方感发生动摇,在此背景下,失地农民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必然受到影响,该群体面临着究竟是城里的乡民还是农民的终结的困惑。

图1 失地农民地方感代际差异
失地农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可在各代际群体之间产生分化,老年、中年和青年群体年龄与身份认同程度呈反比趋向,具体为老年一代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呈现明显的“内卷化”特征,中年一代为“边缘化”特征及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市民化”特征(汪小红和朱力,2014;叶继红,2013)[19-20]。也有研究认为身份认同与空间感知存在联系,将失地农民的空间感知分为物理生存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及经济生产空间三部分,由于这三个空间的失序,造成存在“身份判断模糊——身份归属矛盾——身份感受焦虑”等问题(王晓刚和陈浩,2013;崔波,2010)[21-22]。由于身份认同是个体的重要惯习,因此除了上述空间感知转变的不一致性以外,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也有着自己的建构逻辑。因为社会记忆既具有个人选择性,也存在制度保障性缺失,因此会使失地农民产生角色转换的困境(姚俊,2011;雷辉和邓谨,2016)[23-24]。
综上所述,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具有建构性与被建构性的双重特征[25],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冲击,也与其自身的内部因素息息相关。基于上述文献可总结出,失地农民中的年轻群体,因其教育背景、交往场域发生变化,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会趋向于农民的终结而日趋市民化,与之相反,老年群体带有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情感,即使生存场域发生改变,但依旧将自己认定为城里的“乡民”,而处于中间阶层的中年失地农民,兼顾着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容易陷入身份认同的模糊困境中。
三、失地农民的发展模式——内源式发展或外源式发展
国内关于失地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大多可分为:第一,基于DFID 模型创建的五大生计资本(陈玉兰,2016;王岩等,2010)[25-26],认为失地农民的发展能力与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相关;第二,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且认为现阶段失地农民就业发展能力开发不足(陈琼和贾凤伶,2017;吴春和朱美玲,2012)[27-28]。根据上述对失地农民发展能力的归纳大致可以将其总结为自身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能力两类。由于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会得到一定的征地补偿款,即时体现为失地农民的“财富存量”,相关研究证实失地农民的家庭资产选择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投资风险偏好和金钱稀缺感及心理账户的认知标签、情绪标签影响其家庭资产选择(李岩,2020;李岩等,2019)[29-30],基于上述内容,为解决失地农民现有困境下的发展模式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有学者表明,失地冲击加剧了福利分布的马太效应(周义和李梦玄,2014)[31],从而使失地农民陷入因内外部原因形成的发展困境中,因此,有学者提出与内源式发展模式相比,外源式发展模式之于失地农民生计困境仅存在短期效应(吴春和朱美玲,2012)[32],也有学者认为处于“社会排斥”的相对剥夺状态下(杜书云和徐景霞,2016;杨晶等,2019)[33-34],更需要在政府导向下,构建一种失地农民集体导向型社区(宋辉和郝龙,2013)[35],除此之外,在失地后亦会产生一部分满足型自愿失业农民群体,该群体的特征是在获取失地补偿金后丧失健康生活理性,不愿意再参加生产活动,尤其在“拆二代”和“征二代”中体现较多(贾海刚和孙迎联,2020)[36],为避免该类群体产生次生贫困,政府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归纳和总结,外源式发展路径和内源式发展路径各有其优势和劣势,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农民失地初期,由于其自身生计空间发生变化,前期需要政府主导下的外源式生计空间重塑,适时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培训及相关保障措施,而当失地农民过渡到中后期,则需要依靠失地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加以补充其生计空间的牢固性,保障其后续可持续发展。
四、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研究人员关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崔红志,2019;杨琨和刘鹏飞,2020)[37-38]、征地补偿安置(李中和彭魏倬加,2019;周义和李梦玄,2014)[39-40]以及就业问题(刘昊觊,2019;邵爱国等,2018)[41-42]研究颇多。而对于失地农民地方感、身份认同及发展能力方面研究相对较少且三者处于各自为阵的相对孤立局面。而本文通过“地方感、身份认同与发展能力转型”的路径来梳理失地农民相关文献,采用这一路径是考虑到失地农民自身的心理空间与外部物质空间的内在逻辑性。具体来看,失地农民的“地方感”可能会在失地后发生动摇,长此以往,难免会影响对于自身定位的身份认同,为避免失地农民难以适应新的身份难以融入新的生活,就需要帮助他们形成相互包容、相互认同的“地方感”,以此帮助失地农民构建新的身份认同并利用失地农民禀赋优势的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失地农民的发展能力转型。结合上述文献总结,失地农民群体会在失地冲击后出现整体地方感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及身份认同不明晰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会在失地农民群体之间出现分化,分化的主要原因是代际差异,而关于失地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既与失地农民自身能力禀赋有关,也与外部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有关,最后按照文献内容总结构建出失地农民发展能力转型路径图,为失地农民的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图2 失地农民发展能力转型路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