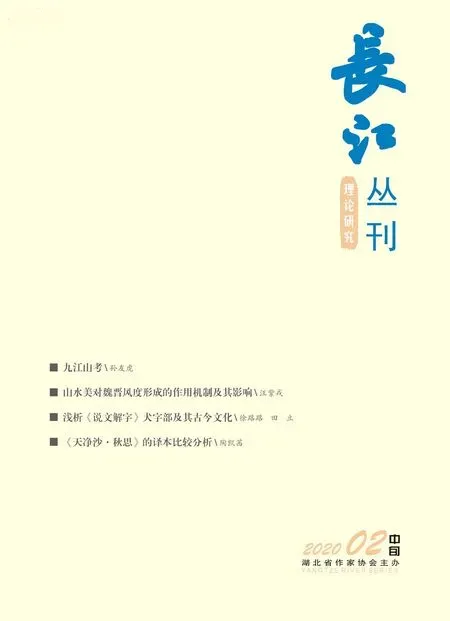交织在平静温和中的人生悲歌
——集体无意识下的《萧萧》
2020-11-19丁笑涵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丁笑涵/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讲述了童养媳萧萧在旧中国童养媳制度下懵懂,无知,跌宕的一生。她十二岁坐着花轿来到夫家,照看着像弟弟一般大小的还在吃奶的“丈夫”,日复一日延续着如此童养媳的生活,却在春心萌动的年纪受人蛊惑,险些落得沉潭发买的悲惨下场。文章以萧萧跌宕起伏的一生,表现出了在人们潜在意识下不予排斥的童养媳制度。这种集体无意识下的童养媳制度造成了成千上万个萧萧的悲剧人生。
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观点是指,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如对罪恶的集体失语,对不良现象的集体麻木,对违法事件的集体参与等,鲁迅《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就是封建社会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牺牲品。在《萧萧》中反映出来的集体无意识,更多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生活记忆与行为模式,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民族劣根性的真实写照。
悲剧之所以为悲,与肉体与心灵抗争的失败,人性的泯灭与丧失有着直接关系。而集体无意识社会下的悲剧形成,则是外来者对于其集体无意识的解读,处于集体无意识下的人,会把如童养媳制度此类不合理制度作为吃饭睡觉一样的常事,没有反抗意识,他们的悲剧看似是童养媳等此类社会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如失贞者沉潭,发买等的悲剧,实则是集体无意识下无法认知悲剧的悲剧。在《萧萧》一文中,集体无意识的悲剧在婚姻的循环往复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出嫁——集体无意识下婚姻的懵懂
萧萧十二岁就做了夫家的童养媳,在别的新娘子都哭的年龄,她是为数不多做媳妇不哭的女人。常言道 :“ 初生牛犊不怕虎”,亦是不知虎的可怕,意识不到虎的危险,这种“不怕”即是无意识的表现。萧萧是从一个疾苦生活的泥潭跳入了另外一个不被认知的泥潭。这个泥潭,在外界的读者看来,就是做童养媳的不幸人生,这种无意识致使萧萧在花轿之上也抛弃了哭泣的想法。懵懂无知的萧萧到了夫家后,白天抱着不到三岁的小丈夫在别处玩耍,劳作,晚上做着些自由自在的梦,尽情释放小孩子的天性。白天的她是童养媳制度下的一份子,他的责任就是把小丈夫养大与他结婚。晚上的她则恢复了孩童的天性,做着像鸟像鱼的梦,自由玩耍,不被束缚。她从本性上来说,还是一个孩子,做童养媳的她只是无意识的对其他童养媳举动的重复,对童养媳制度与文化无意识的践行。只有在晚上她才可以在梦中释放作为一个孩童原有的想象力,表达自己对于一些事物的喜爱与羡慕,在心灵上突破传统意识观念,陈旧的思想牢笼,用这种潜意识的方式弥补自己无法实现之事。这种平静温和中的身体与心理的异化,有悖于人的自然生长规律,而集体无意识下的童养媳制度则是造成心灵与身体异化的最主要原因。童养媳制度下的成千上万个萧萧,毫无怀疑的认为出嫁是“照例该哭哭”“唤丈夫为弟弟”的诸如此类约定俗成之事,并无真正的爱恨情仇可言,只是理应如此便如此了。相对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境地并无抗争意识。
二、出逃——集体无意识下妥协的自救
萧萧在对爱情最懵懂的年纪,受了花狗的诱惑,一天天肚子大了起来。对感情还是一片空白的萧萧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糊里糊涂,不该去做的事,直至肚里有了变化,她才觉得这是不可磨灭的罪证。她清楚的知道对于婚姻的背叛,会让她落得什么下场。还是一个孩子的萧萧,出于对这些事物的畏惧,使她做出一系列看似荒谬的自保行为。食香灰,喝凉水,用一切她能够想到的不为人知方法,守住这个秘密,与肚中不该存在的东西分离,给自己一个生存的机会。萧萧的出逃,并不是对于千百年来童养媳制度的反抗,而是出于对这种制度的敬畏,对于死亡的恐惧。萧萧的无意识是对于反抗童养媳制度的无意识,在童养媳制度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存在于童养媳制度中的她认为这一制度合情合理,自己背叛的做法才是不予原谅的行为。花狗的诱惑使得她不得不在生存还是死亡选择的关头进行思考,她想要活下去,这种活下去的想法促使了她的逃亡,这时的她甚至没有想到去反抗。萧萧是集体中的个体,他在整个集体的无意识中,即便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也不会对困住自己的童养媳制度产生一丁一点的怀疑,在他的思想中,童养媳制度就是合情合理的,将自己的丈夫养大,是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常事。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深知自己犯了错误的萧萧为了活下去,她选择了跟着女学生,一起“逃跑”。这种变相自杀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于童养媳制度的顺从,她是无法摆脱陈旧思想,集体无意识下的一员,同时也是生死在其中,没有反抗意识的一员。不想死和怎样活成了萧萧在集体无意识童养媳制度下对于生命的有意识的思考。
三、出嫁——集体无意识下悲剧的循环
重男轻女是中华民族发展流传下来的落后思想,也是那个时期湘民的普遍思想,他们指望着儿子传宗接代,将自己的血脉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怀了花狗孩子的萧萧因为自己生了男孩,男孩可以充当壮劳力,而免去了被发买的命运。没有被发卖的萧萧依旧难脱童养媳的命运,她要继续完成养大自己的小丈夫并与他完婚的任务。几年后,萧萧为自己的小丈夫生了儿子,进而从童养媳的身份转化为了媳妇的身份。沈从文在文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在读者感叹萧萧童养媳身份结束的同时,又让读者看到了童养媳制度的延续,从中产生新的思考。萧萧与花狗的儿子牛儿,十来岁时,又到了娶妻生子的时候。萧萧抱着小儿子毛毛,站在街边看热闹,看新娘子“照例哭哭”来到门前,成为自己儿子的童养媳,成为下一个自己。从萧萧成为童养媳到萧萧的儿子牛儿娶妻,新的童养媳哭哭啼啼地坐着花轿来作个小媳妇,正好形成了一代的循环。这既是生命传承意义上的循环,又是集体无意识下童养媳制度下无所被认知的悲剧的循环。这些像萧萧一样的小媳妇们,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上辈的行为与活动,她们虽然在表现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坐花轿时萧萧没有哭,而新媳妇儿却照例哭哭,哭与不哭的差异并不是对于童养媳制度意识的觉醒亦或是反抗。“不哭”,即是无意识,“照例哭哭”是对于如萧萧一般大的那些作为童养媳的上一辈湘女的举动的重复,亦是无意识,这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这些举动和行为也印证了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理论中所阐释的,这是一种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
四、结语
纵观小说,沈从文用清新自然的笔调书写淳朴的湘民,剪辑出萧萧的故事作为童养媳制度流传的一个缩影。萧萧的故事本身是一个悲剧,因为她深陷童养媳制度之中,但与此相比,她深陷悲剧之中而不自知,就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以小缩影来看大社会,萧萧是个悲剧,成千上万个萧萧就构成了湘西地区童养媳制度普遍存在下的悲剧。湘民淳朴友善,他们一直在自己自然平静的小世界里安分守己,甚至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新鲜发展的力量采取了敌视和嘲笑的态度,这种无知,愚昧的表现从侧面印证了在他们的世界里,童养媳制度的合理性。他们麻木的按照旧方式,旧习俗去思考,不知不觉间便成为了杀死同胞的无意识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被传统的思维禁锢着,已经丧失了接受新思想的能力。这种本能的排斥,让他们在陈旧的制度下做个“陈旧”的人,毫无新生的萌动思维的力量。对己对人的双重压抑,从内到外的确定了其悲剧的不可避免性。集体无意识的举动为他们奏响了一首平静温和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