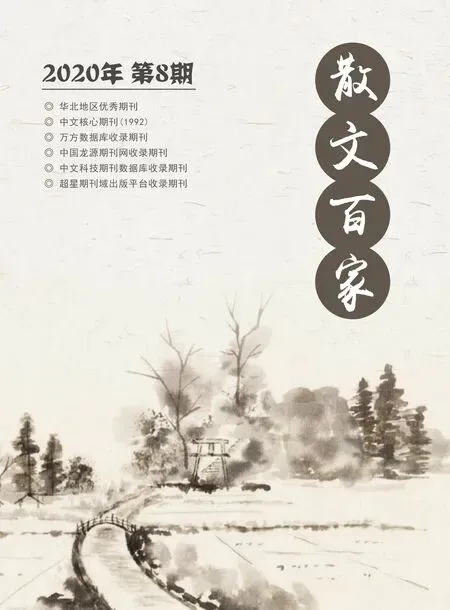狂欢的看客与被遗忘的苦难
——评《檀香刑》
2020-11-19李青璇
李青璇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无法逃离“看与被看”这一问题。而莫言在《檀香刑》一书中,通过塑造赵甲、孙丙、赵小甲、孙眉娘、钱丁等形象,将看客心理和示众文化以一场酷刑血淋淋地剖开在读者面前。莫言在小说中通过赵小甲的“呆傻”视角,构建了独特的动物性感觉世界,并插入猫腔的唱词,天马行空地叙述着这场极其残忍的檀香刑。而在语言上的陌生化处理,更是让文中世界带上了魔幻的色彩。充满“先锋”色彩的《檀香刑》,不仅是充满挣脱宏大政治叙事的倾向,极具后文革时代的风格,更是对文革游街批斗,乃至数千年前封建王朝时期形成的示众文化的批判思考,在莫言的笔下,给读者以心理冲击的不仅是残忍的公开行刑场面,更多是源于看客在观看酷刑时病态的狂欢心理。
莫言将《檀香刑》一书分为凤头、猪肚、豹尾三部分,凤头部分将四个主要人物的言语特点作为小标题,“浪”“狂”“傻”“恨”四字分别概括出眉娘、赵甲、赵小甲和钱丁四人的个性特点,眉娘风情万种,看不上痴傻的丈夫赵小甲,倾心于儒雅的县令大人钱丁;眉娘的公爹赵甲则算是刽子手这一行当里的状元,精通历代酷刑,并且自己能够发明出新的刑罚方式,在对孙丙执行檀香刑时,甚至将行刑过程视为一场不可出错的艺术表演;赵小甲是书中少有的“清醒”人物,在他的“痴傻”视角里,父亲赵甲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豹子,妻子眉娘是一条水桶粗细的大白蛇,县令钱丁则是一只大白虎,莫言对语言进行陌生化处理,通过赵小甲的视角撕开人类为自己描画的高尚表皮,以赵小甲之口说出“知道人的本相就没法子过了”揭露人类内在动物性的丑恶;而钱丁在书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既有读书人的责任感,为民着想,却又深受封建士大夫观念影响,对着上级官员有着天然的顺从和敬畏心理,在做涉及个人利益的决定时犹豫不决,众多因素的影响最终造成了钱丁的结局有着典型封建士大夫的悲剧性。
故事发生在1900年,以“施刑”为主线,通过描写高密东北乡的人事物,串联起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德国殖民山东等一系列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凤头部从眉娘偷情一事延伸牵出人物间的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猪肚部分集中爆发,钱丁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眉娘与钱夫人代表的女德与女色之间的矛盾、孙丙身上的反抗性与被动性的对立,都在一步步推动着“施刑”高潮的来临。在这场刑罚中,赵甲是刑场舞台上的艺术家,由他来主导整场表演的节奏,孙丙是刑场上的戏子英雄,也是整场表演的主角,他的一举一动,是对行刑技术最直接的反馈,而观刑的人们,虽然在故事中鲜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他们早已自觉形成一个群体,一个可以向外传递同一声音的群体,他们的反应是这场刑罚精彩与否最根本的评判,也是看客们,带来了狂欢式的刑罚场面,将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悲伤时刻变成一群人的狂欢。
看客们的狂欢虽在书中着墨不多,但却是文中无法忽视的一股复杂力量,弱小的个体只能够是封建权威和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但当无数个个体集结在一起形成庞大的群体,欣赏不幸的受害者时,他们仿佛又拥有了身居人上的满足感。封建权威的压迫,异化着社会上所有的参与者,如果说赵甲身为刽子手,还需要通过不断强化自己的忠君思想来提高执行酷刑的道义合理性的话,台下的看客们则更是轻松,根本无需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谴责,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引导受害者犯罪,也无需亲自动手结束受害者的生命,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评判刽子手的技术和这场表演的完成度,如同赵甲的师父余姥姥所说的:“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观赏着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平庸的个体仿佛能够通过欣赏酷刑逃离成为封建权威受害者的命运,并将群体仇恨转移到被行刑者的身上,倚靠着压迫自己的封建君权嘲笑“输家”。相较于鲁迅笔下的看客表现出来的麻木冷漠,莫言所创造的看客是狂欢的,而这样的狂欢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失智”的表现呢?
看客心理并没有因为封建王朝的崩塌而消失,这种欣赏别人悲剧以减轻自己痛苦的心理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并且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曾经有在广场催促轻生者“赶紧跳”的看客,如今也有在网络上敲着键盘对陌生人极尽恶毒之语的“键盘侠”,屏幕对面的陌生人成为了看客们发泄生活不顺心的垃圾场。而看客们之所以能够随意地选择一个受害者接受自己的怒火,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缺少对苦难的同情心,缺少对生命的敬畏。而对弱者没有同情,对苦难缺少感知,让苦难已不再是一个人的罹难,而是整个时代的顽疾。
《檀香刑》里是孙丙经历了妻儿被德国人残杀,自己又被执行檀香刑,他的一生无疑是充满苦难的;《活着》中福贵颠簸一生,到了晚年仍然要面对唯一亲人的离世,他也度过了充满苦难的一生,作家们描写苦难并不是让读者在对比中感受到幸存的快乐,而是让读者理解,苦难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对于一条生命的冷眼旁观,可能会带来一个家庭的丧子之痛和另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看客的冷漠是恒定不变,但组成看客群体的个人却能够有意识地去改变自己,主动打破冷漠的高墙,主动向温暖靠近,当人们靠近了温暖,感受到生命的脉搏时,自然也会产生不忍破坏的恻隐和对苦难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