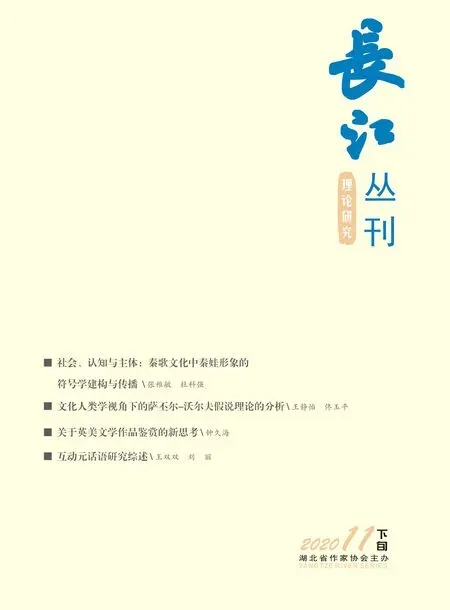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2020-11-19郭一建曲靖师范学院
■郭一建/曲靖师范学院
20 世纪初,随着性科学的确立,性科学研究成果为性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知识基础,才使得性教育成为科学的性教育。性教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到20 世纪60 年代,现代科学的性教育才基本得到公认,并开始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胡珍,2011)。性安全教育是指通过向学生介绍性生理、性心理和性的社会基本特征等教育来帮助学生正确和全面认知“性”,从而消除学生对“性”的神秘感及错误观念,以此来预防学生在性健康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升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的一种教育理念与方式(徐亚吉,门从国,2010)。儿童性安全教育是现代科学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儿童性安全保护的重要途径,对儿童性健康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骋,张秀娟等,2017)。
一、儿童性安全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儿童性安全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儿童性侵害(Child Sexual Abuse)的频繁发生与深远危害来说的。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率先开始研究儿童性侵害现象,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紧随其后(杨倬东,杨欢,2015)。Paul McPherson 等(2012)认为儿童性侵害是发生在成年与未成年之间或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单向性行为,包括以强行或诱骗的方式对儿童实施接触与非接触的犯罪行为。Mark W.Mitchell(2010)和Maureen C.Kenny(2008)分别实施的调查研究表明:1/4 的女孩和1/6 的男孩在18 岁以前都受到过性侵害。Ismail Yahaya 和Joaquim Soares(2012)发现受害人因担心事件暴露一则会伤害他们的父母,或不被他人相信;二则更恐惧施暴者采用极端的方式威胁报复自己,因而选择了沉默,这就为儿童性侵害事件的持续高发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Mark W.Mitchell(2012)还指出在受害男性中,超过80%有虐物的经历,50%有自杀的想法,超过20%有过自杀行为,几乎70%接受过心理治疗,近30%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可见,性侵害事件对儿童及其家庭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就奠定了儿童性安全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儿童性安全教育陆续得到西方国家的推广与普及
第一,立法层面:上个世纪4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州法律就要求对性犯罪者进行注册、登记与公开,来达到一定的警醒作用。9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又开始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立法来保障儿童不受性侵犯(孙秀艳,2009)。英国在20 世纪末开始实施国家课程时,就已经在科学课程中引入性与生殖健康、青春期发育等方面的教学内容。2017 年3 月,英国政府还提交了《儿童与社会工作法》(Child and Social Work Act)修正案,强制英格兰所有中小学校开展性和两性关系教育。另外,英国教育部还认为在小学阶段性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促使儿童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保护自身安全,保障身心健康(李碧静,2017)。第二,学校层 面:Juliette D G Goldman(2005)发现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通过多种教育项目传授儿童预防性侵害的知识,并且通过增加教师参与学习关于儿童性侵害的知识与技能,来帮助儿童提高性安全意识与能力。第三,家庭层面:Ismail Yahaya 和Joaquim Soares(2012)还 发现父母积极参与学校开展的性安全教育项目可以间接地降低儿童性侵害的发生程度。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儿童的积极参与,Maureen C.Kenny 等(2008)研究发现,参与自我保护项目的儿童在避免性侵害的知识与技能以及辨别潜在的性侵害行为方面有着显著的提升,特别表现在自我控制感与自我表现感的增强。从宏观系统角度分析,国外儿童性安全教育得到了领导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大力支持,不断完善的立法、专业化的教育措施以及发生主体及家庭的积极参与,都构成了一个人本主义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系统,这一点是值得十分肯定与借鉴的。从具体社会实践角度分析,国外儿童性安全教育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外性文化与性习俗,因此,探索适合我国本土化的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
三、儿童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可与初步发展
刘文利在其《1988—2007: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早在1988 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性健康教育被正式纳入我国中学教育内容。从此时期开始,我国性健康教育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具体为:(1)第一阶段:1988—1993年。这一阶段,我国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颁布了八项法规或纲要性文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并开设相应的课程,规范性教育三个重要方面的内容:①性生理方面;②性心理方面;③性道德方面(朱广荣,季成叶等,2005)。(2)第二阶段:1994 年至今。这一阶段,国际形势对我国青少年性教育政策方针产生了巨大影响。刘文利(2008)指出尤其是1994 年9 月,在开罗第三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发表的《关于国家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该《纲领》明确指出积极满足青少年教育和服务要求,促使青少年负责任地面对性的问题。随后我国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不断完善政策方针。胡珍在其著作《性爱·婚姻·家庭——大学生性教育》指出2008 年12 月1 日,教育部通过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性健康教育”相关内容纳入健康教育的大框架内,并对中小学校所要完成的性健康教育指标做了详细的规定。刘文利在其《学校如何关注儿童的“性安全”——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性教育全面缺失的反思》一文中也指出2011年7 月30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在发展“儿童与健康”的“策略措施”部分明确提出了大力加强儿童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为适龄儿童青少年提供相应的教育与服务,满足其成长发展需求。相关《纲领》与《纲要》的制定与颁布契合了我国社会背景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为进一步探索儿童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持续化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政策保障。
四、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特殊性促使性安全教育机制迫切建立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家庭监管的缺失、学校教育的缺位、社会功能的影响,使得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屡有发生,因此探索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各界学者高度重视的新问题(蒋平,刘燕,2012)。李桂燕(2014)于2013 年7 月至2014 年7 月通过文献调研、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在山东省留守儿童比较密集的德州、泰安、济宁和菏泽等地开展关于留守儿童性侵害研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直接监护,年龄小,社会经验不足,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够是留守儿童易成为性侵害对象的直接原因,同时又受到农村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的间接影响,迫使留守儿童无法直面所遭遇的性侵害事件,进而给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带来深远影响。曹晋和薛跃规(2017)针对广西偏远地区927 名留守儿童和61 位教师开展调研,研究发现广西偏远地区留守儿童的性保护意识基本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即预防性侵害意识十分薄弱。其原因在于该地区普遍缺失儿童性健康教育,加之该地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家长对“性话题”的天然敏感以及对“儿童性侵害”的全然无知,这无疑给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可见,无论是在家庭层面、学校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需要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性安全教育,亟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困境,积极寻找适合本土化的性安全教育出路。
五、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的积极探索
曹红梅和徐晓阳(2013)选取达州市3 个县的不同农村中学学生为对象,以开展同伴教育的方式,积极探索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同伴教育的构建模式。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同伴教育在知识传授、态度转变和行为改善层面均优越于传统教育,在师资力量缺乏、留守儿童集中的农村中小学实施性安全教育,同伴教育不失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育方式。董泽松,李若天等(2015)通过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农村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年级、双亲均外出、内外向对云南省农村留守儿童预防性侵犯能力均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应积极开展适合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安全教育,促使农村留守儿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同时在进行性安全教育时应结合农村留守儿童掌握预防性侵犯知识和技能的性别差异进而有针对性开展。程子珍,夏文仪等(2017)通过对粤北地区农村的深入调查,分析了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性教育受教育情况及家庭、学校、社会各主体在性教育实施中的缺位现象,从多角度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性教育缺失的主客观原因,并提出要从监护人监管、师资建设、社会培养等方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性教育迟滞的问题。纵观各学者的研究发现抵制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各群体携手努力的事业,只有家庭、学校、社区与全社会各级力量共同联合、相互协调才可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李桂燕,2014)。
六、总结与反思
第一,研究发现,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问题的研究还在初期探索阶段。加之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性侵害事件频频发生,更是将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问题提上日程。第二,传统性文化与性观念忽视了儿童时期性安全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尤其是现代性健康教育理念和优秀传统文化中性观念存在尖锐矛盾,性健康教育主体的缺位是造成儿童时期性安全教育空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人们习惯性选择带有“有色眼镜”去看待儿童时期的性安全教育。学龄前期是儿童性安全教育的关键时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成年人在此时期正面积极地向儿童传授科学合理的性知识,实施恰当的性心理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儿童对性的好奇心,使其树立正确的性态度,有利于防止性功能障碍、性犯罪及性侵害等问题的产生。
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的构建,同时进一步明确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机制的责任主体,并且使之充分发挥相应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的认知差异性,从根源上降低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发生的几率,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对于儿童本身来说,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过程中,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建立生命自觉、自我边界,提高自我保护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虽然,在政策方针层面,儿童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有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并且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但从具体实施层面,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来说,其性安全教育机制尚未完整建立,还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