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窗灯火故纸暖
2020-11-18王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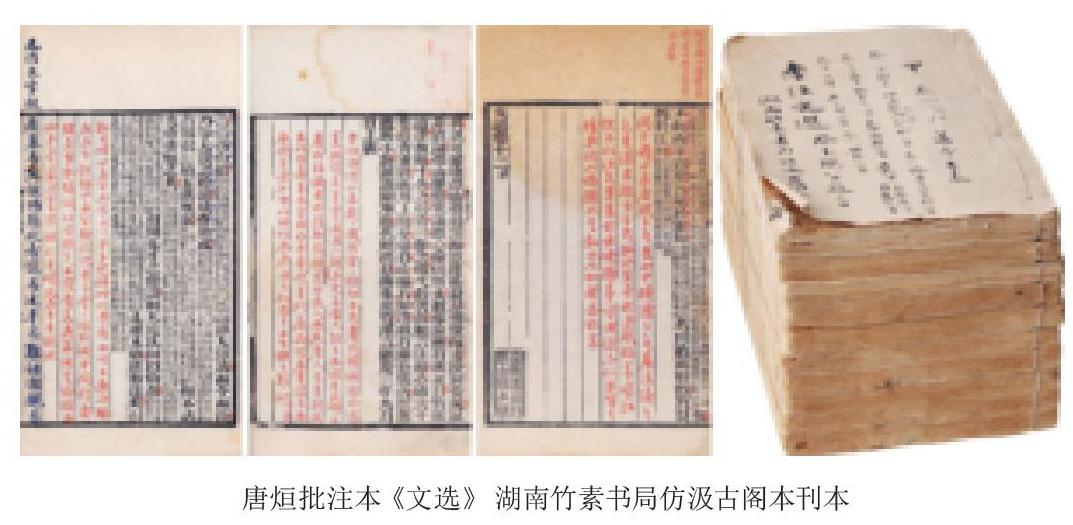
文人爱书古来有之,但藏书是一件费钱、费力又耗时的事情,若不是真心喜爱,恐怕难以持久,若不懂内里门道,也难以为继。晚清士人唐烜兼而有之,他既爱书,也懂藏书,他的事迹或许可为有藏古书之需的今人提供借鉴。
唐烜(1855—1933年),直隶盐山南隅人,清光绪己丑科进士,曾长期担任中央司法部门的刑事审判官。作为一名晚清中层官员,唐烜对版本源流、书林掌故、审美风尚、价钿走势等方面多有涉猎,这些内容皆记录于其《唐烜日记》之中。
从《唐烜日记》可以看出,唐烜在金石碑拓、古籍书画、玉石图章、钱币等领域兴趣有加。如在玉石图章方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五日,有沧州孙姓客向在前门大街牌楼摆古玩玉器摊,近因被街道御史一概驱逐,尚未觅得借栖之所,遂卷包回里,因月前予见伊摊上摆列图章印首三方:一系乾黄,刻山水纽;一系黄寿山,天然;,一系大黄,质甚润泽,唯逊于冻耳。索价五金,予置之而去。今日渠至永泰昌告归,并将三石售于予,坐价三金,随即付之,值不甚昂也。”
当然,在长期的收藏活动中,唐烜还是对书画、碑拓等纸品颇为上心,尤其精于藏书一道。古语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于唐烜而言,读书和淘书一直是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习惯伴其至终老。
与书商称友
唐烜聚书的来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亲身游历,遍访书肆摊位;二是由店铺稗贩代理寻书;三是师友门人的馈赠或交换;四是他人的求助代售;五是抄录。
唐烜买书从不拘泥于店面的大小、档次的高低或售卖者的贵贱,只在乎纸品的价格与质量是否合适。琳琅满目、古典文雅的店铺他逛,如北京琉璃厂的正文斋、文昌馆、荣宝斋等书铺;随地就位的散摊他也驻足细瞧,偶尔还能买到称心之书。如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廿一日记:“又散步街上,遇有卖破书故纸者,‘抢的《六书通》一部、《新奇谐》正续十本,用九千买回。”“抢”字形象地反映了唐烜爱书成癖的心性及淘得好书的意外之喜。
唐烜也经常委托古玩经营者带货上门。其中,为他购书奔波的书商有卢文轩、李福卿、谭竺生、杨书估等几位常客,大都为琉璃厂肆中的“老人儿”和玩书领域的能手,他们各有店铺。在同这些书商交往的过程中,唐烜与他们之间逐渐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变成良师益友。故唐烜不仅能收到不少上佳的藏书,如明刻监本《廿一史》、元代刻印黄鹤集千家注本《杜诗》等,而且其版本鉴定功夫也大有长进,这些都得益于他与这些掮客的友好关系。
走上精品收藏之路
唐烜在京城生活居大不易。他家世清门,素无家赀,后虽任职京官,但官阶不高,差俸有限。同时,他定居京都后,家口丁仆渐增,人事冗杂,应酬繁多,开销不菲,借贷亦是常有之事。因此,用来买书的资金实是他紧衣缩食的结果。
唐烜热衷藏书,也有面对心怡之书一掷千金的壮举,但豪情过后内心又充满对家人的愧疚,毕竟这种豪举需要以整个家庭花销的捉襟见肘为代价。因此,为更好地满足兴趣,唐烜学会精打细算,以藏养藏,走上了精品专题收藏的道路。
受艺术爱好的驱动,自迈入收藏的大门,唐烜就对墨迹灿然的抄本情有独钟,搜求网罗不遗余力。业界知他这一特点,故行家纷纷将许多名家抄校批定的珍品送至他的箧笥中。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李福卿带来《近思录补》四册,乃康熙进士黄叔敬手校之本,内容增减皆为黄氏丹黄涂乙者,笔意老道若行云流水,为黄氏晚年之手笔,唐烜“深喜之”,遂以十六金得之。
在玩书行摸爬滚打、混迹多年,唐烜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熟识各种版本流变,通晓书林逸闻掌故,知悉不良书商的龃龉内幕,也对书市行情与价格定位了然于胸。曾有刘阁(个)臣者,携其家藏手卷三本求售,一为明益府石拓《兰亭》,一为李伯时白描人物,一为怀素《自叙》墨迹,索价甚昂,唐烜讶然不解。在他看来,这些物品大有问题,“然皆赝物也”,实在上不得档次。
精品书籍到手,也要好好保存。唐烜深知字、纸的可贵性,因此,在藏书的过程中,他对古籍旧书等故纸爱护有加,想尽各种办法保护藏书,使之免于破坏。据唐烜自述,他一般用书箱庋藏旧籍,同时为避免虫噬,还用樟木所作匣盒承揽。
从藏书中受益
唐烜藏书绝不是为了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他倾注精力,不吝赀财,耗费心血于此,既是为做学问以实用之,也是托情于书纸,蕴藉心灵。
事实上,唐烜的许多藏书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皆有用武之地。如生活中,唐烜及家人偶会遭逢大病小疾,病痛之下多有折磨,有时医生延之不及,为此他专门购买了一些医书以作参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记:“内子自月初患疮症,节前始平复,继患泄痢,久不愈,拟延医服药,因予连日匆迫未暇。购《达生篇》一册,查得胎前泄泻一方,服一帖而瘳,亦幸矣。”简直是自学成医。
出于职業需要,唐烜还专门拜托书商购买法律案件方面的书籍以强化业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十五日记:“散值回寓,李书估来,携书数种,嘱其购《刑案汇览》一部、《碑传集》一部。”三日后,书商就为他觅得“李书估来,未遇,留《碑传集》一部,《刑案汇览》一匣”。
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更多的时候,唐烜摩挲藏书,细细捧读,目的十分纯粹,只是为悦目赏心,慰藉情怀。尤其是发妻李氏殁后,孤枕难眠,为消长夜,唐烜以藏书为伴,纵情于文字。
唐烜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深以民族文化的衰落而忧心。晚清以来,伴随西方入侵,山河破碎,西学甚嚣尘上,中学渐趋式微,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流失或遭到毁弃。流连于书肆厂甸的他对此有着比寻常人更为直观的感触和深刻体会。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汉学在日本的复兴,以及由此引起的日本人在华不遗余力地大肆搜罗善本佳椠的文化现象。
面对内忧外患之大变局,裹挟于时代下的个人无助,苦苦找寻出路却百思不得其解的唐烜只能继续埋头藏书之中,以便力所能及地为中华传统文化多保留一些薪火相传的信仰火种。
唐烜的友人李濬之在《清画家诗史》中提及唐烜时云:“性沉默,深自韬晦,人罕知之。”由于唐烜为人低调,不自表襮,尽管学问高博,但其诗文书画成就多隐而不彰,更遑论其藏书之癖好,可谓“世鲜知者”。唐烜虽然无法同时代相近的翁同龢、缪荃孙等藏书大家相提并论,但仍不能低估他的藏书活动在有关晚清古董收藏之风的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唐烜日记》更是全面反映了一个以藏书为清雅风尚的中下层官员的书林实况。
王立成,河北省沧州市第三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