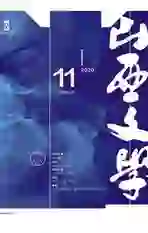规划师
2020-11-18指尖
大约世上某隐秘之处,是存在一个叫人生规划局这种地方的。在那里,一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精灵,运用古老而超前的飞行术,不停穿梭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用铜制的权杖勾勒着人类男女的生命轨迹。为使人们心悦诚服接受喜忧参半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掩人耳目地叠加了诸如妥协、克制、顺从、隐忍等材料,随时涂改矫正,澄清技术细节,以期得到姿态各异,效果不同的实验成果。不无遗憾的是,即便我们可以成功摆脱童年的无知,进入青年、中年乃至老年,学会圆融,学会放下,学会残忍,学会择拣,推诿,变得奸诈,懂得谨慎,却穷其一生都无法寻访到规划局的方位和形状,也没有任何机会推门进入,与规划师迎面相逢,当然更没有提前窥探我们命运走向的机会。
事实上,那些蹲坐在那排密匝匝云杉前面,不停吸烟,沉默不语的师傅们,已极其准确地把握了人生规划局存在的确凿证据。一些时候,某位师傅会突然收敛脸上笑容,仿佛开水中注入冰块,倏然紧缩的感觉。那时,十七八岁的我们,总是敏锐地接收到一种奇怪讯息,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但心里有莫名的悸动。当我们的目光投向他时,他头脸低垂,缩在两腿之间的缝隙,一群蚂蚁军队正浩浩荡荡经过。
这些年过不惑乃及天命的师傅们喜欢喝酒,他们的借口总是天太冷,需要暖暖身子。在1200多米海拔的林区,即便三伏天,也有源源不断的凉意从茂密的森林中沁出,晨昏之时,带给我们彻骨的寒凉。一开始,他们总是很矜持的,小口小口抿着盅里的酒,但渐渐地,仿佛炭火燃出火星,他们身体之内升起了忽明忽亮的火把。有人站起来,试图逃避接下来的豪饮,他当然会被好几双手压回到座位上去。这时候,我们端着刚刚焐好的山鸡,那些沾了浓稠酱汁的鸡块,已完全丧失了山鸡的形状,它们身上最美丽的那两根羽毛,正作为一个摆设,被插在一张画后面。
过不了多久,酒酣耳热,食堂里生出暖洋洋的甜味,让人迷糊。那个声音最高的师傅,显然已有几分醉意,他要出门小解。但我们知道,在屋前的苗圃地里,他会将刚刚喝下去的酒全数吐出,再反身回来时,装出一副永远不醉的好酒量;他们之中,永远不会醉的那个,总是脸色最先涨红,制造出提前要醉倒的假象,而他,也是将这些醉倒之人送回宿舍的那个;高师傅话最少,但他却最容易醉,有次喝完酒,他从食堂的门槛爬出去,抱着门口的李子树笑嘻嘻亲来亲去;小司机的师傅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动不动就生气,大声呵斥小司机,嫌他打水慢了,车没擦干净了,或者是弄丢东西等,有时他们之间还会上演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闹剧。但小司机显然没有长成韩信,所以他在前面慌慌张张的逃跑,乃至鬼哭狼嚎地大喊,而师傅也全无萧何的计谋和策略,只是一味莽撞地追赶,手里拿着棍子或自己的一只布鞋。喝了酒的司机师傅,像一个弥勒佛,笑嘻嘻的,两只虎牙仿佛嘴上的两根门柱,将主人的嘴撑开,迎来送往;酒品最不好的,要算王会计了,他不止会哭,还会伸手拦住每个遇见的人,跪下来,抓住对方的裤腿或衣襟,大声喊爹。他是师傅们中年纪最轻的那个,一时我们会觉得喊师傅们爹,也失不了多少身份。但奇葩的是,他也会喊木瓜树爹,有次用头撞着山楂树干,一树白纷纷的花从树上被撞下来,落了满头满身。更笑人的是,他跪在了黑犬花花跟前喊爹,花花一怒之下,对着他狂吠不已,乃至后来见了他,龇牙咧嘴,露出凶恶的模样,仿佛跟他有过节似的。
所有这些我们看得见的表象,其实都是铺垫,就像大戏之前那场热闹的锣鼓。
有段时间,小司机感激师傅们的全勤出境,说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推动了剧情的开展。作为自己人生大戏的主角,小司机被师傅们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他的人生规划师,早已提前降临于此。他们只需相遇,仅此而已。
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那个女孩担负着如此大的重担,以为,她跟我们遇见的任何一个管村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围着红色头巾,穿着简朴的蓝布衣裤,缩在一群管村人中间,像一个隐身其中的智者,也像一个等待被风吹出人群的人。小司机显然远非一股风,他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超常的分辨能力,乃至他是迟钝的。
他十八岁生日即将来临,在发工资那天,他请假去县城给自己买了件礼物,一条墨绿色的小喇叭裤。当他穿着它,从宿舍里出来,我们第一次发觉小司机有一双笔直修长的腿。而当他走路时,裤子的小喇叭微微向左右张开,仿佛携带着细细的风,有种飘逸感。那条裤子,让人眼热,我们三个女孩和小木匠,都央求着试穿了一遍。他们都说,我穿上跟小司机一样好看。为此,下次回家,我就借穿了这条裤子。但后来我并没有买一条一模一样的裤子,这是件奇怪的事。
这条裤子令师傅们极其反感,仿佛预知到危险降临,他们叫它扫地裤,小司机的师傅还命令他在出车和保养车的时候,不能穿这条褲子,也就是说,只有早上和晚上,小司机才可以将这条心爱的裤子套在身上。
师傅们的酒局从未散去,看似断断续续,其实一直延绵未绝。那个近午时分,小司机去管村给师傅们买酒,他穿着这条裤子,仿佛一棵茁壮的小树,行走在弯弯长长的土街上,吸引了无数管村闺女的目光。那个红头巾女孩悄悄钻出人群,一点一点地,露出自己的脸庞,她规划师的身份,即将暴露出来。
当然,在人们眼里,这只是一个比小司机大五岁的女孩,对他悄悄动心了。
那条绿裤子,像一团绿火焰,吐出的春意,点燃了管村姑娘隐匿的爱火。她不管小司机不过刚满十八岁的孩子,不管自己与小司机正式工人之间的身份悬殊,也不管小司机是个没爹没房的穷孩子,更不管管村人耻笑和鄙夷的目光。她是个大姑娘,已经相过几次亲,也跟管村的后生们相好过一两次,她早已洞悉了男女之间的全部秘密。于是,她出现在供销社的门口,脚边,放着一袋南瓜。有撩逗过的后生过来,要送她回家,她拒绝了。她的矜持,让对方愕然。她一直等到小司机出现,当他给师傅买完酒,准备回场时,她央求他,帮她将那袋南瓜抬回家。
小司机并不懂得拒绝,也或者,他根本就无法拒绝。那是两个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暗自较量吧,引导者只需稍稍运用一点伎俩,跟随者便毫无防备地点头。两个人一人抬着布袋的一角,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在管村长长的街道上,管村闺女的红头巾,和小司机的绿裤子,那么醒目,那些原本盯着街门口槐树叶、猪圈边的小鸡和石墙上印痕的目光,都敛回来,投到这对男女身上。
作为回谢,那女孩邀请他坐在自己家高高的炕沿边上,不久端来一碗荷包蛋。
人年轻时,总是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这是规划局的统一设置,那种对食物的贪恋中,带着少年人对生而为人的快乐和幸福。他当然也无法拒绝一碗荷包蛋的清香。
按钮启动,小司机懵懂无知。规划师所拥有的特殊身份,早已穿越眼前管村的窑洞和院墙,穿越高大的杨树和弯曲的柳树,穿越黑色的鸟巢和飞翔的老鹰翅膀,看到了远方,绿树成荫,花朵繁茂,一些正在生发,一些正在死去。
作为组成小司机多彩人生的点缀,我也被推到了前台,面对这浩瀚的观众,胆战心惊,仿佛有个镊子,正在伸过来,要镊住我,或吊起我,我忍不住逃避,佝偻着,蜷缩着,幻想变成一个没有面目和形态的人。跟我拥有共同身份的新同事,有长达十年的借调生涯,他深谙这种炎凉,慌张,无助和悲切的滋味,目光之中,注满深深落寞。
有一天,在那个四楼办公室里,他坐在桌前,大声念出了报纸上的题目——《被打入另册的人》。阳光刚刚穿透乌木窗棂,整个屋子里呈现出柔和的明亮。显然这句话让他生出某种相似的惊悸和忐忑,那种带着嘲笑满不在乎的声调,怎么能掩饰他的无奈和怨气啊。他坐在背光的地方,眼里隐约闪过一道亮光,之后倏忽消失,整个人委顿不堪。
敲门声适时响起,来自深山的小司机突兀地出现,带着一股久违的清凉,让我兴奋起来。
“你怎么来了?”
他不说话,只笑,用眼神一直在示意我出去。
昏暗的楼道里,只能看到他树干一样的身体,而他的声音,就从树干里沙沙地发出来了。
“她怀孕了,我陪她去医院打胎。”
我一惊。
他到底是跟她有了如此亲密的关系。
中午带他去食堂吃饭,饭后,我送他去车站,在那里,管村那个女孩在等他。
“你们怎么?”
嗫嚅中我开口。
“我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就跟她好了。”
见我惊讶地看他,他苦笑。
他只要吃下她煮的那碗荷包蛋,他就将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步入她规划的大网。规划师用她成人的方法,变成灯火,变成河流,变成大地,而他就是飞蛾,游鱼或者麻燕。他只要路过管村,都会遇见她。她站在家门口,或者街上某个拐弯处。如果小司机是一个人,那么她就会向他招手,他将汽车熄火,或翻身跨下自行车,或停止脚步,她总会有让他停下的借口和理由,一副鞋垫,一件织好的毛衣,几个煮好的鸡蛋,或者一包炒好的南瓜子。他的年纪之中,尚有小孩的顺从,不懂拒绝,不会说不,直到那次,她说晚上来我家喝酒吧。
那是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初冬的寒风将他刮出孤单的宿舍,他曾经的同屋小木匠跟他隔着三十里的距离,在化肥厂的水龙头下,正在冲刷自己身上浓烈的磷肥味道。那张他曾经睡过的床上,放着小司机洗过的球鞋和油腻的修理工具。在门口,小顾被黑犬花花拦住了,于是,花花便成了陪他赴宴的人。他点燃一颗烟,烟头隐约的红星照亮了前往管村的路。那时,师傅们均已醉意朦胧,他们游走在梦境的边缘,一时青春,一时耄耋,仿佛过山车,他们慌张而恣意,无暇顾及从大门出去的小司机。
不等他敲门,她已站在门前。
她的家人,那天都去亲戚家了,只留看门的她。桌上,有金黄的炒鸡蛋,雪白土豆丝,两杯酒,一左一右。
这就是小司机口里犯错的夜晚。来自规划局的图例中,那是一条交叉的,加粗的线段,一条有指向和意图的延长线。
我把小司机送到了桥边,看着他下了桥,薄薄的身体,拐入车站的人群。
小司機结婚的时候,刚刚十九岁,因为不达结婚年龄,他们一直没领证。在农村,结婚证远不如一场婚礼来得重要。婚礼仿佛天地间的宣言,而来自各自家庭的亲戚和嘉宾,不过助胆者,他们或真或假的祝福也不重要,头顶的天神,离人间太远,根本听不见,它只看到了无数的人簇拥着那对新人,便马虎地接收信息,抽身远遁。
我们没有出现在小司机的婚礼上,连小木匠都因出差而未能到场。师傅们却无一缺席,他们在他的婚礼上,又上演了一场豪饮大戏,他们说着小顾师傅听不懂的一些嘱咐,含着忽隐忽现的笑,一杯再一杯。
我们都送了礼物给小司机,床单,毛毯,还扯了料子布。成长中的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心里有最真诚的祝福,想来他也是能接收到的。
我们集体出现在他面前,是几个月后他的孩子满月时。
按小司机媳妇的话说,小司机是一个地无一垄,房无一间的人,她坐在小司机宿舍的床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司机,露出一排细小、浸满黄斑的牙齿,脸色红润,并不难看。而她怀里的孩子,看起来丑极了。她全然一副家人模样,拉着我的手,坐在她身边,“你看,姑姑。”那孩子并不领情,眼睛看着上方很远的地方,嘟着嘴。她又说,“这孩子生下来,脐带又短又粗,再生啊,还是小子。”
十八岁的我,讪讪的,不知所措。
直到来年小司机又当了一个小孩的爹,想起她说的话,开始怀疑她的身份,这是一个极其熟练的母亲,乃至她提前都知晓并掌握了当妻子和母亲的流程,似乎她只需重复,一切便可顺理成章。
小司机终于出师了,那个追赶着打他的师傅也已退休。那几年,场里的师傅们陆陆续续都退休了,一些新工人进场,年纪也小不了几岁,但都喊他顾师傅。在林场,从来不会看人的年龄,而是按工龄来确定你的地位。
他来局里办事,每次都会坐到我办公室的沙发上,不说话,只坐在那里抽烟。如果见有人来,他会站起来出去等,人走了,再坐回原处。给我感觉,他似乎很孤独,但又不确定。
有次他突然闷闷地说,“活着真是没意思。”
我一愣。他依旧低着头吃烟,半晌,估计是感觉到我在看他,他抬起脸,朝我笑笑,二十几岁的人,脸上竟然有一圈又一圈的皱纹,恍惚当年的老师傅。
“其实,我是被她骗了的。她一直说只是跟我耍耍,到后来却用上吊来逼我娶她。娶了她,她又死也不回我老家住,非要让我在管村盖房。我又不是上门女婿,哪有在管村盖房的道理啊。所以就一直住在场里,她不嫌丢人,我也不怕,大不了不过。”
“结婚证领了吗?”
“没。我也跟她放话了,如果想领结婚证,就回我老家伺候我老妈去。”
林场工人越来越少了,空荡荡的场院里,早年的李子树,木瓜树,山楂树,梨树,桃树都不见了,院中间砌了一个花圃,里面种了塔柏和沙柏。小司机一家已从小宿舍搬住在当年的木工房,虽然大,但极其简陋。这种随时抽身便走的姿态,似乎并未难倒那个熟练的母亲,仿佛一切都在她掌控之间,出来进去,依旧笑吟吟的。场院里,爬坐着他们的二儿子。见我诧异,她笑着说,这是为了便于看护,迟点学会走路,自己省心些。她递给他一块坚硬的馍,他专心地去啃噬,他并不清楚,食物之所以被尝到,远非六颗乳牙的功劳,而是口水的功劳。不久,看起来他生气了,将湿漉漉的馍扔掉。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也许他的力气是大人们无法估量的,因为很显然,被他无意掷出的馍与他之间,有一个令人惊诧的距离。而馍块抵达的地方,宛然他最终的目的地。他因之匍匐朝前,爬出被框定的地盘,向着泥土和石块,虫蚁和蚯蚓。
一具正常的身体,他迟早是要直立行走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可以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永远坐在母亲为他设置的位置上,安全,而且也有一定的乐趣。树上的鸟飞到他面前,翅膀上所携带的风声让他瞪大眼睛,并轻微地抖动。
他不知道几个月后,当自己有了行走的愿望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姿态有多可笑,一双变形的腿,一串歪斜的印迹。一个五岁的孩子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看不到自己影子,他甚至不去分辨别人的笑声中所包涵的意味。他只是享受站立起来之后,世界缩短一大截的样子,还有因之而来的无名的欣喜。
而隔着那个花坛,隔着食堂陈旧屋顶上的蒿草,长长的石路顶端,场门口,小司机的大儿子正在欣喜地看着道路尽头出现的轿车。他看到了车窗后面父亲模糊的身影,于是,脸上的笑容撑开,眼睛变长,鼻翼张开,嘴角上扬,他的声音在夏天习习的凉风中,缓慢而又无比坚定地,通过胸腔和气管,从他的喉中喷——你爹!你爹!
熟练的母亲正在纳鞋底,便吃吃地笑了。
我心下一惊。
规划师的权杖落下,它们画下的线段,曲折诡谲充满玄机。
许多年后,我们明白,她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规划师,她应该是冒充的规划师,在偶然的情形下,窥视到规划局的存在,并掌握某种独属规划师的法术,成功蒙蔽了小司机的双眼和心智,让他错以为,眼前这个女人,是他命运的大神。
我在冬天见到小司机,他已长成当年师傅们的样子,乃至我会想象,他也喜欢蹲坐在云杉的前面,沉默地抽烟,偶尔将头锁在双腿之间,那时,一群蚂蚁军队正在穿过。他会大口呵斥那些新来的小工人,让他们为自己打水,端饭。他也喜欢喝酒,一杯接一杯地豪饮,他也会醉,是什么样子的醉态呢?哭,笑,或者沉默着睡去?
但我永远失去了去探究真相的机会。小司机的一头花发让我无法提及任何话题,甚至不知该做何种表情,同情?可怜?云淡风轻?他苍老的样子让人想哭。
那个熟练的母亲,在法律上没有跟他履行过结婚手续的规划师,变成了一张薄薄的黑白相片,在木头框子里,带着几分年轻羞涩的笑,看着出来进去的人们。她的肉身,已成为门外那口黑棺材的填充物。据说她在近几年,胖得不像话,由于体重增加,她走路需要拄着拐杖,这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件残忍且令人羞耻的事。
好在,他们的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开始出外打工,大儿子还娶了媳妇。
“她曾遗憾自己无法承担奶奶的责任。”小司机脸上一圈一圈的皺纹,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凝固在脸上,他说话的时候,竟然感觉他的嘴也被这些皱纹挤小了,在皱纹与皱纹之间的皮肉上,我们好歹找到了他年轻的证据——一小片或长形或方形或圆形的,光滑的皮肉,属于三十八岁的皮肉。
“哼,现在终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有人用手按了按顾司机的肩,试图将身体之中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输给对方。他将肩头松了松,借着取烟的动作,顺便往旁边一闪,将肩上的那双手躲开了。
新院子的篷布让屋子里暗淡极了,无名的窒息感涌上来,让人透不过气。
我们后来才听说,小司机之所以最终在管村盖房,是因为出了一件事。
有人半夜里跳墙进场,敲开了他家暂住的门,那夜,他跟领导在外地调苗。
他忽略着风言风语,仿佛自己还是十八岁的青年,信任这个爱慕自己的姐姐的忠贞。而全然忘记,那位熟练母亲所携带的一切熟练行为的成因。直到,新来同事的臂膀上出现了一个牙印,并向其他年轻人炫耀,他才知道,自己家的红杏,早已出墙无数。
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随着年华逝去的,还有底气。他们从此住在村里,再丢人,也避开了工厂这块意念里的圣洁之地。
她熟练地将小司机玩转手心,熟练地阻止儿子初次行走的时候,是否已隐隐嗅察到一种即将逃离她控制的危险气息?或者她曾得到过一个一旦脱手将永失的预言暗示?这应该不是规划师心愿里的规划吧?就像有些人,具有通灵的能力一样,会不会她终于还是被真正的规划师抓获,作为惩罚,他们之间应该有过交涉,结局是,她用身体当筹码,来换取小司机的生命线段的顺畅完整?但显然这筹码远远不够,所以他们要带走她的性命,让她含着永远的遗憾,在另世,注视着她喜欢的人,并落下悔恨不绝的绵延泪水。
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泛白的记忆让人温暖。
如果可以,我要退回到很久以前,站到东山顶上的那株树边,年轻的他,冒着热汗,抬头仰望,去寻觅鸟的栖所;重现穿着墨绿色小喇叭裤的他,背着军用挎包,沿着长长的石路走向我们的时刻;一条蛇出现,他突然脸色煞白,飞快地爬上低矮的山楂树。不,所有这些都无法成为我们的话题,包括近年的工资待遇,那些曾经熟悉的同事下落都不能说。这长长的几十年时光,像一个紧密的包裹,不能碰触,不能解缠,我怕看到血和泪,看到绝望和悲凄。
我们都知道,包裹中所藏的那个孩子——那个分不清“爹”和“你爹”区别的孩子——已离世两年多了。
空荡荡的院子里,窗棂上的油漆都尚未被风雨刮去,崭新的,仿佛刚刚刷上去般。小司机成为年轻的鳏夫,而寄埋在绿轴沟的妻子,从未跟他领过结婚证的妻子,那个曾经的规划师,住在在坟墓里,也成为了寡妇。
小司机不再开车了,他随着工人们上山,春天去栽树,冬天去间伐。夏天和秋天,在育苗的间隙,他就一个人沿着绿轴沟的流水,踩踏着茂盛的蒿草和野花,去管村闺女的坟前,在那里,他吃烟,仰头观望天空中游弋的云彩,看山鸡从他头顶飞过,野兔从他脚边跑过。坟上的青草,齐刷刷的,仿佛一张毛茸茸的地毯,他会躺下了,闭上眼,听到管村闺女熟悉的呼吸声,还嗅到她熟悉的体味。他睡过去的时候,眼前一片朦胧的红色。
他一直以为,这是生命中最坏的一段时间,从未料到,最坏的,还在来临的路上。
他将新院门锁了,重新搬回场里的宿舍里住,在食堂吃饭,大口大口喝酒。
他越来越喜欢做梦,每夜都会早早躺在床上,等待梦境的莅临。那夜他梦到一口干枯的井,深深的井底布满落叶和枯草,在落叶和枯草之间,无数只灰色的老鼠窜来窜去,发出沙沙沙沙和吱吱吱吱的声响。井边,有个小孩,手里拿着一支柳条,正百无聊赖地挥舞,在他的挥舞中,泉边的树叶更多地飞起来,落到了井底。在他身后,一股大风浩浩荡荡刮来,裹着更多的落叶和枯草。忽然,小孩不见了。在梦里,小司机知道小孩被狂风吹到井底了,他飞快地奔跑着,好像十八岁那年被师傅在身后追赶。在井边,他看见比之前更多的老鼠密密麻麻布满井底,已将小孩身体全部分解,他惊恐地大叫一声。
隔着近百里的公路上,他的大儿子,骑着一辆摩托,在公路上风驰电掣。他刚刚喝完朋友的喜酒,身上带着浓郁的酒气。那夜,他看到了无数碎片般的星光,他毫无犹疑地朝它们冲去。
他和他的母亲,残忍地抛下四十八岁的父亲,顶着一头白发坐在我对面。他们仿佛提前知晓秘密的人,用死亡逃避更大的灾难。他们横亘在他父亲和我及所有人之间,横亘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像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一端,是快乐,一端,是悲伤;一端是生年,一端是往逝。
在被规划的人生中,提前死亡是不是必须存在的部分?像别离,绝交,消失?还是像怀念,伤心,悲怨?白发苍苍的小司机坐在我对面,被烟卷熏黄的手指间,换上了第五支烟。
“我就不是谁的爹,也不是谁的夫。 ”
我的眼泪瞬间溢出眼眶。
朦胧中,纷纷大雪,正将林场和周边的山脉及道路染白,世界纯洁而安静,冷漠而残忍。人生规划局隐约呈现,它就在林场和管村之间,在早晨的雾气和夜晚的红霞中,露出它尖锐而模糊的顶部。
【作者简介】指尖,曾出版《槛外梨花》 《花酿》《河流里的母亲》《雪線上的空响》《最后的照相簿》。先后在《人民文学》 《青年文学》 《散文》《天涯》《美文》等报刊发表过文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