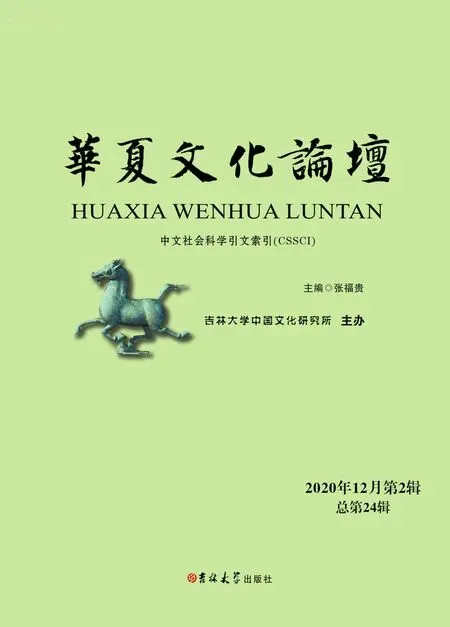郑小琼的“群像者”解读及其外的诗语建构
2020-11-18
【内容提要】被视作“打工诗人”代表的“80后”当代诗人郑小琼,创作初期多从自身女性打工者的视角出发书写一代打工群体独特的生存体验,对其诗歌独特意象的延伸性阐释,清晰勾勒出当代打工者群体性的生存状态。对郑小琼诗歌的“群像”性解读使其作为女性诗人的创作个性遭受某种限定与忽视,并引发了诗人“去群像化”、展示其富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歌创作的努力。本文聚焦郑小琼的“群像者”解读及其外的诗语建构,力图实现对其诗歌更多元的创作解读与价值发现。
郑小琼作为“80后”当代诗人,在创作初期多凭借自身女性打工者的身份与视角,书写一代打工群体独特的生存体验,对其诗歌独特意象的延伸性阐释,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打工者群体性的情感状态和生命轨迹。长久以来,郑小琼诗歌的解读与当代诗歌现象“打工诗歌”密不可分,人们聚焦于其诗歌中“打工者”这一社会阶层的“群像式”建构,这使得诗人郑小琼成为当代诗坛一位“群像者”诗人。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凸显了郑小琼诗歌价值中独特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使她作为当代女性诗人的创作个性遭受到某种强行的定型、忽略乃至阉割。实际上,在郑小琼及其“群像者”诗人形象的构筑以外,她也进行着富有独特创作个性的诗语世界的建构。
一
2007年,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其获奖评语为: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再现了一位敏锐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的感悟。这项荣誉使郑小琼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诗坛新秀”。其实,早在郑小琼打工生活开始后不久,诗歌创作就已然成为她在繁重、无聊的流水线上疲于奔命的空闲时间里聊以自慰的方式。创作之初,“底层”是郑小琼诗歌的一抹底色,“打工生活”则是其创作的中心和主题,因此很快确立了她“打工女诗人”的定位,这一诗人形象的定型与她的“成名”近乎同步。一方面,郑小琼自身及其周边打工者的真实生活状态给予她创作初期的艺术灵感,以诗歌反映和思考现实成为她在创作起步阶段的一个文学夙愿;另一方面,郑小琼以诗人的身份在诗坛崭露头角,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研究界对其打工身份的社会学判断往往优先于她作为诗人价值的判断,诸如“(郑小琼)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定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她以诗歌来完成了对打工者的生存素描”①张德明:《一台大功率的机器在时光中钻孔……》,《作家》,2008年第10期。“(郑小琼)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代表,发出了一种被忽略的声音,呈现了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是对于‘80后’作为社会学和文化概念的一种发展和补充”②王士强:《在“权利”与“权力”面前——论郑小琼》,《新文学评论》,2013年2期。等等评价更多着眼于她独特的社会身份。
当一个诗人的形象,或者说其诗歌被视为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缩影,郑小琼的“群像者”形象就已产生。进一步来说,所谓诗人的“群像者”形象,指的是经由诗人本身或其诗歌,影射和反映了社会群体性的现实图景和生存状态,诗人身份的社会属性往往带有群体性,对其诗歌群体属性的判定往往先于其诗歌艺术性判断。从文化透视的角度来看,“群像者”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标签或者创作倾向,它既是文学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对群体性话语表达方式或有意或无意地创作追求,同时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在文学创作领域里的反映。从创作主体来看,“群像者”的文学艺术创作带有主观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表明“立言”“著书立说”等是文人自古潜在的追求和担当之一。其二,文学创作本身就隐含着针砭时弊、探究人性的责任。鲁迅就曾明确过自己创作小说的出发点:“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撰:《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2页。鲁迅所谓的“为人生”自然主要指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的人生。应该说,文艺带有大众性、集体感的创作思想根深蒂固,同时文学创作主体也倾向于在文艺作品中进行“群像”的塑造。除去作家本身为群体“发声”“立言”的责任感与担当感之外,研究者与读者在作品的阐释与解读过程中,往往惯于朝“群体”概念的方向延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大的“国”“族”抑或小的“宗”“家”都体现着对整体性的家国观念、群体观念的倡导。《荀子》有言:“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家国观念、集体感等等都在强调和关注社会生活的“群体性”。“群”“众”“们”的强烈观念早已根植并成为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文学自古便有“群治”的效用,《论语》有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之名。”其中的“群”是指诗歌可以使社会人群交流思想感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于团结。将社会群体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共性的问题,如《诗经》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群体性”倾向。
封建社会对“人”的个体性的压制是以对“群体性”概念的无限放大加以实现的。近现代以来,由于现代意义的“人”的概念及其价值的重估,关注人民大众、反映和揭示社会群体性的生存状态,成为贯穿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当然,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与救亡的文学主题势必要将人民大众视为主要地书写、宣传与动员对象,群体性的文学书写彼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实现,但“群像”同样也在个体形象的书写中得以呈现、拓展与延伸。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使当代文学“群”的概念更加明确下来。文艺创作深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代言式”的文学表达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诗歌中占据主潮。及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代文学迎来另一个重要的、尝试摆脱宏大叙事与集体性话语方式的收获期,当代文学逐步呈现出浓重的个人化色彩,张扬“个性”和更具主观色彩的超理性与超现实的现代、后现代诗歌逐渐开拓出多元化创作范式的文坛格局。不可否认,“群体性”的文艺创作是当代文艺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当代新诗具有经典性的诗人诗作往往多以“群”为写作背景或以此为出发点,具有自觉的“群像”倾向。
从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视点出发,中国当代文坛向来不缺乏女性诗人、女性作家的声音。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舒婷、翟永明、林白、陈染等女性诗人、作家的相继出现,一度使文坛进一步看到了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作家独特的文学特质,乃至引发对文学概念中的“女性”意义的反思,郑小琼在这一点上显然又与上述作家、诗人等不同。舒婷、林白等以诗歌及小说创作在男性作家为主流的文坛呐喊女性的声音,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女性群体的共鸣,很大程度在于女性作家书写的女性经验更多侧重于对性别体验的刻画,性别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会产生太大的群体经验差异。而郑小琼诗歌书写的不单单是性别经验,她将自身体验以及其所见、所闻、所感知到的性别经验,与自身及其书写对象的阶层经验融合在一起,使这种经验带有特殊性,相对而言不构成普遍性。事实上,郑小琼的名字备受诗坛瞩目的同时,她身份的独特性所带来的某种“敏感”渐渐被有些学者捕捉到、并直指郑小琼诗歌研究中存在的某种偏执,那就是“为了强化她的‘身份’以及公共性价值,而忽视了她作为个体的‘纯粹’和独立意义。”①张清华:《词语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集〈纯种植物〉》,《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郑小琼的“群像诗人”形象及由此而来的诗歌解读方式成为其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
郑小琼的“群像诗人”形象是从其自身与底层打工者之间的身份重合开始的,她构造的是“我”即“打工诗人”的群像性诗歌影像。诗歌中“我”的第一人称的使用,在阅读体验上往往容易向“我们”这样一种群体性的阅读经验展开联想与拓展:“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黄麻岭》)“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生活》)都在以个体打工者的生存感受引入群体性的生存图景。郑小琼早期呈现底层“打工生活”的诗歌里充满词语慌乱的碎片,轰鸣的机器、流水线、电子厂、垃圾、呕吐物、合格率、白炽灯、弹弓、螺丝钉……正向直击了重复而又碎片化的底层打工者的日常世界。与动态喧闹的世俗世界呈现出鲜明对比的是对公共空间“静”的渲染,如下面这首《蓝》:
“静谧的蓝是打工生活的另一面,它的轻
它的浅,容易逝去的也容易霜冻的爱
在流浪飘泊中像微暗的蓝照耀着我
除了爱,除了蓝色的星光,叹息
机台上的铁屑,纸片,它们用低低的声音抹去
车间里的喧嚣,奔波,劳累。剩下一片蓝在爱里
开出一片憧憬,一个未来的梦境”
——《蓝》①郑小琼:《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23页。(节选)
工业时代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机器的巨响中被压制、被消耗、被磨损,与郑小琼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机器的轰鸣声不同,《蓝》以“静谧”为主调,下工后车间里的喧嚣与吵闹终于停歇,在一片温柔的宁静中人也随之从如机器般重复的动作中解脱出来,享受异常珍贵的不用再被出卖的自己的“生活”。两种打工生活的描述清晰勾勒出被叙述者的阶层属性,同时又与日常世俗世界一并贯通。
但很快,郑小琼便意识到“好的诗歌是从个体生命本真出发,然后达到广阔人群之中,是用个体本真扩展群体的特性,不是用群体意识去剪裁个体本真的独特性。”②郑小琼:《深入人的内心隐密处》,《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打工诗人”对郑小琼而言,带来的不仅仅是“被标签化”“被脸谱化”的苦恼,更深层的是对于真实底层生存状态被遮蔽的担忧。读者以为读到郑小琼诗作中“我”的种种,便看到了郑小琼“们”、触摸到底层打工者群体性的生存样态。而郑小琼却在诗歌素材的收集中对底层打工者们的人生百态、对真实的底层生活、对现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些理解更多已经超越了她已有的经验和感知。如果说在创作之初,郑小琼通过诗歌窥见了生存中的自己,诗歌是一面光洁而又寒栗的镜子,映出她挣扎于生活中的疲惫与恐惧。那么,在她随后的创作中,郑小琼则透过更多的打工者、底层民众,发现了何为“生存”。
2010年,郑小琼的组诗《女工记》刊发于《南方都市报》,随后于2012年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郑小琼“女工系列”的创作实则在2004年就已开始,《田建英》中那个“在风中追赶铝罐的老妇人”开启了郑小琼描绘底层女工生存状态的图像世界。《女工记》中几乎每一首诗都以一名女性的名字独立命名,使用偏“实录”的方式加以描摹,或者干脆直接参与诗歌中的“对话”。“女工系列”中,“我”的存在已经显露出与被述者之间的距离,当然填充其间的是诗人浓重的人文情怀。郑小琼在《女工记》里采取了相对理性的刻画方式,在对形形色色的底层女工的描绘中尽可能地放弃了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修饰词,同时频繁出现“我”与女工们直接的对话,使主人公从“我”转移并聚焦到具体女工身上。与一种自觉的“群像诗人”不同的是,郑小琼察觉到自身的“代言”信号时,便有意地与公共性的“群”的标签保持疏离:在诗歌中增加诗人与读者之间的阻拒感,进而从被审视的空间中抽离出来,转变为叙述的“旁白”,即与读者共同成为诗歌作品的感受者。为了实现与书写对象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感,郑小琼记录了个体存在意义内的女工群像,试图揭示底层生活中隐秘的部分。“有时你坐在窗口/沉默 孤独有些忧郁 但是/这样的瞬间 无人关注”①郑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5页。(《姚琳》)诗中的女工们有着相异或相仿的人生轨迹,在如机器般运转的岁月中消耗着青春、爱情和生命。《女工记》尽管是一部底层打工女性的生存实录,期间也流露出对抗传统女性观、女性生存方式等女性意识。更多时候,郑小琼融入到诗歌之中,将个体的感悟向群体性感受的方向上拉抻:“我们不断向生活的深处潜进 现实却/嘲笑我们 我们原以为会走向更广阔的城市/却不幸走进狭小的胡同”②郑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7页。(《竹青》)面对现实世界的无奈与无助、以及渴望反抗和改善生存现状的决心显然是群体性而非个人性的。郑小琼的诗里总隐藏一股向上的力,这股力犹如种子试图破土而出,是一种生命的韧劲与耐力。这种力使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在看似沉静的外表下,暗藏着不息的生命力的涌动。尽管“女工系列”真实地呈现底层女工群体生存图景,但似乎并未突出诗歌的文体特征,带来诗歌与散文边界间的某种模糊感。
对“群像”图景的建构常常使个体形象受到忽视,郑小琼却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突显个体生命的存在样态。在《女工记》里,郑小琼这样写道:“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挑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独立的个体,要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我自己。”郑小琼从不规避自身的生活经历与千千万万的普通女工相仿,这部分人生是她诗歌创作的素材,形成了最初诗风的平实与淳朴。同时,她又寻求在“群”的范围内凸显“个体”的命运轨迹,从而使自己“群像诗人”的标签在其对形形色色、独立生命存在的描述中逐渐淡化。以此方式“去群像化”的努力,又恰恰成为她以诗歌向公众呈现底层打工者生存世界的一面镜子。
不可否认,打工经验和底层生活促使郑小琼走向诗歌,而诗歌又让郑小琼走向更多的“自己”。当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相遇,一种情感便不再具有单一性,同时也不再具有私密属性,它理应面对公共性的价值衡量尺度,而非社会学的身份界定、阶层属性等等局限认知。在群体性经验中彰显个体的独特之处,摒弃群体性经验对个人化、私人化经验的抹杀,摒弃群体经验书写中的某种单一化、复制化和去个性化,无疑是郑小琼“到达广阔人群之中”的一种方式。
三
“在底层 悲伤
已沦为暴唳 不幸的人用伤口
测量着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
看见底层人群不断的分裂 他们是
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
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底层》①郑小琼:《底层》,郑小琼著:《纯种植物》,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45页。(节选)
如果说以真实的生存体验直面底层的生活状态、以诗歌去重新阐释和理解底层生活,是郑小琼诗歌创作的初心与动力。那么,当“打工诗人”的标签预先限定了郑小琼诗歌创作主题及思想上的可能性时,或多或少造成了对这位“80后”女诗人其他创作才华的遮蔽和忽视。诚然,“打工诗歌”并不是郑小琼诗歌的全部,一次访谈中她对自己“打工题材“诗歌的评价是:“它们只构成我在现实瞬间性的对外界的部分感受,没有构成我对外界完整的感受,它们是我诗歌理想的局部。”②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访谈)》,《山花》,2011年第14期。从2009年出版的诗集《散落在机台上的诗》来看,郑小琼已经开始扩容诗歌主题并且语言有了明显的提升。即使这部诗集里的多数诗歌仍以底层打工生活为蓝本,由于词语的抽象化使用和暗色空间感的营造,也使部分诗歌蒙上非现实的、虚幻般的朦胧质感,诸如“黑色工衣裹着白色的躯体与梦境/颤抖的光线间消失的白昼,沿玻璃窗/降临的黑夜,暗淡而有些可疑的天空/那些抽象而虚无的光不小心照亮的念头/它坚硬而冷漠,犹如陡峭的寂静”(《寂静》》深邃与冷峻的基调中透露着词语的锋利。
郑小琼将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己的长诗和短诗,第二类诗歌以打工为题材,第三类则是乡村风格的诗歌。其中,长诗或许更准确地映射出郑小琼的内心及其精神世界。她的长诗《半岛》对嘉陵江转弯处的半岛之景极尽刻画、展开丰富的想象,沉淀出现世浮华之外的平静与悠然。诗人波澜不惊的内心与半岛自然万物的变化结合地如此紧密,同时又因自然之雄变生出对万物与自我、精神与肉身之间关联性的思考。于是,郑小琼写于其中:“尘世/自有其定理,水枯石落,风吹花开/万物以自身的完美呈现它本身”。其次,是郑小琼对乡土世界的情感关照和诗意表达。关切真实乡土中的某种凋敝和老旧成为她乡村风格诗歌的重要部分:“被生活紧紧捆绑着的乡村/它们温顺得有如牲畜 它们低垂头颅/啃着寒霜似的月光”(《所见》)。这一主题与其他“打工诗人”或者说从乡村转入城市的群体形成精神上的共鸣。
就郑小琼而言,与其他书写“打工诗歌”的众多诗人相较,她的乡村题材诗歌中对自我身份和文化选择的困惑并非其写作的出发点。它门更倾向于映射诗人本身对真实乡土世界趋向凋敝,以及自我与乡村自然世界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疏离的担忧和叹息。《返乡之歌》中郑小琼表达了人与真实乡村现实与情感纠葛间的思考:“要用怎样的措辞来复述我们/爱,或不爱,还有责任,无法审判/内心的背叛者,她有一百个背叛的理由。”当然,对乡村世界中纯净、美好部分的怀恋和向往构成其间的点点亮色,诸如“蝉鸣潜泳桂花的深涧 南风梳理着/橘子树的皱纹”“(《潜居》)“母爱像春雨样/落着 真理像沙子样透明而坚硬/信仰像酒液清醇 我将与牛羊归家”(《傍晚》)等又描绘出一种避世般的恬静、旷远与深幽。
郑小琼一方面是直击现实的,她的“打工诗歌”题材、乡村题材创作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她的诗歌又是极度超现实的、充盈着“避世”的渴望。郑小琼诗歌的这一部分却也区别于虚构,长时间的直面和反映现实,诗人似乎更渴望获得现实以外的寄托与安慰。组诗《玫瑰庄园》记叙五个女性的红尘往事,偏散文化。六十年轮回,时间的交错往复中,以此在的现实回溯一甲子前女性的命运轨迹,纷乱的情欲、痴儿怨女的点点滴滴在郑小琼的诗里勾勒得清丽动人。“玫瑰庄园”作为一个密闭的空间,似乎隐喻着诗人逃遁开外部现实世界的一方净土,是她为自己建造的纯粹的女性世界:“我必须放弃回忆中的后花园,回到/现实的世界,就像在生活中我放弃真实的泪水/戴上一张面具,在周围形形色色虚构的人群中/活着,行走,微笑着把手伸向厌恶的人”(《玫瑰庄园》)。《玫瑰庄园》使郑小琼回归女性的身份,唤醒了她作为女性的敏锐嗅觉,用以捕捉那些在机械化生产下被消耗掉、被省略掉的女性的感知和柔软的部分,流淌着浓郁的古典气息。
除去诗歌表现内容与主题的深化,郑小琼对诗歌技巧的探索也尤为引人注目。郑小琼认为当代的诗歌写作,诗人的内心越来越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诗人在写作中陷入某种技术的伪装,被庞大而崇高的坚壳包裹着的诗歌,无法让阅读者感受到诗人本身的冷暖、爱憎、肉体、内心、情感……冰冷的技术,冷漠的语言让越来越多的诗歌变成了一种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什。”①郑小琼:《返回内心的真实》,《作品》,2008年第10期。201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郑小琼的诗集《纯种植物》,可被视为郑小琼从“打工诗歌”主题内核中抽离的一次蜕变。这一次,郑小琼回归作为诗人的起点,进行诗艺原点的探索,其间她阐发了诸多关于诗歌写作本身的思考,譬如这首名为《失败之诗》的诗作:
“在一首失败的诗间 对祖先深怀愧疚
目睹权力将精致的汉语扭曲 被暴力
侵袭过的诗歌 句子与词语
它们遍体鳞伤 像受伤的鸟只
在它颤抖与战栗的意义中
扑闪受伤的翅膀”
——《失败之诗》②郑小琼:《失败之诗》.郑小琼著:《纯种植物》,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15页。(节选)
关注当代新诗对汉语词语的使用和改造,诗歌在词语的日益趋个性化和任意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诗歌语言免受“权力”的暴力、避免对汉语言精妙部分的破坏并保有对传统文化应存的敬意,郑小琼显然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诗集《纯种植物》让人们看到郑小琼以尖锐的词语刺穿现实,从聚焦和关切个体的生存、群体的存在样态的具象现实转向思考时代、历史、时间等抽象现实上。这部诗集语言高度凝练,集中反思了“自由”“独立精神”以及“暴力”间的关联性,整体上漫溢着思想者的凝重。无论是在意象的使用还是诗作的整体基调上都显现出相异于此前“世俗性”写作的诗歌风格,偏于抽象和理性。正如评论家张清华感到惊诧的那样,郑小琼作为一个“80后”青年诗人,频繁地将“历史”“人民”“英雄”“自由”等宏大的概念融入诗句之中。在这些词语面前,曾经在诗歌中“仰视”生活的诗人郑小琼蜕变为一个能够以更宏大、更开阔的视角剖析人性、解读社会,这或许不单单意味着一个诗人诗艺的成熟,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人自由思考的可贵。
“群像者”的诗人定位显然使郑小琼在某种意义上区别于大多数“80后”当代诗人,这一“独异性”的呈现恰如杨克所言:“她将比同龄人有更深刻体验的生命疼痛呈现为一种‘南方经验’,真实地告知了当下的、中国的、底层群体的生存本相。”①杨克:《序郑小琼诗集〈在桥沥〉》,方舟编:《承担之镜:东莞青年诗人散论》,2010年,第160页。郑小琼诗歌的价值显然并不局限于此,毕竟她已经在通过写作实践对此限定进行“突围”,并且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