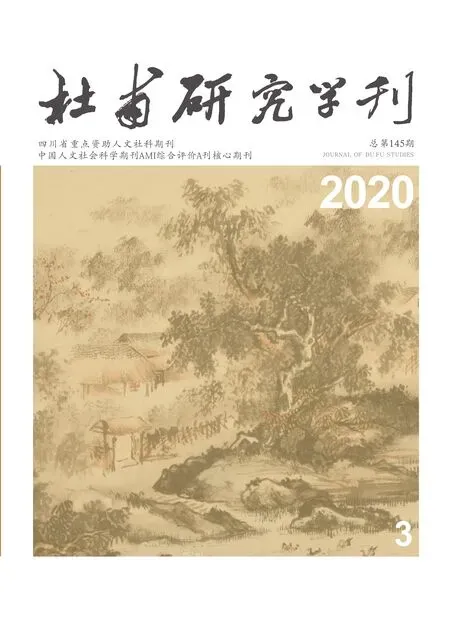彼岸他乡 借石攻玉
——三部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杜甫形象
2020-11-18周睿
周 睿
一、三部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概述
西方语境中对中国文学史的关照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俄语版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国文学史纲要)于1880年由王西里(Vasily P. Vasilyev,1818-1900)在圣彼得堡汇编出版,应该是最早的外文中国文学史。此后,多被学界奉为西方世界最早的规范中国文学史——英语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于1901 年在英国伦敦编纂出版,次年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在德国莱比锡推出了德语版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东方学界中的日本学者也走在前端,1882年末松谦澄(Suematsu Kenchō,1855-1920)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97 年古城贞吉(Kozyo Satakichi,1866-1949)的《支那文学史》、1898 年笹川临风(Sasakawa Rinpū,1870-1949)的《支那文学史》都有草创之功。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海外学者(以独立或合作的方式)重新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当下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有:吉川幸次郎(Kōjirō Yoshikawa)的日语版《中国诗史》(1967)、《中国文学史》(1974),白佐良(Giuliano Bertúccioli,1923-2001)的意语 版La letteratura cinese(1968、2013),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的 法 语 版Chine: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1989、2004),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德语版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99)等,皆在各自偏重的领域有吉光片羽的精彩论述。
而本世纪出版的三本域外中国文学史: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下简称“哥史”)①、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下简称“剑史”)②、顾彬(Wolfgang Kubin)主编德文版《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以下简称“德史”)最为学界所重。该书系按文类和时段以十卷分述、各领其名,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前七卷,第一卷《中国诗歌史》顾彬主笔)③。在欧美学者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此三史同时兼具书写的当代性(均完成于本世纪)、通史的连贯性(皆涵盖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文类的多样性(主流文类之外兼及其他诸多次文类)、学术倾向的代表性(著者皆是相关领域的知名汉学家)、读者的较大覆盖面(在英语/德语界拥有广泛读者且都有中译本回传中文学界)等特征。本文拟以此三部外文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为个案,比较杜甫的文学史形象,探究其在世界文学体系和全球化文学批评思潮进程的域外中国文学史观中的形象生成与误读。
二、以杜甫的文学史形象聚焦欧美学术思维共性
中国文学史的域外书写语境中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理念与欧美学术脉络、政治文化、视野立场紧密相连,实则是“海外中国学”的欧美学术思维的呈现;那么文学史中的杜甫形象的树立,又展现出什么样的共性体认呢?
(一)编纂学养层面
三史中,担任杜甫章节撰写的学者都可谓是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哥史”涉及杜甫形象的第十四章《唐诗》的作者柯慕白(Paul W. Kroll,又名柯睿)④,其对唐代作家作品研究多从宗教文化角度切入,在北美汉学界颇具威望。“剑史”涉及杜甫章节的第四章《文化唐朝》的作者宇文所安⑤是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长于中国古典诗歌、文论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他大部分专著由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联经引进了中文版,在中文学界影响很大。“德史”第一卷第三章专辟一小节《悲诉精神——典范杜甫》,本套丛书的主编暨本卷作者顾彬⑥驰名于德语系汉学界,在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思想史领域都有诸多著作。柯慕白汉名意为“倾慕李白”,宇文所安的汉名不仅用了鲜卑的复姓来表示对中古文化的兴趣,“所安”也是出自《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顾彬名“彬”出自《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三位都不是华人华裔学者,但对中国文学格外倾心,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以中古时期为中心)的汉学名家,对杜甫研究都有相当的心得(特别是宇文所安,其《杜甫诗全译》被学界视为里程碑式的集大成之作),他们接受了西方学术传统的汉学专业(Sinology)学历教育之后从事研究,之后也与华语学界广泛充分互动,兼备中西文化对照的学术视野,能够代表当今欧美汉学的思考倾向和研究水准。
三本文学史基本都是面向本土的英语/德语世界的读者。“哥史”在序言中称,“随着美国大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东亚裔美国公民开始对自己原民族文化遗产感兴趣,许多人希望能够读到一部全面而且目标多元的中国文学史。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是一部当所有的专家和非专家需要获得中国文学的文学类型、作品文本、人物和运动方面的背景知识时,都能够依靠的一部参考书”⑦,将读者目标定为有意于了解中国文学的域外学者和读者。“剑史”亦明确指出“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需要之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⑧。“德史”坦承“于1988 年着手撰写这套曾经被人写过的、卷帙极其浩繁的中国文学史时”的艰辛困难,即使“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文学的总体表述了”,但此次重写仍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次具有代表性的选择”⑨,从而成就了德语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体系建构/重构。可见,三史都希望能够在中国文学史的域外书写中形塑“经典文学史”的地位以求学界认同,并在出版领域占据市场,争取到更多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以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三史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目标,分别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伯克利、哥伦比亚、牛津、剑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英语系以及海德堡、莱比锡、波鸿、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大学等德语系国家的名校东亚系列为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必读书目。由于预设读者是本土读者,故而三史频见英文/德文读者比较熟悉的西方文学作品和人物来参照中国文学史,唤起“似曾相识”的比较文学视野,涉及杜甫的章节也是如此:例如“哥史”中将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Keats)的名句“Poetry should surprise by a fine excess”相提并论,在技巧、象征、音律、感情等方面的深邃则与英国维多利亚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晚年的十四行诗比照;用霍普金斯在写作技巧上的变革以及对后世诗人的影响力度,特别是晦涩句式、复合隐喻、跳韵(sprung rhythm)的探索性运用,与杜甫之于后世(如韩愈、李商隐、黄庭坚等)在诗艺技巧、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抑扬顿挫、意象比兴等方面的影响相对照,而二人之间的对比,在之前的中国学界则很少被提及;而“德史”中出现的对欧美学界已有杜甫研究成果的频繁征引,可见欧美学术话语传统的相互指涉意义。
此外,三史都有中译本,在华语世界,中文读者也能够通过译本了解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并与中国本土的主流文学史比较了解他们的差异。这些中外读者是如何接受文学史中的杜甫形象的,值得考察。
(二)方法学理层面
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强调物质对社会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在西方学界也是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在文学史叙述上,表现为其真实性与本质性要经由具体时代语境的社会风俗、文化风潮、审美风向的共同形塑来实现,“剑史”在中文版序言所提“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的概念,正是这一西方学术话语传统的体现——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首倡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开创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分别是欧、美两地学界的文化研究学术史理念更新的奠基性学理根本,调整文学文本与历史实境/文化语境之间前景和背景、主体与客体、主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经典化”之外寻求次文本(subtext)、副文本(paratext)、隐文本(implicit-text)、潜文本(hypotext)、非文本(non-text)等存在合理性,重新考察/塑造文学文本在历史文化语境和物质条件下的呈现与意义,看似有点“本末倒置”。域外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也延续这样的文学史观念,揭示文学和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习俗、语言之间的互动。比如,“哥史”强调杜甫未能出现在《河岳英灵集》中的原因是“成书之时,杜甫还默默无闻,或者名声并不大”⑩,剑史也注意到了他未能入选《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这一历史事实⑪,重视的是文本周边的话语领域和物质领域;而对杜甫诗中对安史之乱的反思的“正统性”“权威性”“唯一性”文学史定位,“哥史”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只有在杜甫的诗里,才能找到当时文学对粉碎了盛唐的安史之乱的反思,这是一种夸大之辞。这一时期的其他诗人也进行过类似思考,但是他们都没能像杜甫那样令人难忘地捕捉到事件带来的悲苦”,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杜甫诗歌在反映安史之乱中的诗史性,似有不妥;“德史”认为“颠沛流离的日常生活、他的困苦、恐惧、疾病有助于突出个人的私人方面,而让社会角色或多或少退居次要地位”,“用这样一种风格来对抗安禄山叛乱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这种风格不再使社会事件抽象化,而是使之具体化,这时,他想结束这种宇宙学的循环,但正是这种事他做不到,因此日常琐事便取得一种新的地位”,并未强调杜甫的“人民诗人”身份,也有刻意矮化杜诗社会意义之嫌。“哥史”还提到“他并不擅长作赋,杜甫存世的七篇赋都比较晦涩矫饰”,这种“反经典化”倾向拒绝向文化权威妥协来重新反思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方面,尽管杜甫的“赋才”不仅有他进献“三大礼赋”而得以待制集贤院的历史事实,也有自己的诗句来文史互证:“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莫相疑行》),但“哥史”的文学史评价仍然坚持从赋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角度来评判杜赋的“真实”地位,评价标准显然脱离了中国赋学的历史流变和当时的历史语境,这种破除文化权威的所谓“勇气”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由于杜甫正统儒士的文学史地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容挑战,对他的“圣化”可能令他以文学大家的身份遮蔽住当时其他的文学小家的光芒而出现文学史叙事的绝对化和权威化让同时代的其他相近类型的诗人从文学史上隐形,故而三史都似乎“刻意”都未提及“诗圣”之说或“一饭未尝忘君”的“爱国诗人”,而注意到他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属性,“哥史”说“有时他会对过于严肃的自己开一些玩笑”;“剑史”说他“在他晚期作品中我们时常发现一种温和的自嘲,这给他的诗歌一种难得的人性深度”(人性,还要讲深度,立刻使人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恐怕要算是最崇高、最伟大、最深刻的人性吧。),“德史”评《月夜》诗“作为转折的颈联这对双行诗本来应该针对的是历史事件、社会事件或者政治事件:可是没有这样做,而是献给了个人私事——一种性爱渴望,这种渴望在云鬟和玉臂的形象中固定下来”,这样来解杜诗,也都是反权威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所表现出的误读之一。
(三)风格学脉方面
除了之前提及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之外,西方文艺思想和文化研究中常用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英美新批评、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管多受国内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质疑和排斥,但以他者视角介入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领域,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批判后学时代的怀疑精神和重构意识,另一方面也可借鉴他们在抵制不可知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诱导上的努力。“剑史”主编宇文所安深受耶鲁学派解构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经典的建构经由中介(mediation)的选择和定型“提醒我们过去的人做出的价值判断和现在如何不同”,说明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不断“建构”传统的过程。在“剑史”中,他认为杜甫“诗史”的由来只是因为“杜甫诗中总有其它作家无法比拟的个人细节,当这些细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交织时,杜甫在后世赢得了‘诗史’的名声”,并不同于传统文学史须使杜甫的政治忠诚情怀与之密不可分,不是强调“道德至上”的定性评价,而是从文本生成角度来理解文学经典化问题,这在国内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论;此后又评论他夔州时期,“在相对孤独中进行创作对他是一种解放;他变成高瞻远瞩的梦想家,运用对仗和诗歌语言内在的不确定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诗句”,这里“梦想家”一词原文是visionary,英文中既有远见卓识的褒义,也有耽于空想的贬义,这种定义在传统文学史上极少用在“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身上。顾彬在“德史”评价名篇《春望》“缺少结尾本来就有可能实现的宇宙学和解,这种嘲弄只能被视为对付和谐明显缺乏这种状况的尝试”来解释杜诗晚期的“破碎性”的具体呈现,反思其作品在阅读和接受中“不能形成意义之处去构建意义的尝试”。如此这般的解构认识,可能会打破对杜甫文学史形象的既有主流印象,但亦要提防对经典诗人的庸俗化解读。
在叙史风格上,三史都有意识地尝试通过互文性的历史文献文本的生动细节来再现杜甫的人文情怀,让叙事带有戏剧性甚至虚构性(fictionality),正如孙康宜说“剑史”应该popular(平实)而非mediocre(平庸),“深入浅出”,“不是去媚俗,不是去妥协,而是要忠于事实,是要严谨的”,这种文学史书写方式带有虚无化的危险,故而在以严肃著称的华语学界的历史书写中是很少见的。“哥史”在分析杜甫对“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悲苦,提到了几首近体诗和古体诗,其中全文引用《羌村》其一,在交代写作背景时说他以“极大的温柔”(intense tenderness),这样的叙事让杜甫的“忠实深情的丈夫与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德史”更进一步还原杜甫的家庭身份,评《月夜》“一反当时的习惯,不是把一个姘妇或者一个歌女,而是把自己的妻子置于性爱观赏的中心”,戳开诗评家从未道破关于“性要求”的事实。“剑史”也是如此,评价杜甫成都诗“有一种用轻描淡写的语调表达出来的轻快,完美的形式控制和幽默的独白达到了平衡”,进而举例说他的儿子“激动地向他报告江上发大水了,江水就在充满沉思、不慌不忙的诗人眼前迅速涨起:‘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这一叙述解构了杜甫可敬而不可亲的“诗圣”形象,刻画的分明是一位有生活情趣、充满哲思的邻家老叟,连他的家人也显得如此烟火气、童真十足。如此真实立体的叙述形象、传神灵动的叙述风格、情节导向的叙述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文学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读起来饶有趣味。尽管这一点可能比较多招致国内学界的严厉批评,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
三、比较视野下域外书写的杜甫文学史价值之再评介
尽管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较为新颖且有趣的视角,但客观而论,这些文学史对杜甫的文学史价值的定位与国内通行的文学史并没有本质上的出入,但是有些问题值得特别指出加以辨析。通过对比国内通行的一些文学史(如袁行霈、郭预衡、章培恒、游国恩、刘大杰、乔象钟等版本),可以发现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杜甫形象的具体表征和问题所在。
(一)碎片化体系构建
中国文学史书写惯例,一般是体系化地介绍作家的时代风貌、生平思想,接着对其作品分期分类,之后概述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最后略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并挑选其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免不了意识形态的痕迹)的作品加以分析;但三史对杜甫的文学史式叙述则以碎片式呈现。由于杜甫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价值,各家文学史都是单列章节予以专论,篇幅也较为饱满,以凸显出杜甫的文学史地位,例如“郭史”24 页,分为杜甫的生平和思想、杜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影响四节;“袁史”15页,由社会动乱与诗人杜甫、杜甫的律诗、杜诗的艺术风格、杜诗的地位与影响四部分构成,二书结构相似,书写篇幅巧合地均占同书《隋唐五代文学》一编总量的7%;“乔史”更是用两章59 页的篇幅加以细论,体系严整规范,评论细致深入。虽未洗陈陈相因之嫌,但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有地位的体认是毋庸置疑的。相比而言,西方三史则依照自由学术范式,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比较不受规则限制而略显随性。“哥史”的杜甫叙述放在第十四章《唐诗》第五小节《八世纪诗》之下,除了伴随“李杜并称”寥寥数语后,对杜甫的专论仅占两页;“剑史”稍长,系于第四章《文化唐朝》第四小节《叛乱之后》之下有三页多,这与国内文学史的惯例反差颇大,如此篇幅显然在勾勒杜甫的文学史地位上捉襟见肘。除了篇幅之外,三史在叙述上也显得零散碎片化:“德史”虽然篇幅稍多,不过,二十多页的内容无论是体系上还是条理上都略显混乱,侧重透过宇宙学意义和语义学结构去阐释杜诗文本而并未着意构筑清晰的杜甫(诗史)形象,读起来更像是单篇学术论文。“哥史”在“李杜”的出场上用了七十多字简单介绍了杜甫籍贯、家世、先祖、作品在当时选集的收录情况,稍后再介绍了杜甫的文化地位、生平大事、作品情况、诗中形象(以《羌村》为例)、民胞物与(如“三吏三别”、《病马》《缚鸡行》)、诗艺评价(近体诗、《秋兴八首》),最后对他的赋作了定性,之后以此引申到盛唐其它文人的赋创作情形。“剑史”把杜甫安排在“安史之乱”的历史讲述后,以“匿名”的方式(a young man)登场,大概是基于他在当时并未引人注目的“事实”,直到最后交代他于770 年过世才让读者“猜中”谜底;接着便是叙述“诗史”的由来(前文已论),年序式地提到杜甫个人生平、时代事件与作品表现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一些人物(如一位失宠朝臣[房琯]、当地长官[高适])和地域(如成都草堂、夔州江居)等细节稍加铺陈,叙及杜甫过世之后,介绍他的作品结集、人物评价和后世影响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提到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在数量上与杜甫匹敌”,但他们在当时深受赞誉,作品入选唐人文集,与杜甫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物质文化史角度探寻杜甫不为唐人所重的原因。总体来说,三史的叙事能在中国文学史惯有思路之外另辟蹊径,然其流弊恐亦肇于此,碎片式叙事难成体系,甚至有过度情感代入而走入“传奇”的歧路的危险。
(二)另类化经典破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文学研究的文化障碍日渐消解,域内外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有趋同的倾向,但彼此之间在价值观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却很明显。国内诸史在对杜甫经典文本的引述、选辑和解读上虽然不免受到阶级为纲、道德为尊的上一代研究观念的影响,但在经典杜诗的判断上基本一致,所选作品大多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以国内主流的文学史(袁、郭、游、刘、章诸史)为例,各自提到的杜诗数量在50-100 首左右,在涉及杜甫身世时无一例外会引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现实主义杰作不会漏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北征》、“三吏三别”、“二哀二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史”精神实例举证《三绝句》,同情民众的情怀必列《又呈吴郎》,律诗技艺出神入化少不了《春望》《登高》和《秋兴八首》,还有如《望岳》《月夜》《梦李白》《春夜喜雨》《蜀相》《戏为六绝句》《咏怀古迹五首》《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也是公认的经典,对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来说,这些代表作是不能绕过的,像“袁史”提及杜诗作品64 首/组,引用全诗或章句多达41处。但到了西方三史这里,杜甫代表作出现了陌生化的反经典趋向。“哥史”选杜诗十二首(组),分别是《春望》《月夜》、“二哀”、“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等经典作品;“剑史”提到杜诗数量与“哥史”相当,选了“二哀二悲”、“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等经典;“德史”则选择《旅夜书怀》《春望》《江汉》《月夜》《梦李白》《秋兴八首》(其一)等八首作品全文加以评析,可见三者在作品汰选上标准较为一致,没有推介更多作品可能因为限于篇幅,但是对很多经典作品完全不置一词,还是略觉遗憾。如果说“哥史”全文(也是唯一)引用《羌村》还不算太奇怪的话,“剑史”出现的三处引文分别选自《江涨》、《破船》和《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三)的数联,则在国内书写的文学史中几乎从未选入。“德史”在文本阐读中亦“巧合地”选了《破船》(另选《独立》一诗也是诸史基本不选的作品),并对其评价颇高:“借助破船的隐喻,……让破船成为西方国家生存隐喻的范例”。以宇文所安为例,其选诗标准与他的学术价值取向和研究理念方法以及个人兴趣偏好都息息相关,他主张文学史叙述处在一种不确定中,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检视,以往认为的“经典”可能会固化对作家作品的偏见,因此造成对其他类型作品的忽视,这一点他在后面评价杜甫作品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时也有提及,他自己另有文提到过这样的事实:“九世纪中叶前后,顾陶编撰过一部庞大的《唐诗类选》,这部选集已经佚失了,但是在一部南宋笔记里,我们看到入选杜诗的列表,在当年顾陶所选的那二十七首杜诗中,只有三首是我们现在还经常阅读的”,由此来叩问“当时的人读的都是哪些诗”这一问题。这种对“非经典”的另类化关注刻意打破了中国读者对杜甫的传统期待视野,提醒杜甫的接受存在历史性和流动性,而非一成不变的,但我们应该看到,过分强调“非经典”的意义很可能会丧失文学史的主体价值,很难说能保证学术研究的超脱性的公正。
(三)随性化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基本功,在域外文学史的杜甫书写中,一些文本分析既精彩细致又有温度情感,虽然不免随意和琐碎。“哥史”在叙述中较少解读具体文本,而是给出一些标签式的评价,如“忠诚的国民、坚定的官员、忠实深情的丈夫与父亲”,或“杜甫对生活苦乐交织的真挚感,是所有其他中国诗人都未曾到达的醇厚境界”,也会剔除一些意识形态的道德评价,更关注于杜甫的人本主义,“杜甫对从人类到动物(如《病马》和《缚鸡行》)所有生物遭受的创痛都抱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杜诗最引人注目的特质之一”,但这里既看不到文本细读的痕迹,也缺少与约定俗成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应(如杜甫广为人知的“民胞物与”精神),挑选的证据文本虽然没有问题,但在典型代表性上却很薄弱。对比主流国内文学史,“郭史”将《病马》放在杜甫“借物自喻”的题材下,言其“多咏马、鹰、松柏等神俊高洁之物”,认为“其中分明寄寓了诗人不幸的遭遇”,这与哥史认为对他物的“同情”并非同一标的;《缚鸡行》仅被“刘史”用以论证“杜甫无论对祖国,对家室儿女,对人民以至于草木虫鸟、茅屋草堂,都充满着热爱和同情”的观点,只寥寥几语。柯慕白选择这两首诗来论证杜甫“民胞物与”思想,似有些随意。“剑史”的文本细读要细致一些,例如宇文所安在论述《北征》是“乾坤含疮痍”的见证时,在肃宗向回纥借兵的历史细节上加以发挥,认为杜甫的评价“此辈少为贵”是“绝妙的模棱两可(wonderful ambiguity)”,并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以把这句诗解读为赞扬回纥军队的英勇(即使仅有少数,也很珍贵),也可以理解为此辈越少越好”;国内文学史很少提到此例(如“袁史”评《北征》强调叙事的细节描写,对此句未置一词,一般对杜甫遣词用句、语含讥讽的双关名句都引《赠花卿》)。再如他提到杜甫秦州诗的有些主题很特别,以《除架》为例,“以拆除葫芦架比喻抛弃不再有用的物或人”,近似提法在“游史”中的表述是“在咏物诗中,有的直接和现实联系,如《枯棕》《病橘》等;有的则是借物寓意,因小明大,如《萤火》刺宦官的窃弄权柄,《花鸭》刺奸相的箝制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文学史未提及《除架》,故而无从比较“主题特别”的深旨。而后叙至成都诗,以《破船》为例展开文本阅读,在交代了诗本事之后说“诗的结尾有典型的杜氏风格”,说他“意识到自己最喜欢的不是沿江而下,而是能够待在原地,坐在船里,创造溯江而下的诗歌”,有趣的是,顾彬看法正好相反:“停在‘港’里意味着耽误他的人生幸福,但他再也不想谈到乘船出游和某一目的地,而宁愿成为他自身命运的观察者。”二人的解读都很费解,为何以此首诗来代表杜甫佳作众多的成都诗?杜氏典型风格是什么?如何理解他的“温和的自嘲”和“难得的人性深度”以及“再也不想谈到乘船出游和某一目的地”?从所引文本看杜甫流露出对“世乱遭飘荡”的叹息,王嗣奭《杜臆》评论较为客观:“公盖以此二物(水槛、浮槎)为草堂中乐事,避乱归来,二物俱坏矣……此公所以感故物而兴悲也”;又云“故者可掘,新亦易求,具舟何难,直以奔窜之频,白屋不能久住,而何有于扁舟,所以悲也”;宇文所安和顾彬在阐释上都有点儿剑走偏锋,甚至偶尔还有误读之嫌,并不能跟国内文学史在文本解读上的功力等量齐观。“剑史”还说杜甫夔州诗在“运用对仗和诗歌语言内在的不确定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诗句:‘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杜甫在夔州诗艺上已臻完美,国内文学史一般都会以《登高》为例,如“郭史”引《诗薮》云“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而为“古今七律第一”;“袁史”引杨伦观点:“杜集七言律第一”,用了三百多字评价此诗。而宇文所安刻意求新而选用这首鲜为人知的“次要作品”来表现文学史书写的反经典倾向以彰显自己对杜甫文本的熟悉,此联语意精工程度恐怕还不如它在宇文笔下的英语译诗的效果:
Myself and the age:a pair of tangled tresses,
Earth and Heaven:a single thatched pavilion.
这也凸显出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特点:文学史书写的文本细读不是章法固定的,容易受到撰史者本身的学养兴趣和价值取向的影响而呈现出随性零散的(东方主义?)特征。“一史一面,千史千面”的格局对文学史书写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碎片化、另类化、随性化的三种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并未能在学理层面超越现有国内主流中国文学史。
四、域外构建的杜甫文学史形象的文化影响
域外书写的三部中国文学史中建构的杜甫形象对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带动了海外杜学的持续发展。新世纪以来,杜诗英译活力不减,出现诸如基思·霍尔约克(Keith Holyoak)《对月:李杜诗选》(Facing the Moon:Poems of Li Bai and Du Fu)、乔纳森·韦利(Jonathan Waley)《春望:杜甫诗选》(Spring in the Ruined City:Selected Poems of Du Fu)、珍·伊丽莎白·沃德(Jean Elizabeth Ward)《被记住的杜甫》(Tu Fu:Remembered)、大卫·杨(David Young)《杜甫:诗史一生》(Du Fu:A Life in Poetry)、马克·亚历山大(Mark Alexander)《杜甫小册》(A Little Book of Du Fu)等选译本以及詹姆斯·墨菲(James R. Murphy)《墨菲译杜诗》(Murphy’s Du Fu,Vol.1-4)的全译本,这些译者几乎都不是学界中人,通过把握译介中的杜甫(Du Fu in Translation)文学史形象来实现杜甫的再度/多度传播。就汉学界而言,早期霍克思(David Hawkes)《杜甫初阶》(A Little Primer of Tu Fu)、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甫诗选集》(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戴维·亨顿(David Hinton)《杜甫诗选》(Selected Poems of Tu Fu)、周杉(Eva Shan Chou)《再议杜甫:文学丰绩和文化语境》(Reconsidering Tu Fu: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在近二十年有再版。“剑史”编者宇文所安于2016推出历时八年完成的《杜甫诗全译》(The Poetry of Du Fu),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师岱渭(David K. Schneider)2012年的《儒家先知:杜甫诗歌中的政治思想》(Confucian Prophet:Political Thought in Du Fu’s Poetry)挖掘杜甫长安时期作品中的政治理念,圣十字学院的郝稷(Ji Hao)2017年的《杜甫及杜诗在中国古代的接受史》(The Reception of Du Fu and His Poetry in Imperial China)关照接受史中的杜甫其人其作的流变历程,他们清晰的史论视野,皆可见域外构建的杜甫文学史形象的投射痕迹。译成中文的西方三史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研究论文层出不穷,这都推动了对诗圣杜甫的再认识。
2020 年4 月6 日,英国广播公司BBC 播出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China’s Greatest Poet),引起海内外线上线下的观影热潮。这部仍略带东方主义色彩的纪录片“原址重建”般推介杜甫这位世界文化名人,题名取自英语世界第一本研究杜甫的洪业(1893-1980,号煨莲,福建福州人)所撰同名专著,演员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所诵诗作多引该书译文,制片人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提到,纪录片引诗的翻译综合参考了诸多汉学成果,片中也邀请到宇文所安、刘陶陶(牛津大学中国文学讲师)、曾祥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洪业《杜甫》中文译者)等专家嘉宾进行访谈。译介的杜甫是中国伟大的诗人,更是世界伟大的诗人,文学史、译作集、纪录片在杜甫在海外的传播形象上形成某种同频共振。
“重写文学史”对于文学史现象的反思在域内外学界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关注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并不是要放弃本土文学史的范式,而是探讨和反省中国文学史观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这不仅能够更新固有传统文学史观,寻求某些根深蒂固僵化观点的突破,更能够拓展研究视野,在学术交流对话中丰富研究手段,拓展理论深度。以域外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杜甫形象分析比较为个案,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西方学术传统和话语惯性,以“后学”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来解构和审视文化和文学,有可能会导致结论错误或者阐释过度;另一方面也看到杜甫的经典地位并未被撼动,虽然在文学史叙述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碎片性、另类性、随意性等陌生化取向,但对杜甫文学形象的差异表达仍然具有一定价值,有助于我们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之下重新审视其文化意义,丰富中国文学史的图景和杜甫的文学史形象。
注释:
④柯慕白,1976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起就职于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文明系,T’ang Studies《唐学报》前主编,代表专著包括《中古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集》(Essays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Routledge,2009),主编《中古中国诗歌:文本、语境与文化》(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Text,Context,and Culture,Brill,2014),参编《早期中古中国手册》(Early Medieval China:A Sourceboo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牛津中国古代文学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 900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等。
⑤宇文所安,1972年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1982年起执教哈佛大学,代表专著包括《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The Late Tang: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小词而已》(Just a Song: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翻译《诺顿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 W.W. Norton, 1996)、杜 甫 诗 全 译(The Poetry of Du Fu,De Gruyter,2016),参编《牛津中国古代文学手册》等。
⑥顾彬在明斯特大学、维也纳大学、波鸿鲁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工作,1985年开始执教于波恩大学,《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Zeitschrift zum chinesischen Geist)、《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主编,代表专著包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Der durchsichtige 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中国传统戏曲》(Das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Theater:Vom Mongolendrama bis zur Pekinger Oper,Saur,20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