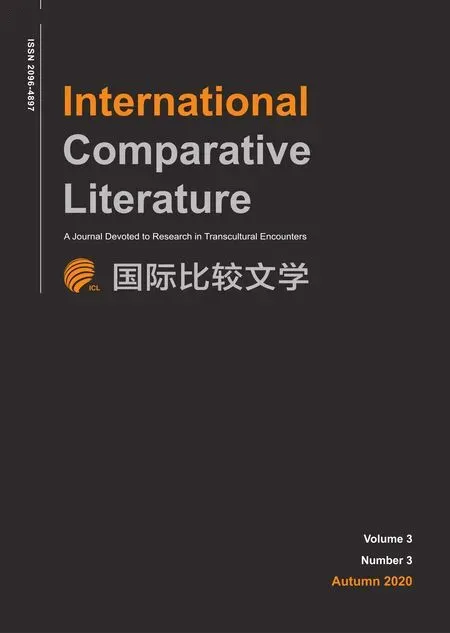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
2020-11-17汪尧翀
黑格尔构想的“现实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大部分:前者处理自然科学的基础概念,后者则囊括了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论域。黑格尔试图从自我理解的理性原则出发,为差异纷呈的全人类领域提供一种“整体论”说明,即在“体系”前提下辨析理性原则之于自然与精神领域的分殊:自然现象与心灵现象皆立足于同一个世界;而心灵现象所表征的自由,根本上又不同于决定自然现象的因果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概念框架及理解原则。换言之,对存有一元论(ontological monism)前提下心物二元论之相容性的研判,已是黑格尔思想当代效力的核心争论点。1参见刘创馥:《黑格尔新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83—210页。[LIU Chuangfu,Heigeer xin shi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egel),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9,183—210.]如果说,当代黑格尔研究在分析地推进上述议题的普遍性方面成果斐然,那么,黄金城的近期力作《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则从思想史角度为理解黑格尔的“整体论”现代性方案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历史语境及批判内涵。
作者开篇即申明:“本书的预设是,德国浪漫派的有机体话语构成一种审美现代性方案。”2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qingnian Heigeer yu shenmei xiandaixing huayu (Organic Modernity:The Young Hegel and The Aesthet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9,8.]有机体作为思想范式,在后康德观念论史中具体表达为自然哲学的发展与建构,并结晶为一元论对二元论的克服。在这条主线之下,作者持续聚焦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共同智识语境,即浪漫派的有机体世界观,并以追问黑格尔与谢林的决裂为终点。全书以此问题意识为主导,实际上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思考自然精神化之不同阶段的重构,不妨借一著名的隐喻将之描述为自然哲学的三次浪潮。有鉴于此,我想分三步来评论此书的核心意义:首先,前两次浪潮展现了黑格尔分有浪漫派有机体世界观,建构体系思想的运思过程;其次,第三次浪潮终于黑格尔与谢林之争,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借道黑格尔思想关切现代性问题的创造性思考;最后,在重述全书脉络的前提下,我试图从另一种对抗性的思想史进路出发,谈一谈有机体范式的深刻启示。
自然哲学浪潮
黄金城此书的切入点颇具创见性,他发现康德以降的观念论史所育出的审美现代性话语与有机体思想之间的独特联系,并以此为勘查点,出入于康德之后的诸种现代性方案,后者皆因康德确立但并未能彻底解决的自然科学与人之自由的关系而起。对德国观念论而言,人之自由始终是其拱顶石,因此之故,自然哲学应运而生,不懈地试图将与人无涉的、或仅作为认知表象而存在的自然科学之自然,转化为浸润于人之主体性的有灵自然。用拜泽尔(Frederick C.Beiser)的话说,“所有自然哲学的理想:一种对科学的诗意呈现。”3(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观念》,黄江译、韩潮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28页。[Frederick C.Beiser,Langman de lüling:zaoqi Deguo langmanzhuyi guannian (The Romantic Imperative: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trans.HUANG Jiang,ed.HAN Chao,Beijing:Huaxia Press,2019,28.]但作者并未简化上述历史叙事,反而精心披露自然哲学颇不顺畅的发展道路,诊疗其经浪漫派而误入的歧路。作者认为,青年黑格尔于此风起云涌之际,熔时代关切与现代性的复杂性认识于一炉,终究扬弃了自然哲学的芒刺,创立了集观念论之大成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哲学浪潮恰好可以视为黑格尔体系思想的论辩前史。
自然哲学浪潮的第一次冲击,激发了伯尔尼时期的青年黑格尔酝酿其宗教批判。黑格尔彼时一方面受教于康德的理性宗教思想,要求将信仰体现的自由意志,从压迫式的传统宗教“权威”,即仪式、偶像、教条乃至拜物教——或一言以蔽之、包含统治关系的“机械论图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认为,权威宗教即彼岸视角仍内置于康德的伦理神学,故而上帝仅作为调节性理念(亦即实践理性的悬设)存在:自然仍是机械论图景中的客观物,而非精神化的存在——这正是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的契入点。面对机械论与有机论的对峙图景,青年黑格尔酝酿了自身的思想转向,认识到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不能满足理性的真正需求。理性要求的是重建形而上学,从而将一切区分(尤其是康德意义上的知性与理性,因而是现象与物自体的界分)包括进来,即“一个统摄一切理念和实践悬设的体系”。4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112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112.]
第二次自然哲学浪潮则进一步将青年黑格尔从权威宗教批判推向了浪漫派(荷尔德林)的统一哲学理念。此时,黑格尔已来到了法兰克福,开始思考如何从“爱”的经验中重构宗教的正当性,以便取代权威宗教的僵化。爱作为一种生命感觉,作为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和解经验,位于统一哲学的根基之处。但黑格尔最终认识到,爱的效力始终依赖于“统一”与“分裂”对立的思想范式,归根结底体现了统一哲学的非辩证性质。换言之,“爱在诸法权形式中达到了其可能性的界限,它不足以达成真正的和解。这是青年黑格尔独有的洞见。”5同上,第174页。[Ibid.,174.]
作者通过对黑格尔论“爱”的手稿详细考察,洞察了黑格尔克服浪漫派统一哲学的枢机,即自觉地将对“爱”之统一性的关切与“现存的市民社会”的问题域结合在一起。换言之,黑格尔肯认作为统一哲学的“和解”,但已觉察到了其抽象性(即空无)和片面性(即无规定性),即未能把现存物即现实性囊括进来:“真正的统一并不在于存在,而在于分裂或对立的生产过程本身。统一性的形成过程,或者说,统一性的事件本身,而非这种统一性据以来被推导出来的基础,才是真正的绝对者。”6同上,第178页。[Ibid.,178.]可以说,青年黑格尔借关切现代性之复杂性的知识准备,已为与浪漫派的彻底决裂埋下了伏笔。7有必要提及拜泽尔出于“早期浪漫派”的独特研究而得出的关于黑格尔体系思想的苛刻论断:“它实际上只是对早已由诺瓦利斯、施莱格尔、荷尔德林及谢林所提出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最晦涩累赘的表达。[……]是时候让黑格尔主义者们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英雄是‘兔中之鳖’了,赢得身后名只因为他是一位更踏实的苦干家。”但是,若考虑到拜泽尔的意图在于强调早期浪漫派“非体系”的整体论(holistic),即体系是其范导性目标而非必须实现的形态,那么,这两种论证路线不仅相容,而且在评论中,我或许会稍微脱离作者原意,倾向于从“整体论”视野理解黑格尔。参见(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第95页、第102页。[Frederick C.Beiser,Langman de lüling(The Romantic Imperative),2019,95,102.]
审美主义与“整体论”
相比前两次自然哲学浪潮,第三次自然哲学浪潮的思想史意义则突出于一场对抗:它既标志着基于有机体概念的审美现代性方案在谢林同一性哲学中走向顶峰;同时,又标志着青年黑格尔的体系思想日趋成熟。第三次浪潮最终涉及政治哲学问题,带出了现代理性主义批判在后康德观念论语境中的两种结果:其中一方是审美主义,另一方则是“体系”思维,分别代表了谢林与黑格尔对有机体思想的不同理解。
作者细致勾勒了谢林有机体思想演化的导览图。在他看来,谢林把有机体擢升为哲学原则,提供了对“一即万有”原则的创造性阐释,即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不过是“自然”茁生的不同阶段:“在身与心之间,没有类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区别。而在整个自然当中,渗透着一个唯一的生命力,它演化为不同的组织和发展层次。”8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250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250.]有机体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德国观念论美学:从康德到席勒,艺术作品有别于有机体,仍服从于“整体—部分”的阐释框架;而谢林的自然哲学则使“形式—质料”的解释框架焕发了生机,视两者为同一理智的不同方面或潜能阶次,从而使艺术作品作为有机体出场。这种审美主义,即天才美学和自然哲学的合一,为现代性方案贡献了保守主义话语的核心语义对立:机械体—有机体。因此,有机体的历史语义学潜能发轫于谢林:“在1800年前后的政治话语中,谢林的国家有机体理念确乎开启了一种范式转换,为政治浪漫派提供了通行的理论表达形式。”9同上,第270页。[Ibid.,270.]换言之,谢林国家有机体思想的保守主义性质,既有其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但也显示了浪漫派审美主义的某种歧路。10参见(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7—131页。[Jürgen Habermas,Lilun yu shijian (Theory and Practice),trans.GUO Guanyi,LI Li,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2010,127—31.]
因此,青年黑格尔最终挥别了浪漫派(谢林)的艺术主权论,从而将有机体设想为科学之“体系”,虽然显示了与浪漫派思想的亲和,然而更多是在诊疗时代政治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理智直观只能让精神重新没入自然的简单性中。而精神倘若要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进而真正对现代性进行规定,那么,精神必然要展开为一系列相互对立而又统一于更高的普遍性的环节。精神的诸环节也必将表现为一种有机体结构,而这就是体系。这个体系也正是精神的扬弃自身即扬弃其‘是他者’的总体性进程。体系理念是‘事实’的需求,也是‘时代的哲学需求’。”11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346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346.]实际上,强调谢林与黑格尔的分歧,尤其涉及考量谢林国家理论与黑格尔法哲学迥异的效果历史,是非常复杂的论题,仅就此书的论证线脉而言,不妨收敛为基础主义与整体论这一组二元对立。前者实际上指将下述主体哲学描述——“主体性把自己外化出来,目的是想把对象化重新融入到自身的体验当中”1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Jürgen Habermas,Xiandaixing de zhexue huayu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CAO Weidong,Nanjing:Yilin Press,2011,165.]——推向极端的模式:这种体验往往指一种奠基于主体性自我关涉的总体化体验,例如浪漫、诗乃至国家。在此意义上,审美主义则是其借道艺术的一种独特形式。13作者提请读者注意审美主义(aestheticism)/唯美主义(aesthetism)的区别,参见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13、274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13,274.]后者则是弱规范意义上的相容论,旨在寻求一个整全视野,以便容纳现代性分化所必然导致的诸领域的话语论证。14此处借用了霍耐特对“弱规范”的规定性,即指黑格尔强调经验的合理性批判取向,以有别于《法哲学原理》中饱受诟病的国家论;与之相对的是康德主义“强规范”。参见Axel Honneth,Pathologien der Vernunft: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16),58.对黑格尔建立在主体性自我确证逻辑上的国家理论的批判,参见(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43—48页。[Jürgen Habermas,Xiandaixing de zhexue huayu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43—48.]
作者对这组对立范畴的思想史处理,体现了长期关于德国保守主义思想之运思脉络的精良思考。换言之,理解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追问如下论题:阐明现代性的复杂性,不可能从“爱”与“美”的审美主义路向得到实现,但是否能从更基要、更原始的奠基概念(诸如自然、精神)出发得到实现呢?进一步说,现代理性主义究竟于何种程度上才能达到其客观的自我理解?确实,黑格尔的回答代表了后康德观念论的逻辑顶点:“只有完善的体系,才能把握现代性的复杂性。”15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293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293.]作者关于黑格尔“体系”概念的细致解析,尤见理解德国观念论进路的深度及创造性。无论“体系”一词在德国观念论的效果历史中如何声名狼藉,作者的精彩分析都有助于减轻关于黑格尔成熟体系思想的误解——当然,并不是说黑格尔思想能够完全规避因保守主义及乐观主义招致的批评——但应更多关注其体系建构的方法及理念。从此意义上说,作者所精心勾勒的谢林与黑格尔之争,在克服现代性之复杂性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上,最紧要也最关键之处仍是区分基础主义与整体论视野。哪怕稍微沿着这种区分的效果史走上一段,也很容易看出阐释所显示的黑格尔思想方法之于“整体论”的核心意义。
如果从社会整体论视角考虑上述政治哲学论争,那么,黑格尔哲学最具活力的效果史可谓经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政治理论或文化批判传统。马克思决定性地开启了“精神”概念的去先验化,并带来了一个积极后果,即自然从其精神化的主体哲学进路中摆脱出来,转渡为自然的历史化(或其通行表达即“自然的人化”)。从历史唯物主义进路着眼,自然的历史化表达为人之社会行动的结果,其合理性必须依托从意识哲学到交往行为理论的范式转型,才能够彻底摆脱“历史自然化”隐患:后者实则继续深陷于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即认为历史不过是据自然科学规律而重新配置的物质材料。16参见Albrecht Wellmer,“Kommunikation und Emanzipation,” in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eds.Urs Jaeggi und Axel Honneth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7),471.显然,对这种粗糙的、实证主义式形而上学的拒斥,早已包含在青年黑格尔关于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思索之中:“人只有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展现于自己面前,使这种展现成为自己的交往对象,在这种展现中享受自身,才成其为人;他必须感到这种被展现的东西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17黑格尔,《不断扩大的矛盾》,转引至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295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295.]
有机体范式的启示
总之,此本论著得之于作者对德国观念论史经年累月的耕作,不仅是难得一见的耐心之作,而且是充满了迷人历史细节的精心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遣词造句上的匠心,使论述艰涩对象的话语也增添了丰富的韵味。作者的宏阔视野及深厚素养,更是使论题远超一般意义的文艺专论,进入了现代性基本问题论争的思想史层面。因此,对一部思想史著作提出思想史的质询,是向之学习的最恰当方式:任一严肃的思想史叙事都不惧置身于更广阔的论辩史。同样,这部论著也邀请读者尽情地察看可能招致的问题。总体上看,作者选择重建青年黑格尔的有机体思想,无疑是一次相当精彩的黑格尔主义演出。从康德主义视角勘查这一路径,也许是吸收其启示的最佳选择。
双方的争论核心问题仍是如何捍卫自然科学的合理性。至少,就捍卫自由的社会条件而论,自然科学难以被替代或轻易抛弃。显然,把自然提升为思辨哲学的对象或自然价值化,无法真正克服现代性危机。有机体世界观的价值在于纠正唯科学主义的偏颇,但自然价值化本身并不能替代科学的合理性,统一体验本身作为某种可还原的“基础”,也不可能替代现代性之复杂性问题。顺便说,自然价值化的一种思想史效力表达为客体优先论,后者始于谢林自然哲学的影响,经布洛赫这位“马克思主义谢林”中介,最终在后现代取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波德里亚那里大获成功。18参见(法)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Jean Baudrillard,Zhiming de celüe (Fatal Strategies),trans.LIU Xiang,Dai Abao,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5.]但客体优先论的基础主义取向也证明,科学之于生活世界的进步价值确实难以在主体哲学模式之下得到辩护;换言之,在通过理性的他者(客体)来消解理性(主体)之强制的视角下,任何科学陈述的真理价值都能够被还原为派生的统治关系加以摒弃。
不过,即便是在更有力的康德主义当代版本中,黑格尔的因素也在其中扮演着矫正要素的角色。19“结果,在他之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握理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参见(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1页。[Jürgen Habermas,Xiandaixing de zhexue huayu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51.]这样,有机体思想中最具诱惑力的形而上学维度,才能转化为“整体论”的规范视野。虽然,两者的调和至少在特定领域也难以与基础主义相容。例如,一个典型的遗留问题是,在沿着黑格尔—马克思路径发展的批判理论中,审美经验最出色的一元论或基础主义解释,便无法兼容于认知及道德领域的规范转型。20关于此问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参见汪尧翀:《通向审美复位的新异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传统的观念论根源及其克服》,《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13—25页。[WANG Yaochong,“Tongxiang shenmei fuwei de xinyihua lilun:Falankefu xuepai meixue chuantong de guannianlun genyuan jiqi kefu” (A New Alienation Theory Leading to Aesthetic Restoration:Overcoming the Idealistic Roo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Aesthetic Tradition),Wenxue pinglun(Literary Review) 3 (2020):13—25.]换言之,现代性之复杂性问题(分化)与合法性问题(统一)是并置的,前者依托康德为现代性所拟定的分化视野,后者则源自现代性哲学话语内在的整体论要求。无论如何,基础主义确实可以算作黑格尔有机体思想解读的一个不良版本,而康德主义的规范立场更像是防止现代性自我确证落入其陷阱的一道保险。
实际上,作者在赋予“有机的现代性”作为现代性方案之证成的深刻意义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21参见黄金城:《有机的现代性》,第354页。[HUANG Jincheng,Youji de xiandaixing (Organic Modernity),354.]这启发我尝试超出作者的思路,提出如下问题:一旦有机体的现代性要求达到其客观上的自我理解,即拒绝让“精神”重返原初简单性的审美主义,而是要求把握“精神”本身的复杂性和统一性,那么,它将过渡为何种形态呢?这种过渡难道不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走出观念论模式的诉求吗?这种要求最精彩的版本已经呈现在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精神”概念的重构中:哈贝马斯把“精神”理解为主体自我确证的“媒介”而非“基底”,这样便能够从他者(即基于主体间性规范的社会互动主体)的视角来把握主体。一旦对“精神”进行去观念论的理解,消除基础主义及坚持分化论证就能够并行不悖。
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有机体思想所内蕴的整体论特征才能真正获得其自我理解。可以说,在他在中建立自身,这一黑格尔分享有机体思想而获得的天才直觉,经青年马克思决定性的去先验化,再经批判理论当代发展的范式转型,获得其之于现代性的规范意义。一言以蔽之,如同观念论自然哲学之为其时代“自由”的先验前史,“有机的现代性”一旦获得其自我理解,也将成为“交往的现代性”的先验前史。这意味着,观念论主体终将走出“有机体”贮藏星光的矿脉,进入语言批判的星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