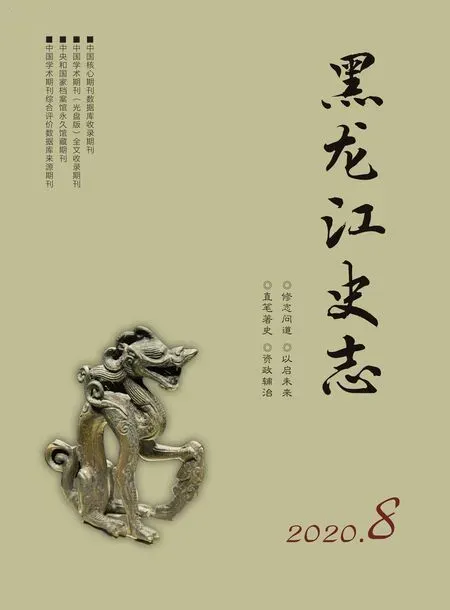“书”途同归
——近代北京第一座图书馆建成始末
2020-11-17王学斌
王学斌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这一从西方泊来、经由日本翻译后传入中国的现代化名词,是作为供人借阅、学习的场所而存在,它在近代西方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对中国而言,近代图书馆、图书管理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则处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激烈斗争的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传入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图书馆理念传入中国,一些开埠较早的城市已经有图书馆,但多为外国人开办,规模较小。真正意义上由中国政府创办的国家图书馆,是1912 年建成的京师图书馆。作为近代北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通过各种方式收藏了大量书籍,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休闲活动,起到了全国示范性作用,更是以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推动了近代北京城市公共基础建设的发展。
一、从藏书处到近代图书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蕴藏在浩瀚的典籍中,因此我国自上古以来便有保存文献的制度。在近代图书馆出现之前,中国历代政府与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官吏、士绅都喜欢藏书,他们将一些珍贵书籍的残本、孤本收集起来以供收藏和阅读。与西方国家的图书馆不同,中国古代的藏书处重于“藏”,官方的如元代秘书监,明代文渊阁,清代内廷四阁;民间如天一阁、海源阁等,都是重要的藏书所在地,但这些馆舍中的书却无法寓目,不仅宇内读书人,即使是朝廷的高官词臣,也不轻易得见,其意主要为保存而非利用。就名称而言,它们也并无通用名称,具体大致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没有名称。汉唐时期的官府和私人藏书处所,基本没有名称。二是有名称,但并不专用。如汉代的东观兰台、唐代的秘书省、集贤殿书院、宋代的“三馆六阁”、清代的武英殿等,虽然是藏书处,但并不是专有名称,因为藏书只是这些机构诸多功能的一部分。三是有专有名称,却并无通用名称。如“天一阁”“八千卷楼”“知不足斋”,以及“堂”“馆”“轩”“园”等。[1]就此而言,中国古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这一近代化机构的相关思想及形成,是经过西学东渐和鸦片战争后逐步传入中国的。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一批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来到中国,展示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物质文明,并初步介绍了一些图书馆思想,但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这些西方的制度和科技只是昙花一现。直到进入19 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再次东来,开始在南洋华人中传教和教授西学。马礼逊作为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新加坡、马六甲等地开办学校、出版书籍报刊,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在其所著《外国史略》中就曾多次提到西方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例如葡萄牙“书院积书册八万本”;荷兰国“国内大开书院,学士云集,讲术艺,小学馆二千八百余处,大书院四处,皆聚印翻译之书”;英国“其大学藏书六万本”。[2]这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对图书馆的最初介绍。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文明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关于近代图书馆的思想和建设也随之进入国人视野。传教士和外国殖民势力先后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建立了一些图书馆,如上海的工部局图书馆、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香港公众图书馆等。但是这些图书馆是非官方性质的,多数由外国人管理,且“专供传教会会士研究参考之用,后来有所发展,凡教会中人,或由教会中人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同意后,亦可入内阅览,但为数极少”。[3]除了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图书馆外,晚清有识之士对于这一近代化事业也产生浓厚兴趣,不断对其进行考察,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沉淀,最终在清末新政时得以付诸实践。
二、清末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革新之机”又渐渐“萌发于下”,许多有志之士对欧美和日本的书籍进行大量翻译,并考察其立国之法。1905 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更加刺激了清政府改革的决心,慈禧太后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开始了预备立宪运动。在此期间,清政府在国内广泛提倡西方的先进思想,模仿西方各项制度,西方图书馆观念作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由此得到进一步传播。
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于1901 年颁布上谕,通令各省设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清政府亦实行了新的教育制度,即《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这些章程中,提到了设立学校图书馆的细节。如《大学堂章程》“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节规定:“大学堂当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咨考证。”“教员管理员章”第二十节规定:“图书馆经理官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秉承于总监督。”[4]此外,学部还拟定了《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并将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辅佐和咨询机构。学务公所分为六课:总务课、专门课、实业课、会计课、图书课、普通课。其中图书课负责编译教科书、参考书,审查本省各学堂教科图籍,翻译本省往来公文书牍,集录讲义,经理印刷,并掌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5]清政府通过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分工,第一次明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图书馆管理架构,这既有利于图书馆的管理,又推动了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对政府提倡设立图书馆具有积极意义。
清政府在广泛开展各项改革的同时,于1906 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预备立宪过渡期。为实行预备立宪,学部于宣统元年(1909 年)上《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制定了各阶段的筹备事宜。其中预备立宪第二年的筹备事宜中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两项;第三年的筹备事宜则包括“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6]清政府意欲在预备立宪的前三年完成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的建设工作,并通过各项图书馆章程规范全国的图书馆管理。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关于图书馆“官制”的设立和在全国建立图书馆的计划,表明清政府对图书馆事业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积极姿态和意向,也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宣传西方图书管理理念、倡导设立新式图书馆的思想和活动已经从民间的自发行为上升到了国家的自觉行为。
与清末新政之前不同,预备立宪时期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总体来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其创办公共图书馆的主体不是开明绅士而是各地封疆大吏。正因为如此,一批地方官员纷纷奏设图书馆,如1906 年《湘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折》,1907 年《安徽巡抚冯煦奏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1909 年《山西巡抚宝芬奏山西省建设图书馆折》等。由于各地督抚的参与,在清末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创办图书馆的热潮,并形成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这场运动包括公共图书馆的创办、图书馆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图书馆观念的广泛传播等内容,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基础。
三、京师图书馆的筹建
随着全国掀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清政府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筹建京师图书馆,因为它具有国家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对全国其他图书馆事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也是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京师图书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作为京师图书馆创立的首倡者,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李端棻在1896 年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其中称:“……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自京师及自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看读。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7]李端棻是第一个向清政府呼吁建设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图书馆的官员。此后,罗振玉在李端棻建议的基础上,于1906 年再次向中央政府上奏,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划:“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默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兹将京师拟设图书馆之办法条陈如下:一曰择地建筑也。二曰请赐书以立其基业也。三曰开民间献书之路也。四曰征取各省志书及固金刻石也。五置写官。六采访外国图书。”[8]
经过李端棻和罗振玉的先后奏疏,清政府关于建设京师图书馆的思想日趋成熟,并逐渐开始施行。“闻政府会同荣中堂提议设立京师大图书馆,仿英伦藏书楼规模,调取各省书籍,分类库藏,以备浏览。并拟附设西书室专藏欧美各国有用新书。现已电咨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饬其速为搜罗齐送,以备库设。庶于政学商工各界,均有裨益。”[9]1909年,学部拟定了《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其中称“本年应行筹备者,有在京师开设图书馆一条奏蒙。即时修建馆社,搜求图书,俾承学之士得以观览,惟是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祥,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10]鉴于当时主持学部事务的张之洞因病无法处理各项事务,“学部虑公(张之洞)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同年八月初五日学部“奉旨依议”,并“派编修缪荃孙充监督,学部郎中杨熊祥充提调”[11],京师图书馆遂正式投入建设。京师图书馆设立后,广泛从国内外搜罗各类书籍,一些散落在民间和国外的珍贵书籍陆续被收入其中。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函送影本《永乐大典》一册到部,计卷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五和一万九千七百八十六共二卷合行发给该馆,妥为库藏。”[12]经过3 年的建设,1912 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当时馆内有藏书5424 部,151375 卷,52326 册,是当时国内较为完备的图书馆。
图书馆建成后,引起了社会的重大反响。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都争相参观借阅。一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参观京师图书馆之后,作文感叹道:“窃惟奎璧光辉,天上辟图书之府;瑯环清秘,仙人重福地之藏,通巴陵地道。龙威之宝籍森罗,登宛委峰颠;轩帝之玉书昞晬,洎乎周史,则典藏室。汉京亦有兰台制,既宏焉,来亦旧矣。顾览鲁史之策书,仅传宣子;阅东观之经籍,惟闻黄童,亦有秘藏,固不与民共也。民国肇造,百体更新,用收清室内府之藏,大开汉代献书之路,遐征尔集,以成兹馆,岁椎轮于大辂,己冠冕于上京。其善本书室,书或脱简,卷或残帙,然羽陵坠简,总属奇珍,大酉遗篇,不嫌断壁。四库书室,清代内府旧藏也,插签分部,序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胪函,色别乎赤青白黑,天禄石渠。汲冢鲁壁,三坟八索之奇,七略九流之异,与夫宋元之桑椠,齐梁之写经,靡不缥缃充栋,絭帙盈厨。虎观儒生,手钞冗便;鸿都多士,口诵皆欢,亦足扬上国之光,壮斯文之气矣。”[13]
京师图书馆建成后,清政府已经灭亡,遂移交北京政府接管。由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战争不断,经济凋敝,导致京师图书馆的发展面临许多困境。第一,馆舍无定所。京师图书馆从落成初始馆舍便不断变迁,由广化寺到南社旧址再到北海官房,一直没有固定基址。第二,经费短缺。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将大部分款项都用于军备和战争,对教育部门的经费屡次积欠,京师图书馆职员的薪资也无法按时发放,办公及房屋修缮等公共费用更是经常赊欠,这些都使得图书馆馆务难以维系,无法扩充和完善。第三,馆长更替频繁。京师图书馆从成立伊始馆长便不断更换,从1912 年到1927 年几乎达到每隔一到两年馆长即更替一次,先后任职的有江翰、夏曾佑、袁熙涛、傅岳棻、王章祜、马邻翼、陈垣、全绍清、马叙伦、张国淦、吕复、陈任中、梁启超、郭宗熙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和饱学之士,但许多人都是由教育部次长兼任,专职者较少,对图书馆的工作很难全力以赴,从而限制了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京师图书馆还违背西方公共图书馆免费阅览的科学主义精神,实行收费,同时其中官僚习气严重,“入 门 则 隶 役 慢 客 ,入 室 则 官 气 犹 浓 ”。[14]
四、结语
虽然京师图书馆建成初期面临诸多困境,但在不断改组的情况下,仍旧缓慢发展。民国成立后,1925 年“教育部于十月一日提出阁议,将京师图书馆改组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应领经费四千元,由财政部直接拨付,于十二日起移交”,[15]并聘任梁启超为馆长。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将其与北海图书馆合组,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纵观京师图书馆的曲折发展历程,它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变迁,还见证了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强大生命力: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设图书馆,到国人吸收和宣传先进的公共图书馆思想,并由政府倡议,最终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了各级图书馆。同时,作为国家公共图书馆,它还承担了文化传播和民众知识启蒙的功能,并从客观上打破了阶级限制和身份差异,使男女老少都可以入馆借阅。京师图书馆的设立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近代北京城市的公共资源建设,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1]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马礼逊.外国史略.(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Z].上海:上海著易堂印行,1897.
[3]葛伯熙.徐家汇藏书楼简史[J].图书馆杂志.1982,(2).
[4]张百熙等纂.奏定学堂章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5]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学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李侍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N].时务报.1896,(6).
[8]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J].教育世界.1906,(130).
[9]时闻:议设京师大图书馆[J].直隶教育杂志.1908,(20).
[10]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N].学部官报.1909,(100).
[11]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G].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训令:第四百五十三号(八年十月十五日)令京师图书馆:发交美国影本永乐大典一册仰京师图书馆查收[N].教育公报.1919 第6 卷,(12).
[13]参观京师图书馆及国子监记[J].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1).
[14]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8)[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15]京师图书馆之改组[N].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6 第2 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