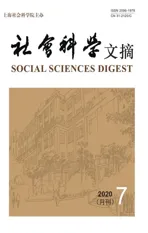空间、结构与网络:社区情感治理的三重论域与实践路径
2020-11-17
从情感到情感治理:社区治理的情感转向
长期以来,作为与理性主义相对的情感研究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议题。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幸福、德性、友爱”,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及的“同情、美德、激情”,有关情感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现在已经扩展到治理领域。
情感治理的内涵与价值是学者们首先关注的议题。Thomas Dixon认为情感更加侧重那些身体性的、非认知的及无意识的感受,是对欲望、激情、感情和情操的综合感知,既与个人体验或人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情感、集体行动密切相关,有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预期性情感之分,是行动主体对于客观实际的主观性反应。治理场域下的情感治理需要对情感生产过程的不同主体间关系干预协调,达到柔化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一方面是实现“善治”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也是推进社区情感治理的重要手段及目标,并以此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情感治理理念,如“情感提升”“情感体制”“缘情治理”。也有学者对情感治理的共同体特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共同体的实质是共同情感,重建共同情感需要让人体验到归属感与意义感,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培养对社会群体依恋与忠诚,要关注情绪氛围,用“情结”链接不同主体,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家”的温情,让情感作为联结社区多元主体的“黏合剂”。有些学者将情感治理扩展到了社会层面,认为需要从社会心态、群体心理及个体情绪方面开展情感治理研究,在新媒体的作用下情感治理与社会心态都发生着变化,需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把握情感治理的对象。其实,对情感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是沿袭了情感的共同体属性,如涂尔干认为集体情感是社会分工的情感纽带,具有社会性价值,明确指出“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而滕尼斯则更加注重群体基础形成的“共同体”情感;路德维克·弗雷克的“思想集体”也具有此种倾向,认为情感可以通过象征性与集体形式蔓延传播,共同情感是基础。
目前,作为本土化实践的情感治理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现有研究更加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在国家与社会场域下对情感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价值、正当性做出了充分讨论,缺少情感治理的微观性视角。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服务社区化的倾向下,社会治理的重点场域现已下移到社区,社区的治理逻辑也不同国家及社会,如何在社区场域中充分发挥情感治理的内在优势,实现治理方式本土化创新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与民众美好生活需求满足的有效性,仍然需要本土化的不断探索。
空间、结构与网络:社区情感治理的新面向
情感治理的目标指向是对相关主体公共意识与集体认同感的再造,而这种再造是对于社区空间价值层级的反应,需要通过情感性营造赋予社区空间独特性与包容性价值,打造赋有情感的公共空间、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增强社区的可读性。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一种搭配与安排。社区结构的自我定义也需要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探索与分析。社区治理的实践对象是不同的主体,无论是民政部倡导的“新型社区管理体系”还是学者对城市社区“一核多元”治理结构的论证,都是对治理主体的重视。这恰好也是社区情感治理重点关注的对象,情感治理的实质就是不同主体间利益协调的过程。因此,社区情感治理的结构也需要回归到主体意识层面。
社区治理是不同的社区参与主体间权利配置与主体关系重构的过程,最终指向于主体间协同共治与社区发展,而网络关系的再造就成为社区治理重要议题,这也是情感治理的目标指向。一方面,基层政府从其政治属性出发,通过情感性投入塑造社区相关主体对其合法性的认可,让相关主体接纳并拥护政府决策,达到管控目的,社区主体是政府行政网络的重要组成主体;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从自身的社会属性出发,通过情感性投入缩小政府服务供给与社区主体服务需求间的张力,动员行政力量以外的社会资源,以居民自治与区域共治的形式,实现民众需求的满足与社区发展,达到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致力于公共服务供给的目的。前者属于纵向性的情感网络塑造,后者是横向情感网络的链接,社区居民都是重要的网络动员对象与情感治理主体。
社区情感治理的实践化路径
社区情感治理是通过情感再生产实现主体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过程,空间、结构与网络是情感治理的基本维度,需要从“对物有感情”“对人有感情”“对事有感情”三个层次进行推进,这既是情感治理的基本内容,也是情感治理的行动方向。
(一)社区情感治理的空间层面
1.促进社区情感空间多面向塑造,明确各自蕴含的情感功能
社区空间具有多维价值,不同的空间布局承接着不同的空间功能。社区情感空间的塑造需要从公共空间、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层面进行。现有的社区空间具有很大的排他性,以此形成“封闭社区”,不利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自由流动,仍然需要通过新建、改建的方式加强公共空间的塑造,为社区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休闲活动提供空间支持,满足居民对日益增长的休闲、交往需求。作为环境中的人,社区居民需要与环境进行交流,小区绿化、小区景观所承载的社会性价值与情感寄托已经成为增加居民与自然环境相处的重要方式。文化空间的塑造则是体现社会性的基础,社区居民通过对空间文化的感知,可以将空间的物理性价值上升到情感性认知层面,它是情感治理的柔性空间,存在于社区治理的每个方面。
2.打造多样化的“社区意向”标识,不断提升社区的可读性层次
社区意象就是对特定社区空间的记忆与情感元素,缺少对社区空间的记忆与情感元素很难形成稳定的社区认同。而这种空间记忆一直都是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重要情感标识,这种标识既可以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小区花园,也可以是小区道路,这些社区意象与主体的行为、感情交融在一起。在社区的情感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地增强社区意象的可读性,培养社区意象元素的独特性并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社区意象的可读性是一个社区情感基调,这种情感既可以蕴含在社区空间结构中,也可以体现在时间脉络中,同时也反映在居民的日常交往过程中,这即是社区治理主体与空间的情感结合。
3.打造“家”的空间认同、情感归属,推进以“德”治理发展
情感治理与“家”秩序的空间重构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在情感治理中,“家”的隐喻在于对共同体复兴提供了具有稳定性与忠诚性的情感支撑,是社区情感再生产与公民精神的回归,不仅需要在社区中积极塑造“家”的空间认同,而且也要有“家”的情感归属。就前者而言,需要在明确社区标识,增强社区可读性的基础上优化社区空间布局,融入儿童友好社区与老年友好社区服务理念。就后者而言,以服务为导向,加强社区服务个性化与品牌化塑造,坚持分类服务,及时回应不同类型的居民需求。需要结合社区治理,加强德治工作的社区化实践,既要挖掘传统文化中德治发展观,也应立足现代社会,融入治理理念,提升德治的情感性层次。
(二)社区情感治理的结构层面
社区情感治理的主体结构是集个体、群体与组织于一体的,这种主体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主体间性,致力于培养社区主体“对人有感情”,需要多重实践措施的多向推进,以把握主体间的情感脉落。
1.通过多重性方式,准确把握个体-群体-组织的情绪信号
为提升情感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需要在把握个体、群体与组织需求的基础上精准把握主体间的情绪信号。与其他主体相比,居委会在把握多主体需求中具有积极作用,可以通过社区服务、上门走访加强与居民联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个体性问题演化为群体性问题,从而引发社区居民不满,重点做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与情感安抚工作。优化公众导向的意见反馈机制,提升投诉上访工作效度,确保意见投放—意见流通—意见处理—意见反馈机制的畅通有序,及时消解个体、群体与组织“怨气”。
2.搭建社区协同治理平台,及时消弭社区消极情绪
要达到解决社区主体利益分化的问题,促进社区的再组织化就需要搭建社区协同治理的服务平台,为更多的个体、群体与组织寻找共识价值的服务平台。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建在“条”“块”资源整合中的积极效度,通过党建服务平台的建立,促进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及时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展社区共治服务平台,通过情感式的关系认知与接纳,促进公共情感意识的形成。需要在吸纳社区居民、群众团体与组织的基础上重点吸纳物业、业主委员会以及社区驻区单位的入场,促进社区事务的协同解决与主体资源的整合投入,塑造区域共同体与区域归属感。注重社区枢纽型组织的功能发挥与互补,促进社区组织联合会、社区基金会、社区组织的联合发展,壮大社会力量介入情感治理的行动系统。
3.发挥社区精英作用,促进个体、群体与组织融合
情感治理的最终指向在于实现主体关系的再造,需要找到促进个体、群体与组织结构不断优化与整合的关键力量。实践中要从加强社区精英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开始,通过主动向社区精英介绍近期社区活动、服务安排、发展需求的方式,将社区精英的情感需求与社区发展的情感塑造结合起来,培养社区参与的共同体意识与公共精神。发挥社区精英熟悉社区、主体资源多的优势,扩大社区居民间的联系,适时成立群众团体与社区组织,实现居民的再组织化。以社区精英为行动领袖,积极创建社区共治服务平台,围绕着社区发展,加强与物业、业主委员会、驻区单位间的联系,实现社区共治。
(三)社区情感治理的网络层面
社区情感治理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纵向的情感注入与横向的情感认同构成了网络的两个基本面向,需要围绕着如何增强社区主体对政府的情感认同与如何搭建社区服务网络的价值命题,立足于社区主体培养“对事有感情”。
1.扩大居民参政议政范围,柔化政府与民众组织边界
从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居民很少直接参与到政府决策,政府决策悬浮于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府与基层民众的心理距离,彼此间的情感链接较弱,容易弱化纵向情感网络对社区居民的吸纳度。为扩大社区情感治理的纵向深度与有效性,需要在后续的治理过程中不断扩大居民参政议政的范围与力度,规范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在选择居民代表时既要考虑到居民代表年龄、性别的差异性,也要将职业类型、社区活跃度、社区影响力纳入到居民资格的选择中。政府部门要积极地回应各居民代表的需求与意见,可以通过“一代表一回馈”的方式培养居民参政议政的个人荣誉感与组织归属感。在社区自治、社区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居民工作评议,增强政府与居民互动的深度与频次,柔化政府与民众的组织边界。
2.发挥社区文化融合积极性,提升主体的情感认同
情感治理是通过社会支持与主体互动实现,需要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塑造社区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就传统层面而言,一方面要考虑到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道德传统、风俗习俗,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社区共同体探寻属于社区特有的文化标识、人文事迹、历史变革,唤起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记忆与集体认知。在现代层面,需要将社区文化与国家治理、城市精神、社会倡导、社区发展相结合,因时制宜地塑造区域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现代文化,提升社区主体对国家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实现文化传递的社区化,促进政治网络与社会网络的相互链接,彼此互融。
3.将政府“大叙事”与社区“小叙事”结合,实现情感在地化
社区情感治理是政治网络与社会网络的双向结合。在科层制的政治网络下,社区居民更多是治理的对象,以普遍性准则与共同目标实现社会秩序再调整与社会认知的统一,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行动路径,是“大叙事”的执行逻辑。但社区情感治理的场域在社区,对象在社区,需要有基层性、偶然性、非标准化的发展与情感投入,是局部性的、小部分的、非统一性的“小叙事”的典范。情感治理更多是需要“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实现情感的在地化运作,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基层服务体系建建立、拓展真情沟通渠道,深入基层社区把握居民服务需求与社区发展的痛点、难点,促进政府话语与居民话语的情感融合,而且需要进行权力下放,给政府与群体、组织及个体的社区融合创造条件,营造共建、共治、共享行动氛围,争取基层居民支持,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社区情感治理: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再造
社区情感治理是对社区主体关系的重塑与社区秩序的再调整,最终指向打造“有温度”的社区,对于“有温度”的社区何以可为的理解,本文认为空间、结构与网络是社区情感治理的基本论域,也是“有温度”的社区得以可为的三个层面。其中,空间是社区情感治理的重要载体,需要致力于培养社区主体“对物有感情”;结构则是社区情感治理的主体框架,最终走向社区主体“对人有感情”;网络则是社区情感治理的链接机制,可以达到社区主体“对事有感情”的目的。
情感治理是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治理体系强调制度、技术优先性不同,情感治理更加注重对情感的管理、共同体意识的培养、集体道德的发挥以及非正式控制的积极作用,通过情感性链接协调主体间关系,将松散的社区主体发展成为联系紧密的组织,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是对社区治理方式的再造。可以说,基层情感认同所具有的合法性价值是可以超出法律规范带来的合法性,基层民众对于国家政府认同更多地依赖于情感与价值。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情感价值的形成与链接,在社区治理中可以柔化政府、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及其他主体的边界,易于情感能量的汇集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再结合特定的社区事务可以推进社区自治与共治服务工作的开展。社区情感治理将居民主体性价值、主体间关系重构与德治视域下情感再生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治理重心下移至社区后的理念转化,是一种基于非正式制度之上的治理创新,与正式制度相互融合,可以提升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实效价值。
现代社区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社区治理的现实价值是基层治理的重点。社区情感治理倡导的情感主义与制度、技术所蕴含的理性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互补性,将社区情感治理纳入到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中,对于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心态、把握现代性与国家治理何以在地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