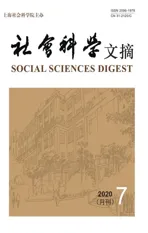财产与上层建筑要素的辩证关系: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洞察及其思想史意义
2020-11-17
恩格斯不是在晚期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才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他在写于1844年2—3月的《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一文中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他在这一文本中不仅把解读视域拓展到了财产关系与国家、法等上层建筑因素的辩证关系的层面,而且还从英国宪法制度这一具体的、历史的语境入手,清晰地阐述了这种辩证关系是如何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同时,他不仅揭示了英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矛盾性,而且还敏锐地抓住了英国人宁愿相信宪法的谎言也不愿正视现实法治实践的不道德性这一现象,这为他(与马克思一起)后来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等问题上得出科学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英国宪法制度的财产关系基础
准确地说,《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不是一篇孤立的论文,而是紧接着《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而来的。在后者的结尾部分,恩格斯已经谈到了财产的统治与国家形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的整体思想水平来看,他所讲的财产的统治已经是基于财产关系的现代私有制的统治了。因此,当他说财产的统治必然反对国家、瓦解国家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现代私有制社会必然反对旧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样一来,在理论层面上指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财产关系的工作应该说已经完成了。
当然,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致力于从当时英国的具体语境入手,去剖析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到底是如何具体地决定国家、法等上层建筑因素的性质的。对他来说,现实实践中发生的情况远比理论层面上阐述的观点要复杂得多,况且就当时来说,作为欧洲最发达国家的英国在恩格斯看来也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以,为了弄清经济关系对政治国家起决定作用的具体机制,以便把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理解从一般的定性分析层面推进到具体的历史性剖析的层面上,青年恩格斯把解读的重点深入到了英国的政治及法治等领域。
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一文,我们对这一文本的解读思路就会更清楚一些。在文章的一开头,恩格斯首先对英国在财富增长、政治自由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描述。而他自己所要做的,正是通过对具体的英国史尤其是立宪君主制的发展史的研究,来揭示英国政治史的财产关系基础,从而对英国的政治及法治状况作出科学的解读(至于英国的财富状况,他已经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中作出了批判性的解读)。
恩格斯指出,英国宪法制度(立宪君主制)被一些托利党人称为英国理性的最完善的产物,这种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对这种宪法制度的非历史性解读之基础上的,它假设性地把英国立宪君主制在1844年的状况理解成对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的立宪君主制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不仅无视了英国宪法制度在1844年的糟糕状况,而且更是错失了通过解读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发展过程而看出其背后的财产关系基础的机会。在恩格斯看来,这两者的不同不应该被理解为后者对前者所建立的理性的宪法制度的倒退,因为即使是1688年的立宪君主制度也根本不是建立在所谓的理性基础之上的,而无非是当时英国各派力量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内在矛盾在英国宪法制度建立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着了。而这一制度往后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过程。恩格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解读英国立宪君主制度的发展过程的。他清晰地看到了近五十年来老托利党人的渐渐消逝以及新托利党人的政治实践原则的转变,他们居然采用辉格党人的那些政治原则了。而辉格党当然也在经历着重要的变化。总之,1844年的英国宪法制度所呈现的是把1688年该制度中已存在的内在矛盾激化到了顶点状态后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英国财产关系的复杂性与宪法制度的吊诡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导致了上述这种矛盾的激化与发展呢?恩格斯说,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如果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那么,在立宪君主制下特别是英国君主制下,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尽管恩格斯在紧接着这段话的后面的确提到了纯粹的君主制、纯粹的贵族制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会引起恐怖,但此处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切不可把恩格斯所说的“恐惧”理解为对上述三种恐怖制度的恐惧,他此处的解读重点也并非在于对国王、贵族等统治阶级的批判。恩格斯讲的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而不是对某种他物的恐惧。他之所以要把国家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对自身的恐惧,那是因为在他看来,现阶段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达到以回到人自身为本质特征的自由的自主联合阶段。由此,不管是处在基于财产统治的现代私有制阶段的国家,还是仍然处在基于抽象主体性原则的封建专制阶段的国家,其中的人们都由于没有回到人自身而无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他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对此已有论述),因而对自身还处在一种恐惧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此处所讲的恐惧,其实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对恩格斯来说,被托利党人视为英国理性之最完善的产物的英国宪法制度即立宪君主制,只不过是人们在尚未明白国家之本质的前提下,把君主制、贵族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这三种各自都会引起恐怖的制度形式拼盘在一起的产物。难怪他会说这种立宪君主制代表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达到了最高程度。
那么,这种最高程度的恐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恩格斯看来,它体现在英国立宪君主制的三个要素之上。首先是君主这个要素。按照英国宪法制度,国王在理论上应该拥有三分之一的立法权,可实际上国王的权力已经等于零。但此处真正吊诡的是英国宪法缺了君主制还不行。在恩格斯看来,在这件极其吊诡的事情上面,我们能看到的是英国人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他们一方面不想给国王以任何的权力,可另一方面又维持着对这个无支配权的国王的膜拜。其次是贵族要素。恩格斯指出,人对自身的恐惧这种状况在英国贵族即上院议员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实际上,上院议员的活动已降低为纯粹的、无意义的形式,只是偶尔上升为某种惰性的力量”,可另一方面,就像国王所受到的待遇一样,上院的这些贵族议员正是因为他们的软弱无力,反而得到了各党派的维护。最后是下院的情况。恩格斯指出,在这个把全部权力集中于自身的下院中,照理说应该有纯粹的民主制,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1688革命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中,普遍存在于英国城市、乡镇及农村选区中的是封建特权的影响以及各种各样无耻透顶的贿选。即使是在英国的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情况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在一些大城市中,统治权才真正落到中间阶级手中。按照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下院应该是由中间阶级所控制的,但实际情况是除了在一些大城市外,下院的权力总体上还是受到土地占有者等封建特权阶级的控制。
恩格斯指出,这种最高程度的恐惧除了在立宪君主制的三要素上体现出来之外,还体现在英国宪法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权力上,如立法时的议事规程、议会的特权、国教会的权力以及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的权力、结社的权力、人身保护的权利等一系列公民权利上面。既然这种恐惧如此普遍地存在着,那么,它到底是由什么所导致的呢?在恩格斯看来,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财产的统治。“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是财产在进行统治。财产使贵族能支配农业地区和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工厂主能决定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贿赂来加强自己的影响。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明确承认了。”我以为,恩格斯此处是在表达这样的意思:虽然从理论上说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度是在超越了基于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之后才出现的社会形态,但就英国的具体实践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这里,贵族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依然在现有的财产关系中拥有地位从而获得了支配的权力。这就说明英国的财产关系只是某种混合体,它并不是单纯地建立在资本家阶级的统治之基础上的,而是夹杂着贵族、中间阶级等各种势力的作用,尽管从总体上说中间阶级的势力显得最强大。应该看到,恩格斯通过对这种具体的财产关系之内涵的分析,切实地推进了对国家、法等上层建筑因素与所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上述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国家、法等政治要素与生产方式等经济要素之关系的论述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这一文本中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决定作用的相关论述,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最后部分还有一小节即“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里不仅有对现代私有制决定现代国家等观点的再次阐述,而且还有在具体实践层面对上述观点的更为细致的剖析,譬如,指出了在有些国家中由于还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因而在国家层面上仍然不能算是现代国家的完善的例子。应该说,此处所讲的观点跟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中所说的由于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因而导致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吊诡性的观点很相似。我以为,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创作这部分观点时,可能是由恩格斯提供了初始的观点,然后再由他们两人共同讨论和决定的。因为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并没有把解读的重点放在对某种具体的市民社会的剖析之上,而是主要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必然被超越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迈进等观点的阐述上。正因为如此,我才作出上述推断。
上层建筑要素的虚假独立性
由于恩格斯侧重于从具体社会形态的层面上来推进对财产关系及宪法制度的复杂性的认识,所以,他在《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中还触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层面,即宪法等上层建筑要素的独立性是虚假的、关于这种虚假独立性的认识及相关舆论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等观点。从对英国宪法制度的批判性解读中,恩格斯发现其理论与实践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英国宪法实际上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全部漫长的立法过程纯粹是一场滑稽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以致这种矛盾已经不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比这种滑稽现象更加吊诡的是,英国人偏偏不承认这种客观现实,而且还更乐意相信自己真的生活在立宪君主制这种宪法制度中。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宪法制度之虚假独立性及其欺骗性的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尽管英国宪法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是由英国议会在1689年所通过并由国王加以承认和宣布的“权利法案”来奠定基础的,但如果真以为立宪君主制这种英国宪法制度体现的是国王和议会成员的主观意志,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在立宪君主制建构之初它所体现的就是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利益斗争的结果,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财产统治的力量。英国立宪君主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什么主观意志或法律精神,而是财产关系的统治或者说是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关系的统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英国人还不能看出这一点,“因为人民还没有弄清楚财产的本质,因为人民一般说来——至少在农业地区是这样——在精神上还是麻木的,所以能容忍财产的专制统治”。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会对立宪君主制这种空洞的宪法概念抱有极大的热忱,尽管它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抽象的名称而已。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随着财产关系的不断发展,英国宪法制度的空洞的名称必然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作为其本质的财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会不时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当这种财产关系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越来越成为人们走向“社会的民主制”过程中的障碍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英国宪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择的,不是直面和承认实际存在的事实,而是用更多的谎言来弥补和掩盖前面的谎言。恩格斯此处所讲的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在基于财产统治的私有制形态中的社会功能问题。应该说,在1844年2—3月间,恩格斯能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推进到这样的理论深度是很不容易的,他实际上通过对英国宪法制度之具体内涵的分析,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当然,与《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相比,他们在此文本中的阐述要更加详细:“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他们把这种现象界定为本末倒置,并对“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我以为,上述两个文本在对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的解读上具有相似的思路。如果我们再把恩格斯后期的一些理论思考也联系起来,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晚期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经典阐述,也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他在上述文本中已经打下的重要思想基础。
令人颇为遗憾的是,恩格斯的这个如此重要的文本在当代国外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他们往往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直接跳跃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而只看到恩格斯在前者中对私有制之不道德性的批判以及在后者中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实证性研究。这一结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恩格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界定与评价。我们知道,特雷尔·卡弗教授是国外学界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著名学者,事实上,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也没能很好地规避这一缺陷。在有些国外学者的解读视域中,恩格斯作为对经验现实的中立的实证研究者的形象,似乎是跟他在哲学能力上的先天缺陷相关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关注到青年恩格斯的《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等文本的话,他们就应该不会这样想了,因为这一文本不仅在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切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