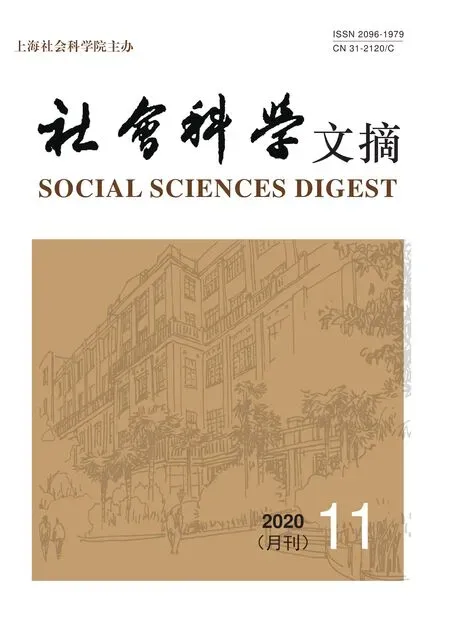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
——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
2020-11-17
随着美德伦理学在西方世界的复兴,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看儒家哲学的中英文著作、文章和学位论文也汗牛充栋,很多人认为儒家伦理学就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但还有一些学者,如李明辉、安乐哲、萧阳等,却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这几位都是非常严肃的学者,也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因此我愿意在此就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他们商榷,以期得到他们的指点。
李明辉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
台湾学者李明辉一直认为儒家伦理学跟康德主义更接近,所以他反对用美德伦理学来解释儒家伦理学。
李明辉反对将儒家伦理学看成是美德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认为,“‘义务论伦理学’与‘目的论伦理学’之划分既是以二分法为依据,两者便是‘既穷尽又排斥’的关系”。根据这样一种两分法,美德伦理学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系统存在的空间。因此一个具体的伦理学形态,包括儒家伦理学,要么是目的论,要么是义务论。所谓的美德伦理学,只可能作为这两种伦理学类型的次级类型。也就是说,只有目的论的美德论(在这里美德从属于目的)或者义务论的美德论(在这里美德从属于义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李明辉之所以说义务论和目的论是对伦理学既穷尽而又相互排斥的分类,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行为或行为规则之所以有道德意义,其最后判准”要么“在于其产生的非道德价值”(目的论),要么“在于其自身的特性或行为者的动机”(义务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伦理学都是想确定一个行为或行为规则的道德价值,即其对错。但美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一个行为或者行为规则的对错,而是一个人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伦理学分成两类:一类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行为的对错,一类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的好坏或者具有美德还是具有恶德。根据这样的分类,义务论伦理学和目的论伦理学都属于前者,而美德伦理学则属于后者。
对我上述的划分的一个可能反应是:一方面,作为一种伦理学,美德伦理学怎么能不关心行动呢?另一方面,义务论和目的论不是只关心行动,而且也关心作为行为者的人!关于第一方面,我的回答是,美德伦理学不仅讨论人,也讨论人的行动,不仅讨论人的品质,也讨论道德原则或者行动后果,但后者都可以从前者推导出来并可还原为前者。例如行动的对错是由从事这个行动的人的品质的好坏决定的(对的行动就是具有美德的人在有关的情形下典型地从事的行动),道德原则是从人的美德(由此推出肯定的原则,如应该做勇敢的事)和恶德(由此推出否定的原则,如不要做鲁莽的事)推出来的。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第二方面,因为这也正是李明辉所强调的。由于他是个义务论者,他主要关心的是义务论伦理学与美德论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他也注意到人们通常在这两者之间作这样的区分:“(1)‘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义务’(duty),‘德行伦理学’强调‘德行’;(2)前者强调‘原则’(principle)或‘规则’(rule),后者强调‘性格’(character);(3)前者强调‘行为’(action),后者强调‘行为者’(agent)。”但他否认这样的区分,说义务论伦理学不仅关心义务,也关心美德;不仅关心原则,也关心性格;不仅关心行为,也关心行为者。
我们要确定一个伦理学属于哪一类型,要看在这个伦理学中哪个概念具有首要性。就好像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有美德概念,也可以有义务概念和行动后果概念一样,义务论也不仅有义务或道德原则概念,也可以有美德和后果或者目的概念。前者之所以是美德伦理学是因为美德是其首要概念,而所有其他概念都是从这个概念推导出来或者从属于这个概念;后者之所以是义务论是因为义务是其首要概念,而所有其他概念都是从义务概念推导出来或者从属于这个概念。
由于他根本否认美德伦理学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形态而存在,李明辉对于那些认为儒家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的学者的回应也基本上就是说,这些人用美德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的策略只会治丝益棼”。我所关心的是李明辉自己有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在这一点上,他似乎采取的是排除法论证。由于在他看来,先秦儒家的伦理学是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因此它就不可能是美德伦理学,至少不可能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美德伦理学。我们知道李明辉在别的地方作过很多讨论,认为儒家伦理学是康德式的义务论,如果我们采取他的排除法论证了儒家是美德伦理学,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说它不可能是义务论的伦理学。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李明辉用来证明儒家伦理学是义务论因而不是美德论的论证。这个论证根据的是《孟子·梁惠王上》首章中所谓的“义利之辨”。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仁义,而不是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认为,孟子不是一个后果论者或功利主义者,但他是如李明辉所说的是一个义务论者,还是如我所认为的是一个美德论者,则至少并不明确。关键是要确定孟子在这里说的仁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仁义的首要意义是指我们作为立法者在排除了所有经验的因素以后靠纯粹的理性而确立起来的、规范人的行动的义务或者道德原则,那么孟子大概是个义务论者,而如果仁义的首要意义与人性有关,是人生来具有的使人之为人的内在特质和品性,则孟子更像一个美德论者。
在《告子上》首章孟子与告子的对话中,告子为了表示孟子观点的荒谬性,将孟子的观点表述为以人性为仁义,而对此,为了证明仁义为人性,孟子回应说,如果不以仁义为人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荒谬情形:要使人有仁义,就必须毁坏人性。在《尽心上》第十八章,孟子又说仁义作为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当然,说仁义是人性,不只是说他们是人生来就有的东西,而且意味着他们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孟子在《离娄下》第十九章不仅说明了有无仁义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而且说明庶民与君子的分界线就在于前者去之,而后者存之。因此,当一个人没有了仁义,孟子不会说这个人的行动违背了道德原则、这个人违背了其义务,而是说这个人有了缺陷,甚至不再是人了。当然,仁义作为人性的道德品质,虽然本身不是行动,但有在恰当情况下发出行动的自然倾向。因此在《离娄上》第二十七章,孟子不仅说明了仁义作为内在之人性、之美德会外发为行,而且说明了发自仁义这样的美德的行动是自然的、自发的、愉悦的行动。在《离娄下》第十九章中,这样的行被称为“由仁义行”,并与“行仁义”相区别。孟子在这里称赞的“由仁义行”是对具有美德的人的行动的非常恰当的描述。
在孟子那里仁义(礼智)是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人性概念对于美德伦理学如此重要。我们说美德伦理学主要关心的是人的好坏问题。但好坏是个规范性概念,那么这种规范性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一个人之好坏呢?大多数美德伦理学家都诉诸人性概念。因为人性就是使人之为人者,因此一个好的人就是将人之为人的特征较好地体现出来的人,而一个坏的人则是没有将这些特征很好体现出来的人,因而是与别的存在物特别是动物没有(太大)差别的人。
安乐哲和罗思文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
安乐哲和罗思文也曾撰文反对将儒家伦理学看作是美德伦理学。如大家知道,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早期儒家伦理学可以更好地看作是角色伦理学而不是美德伦理学或者任何别的西方伦理学类型。我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理由,而不是去考察角色伦理学是不是对儒家伦理学的恰当刻画。
虽然他们也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康德主义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能更好地刻画儒家的道德生活观,但还是反对将其看作是美德伦理学。他们对此有一个一般的理由,它也可以用来反对将儒家伦理学看成是康德主义或者后果主义或者任何别的西方伦理学。这个一般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某种伦理学的历史形态作为标准来衡量儒家伦理学,我们总会觉得儒家伦理学较之用作样板的西方理论有些缺陷,而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阅读儒学经典呢?这个看法我也非常同情,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问的是,(例如)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比起来谁更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避免安乐哲所说的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当我们说儒家是美德伦理学时,我们不是以美德伦理学在西方的某个历史形态为尺度,用它来量度儒家;相反,我们应该用美德伦理学的理想形态为尺度,用它来量度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美德伦理学的历史形态。
安乐哲和罗思文反对将儒家伦理学看成是美德伦理学还有一些具体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美德伦理学讲的具有美德的人太抽象,至少较之作为家庭成员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的角色更抽象。当然他们也承认,这里只是抽象的程度的问题。我们以他们文中反复使用的母亲这个角色为例。既然我们可以使用如母亲这样的已经高度抽象的概念,那我们用再高一度抽象的人这个概念就一定有问题吗?这里我们不会出现相反的问题,即既然我们可以用人这样的高度抽象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动物、有生命物、物这样更高度抽象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伦理学,而伦理学关心的是人应该是什么和做什么,而不是动物、植物和所有物应该是什么和做什么,因此抽象到人的概念,对于伦理学来说,是不高不低、恰如其分的抽象程度。
要知道一个好的人的品质,即美德,我们就需要了解什么是人,或者说什么是人性,即把人与别的存在物区分开来的独特性。这就涉及了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美德伦理学不能用来刻画儒家伦理学的第二个理由:美德伦理学把固定的、最后的东西(人性或者人的美德)放在经验之前,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在经验中实现的东西;它倾向于“对什么是人的存在(human being)提供一种回顾性的因果的或者目的论的说明,而不是对如何变成人(becoming human),即对人的变成(human becoming)作出总体性的、前瞻性的和脉络化的说明”。作为回应,我们可以作两点说明。首先,说“变成人”或者“人的变成”实际上已经事先假定了人的概念,因为很显然变成人(becoming human)、人的变成(human becoming)不同于变成狼(becoming wolf)和狼的变成(wolf becoming)。这是因为人的性和狼的性不同。其次,虽然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在什么是人性的问题上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但在认为人性是人生来就有这一点上,则持有相同看法。例如,在《离娄下》十九章,孟子没有说君子是变成与禽兽相异者而庶民没有,而是说君子保存了其生来就有的与禽兽相异处,而庶民则没有。
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第三个主要理由是美德伦理学强调的是个体,而儒家伦理学强调的是关系和由这个关系构成的角色。如果我们要强调的是个体总是在关系中的个体,而关系总是个体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德伦理学也是注重关系的。我们应注意到,对于美德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的麦金泰尔本来就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不满,因而也是强调关系的当代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虽然他始终强调自我是社会性的自我,麦金泰尔也反复说明“但这也并不像有些理论家以为的那样,意味着自我不过就是它所继承的各种社会角色”。很显然,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观点就是麦金泰尔所不同意的“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在我看来不仅这种没有主体的关系观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而且说儒家持这样一种观点也缺乏文本的根据。
萧阳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萧阳刚刚发表了《论“美德伦理学”何以不适用于儒家》一文。他说迄今为止认为儒家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的学者由于都没有区分美德伦理学和关于美德的理论,因此“这些学者至今依然还欠我们一个关于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证明”。萧阳进一步说,以美德为基础概念的“美德伦理学”不能用来描述儒家伦理学。
萧阳的第一个论证是以《论语》中的“礼”为焦点。他说,“至少就好礼这一美德来说,‘礼’是基础概念,‘礼’是在独立于好‘礼’这一美德的条件下先被给出的,再从‘礼’这个基础概念衍生出来‘好礼’这一美德概念”。虽然萧阳承认《论语》总体上也没有把礼作为基础概念,他没有进一步去问《论语》所体现的伦理学到底有没有基础概念。如果有,礼与这个基础概念的关系又是什么?如果作了这样的追问,我们就会发现,仁也是在《论语》中体现的孔子的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关键是,在孔子那里仁与礼哪一个更重要?或者用萧阳的话说,哪一个是基本概念,哪一个是衍生概念?我认为在孔子那里礼是实现仁的工具或手段,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孔子认为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可以改变的(有损益),而仁是不变的;二是孔子有些话清楚地表明礼是从属于仁的,如在《八佾》篇第三章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而如果在《论语》中,仁是基础概念,礼是衍生概念,那么体现在《论语》中的伦理学还是美德伦理学。
萧阳关于不能用美德伦理学来刻画儒家伦理学的第二个理由陈述得不是很清楚,但它似乎涉及美德伦理学自身的一个问题,而在他看来儒家伦理没有这个问题。这与他说的独立性教条有关。所谓的独立性教条就是指,(例如)由于在美德伦理学中美德是个基础概念,其他概念都衍生于这个美德概念,或者说不能独立于这个美德概念,但美德概念本身独立于这些别的概念,因此不能用别的概念来定义美德。其结果就是要么这个基本概念无法定义,要么可以被其他概念定义,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就失去了其作为基础概念的地位。我曾以朱熹的伦理学为例,说明儒家的美德伦理学何以可以给美德提供一个并非循环的定义而同时又保持美德在这个伦理学中的首要性。
萧阳用来论证儒家伦理不是美德伦理的第三个理由是,在孟子的伦理学中作为基础概念的是人伦概念,而不是美德概念。所谓的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萧阳这里特指孟子在《滕文公上》第四章提到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但人与人之间的这五种关系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例如,可以有好的父子关系,也可以有不好的父子关系。那么用什么标准来确定什么是好的关系、什么是不好的关系呢?或者我们怎样保证有好的关系而避免不好的关系呢?孟子在《滕文公上》第四章中讲得很清楚:靠美德。
结论
我在上面考察了三位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观点。我有没有证明儒家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呢?恐怕没有。我有没有证明儒家不是这些学者所认为的别的伦理学(如李明辉的康德主义的义务论和安乐哲与罗思文的角色伦理学)呢?本文根本没有试图去作这样的证明。本文只是想表明,这三位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论证并非完全令人信服,至少在我看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