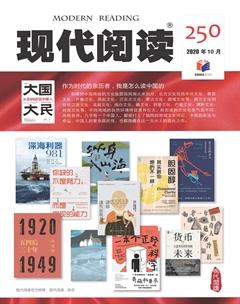中国的实体书店会崩溃吗?
2020-11-16朱晓剑
朱晓剑
前几年,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帖子《中国实体书店崩溃的真相》。
我看了那个帖子,猛一看,分析也有合理之处。但要说中国书店的死亡,怕还是为时尚早。
中国书店的类型和发展史,与西方书店有着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书店的服务功能,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加强,使书店更具有活力。
不必言说网络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其实也跟文化政策有关。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出版业经营中,书店是最重要的一环,新书的价格在实体书店、网络书店之间差别不大,其旨在保护实体书店正常运转下去。但比较我们的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新书网购价格相对折扣较低,如此才有了实体书店运营的艰难。
有趣的是,日本大型连锁书店紀伊国屋书店收购了村上春树最新散文集《职业小说家》首印10万册中的9成。此次纪伊国屋书店的大量收购意味着线上书商手中只有5000册书,其余9万余册都将在纪伊国屋书店和全国多家书店发售。这一行动旨在“其全部配销均优先日本实体书店,以期将该国读者从网络书店唤回实体书店”。这一拯救计划虽只是个案,却还是有着代表意义。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我去西安的关中大书房,看到海豚出版社的不少新书在上架销售,其中多数为五折。应该也是海豚出版社支持实体书店的一种策略。据了解,海豚出版社的此举只针对有特色的书店做的一项活动,其侧重点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疑,这是出版机构谋求更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实体书店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毋庸置疑,中国的不少书店,无论规模还是经营策略,与欧美及日本等国书店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国内的一些城市旅行,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一些地标性的书店,如天津的天泽书店、西安的关中大书房、拉萨的时光旅行书店、合肥的保罗的口袋书店、南昌的青苑书店,等等,它们的存在构成的书店风景,尤其值得关注。
此外,国内的实体书店与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实体书店中销售新书的书店之外,不少城市还存在着大量的旧书店,至于旧书摊就更多了。在爱书人、藏书家阿滢主编的《中国旧书店》中有详细的记录。
有一种职位叫书店编辑
最近,读吴兴文先生的《书缘琐记》。其中的《推动书店的新形态》说:
最值得一提的是,刚开始提到的幅允孝从事的第一个工作案例:东京六本木之丘书店,以旅行、美食、设计、艺术四大主题,对生活形态提出新的建言,构成前所未有的书店形态。于是他将马尔库斯的文学作品,放在“旅行”书柜的“南美”区,布列松《In India》过去一向摆在摄影书柜,现在放进“印度”的架上……通过这种打破既定分类的概念,进行所谓的“书柜的编辑”,比前面提到打破既有的学术分类更进一步,让读者有“是否有什么好东西”吸引他们前去,或者将暧昧抽象的想法转换成具体商品的陈列。
这里说的是“书柜的编辑”,实际上所担任的角色是书店编辑,所做的工作正如幅允孝说:“书店不只是卖书而已,应该是将聚集在那里的信息加以重新包装,进而产生创意,创造出新的商品。肯定还有许多销售点尚未被注意到。”
我曾在《书店病人》一书里提到过书店的图书分类、陈列是一门大学问,列举过成都的今日阅读书店的独特分类法,打破传统书店的分类、陈列模式,才能获得新生。这个图书的分类、陈列所涉及的内容既包括消费心理学,也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关。当我们还在纠结于书店为何卖咖啡、卖文创产品时,书店的形态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今天,大众的文化消费习惯,一直都在悄悄改变着。做书店,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墨守成规做下去,固然可一时存活下去,却难以持久。
不管怎样,书店把书交到读者的手上,才能实现书的价值。书店编辑正是对这种理念的执行,让读者开启一段阅读之旅。
(摘自金城出版社《我在书店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