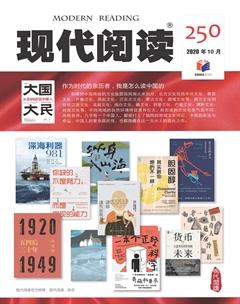以搜集全球经济情报为目的的美国法律
2020-11-16阿里拉伊迪法意
阿里?拉伊迪 法意
这份文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明确国际贸易惯例的现实做法,分析美国集团实施的新一代腐败模式与其展露出的信息控制技术,从而揭露美国政策隐藏颇深的双重标准。
这是法国一家经济情报公司出具的报告的开头。研究内容是:美国将国内法和域外管辖权作为称霸世界经济的工具。这份报告撰写于1999年的4月,从那个时候,也就是20世纪末开始,法国人就在关注美国法律带来的影响了。这份报告只送到了极少数人的手里。在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40大公司中,基本上只有几家大公司的高管拿到了这份报告。法国的情报部门也是这份报告的读者。
报告作者对美国盟友毫不留情。他们指责美国打击腐败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并借此获取欧洲公司的商业机密。腐败不过是一种借口,是“特洛伊木马”,其实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从根本上改变众多国家的经济体制,“邀请”它们采用新自由主义规则。“受美国利益驱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常以防范腐败风险为由,对处于制度结构性调整的国家推行私有化。”私有化意味着收回国家及其代理人对公司的管理权,从而减少腐败,在私有化后,新公司的所有者就无须对批准公司的当权者负责。报告作者没有被蒙骗,他们不相信美国真的在扮演其声称的“白衣骑士”的角色。
1977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应运而生。这部法律被描述为美国公民与他们的公司之间“雷声大、雨点小的和解”,主要是为了恢复因水门事件和多家跨国公司卷入海外丑闻后被动摇的国家信心。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毫无疑问,这些丑闻严重削弱了“美国制造”的冠军形象。因此,美国政府便组织起来,以便与美国外交部门一起各司其职,更好地协调公司事务。一方面,美国政府动员世界各国采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规定的反腐败斗争规则;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则通过离岸金融平台进行重组。“新一代的腐败模式已经形成,并成为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个新一代的模式利用全球信息网络,捕捉世界各个角落的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用于服务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如何应对这样一套提前设计好的完美机制呢?上述报告的作者认为,欧洲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美国的反腐败斗争规则,也不能仅要求加强对避税港的监督,欧洲必须建立一个可与美国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匹敌的情报中心,以平等的武器装备与之竞争。“欧洲集团要采用一套无懈可击的加密算法,来更好地保护它们的情报资产和通信记录,同时建立战略情报系统,监测、分析和反击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虽然20年前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起作用,但无论如何,它们警示了人们应小心美国当局强大的经济情报搜集能力。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國的全球监听计划,法国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这份报告被埋藏了20年,因为法国当时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是,“这是在给我们的美国朋友泼脏水”。
盗用反腐败的名义,为“美国制造”服务
美国有自己的小算盘,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总是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
从1977年开始,美国人就只有一个目的:让全世界都使用他们的反腐败法律,这样他们的公司就可以以平等的法律武器与外国公司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7年签署了《反对在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这意味着美国人的目的已达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法使各国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倡议,这将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完成。
世界银行前区域总监彼得·艾根于1993年在柏林成立了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的宗旨是打击腐败,它在一百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腐败排行榜:按照从最不腐败国家到最腐败国家的次序进行排名。在榜单中垫底的国家意味着其商业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在该国做生意就会显得十分可疑。事实上,评估的标准是以对政治家、商业领袖、专家和学者所做的调查报告为基础而得出的一个腐败印象指数。
这就是透明国际总是被诟病其全球腐败指数的制定过程不透明的原因。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深表怀疑,他们担心透明国际的腐败印象指数只体现了看得见的腐败。这“不是一只眼睛,而是一个焦点,我们透过焦点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事实画面。因为我们透过焦点观察到,一些事实在增长,另一些事实却在逐渐减少。腐败印象指数没有让腐败行径大白于天下,它只是将黑暗转化为半明半暗。”
另一种对透明国际的批评声音是,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基金会和跨国公司。法国前右冀议员、两份关于经济情报议会报告的作者贝尔纳·卡拉永指责透明国际与英国方面的利益密切相关。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宝洁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它们实际上都是该组织的慷慨捐助者。透明国际发布的排行榜虽然有待完善,但仍是经济领域中最权威的榜单。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一贯采纳这个排行榜,而且媒体在报道时,也将这个排行榜作为唯一的参考依据。
1995年,澳大利亚人詹姆斯·沃尔芬森(1981年成为美国公民)接管世界银行,而他将反腐败斗争列为最优事项。世界银行开始以反腐败斗争的名义干涉各国内政,并要求各国将其所有经济公司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詹姆斯·沃尔芬森发现,透明国际是开展反腐新斗争的理想战略伙伴,于是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影响力和资源来帮助这个成立不久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不是透明国际的唯一跳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与它志同道合,这尤其体现在于1997年签署的著名《反贿赂公约》的制定过程中。
透明国际的工作给美国带来了利益,这是一种巧合吗?无论是否有意,透明国际帮助世界各国制定了类似《反海外腐败法》的法律规范,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重新确定了美国情报部门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地位。
人道主义的工具化
透明国际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法国前总检察长皮埃尔·梅朗同时也是国家反贪局的前身——中央预防腐败中心的负责人。他称“这套权力与影响力交织的网络是美国高效率的源泉,是目前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梅朗识破了美国“白衣骑士”的形象背后隐藏的掠夺性战略。他解释说,不能天真地相信美国的反腐败言论。“这些‘善意的提议,这些标榜的美好意愿,所表达的都不是真正的消除腐败行为的愿望,而是让竞争对手信誉扫地,从而为美国利益开辟新市场的倾向。”损害竞争对手的信誉,为自己保留最好的商机:美国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情报战,由非政府组织组成一支“军队”,在搜集有价值的情报的同时,传播些漂亮的空话。
皮埃尔·梅朗所说的网络战略从1961年开始实施,更确切地说,是从1996年11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的时候开始实施的。这份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文本促成了对外发展援助机构的建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战斗部队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管理美国非军事对外援助项目的预算,每年约300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初,在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展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运动,主要目的是促进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的人权与民主。运动宗旨很简单:捍卫一种始终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观。福特基金会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一起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成为“遏制战略”的主要载体之后,福特基金会资助并保护了所有的新一代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都处于国际人权或者环保斗争的前沿。
由于资助和支持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外国的政治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机构将其部分活动调整为打击经济犯罪。早在198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启动了一个打击拉丁美洲区域欺诈和腐败的项目,这不仅使拉丁美洲公民开始关注腐败问题,同时还帮助他们打击腐败。该项目还培养了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促使他们亲自参与国家治理,并提高政府透明度。
在拉丁美洲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目标转向了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机构利用其位于非洲大陆的众多办事处,开始敦促非洲进行反腐败斗争。它出钱资助了相关的教育和培训,这些任务由当地的透明国际组织代表来执行。它还与其他组织开展密切合作,譬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非洲全球联盟等。在20世纪90年代,反腐败斗争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先事项之一。
打击犯罪来孝敬“老大哥”
为了让西方国家都遵守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一项计划以及相应的实施手段——通过搜集和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情报来追捕全球的不法分子,使美国成为打击犯罪的全球领袖,并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控制和惩治犯罪行为的方式。这项计划就叫作“国际犯罪控制计划”,这是美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它的宗旨很简单,即编织一张全球安全网,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安插美国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成员,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海关部门、中央情报局等。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32个国家设置了办事机构,它还打算进一步扩张。
这套机制可以追溯到1995年。一切都始于PPD-42总统令。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因冷战的结束而满心欢喜,但仍然担心“仇恨与不宽容的面孔依旧存在”。必须将新的敌人,也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犯罪作为优先打击事项。克林顿要求政府与各部门积极协调,努力打击国际犯罪,加强与各国的密切合作,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国际犯罪控制计划具有明显的域外管辖意味。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弗里在1997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无法只在本土范围内打击犯罪。为了打击这些犯罪组织,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同时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美国境内与境外保护美国人的权益,联邦调查局研究了多种方法,通过加强我们的域外管辖权,给我们的政府部门提供培训,以便在境外打击犯罪行为。”
在美国境外提前查获的犯罪分子越多,他们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就越小。然而,与官方声明完全相反,国际犯罪控制计划的全球网络首先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它使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能够正大光明地“扫描”全世界,搜集机密情报,追踪并消除来自境外的威胁。这一切都源于非政府组织、智库、咨询公司和跨国公司互相勾结形成“生态系统”的精心策划。
美国的金融战争
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包含多条战线,金融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战线,其主要目的是切断美国的敌人获取资金的渠道。
胡安·萨拉特之前就是金融特种部队中的一员,曾经担任实施打击金融犯罪战略的总指挥。“这场隐秘战争经常被低估或者被误解,但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它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胡安·萨拉特认为,经济战争是当前冲突的主要形式。“当代国际冲突不属于军事领域的问题,而属于商业领域。这些战争不是必然在实地战场上进行的,公司的董事会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地缘政治首先是关于金融和商业武器的问题。”事情現在已经很明朗了:美国人将商场视为战场,公司就是装甲师,而金融市场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战争中,他们觉得自己是优秀的战士。
胡安·萨拉特同时观察到俄罗斯等美国竞争者的“侵略性”行为。2008年夏天,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人了解到,俄罗斯向中国提议:出售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贷款抵押公司房利美与房地美所持有的债券。房地美公司当时管理着5万亿美元的贷款,它的债务高达1700亿美元,而中国就占了1000亿美元。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将它们的债券全部出售,那对美国经济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美国政府将被迫斥巨资来维持房地美公司的正常运营。 “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包括它的一些盟友,正在加大力度限制美国利用美元作为权力杠杆的能力。”
在大规模的反抗面前,美国依旧稳如泰山。因为它享有众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本身的市场吸引力、拥有可以作为储备和兑换货币的美元、全球市场监测和监管的重要地位,以及多年累积的口碑,更何况有时战争还是它自己挑起的。在胡安·萨拉特看来,欧洲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总是畏首畏尾。既然欧洲人撒手不管,那就只能靠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加倍努力了。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隐秘战争:美国长臂管辖如何成为经济战的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