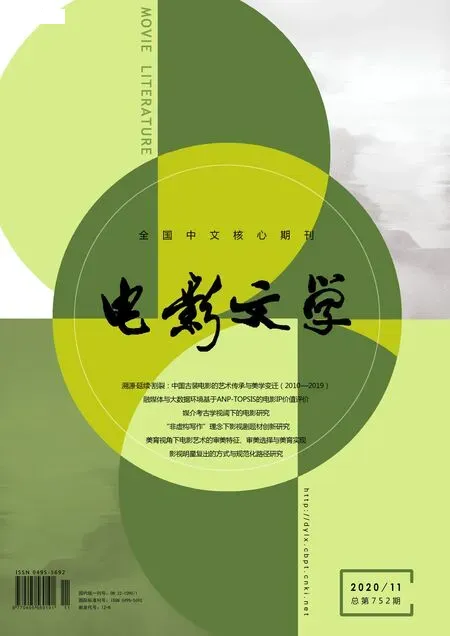《1917》的单线叙事与审美表达
2020-11-14张驰
张 驰
(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 100000)
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自编自导的电影《1917》,一经上映便成为同时期最受瞩目的影片,不光获得高票房收入,还拿下众多重磅国际电影奖项。影片讲述一战时期的两名英国士兵要在8小时内将停止进攻的指令传达给向前方指挥部,挽救1600名士兵的故事。情节本已简单平实,导演更加挑战性地采用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和单线叙事结构方式。
“摄影机追逐着两个人的步伐前行,时间的流逝就是现实的时间流逝,他们面对着现实困难,要的就是这种‘live(现场)’的感觉。”导演门德斯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谈道。正如安德烈·巴赞将“长镜头”定义为一种旨在展现完整现实景象的电影风格和表现手法,一镜到底高度“遵循了时间在时空上的统一”,造成了记录生活的幻觉,最大限度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而对应采用的单线叙事结构方式,则更加集中地将观众视线引向主人公视角,跟随他去看发生的事实、感知经历的体验。二者的有机结合,让观众不再需要对银幕上的时空、人物、事件进行理性缝合,反而可以完全坠入与剧中人同行的时空之中,将沉浸感推到了极致。然而同时,这种创作方法若处理不当也必然带来束缚与局限。
单线叙事作为经典叙事方式——线性叙事中的一种,在电影中并不常被广泛并直接加以使用。简单的故事、单一的线索、不变的视角,容易引起观影者的审美疲劳。尤其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人们更热衷于沉浸在对多重线索、复杂的结构,打破规律、无序的碎片信息进行的分析、判断和处理中,从而产生一种解密式的游戏感,电影的叙事方式也便随着大众的审美习惯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的单线叙事很难再满足观众,甚至有评论称《1917》为了追求真实而做出了很多牺牲。然而一部获得如此成功的影片难道仅凭借“一镜到底”的技术手段吗?让电影大师斯皮尔伯格也称之为“具有革命性的作品”显然不会那么简单,谙熟于电影艺术的门德斯没有老老实实遵循着传统规则,而是默不作声地在单线叙事的外形下做着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从人物设置到戏剧性结构,都打破常规地制造着另一种模式,在保持完美沉浸式真实感的同时,具有巨大的戏剧张力,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表达。
一、人物的“颠覆性”转变
电影人物是影片戏剧性张力的核心,写戏其实是写人。电影叙事中的单线叙事对于人物常用的戏剧手段是反转,发生在主角身上的变化通常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虽然反转会造成较强的戏剧性和张力,但过于激烈的突变会带来人物形象失真的损伤。因此电影创作中常用的方式是,闯入性戏剧性事件导致人物激变。而门德斯在《1917》中并没有因袭这种做法,他对人物转变的设置进行了突破性尝试。他并没有完全固定一个主角,而是将剧中的两个角色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视为一个人物,形成了更广域的主人公概念,突破单线叙事单一主角带来的禁锢,既将人物激变的戏剧张力发挥到最大,又保持了渐进的自然性。
门德斯的这种反转其实就是置换人物型的“颠覆性”转变,导演设置的主人公并非布雷克或斯科菲尔德两个单独个体,而是将两人捏合而成的战争中的“某个人”,这个“人”经历过理想主义的消亡,也经历了人性与情感的觉醒。这就与传统的单线叙事的反转有很大差异,传统叙事反转通常有几种路径,或是以一个秘密的揭开导致人物观念的颠覆,或是掩盖一部分信息给观众造成对人物形象的错觉,当谜底揭开时正邪顷刻反转,而这种处理则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辨识信息的真假,人物自身并没有变化,反转来自观众对人物的认知重塑。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经典模式,是使人物处于众多因素碰撞下,多重戏剧事件汇流成河,形成一层层渐变的推力,而当影片结束时主人公已与开始时截然不同。
从故事发展能更清晰地看到门德斯叙事反转原则的不同寻常。通常,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具有较强的自觉意志,影片《1917》也是如此,开始时布雷克是行动动机的发出者,送信不单是解救1600名士兵,更重要的是他哥哥也在其中,而斯科菲尔德是被布雷克选中同行的人,因此影片前半部处于主动的布雷克自然被视作主角。作为主人公布雷克不光是行动的推动力,在情感上也是主动者,他热情冲动,重视亲情,是家人与朋友中主动连接情感的一方;他是英雄主义者,接到任务时不会考虑可能面临的障碍,只抱有必胜的信念,并将获得荣誉视为最高价值;他有理想主义情怀,眼中看到的是爱与希望,在被毁的牧民庄园里他关注的是樱桃花和童年回忆。他说“砍断的树果,种子还会发芽,长出更多”,将毁灭看作重生。因此,布雷克在面对被击落的敌方飞行员时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相救,但意外的回报却是致命的一刀。而布雷克的死亡并没有中断故事线,导演巧妙地将视角切换到斯科菲尔德,而后者与布雷克的性格恰恰相反,内向被动、谨慎理智、带有悲观现实主义倾向。他逃避情感甚至害怕回家,同样的农庄在他眼中是残破的卧室、空架子床、丢在地上的娃娃,“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他眼中战争之下的家园意象,被毁掉的一切。他将荣誉视作无意义还不如一瓶啤酒的价值,他理性地将一切去掉浮华的外衣,只追寻本质的意义。所以当布雷克突如其来地死去,斯科菲尔德瞬间被推上主动者的位置,成为后半部的主角,就造成了人物戏剧性反转的效果,人物的变化,使得影片镜头语言的色彩也随之变化。这与电影《绿皮书》中经典模式的反转不同,《绿皮书》中白人司机托尼经过与黑人钢琴家唐跨越南美的巡演之旅,在一次次碰撞后不光改变了对黑人的看法,也改变了自己。这种处理方式对人物挖掘较为深入,形象丰满立体,但节奏相对舒缓。而《1917》的人物转换则引起巨大反差,采用如此剧烈的反转也正是制造人物内在张力的时机,人物切换后随之相应的人物心理动机变了,主人公视角也有了新的方向。但由于斯科菲尔德的始终存在,人物并未产生割裂感,观众反而自然而然地顺着他的路线感受激变带来的冲击和未来发生的改变,因为我们最终通过他的眼睛在浮尸满布的河水中看到了飘零的花瓣,也听到了怀念家乡的歌谣。导演打破传统单线叙事的人物设计,创造性地将“主人公” 设定成一个更广域的人物形象,并将人物的激变与渐变辩证统一于其中,使单线叙事与一镜到底的局限反而生成一种独特的戏剧魅力。
二、结构中戏剧单元的设置
电影的单线叙事是按照单一的时空间流程发展的叙事结构,线索脉络相对简单清晰,是其最大优势,但线索的单一也容易导致审美疲劳,使观影效果大打折扣。通常在单线叙事中除却反转外,加强事件的因果联系也是增强戏剧张力的重要方式,即前一个事件的果作为下一个事件的因,形成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锁链式结构。但在《1917》中,故事的结构并未采用因果连接,甚至有意淡化情节间的必然联系,而是跟随时空的转变推进情节的发展。门德斯更像是在导演一台舞台剧,将整个故事切分成多个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各自的节奏与氛围,相对独立又前后贯穿,单元时空间的更迭相当于舞台上的换场。更独特的是,每个叙事单元不光淡化联系,拿掉其中的某一环节,或是置换几个环节的位置,整个故事似乎依然成立。门德斯打破了单线叙事的局限,为时空展示开拓了巨大的空间,这样叙事非但没有导致戏剧张力的损失,反而更增强了观众的注意力。
首先,电影的故事悬念设置。导演将长镜头与单线叙事紧密结合,在产生跟踪式的沉浸效果之外,观众与剧中人都无法从其他线索中获得与未来命运相关的信息,在险象环生的战争中,势单力薄的两个人肩负着拯救1600人的重任却可能随时遭遇不测,这本身就有悬念性。这种随机性和不可获知性引发观众多种猜测,而单线叙事又将观众紧紧把握在主线发展之上,每一个场景变化都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影愿望,不至于游离在故事之外。其次,是随着主人公行进带来的空间变化,导演不断引入戏剧元素,每一个单元都有完整的戏剧结构与节奏,营造出或紧张或诗意的情境,总体贯穿起来呈现出起伏多变节奏效果和丰富持续的戏剧张力,将观众的注意力更长时间地维系在影片中。
门德斯在《1917》中的空间设置极有特色,他按照场景的变化来完成故事叙事,影片大致可分为五场——后方阵地、无人区、被摧毁的牧民农庄、战火中的残破城市、前线战场。围绕着每一个场景都是一场独立的叙事,在不同的叙事空间中,有着人物不同的视点和情感变化,使得整个故事结构立体、饱满并富有深刻含义。从进入无人区,主人公经历了最初的紧张恐惧,发现德军撤离暂时的舒缓,爆炸突发遭遇险境,和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对未知艰险的接受与释然。这一过程呈现出起承转合的戏剧布局,富有极强的节奏感和张力。即使在最初相对静止的段落,巨大臭水的弹坑、遍地死尸与老鼠、铁丝网扎破手掌、飞机飞过发出轰鸣,导演营造出危机四伏的情境时不断引入响动划破寂静,让神经始终处于紧张,场面越静张力越大。突发事件炸弹爆炸,则将这个单元的戏剧性推向高潮,在此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对任务的心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战火中的残破城市单元,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和风格。段落的整体节奏较快,从与狙击手的较量开始,主人公不断遇袭,并且始终被追击和逃离。而在这紧张的动作之外,熊熊燃烧的红色火光、文明遗迹般的残垣断壁、废墟中的教堂十字,营造出一种梦境般的浪漫氛围。充满神秘的黑暗环境与具有冲击力的火光强烈的明暗对比形成戏剧舞台光效,呼应着外在恐怖笼罩与内在的激烈反抗之间的冲突。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片深陷杀戮的城市之下,主人公竟在逃入地下室时遇到少女与新生儿,隐藏在地下的爱与善和生命力同地面之上的暴力邪恶与死亡形成巨大反差,主人公也暂停脚步,给予、被给予着爱的关怀,整个段落的节奏也舒缓下来。
由此可见,门德斯在电影语言上的使用颇为熟稔,《1917》的大获好评并不意外,他的单线叙事中每个戏剧单元都有着相对独立的重心与节奏,而且彼此之间也不可拆分换位。就《1917》而言,导演虽然未在事件单元之间设置因果联系,但遵循了人物心理与情感线索的递进,每一个戏剧单元的结束,人物的心理动机和内心情感都在发生变化,成为推动下一步行动和选择的动力。内在联系的紧密性,使得观众不会产生断裂感,反而更专注于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门德斯对时空间的选择也有独特的考量,空间的选择是导演对世界与人生的哲学思考,影片的深度和厚度就来源于此。无人区的惨状展示着战后的情景,提醒人们战争留下了什么;牧民庄园里布雷克被德国飞行员刺死,意味着被入侵的家园和敌人的残忍与顽强;战火中的城市废墟和少女让人们看到战争真正的受害者;最后的战争前线则是战争进行时,士兵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导演试图用每一个单元展示战争的一个面,将纵向的叙事拉成横向的广阔视野,造成了多条线索的幻觉,当各单元串联起来则看到了战争的时空全貌。影片最终将探讨的多个主题——英雄主义、荣誉的价值、家园与亲情等——指向到一个母题:战争的无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这就是门德斯独特的叙事魅力,将单线叙事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在不经意间融入了心理叙事和多条线索的影子,大大突破了单线叙事的局限,形成更具戏剧张力,更具真实沉浸体验的审美表达。
导演门德斯在以往作品中就呈现出跨类型的特征,他善于打破常规将更多的创作手段和艺术风格融合,传达出更深层而独特的思考。在《1917》中门德斯打破了单线叙事的传统模式,把浑然天成的拍摄技术及具有戏剧性的时尚视听语言融合在一起,造成更为沉浸而丰富的迷宫般的幻觉,形成独特的审美表达,为长镜头单线叙事开辟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