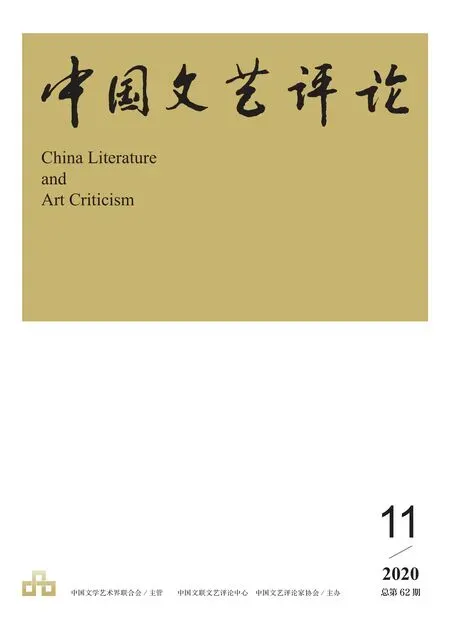新科技视域下艺术的场景化呈现与审美转向
2020-11-12彭渤
彭 渤
随着艺术与科技日益相互交织,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扩展。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艺术创作也越来越走向多元和个性化,技术加持使文艺呈现与创作发生从二维空间到三维再到虚拟多维的转变。“新科技”是一个全新概念,涵盖了人工智能、大数据、5G技术、生物科技、万物互联等一系列技术。新科技的发展促进了AR、AI、算法推送、VR技术不断发展和成熟,也促进了文艺呈现方式的改变。
一、艺术的场景化呈现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指出“移动互联网时代是没有硝烟的场景争夺战,未来竞争的核心要素也将是场景”。何为场景?梅罗维茨在其著作《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场景既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创造出来的“信息场景”,即由媒介信息营造的行为与心理的环境氛围。就场景的形成而言,视听结合方式远大于文字表达的效果,如今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已处于一个“读图时代”。这个“图”不仅包括图片(静态影像) ,还包括图像,即声画同构、视听一体的活动影像或视频。相较于文字记载、静态展示和口语相传方式的文化传播来讲,VR、AR、MR等新技术具有更强的感官感受性,为观众提供了更好的场景体验和艺术感知。
喻国明教授指出,随着信息速率的增加,视频语言将代替文字语言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视频语言相较于单纯的文字表达来说,参与表达的元素多元且复杂,必定会深刻改变延续多年的传播表达范式。比如,湖北省博物馆的VR技术在线试穿汉服,汉服是中国衣冠上国、锦绣中华的表现,但由于在博物馆观看的汉服多是出土后的样态,难以看清全貌,在线试穿汉服则可以通过高清画面和沉浸式体验,让观众领略汉服的真实风貌。再如,曾侯乙编钟被中外专家称之为“稀世珍宝”,不可能让观众敲击实物。但头戴VR设备敲击“曾侯乙编钟”,可以让观众在虚拟呈现的场景中体验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从而体会古代中国艺术的魅力。
沉浸在VR、AR视觉感触中,文艺作品的解读方式也随之改变。《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盛况,画面栩栩如生。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也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台北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VR》整幅画卷采用3D动态展现方式,多点触控,方便观众放大或缩小每一个细节,再加上5G+8K+VR的高速率和高带宽,使画中人物的动作、相貌都可以通过超高清影像清晰呈现。《清明上河图》有三个主要场景——郊外、汴河、街市,借由VR体验,让人真切感受到了高低错落的建筑、汴河桥下的风光、郊外民间的风情,而且还能更真切地了解画中小故事和小场景。比如,在VR视角中换上正确的生旦净丑的衣服,才能进行表演;在餐馆中将不同的食物颜色进行正确匹配,才能开始上菜,这就将饮食文化与历史场景巧妙融合,让观众在了解古代饮食文化的同时欣赏艺术。“视觉化、可视化相较于书本与单纯图画来说更容易营造场景,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倾向于高度的视觉化,可视性和视觉理解及其解释已成为当代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活动的重要维度”。“5G+文博”的云展览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融合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孤岛效应”。比如,中国移动咪咕推出“场景+技术+内容”的新文创模式,弥补了观者无法身临其境的缺憾。咪咕集合国内各大博物馆的VR特展,让观众能够通过多角度随意切换,观赏到文物展品的各种细节,让博物馆走出地域限制,走进普通家庭。
穿戴技术也参与到了艺术创作之中。比如比尔·沃恩和菲利普·德摩斯共同制作的机器人表演《地狱:人机共舞》,这个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安装于观众的身体之上,观众成为作品中最为灵活的部分。根据穿戴的不同机制,观众可以自由移动,亦可将身体全部交由机器控制。人与机器在互动中,展示了华丽的“机械舞”。全息影像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已成过往的艺术的魅力。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代芳华邓丽君》,让观众时隔多年再次听到邓丽君的浅唱低吟,唤起了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最初的记忆。当代歌手与邓丽君实现了“同台”演唱,让人恍惚感觉她不曾离去。再如,优酷推出的“北斗星”技术可以推算出在《长安十二时辰》中让观众情绪高涨的剧集,这有利于在拍摄和剧集制作中提前进行场景建构。
“数字时代的沉浸式艺术及其被体验都是人类生活习性和审美需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场景化体验适应了当前受众的审美习惯和体验感受。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和5G技术下的低延时、高速度、高带宽使VR、AR技术得以更进一步发展,营造不同场景的成本也变得更低,更有利于观众在不同的虚拟场景中体验与文艺零距离接触的乐趣。
二、艺术的审美转向
传统的审美观看多是二维状态下的凝视观看,是主体和客体保持相对距离下的观看,并且主体不参与客体的创作过程,只是一种艺术精神上的领会。随着5G、VR、AR、AI等技术的发展,人对事物的认知感也在发生变化。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认为,触觉交流文化已经来临。比如,腾讯与故宫合作制作的《故宫如梦》探索出了“5G+4K 超高清+互动多结局+场景沉浸”的创新形式,令参观转变为沉浸式动画体验。巴黎梵高沉浸式博物馆展示了梵高的两千多幅画作,音效、光影、画面的同步,让空间界限变得模糊,观者自然地进入客体叙事之中,忘记了现实身份与环境特征,在梵高的世界中游走,感受其对农民、田野生活的热情,也感受作品中的悲悯情怀。“虚拟世界的审美体验紧密关联着生理的美感,或愉悦或痛苦,或快乐或伤心,或喜忧参半或悲喜交加,虚拟空间或数码幻觉可以在使用者或参与者身体上生成伴有意识和意义的特殊审美感受”,可以让人呈现出一种“瞬间失忆”,使得生理和认知处于缺席状态,也就是肉体和精神出现分离状态。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艺作品的呈现形式,随之带动审美转向,由之前非介入式审美感受转向了介入式审美。
随着新科技5G的发展,短视频也迎来了巨大机遇。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围绕生活、学习、就业、情感问题等进行情景化艺术创作和自我演示。《2020年短视频价值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用户在抖音平台上共记录近千万次新生、高考、毕业、婚礼等生活瞬间;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众多或温馨或搞笑的“宅家”生活视频也由短视频平台传播至全网,拍摄手法和内容创意越来越新颖。快手达人“白马小志”通过化妆加上才艺的展现,表达出对看颜值或者通过颜值和穿着来评价人的不正确价值观的不满。被称为“俄罗斯赵本山”的彼得洛夫董德升,通过抖音记录自己丰收的喜悦,展示农民的朴实生活。技术发展使传播权和创作权下放到普通人手中,被赋权的大众越来越按照自己的感官体验和生活经验进行创作,题材涵盖了社会方方面面,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讲,短视频创作都表现出强烈的娱乐色彩。进入5G时代后,短视频的内容逻辑将发生巨大变化,进入以专业生产内容(PGC)为主的阶段,PGC模式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使短视频产品内容更加专业。2018年是短视频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建立秩序的一年。随着万物互联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传播已经突破媒体、社会和行业壁垒。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技术发展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新科技更带动了流量的巨大市场,视频行业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在竞争中都逃离不了优胜劣汰的原则,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视频发展将会朝着专业化、多元化发展。经过大浪淘沙,优秀作品将会留下,受众的审美素养也会不断提高,并进入良性循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也同样实现了人类自我审美精神领域的进步。艺术表现形态变化和艺术创作观念更迭,更深层次地显露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新科技对文艺影响的思考
媒介即信息,媒介发展必将带来文艺生态的变革,技术的发展必然促进受众审美领域的拓展,但是技术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文艺的泛娱乐化与庸俗化现象,艺术的原有价值容易被解构。
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带来非物质化艺术的呈现。以非物质化的新形态为表现特征的艺术空间的出现,随即成为高技术条件下艺术生态发展的新动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演艺产业的呈现方式。比如,西安《大唐不夜城》以数字灯光效果展现出西安夜晚的繁华景象,但在缺少数字技术的情况下,艺术魅力将会减损很多,这些非物质化艺术呈现方式,在带来“奇观”感受之后,又留给受众哪些文艺价值,值得我们思考。文艺创作是精神的交流。文艺最可贵之处是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灵魂的碰撞。5G技术的发展催生了VR技术的成熟,比如“《清明上河图》3.0”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手段,给游人沉浸式的美好体验,但依然是静态书画作品《清明上河图》的复制性数字产物,在VR、AR技术下呈现出一种“超真实”的模仿艺术状态。鲍德里亚在《象征交往与死亡》一书中提出“仿像时代”这一概念,认为仿像时代是受符码支配的时代,“艺术在这一超现实的仿真原则下可以进行自我的无限再生产。在超现实的仿真原则中,艺术死亡了”。这样的说法虽然夸张,但也告诉我们,在科技热潮之下不能忘记艺术的本质,要避免科技过度超越文艺边界,从而走向异化与对文艺的消解。虚拟技术呈现也将带来传统演艺人员的减少,如《天酿》运用科技光影投射创造了似真似幻的奇观,讲述了茅台酒的发展历程,而科技光影的运用减少了演职人员的参与。然而,演员的作用不仅是演绎故事,还应表现精神。美国剧作家伊塔里认为,“戏剧不是电子的。它不像电影,也不像电视,它要求活生生的观众和活生生的演员同时出现在一个同一的空间内。这是戏剧独一无二的重要职能和优点”。威尔逊在《论观众》中提到演员在某种意义上是祭司或主持宗教仪式的教士,而观众则和演员一起表演,如同共享圣餐一般。这样的现场效果显然是目前的数字技术还无法呈现的。
技术是中性的。使用技术的主体是人,在技术创作中加入更多的社会才智和社会情感,才能避免过度追求感官猎奇而忘记艺术的本质。在很长一段时间,技术都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处于被动为艺术服务的状态,而随着科技进步,技术对艺术的主动参与越来越明显。比如《变形金刚》《复仇者联盟》《侏罗纪公园》等电影的场面宏大,视觉呈现强烈,新科技成为内容呈现的主要参与者,但观看之后给人留下的却是精神的空虚。当新科技在参与文艺创作中脱离了艺术内核束缚,肆意驰骋在文艺创作中,我们更应努力让精神得到升华。文艺创作需要在艺术精神和审美规范的引领下进行,拒绝艺术的批量生产,创作出有思想、有温度、有道德的作品,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大众内心深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不能被追求感官刺激、猎奇等错误价值观所污染,真、善、美是永恒的追求,艺术创作不应成为技术的附庸。新科技是文化创新的必然要素,这就要求我们深层次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深入领会传统优秀文化的艺术精髓,坚守道德底线和正确的审美标准,平衡好当前智能技术、大数据、5G技术等与艺术创作的平衡,在满足公众对便捷体验和生活愿景需要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唯上论”、受技术的奴役,而要将新科技作为艺术呈现的重要保障,减少浅层次文化输出,延伸艺术表达的深度和广度,创作出彰显民族精神内涵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优秀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