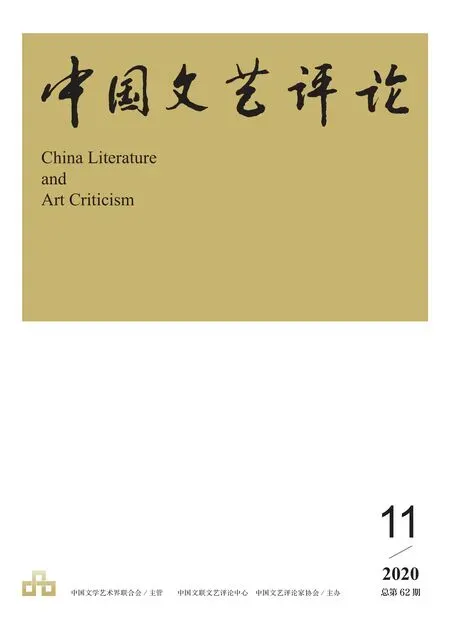以寓庄于谐的喜剧手法拓展主旋律电影表达空间
2020-11-12陈佳冉
邓 凯 陈佳冉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自2020年国庆期间上映以来,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作为一部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主旋律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如何“解题”,如何将严肃的、理性的、宏大的时代命题进行艺术化表达?《我和我的家乡》以一种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表达方式,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一、把观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作为电影叙事的情感基点
用影像的方式来解读、表现巨大的时代命题,途径有千万条,但最优的选择总是少而又少。怎样艺术化表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形象解读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上,自然会有一张张图表、一个个指标来完成一系列的确认。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出台的这些惠及民生的政策,到达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给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带来了怎样的获得感?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政策是为人服务的,是用来保证整个社会良性运转的。人民大众由此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政策才是实实在在落地了,发挥了实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普通人,从个体的真实感受出发,是把主旋律演绎得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最佳途径。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就是把镜头放低,对准我们身边那些脚下沾着泥土、眼里闪着光芒的普通人。他们个体的变化,就是时代的变化;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新时代的风采。
也许,观众习惯于将《我和我的家乡》和2019年热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相比较。这种比较是非常自然的,类似的宏大主题,相同的叙事方式,不少再度出场的熟悉面孔,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其实,这两部片子合在一起,诠释的就是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根深蒂固的“家国观”。人民对国家的感情,更多时候就像仰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的国旗,那是一种高过头顶的、需要凝视的庄严与肃穆;而对家乡的情感,则是从怀中掏出一封家书和“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温暖与牵挂。
很多网友都有同样的感受——对自己的家乡,我可以说不好,但你不能贬低。这种对家乡貌似狭隘、偏执的感情,其实更真切、细腻,也最能引起普遍的共鸣。《我和我的家乡》恰好就选择了家乡情结作为叙事的情感基调,用结构紧凑又富于张力的五个故事,诙谐幽默、笑中带泪地描述了“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家乡》由五个故事单元组成:《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五个单元,各自为战,服务不同主题,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上没有任何关联;但每个故事单元都有一套自洽的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戏剧冲突和角色定位,自成一体。整部片子似乎缺乏叙事主线,但不难发现,与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五个故事单元都有自己的主题:《北京好人》聚焦全民医保,《天上掉下个UFO》侧重科技兴国与乡村旅游,《最后一课》关注教育扶贫,《回乡之路》讲述环保与数字经济,《神笔马亮》书写东北振兴和驻村第一书记。五个主题,形象图解了党和国家所要求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愿景。五个单元,通过故事来讲述个体感受,虽然“自说自话”,但由“我和我的家乡”这样一个情感闸门来统摄,主创的意图与观众的期待达成一致,观影时自然不会产生违和心理。相反,恰恰是找到了“我”和每个人都有的“家乡”——这种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影片叙事的情感基点,《我和我的家乡》才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共情。
二、以强烈的戏剧张力赢得观众心灵共振
电影对五个故事的发生地做了刻意的选择——东(浙江千岛湖)、西(陕北毛乌素沙漠)、南(贵州苗寨)、北(东北乡村)、中(北京与衡水),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中国的版图——一个都不能少;刻意地选择了代表性人物,《北京好人》中的骗保小市民、《天上掉下个UFO》中的农村发明家、《最后一课》中的失忆老教师、《回乡之路》中被人误认为骗子的治沙英雄、《神笔马亮》中的驻村第一书记,这些丰富的角色设置,让表达的题材多样化,也与现实生活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复杂性趋同。
作为五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大拼盘,篇幅的极度苛刻,迫使导演舍弃掉许多铺垫性的描述,只留下表意功能更为强大的戏剧元素,虽然风格有些跳脱,但故事链并不脱节,硬碰硬的快节奏,情节推进丝毫不拖泥带水,反而有较好的留白效果,充分尊重了观众与时俱进的审美能力。
除了把家乡情结作为情感的基调,不难发现,在每个故事中,导演都设置了一个更小角度的情感元驱动力。比如:《天上掉下个UFO》中,因为直线距离一公里的两座大山的阻隔,一对恋人生生变成了异地恋;《最后一课》中,年轻时的范老师不想看到该读书的孩子全去喂猪,于是就一家一家去找;《回乡之路》中,老师面对漫天黄沙,对学生们说,“你们考出去,谁也不要再回来”;《神笔马亮》中,马亮对秋霞说,“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我能做点什么呢?”这些三言两语的个性化表达,其实代表了无数有相同境遇的观众的心声,有着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它构成了剧情推动的重要原动力,也是让叙事结构稳固的软力量。
五个小品一样的故事单元,每一个故事都设计了一个“骗局”,骗局就像一座座迷宫,在设局与解局中最能发挥小品的叙事张力。《北京好人》中,张北京不舍得借钱给表舅看病,策划了一出骗取医保的局;《天上掉下个UFO》里,农民发明家黄大宝为了心上人,一而再再而三给UFO的骗局圆谎;《最后一课》中,当年范老师在望溪村教过的学生们为了帮助治疗老范的阿尔茨海默症,自发组织情景再现1992年的简陋教室,这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骗局;《回乡之路》中,网红带货主播闫飞燕一开始认定乔树林的骗子身份,没想到最后剧情完全反转;《神笔马亮》里,惧内的驻村第一书记马亮,用手机视频直播一个个虚假的俄罗斯景观欺骗老婆,放弃留学去驻村扶贫的事实。
电影与观众常常是一种相互征服、相互说服的关系。电影通过塑造人物、设计情节、暗设悬念、制造冲突、引爆情感,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赚取观众的眼泪,激发观众的笑声,让观众完全忘掉自己,成为剧情的一部分。但观众首先是一个接受者、评判者的角色,要进入电影的圈套其实并非那么容易。面对《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骗局”,观众首先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剧情是如何解套的。《北京好人》中,张北京这个人物形象一出场就与观众心里的预期有较大的差距——河北衡水老家的表舅想借钱做手术,张北京不想借又不忍心,就想了个用自己的医保卡帮老舅治病的 “歪招”,于是就有了抽血时舅甥俩演的一出“双簧”,逃离医院前的“亢奋”举动,葛优演的张北京穿着病号服在医院楼道里来回奔跑,这就是“北京好人”?可是转念一想,“好人”首先也是人吧!多年没有来往的表舅到北京讨生活,一把年纪做外卖员,攒不下几个钱,七八万的手术费的确是个巨大的负担; 张北京在酒店停车场工作,好不容易攒下些存款,想买辆车在工作之余开专车挣点钱,这也不难理解。等到两人“解放天性”壮着胆子开始行骗时,他们内心纯良的本性就成了行骗的障碍,把他们置于哭笑不得的窘境。张北京就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揣着自己的小算盘,又不乏普通人的恻隐之心,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舍己为人”,而是我们身边的为人为己,关键时刻能够舍己的好人,一个亲切真实、活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大家理解、让观众哈哈一笑的北京好人。从对“北京好人”的质疑到对“北京好人”的理解和认同,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主创把戏剧的张力演绎得淋漓尽致。
把《北京好人》作为开篇单元,大概有主创特别的用意。将镜头对准一个有缺点的普通人,非常有带入感;张北京作为一个老家在衡水的新北京人,他的心中盘亘着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这与大部分电影观众的境遇何其相似。这大概是主创在剧情之外精心设置的一个与观众的情感沟通方式。尤其难得的是,《北京好人》一开始就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医保对于农村的重要性、数字经济时代新业态的发展对劳动力生存环境的挤压,等等,这些使电影平添了一份厚重感和问题意识。
戏剧张力在《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中也体现得很充分。《回乡之路》里邓超饰演的乔树林一开始给观众的强烈印象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在飞机上再三借校友身份与网红带货主播闫飞燕搭讪套近乎,接着打肿脸充胖子炫富。可最后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带着家乡群众在沙漠里种苹果,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终于让风沙扑面的家乡变了样。结尾抖的包袱让剧情大反转,令人动容。《神笔马亮》中,沈腾扮演的马亮收到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却要放弃这个机会去茴香村当驻村第一书记扶贫。练摔跤的妻子秋霞去单位大闹一通。惧内的马亮不得不用自己的画笔在村里布置了一间宿舍,虚设了一派俄罗斯风貌。这种巨大的冲突最终在“向日葵田拍照”和“秋霞杀回茴香村”这两个环节中,让人物的情感动机与故事逻辑得到了统一。
五个单元的表演风格多少都有些夸张,处理现实生活故意有些变形,但并没有让观众反感。因为这个骗局有真实的现实根基,有广泛的情感基础,有观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所以《我和我的家乡》能引起观众的心灵共振。
三、用喜剧手法嫁接严肃题材获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采用了电影拼盘式组合的叙事新模式,《我和我的家乡》则在强化这种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彰显了寓庄于谐的喜剧风格。五个单元风格虽有差异,但在一个大的主题的统摄之下,更像是一部主旋律的变奏。恰如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所言的“用和弦代替单音,在电影题材内容、样式及片种上,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
喜剧性的调侃风格是《我和我的家乡》大受欢迎的法宝。喜剧元素的设置,一个接一个的包袱,高度浓缩的情节冲突,主演分寸适度的演绎,都彻底征服了观众。
宁浩在导演《北京好人》时,发挥了其擅长的底层叙事与黑色幽默,偷盗电影和越狱电影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这里也似曾相识。张北京与表舅在候诊室的戏份不长,但真正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患者的出现、两位警察在身边落座继而对表舅的盘问等细节增添了电影的紧张感,滑稽效果十足。
徐峥导演的《最后一课》赚取了观众最多的眼泪。范伟扮演的老师因患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停留在1992年在千岛湖畔望溪村支教的时光。为了给父亲治病,儿子小范联络范老师当年的学生们,大家“合谋”,喜剧感十足地还原了28年前那间漏雨的教室。当范老师从瑞士回国重新踏上当年支教过的土地,那里的山水、一草一木,瞬间唤醒了他的记忆。观众的情绪也像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索,酝酿着一股强烈的情感张力。直到范老师为了帮助姜小峰完成黑色画作,冒雨回去取颜料时摔倒在水中,观众的情绪被引爆。在这个单元里,主人公的个体记忆与交错的时空来回转换,使每一幅画面都饱含着丰厚的意蕴,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一部喜剧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主演展现了精湛的功力,寓庄于谐,庄谐有度,细节处看似不经意却大有内涵,台词更是趣味横生、令人捧腹。镜头温暖,对大地美景的俯瞰,犹如一首抒情诗,寄寓着对家乡、对美好未来的无尽畅想。有观众说,“看《我和我的家乡》,笑着笑着就哭了……”这种率真的观影感受,并不是个例。
值得商榷的是,由于时长的限制,这部影片的个别单元在情节推进和人物形象的建构时,缺少必要的交代和铺垫,导致说服力有些弱化。同时,在故事单元与单元的衔接上,每个故事的结尾突然用数量众多的人像特写组成一面“人物墙”,与故事本身关联度不高,给人硬植入、往主题上硬靠的感觉,不如从整部片子的大主题方面寻找介入的角度,强化各单元的相关性,应该更能形成浑然一体的感觉。
曾几何时,主旋律电影由于其特定的要求,也由于创作者思维的自我设限、故步自封,给观众留下严肃、空洞而刻板的印象,令人敬而远之。令人欣慰的是,《我和我的家乡》与近年来其他高人气的主旋律影片一起,从生活中获取灵感,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创新表达方式,用喜剧手法嫁接严肃题材,获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主创团队和广大观众处理和接受这类重大题材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这种自信,表现在国人越来越经得起调侃了,越来越可以自嘲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自信,是国民心态的成熟与放松;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是对时代进步的认同,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