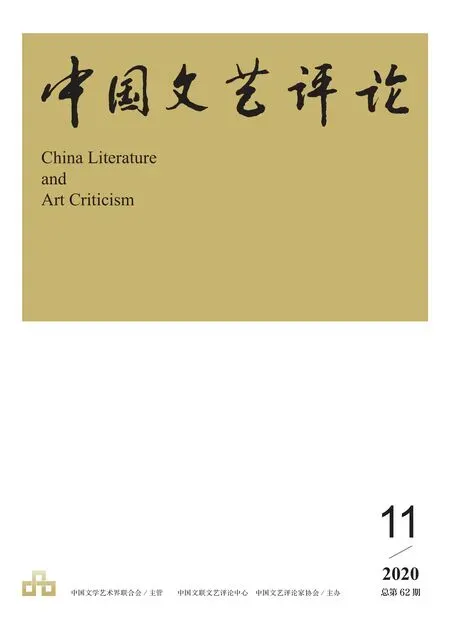让抗疫歌曲成为一场“驰援”
2020-11-12康伟
■康伟
《中国艺术报》社总编辑
抗疫歌曲无疑是抗疫文艺中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存在。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既将以其不可复制的艺术景观、文化图谱留存于中国歌曲创作史中,也将以其激发的心灵慰藉、精神力量铭记在人们心头,更将以其宏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铭刻在历史记忆里。疫情之下被迫长时间处于隔离“孤岛”状态的人们,可以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传播链条中,通过极具传播性的歌曲链接起超越歌曲艺术的生命体验。这样极其特殊的历史情境,新技术加持和赋能造就的传播生态,造就了抗疫歌曲创作的“铺天盖地”。而由此相伴的关于抗疫歌曲创作的论争和言说,进一步将抗疫歌曲置于社会的焦点之下。
仅以《中国艺术报》为例,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艺术报》自觉地、创造性地突破传统媒体局限,充分发挥文艺专业媒体优势,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强国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了一百多首原创抗疫歌曲音频和视频,以及相关的歌词、歌谱,总点击量超过1100万。这些歌曲,既有音乐界名家之作,也有普通市民、医生、公务员等非专业人士之作,是抗疫歌曲的一个生动侧面和缩影。而它们只是潮水般涌至报社新媒体收稿平台的歌曲作品中的极少一部分。在新媒体平台以视频和音频形式推送歌曲作品的同时,我们也在《中国艺术报》纸媒上组织刊发了《音乐战“疫”:“铺天盖地”之后,如何“顶天立地”》等关于抗疫歌曲的文艺评论,直击抗疫歌曲创作中的亮点、焦点、难点和痛点,产生了强烈反响。自《中国艺术报》创刊以来,从未如此集中地传播过这么多数量的歌曲作品,也从未在短时间内收到数量如此之多、地域来源如此之广、行业覆盖如此之全的歌曲作品。主动联系我们、向我们投稿的知名音乐人和各行各业的创作者,其抗疫歌曲创作热情之高,让人产生强烈的内心震动。这是抗疫歌曲“铺天盖地”的生动案例。而放眼全社会,抗疫歌曲早已溢出音乐专业圈的边界,成为一种跨界破圈的文化景观和社会景观。文艺界(音乐和非音乐、专业和非专业)、传媒界(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移动端)和社会各界(各行业、各阶层)构成抗疫歌曲创作、传播的有机链条和生态圈,可谓蔚为大观。
当然,对抗疫歌曲优与劣的辨识与判定,对抗疫歌曲社会功能、艺术功能关系的把握与评说,对优秀抗疫歌曲经典性的命名与确认,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沉淀与省视,但在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当下,如何观察并判断抗疫歌曲的“铺天盖地”和“顶天立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诗人沈苇这样写到:“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借用这句诗来言说抗疫歌曲,我们可以说:一首优秀的抗疫歌曲就是一场“驰援”。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追问:一首抗疫歌曲何以就是一场“驰援”?如何让一首抗疫歌曲成为一场“驰援”?而那些失败之作,又怎能承担起“驰援”的使命?
所谓一首抗疫歌曲成功的“驰援”,是指其以自身所具备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对疫情中处于困境中的人所起到的抚慰和激励。疫情之下,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困境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驰援”。在我看来,抗疫歌曲要想切实承担起“驰援”的重任,实现“治愈”的“疗效”,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点。
一是炽烈的生命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五个方面的概括,生命至上居于首位。这是非常精准、非常温暖、非常深刻的提炼。从伟大抗疫精神的这个内涵回望此前的抗疫歌曲,将生命至上意识作为考察其成效、成色、成败的重要标尺之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管是对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哪一个方面的书写和表现,都要将尊重生命作为基本要求。炽烈的生命意识,是文艺创作特别是与灾难有关的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只有以炽烈的生命意识和真切的人文关怀去面对一线抗疫英雄、与疫情作斗争的患者和疫情之下命运与共的每一个人,只有以炽烈的生命意识去思考抗疫斗争中的奉献与牺牲,创作者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至上的神圣感、庄严感,才可能有心念苍生、大爱苍生的悲悯情怀,由此才可能在创作中真正做到尊重生命、避免人文关怀的缺位,才可能不戏谑、不隔膜,才可能去机械化、去片面化、去简单化。没有生命意识的抗疫歌曲,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二是浓烈的情感温度。《礼记·乐记》有言:“唯乐不可以为伪”。简单说来,就是音乐来不得半点虚假。《礼记·乐记》还说:“歌,咏其声也”。也就是说,歌要表达心声。虚情假意,无动于衷,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音乐的。关于疫情的空洞廉价的悲情,关于抗击疫情的矫揉造作的豪情,实质上是有害的矫情和寡情,或者是虚妄的热情,不仅难以打动人心,反而容易让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只有真正以艺术家真切而深刻的生命体验,接通与人、与家、与国、与世界的情感通道,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与人共情共鸣,才能以情动人。特别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能否准确把握歌曲创作中的情感书写,是歌曲创作能否走进处于巨大困境中的中国人内心的关键。共克时艰的命运共同体之下,爱国情、亲情、爱情、战友情,柔情、悲情、豪情、激情……各种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成为抗疫歌曲词曲创作扬善念、接地气、动人心的内在原动力。同时,要把握好情感浓度,饱含感情而不滥情、煽情,表达真情而不消费感情。
三是强烈的艺术品格。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艺术创作必然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功能,甚至是社会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在举国抗疫的历史条件下,抗疫歌曲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广大音乐工作者以及抗疫歌曲承担起了应尽的责任。所以,“铺天盖地”并不应该成为指责文艺创作“消费灾难”的说辞,抗疫歌曲的“应急”式创作亦有其合理性。但“铺天盖地”之后,以“顶天立地”的标准来反思抗疫歌曲创作,也绝不是夸大其词。恰恰相反,“顶天立地”应该成为抗疫这样重大主题的文艺创作的自觉追求。回顾特定历史时期的歌曲创作,那些经典之作,无一不是既承担起社会动员功能又具有强烈艺术性的作品。以抗战歌曲为例,《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作品,都是社会动员与艺术创造浑然一体的“顶天立地”的杰作。而“顶天立地”并不是仅仅从主题上、立意上来看那么简单。“顶天立地”并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音乐创作想要真正实现“顶天立地”,最终是要靠作品来说话。那些不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能对关于抗疫的时政话语、社会话语、新闻话语、社论话语、文件话语、报告话语进行歌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作者要么是缺乏创造性转化的意识,要么是缺乏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使“顶天立地”丧失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从而也使“铺天盖地”成为一种假象。
兼具炽烈的生命意识、浓烈的情感温度、强烈的艺术品格的抗疫歌曲,总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引发强烈共鸣。比如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无论词曲,都直抵人心。“为了你,我拼了命”的真情告白式开篇,“撑起多少个黑夜,绝不让生命叫停”的坚定与深情,“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的主题咏唱,“你有多痛我就多痛心”“无法拥抱却离你最近”的命运与共,直至结尾“真情守望,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的民族精神,词曲都做到了情感饱满、动人心弦,同时又打通了个体与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情感通道和精神通道,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传播力,成为抗疫歌曲创作中的优秀代表。
中国抗疫之战尚未收兵,期待音乐工作者在对抗疫歌曲创作进行沉淀与反思之后,自觉将创作与抗疫史诗相匹配之作、与人民内心情感相呼应之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合之作作为艺术动能和执著追求,为中国抗疫留下厚重而感人的音乐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