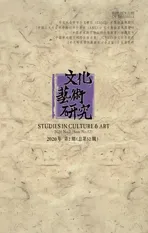美术片《大闹天宫》中小猴的“劳动”图像研究*
2020-11-09刘双花
刘双花
(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北京 100044)
美术片《大闹天宫》(以下简称《闹》)完成于1964年,是新中国“十七年”动画片的巅峰之作。上集完成于1961年,同年上映;下集完成于1964年,遭禁播,1978年得以上映。1961年的影评大多讨论影片本身的创作过程和情节内容等。1978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几篇影评,主要是声讨“文革”的失误,讨论影片的价值。其中,《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观众来信常被引用:“眼前,一片绮丽的色彩和种种迷人的景象。云雾飘渺,层峦叠嶂,花果满山,一群小猴摘着桃子,荡着秋千,活蹦乱跳地嬉戏其间。稍远处的山中有一带银白的瀑布……两个小猴走上前去用长矛轻轻一挑,那瀑布便像幕布一样左右分开……”[1]这段话描述了影片以小猴为主体的精彩开场。
小猴角色出场时间虽然占影片总时长的近四分之一①影片总长106.5 分钟,其中小猴出现的画面约占30 分钟。,为成就影片经典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作为配角却极少得到关注和研究。片中小猴与果实、瀑布等自然物发生关系的行为图像,与同期宣传画和年画“爱劳动”主题有着颇为相似的图像模式,又与斗争图像一同构成小猴的主要行为,这恰恰契合有关“红小鬼”的主要活动是“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记载。[2]据此,本文将小猴作用于自然物、具有劳动性质的行为及图像称为“劳动图像”,并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小猴劳动图像是如何塑造的,传达了何种信息?二是其创作思想源自何处?
一、劳动图像的表达和意涵
《闹》改编自小说《西游记》前七回。对照小说相关文字叙述,可知影片在小猴行为设计上作了大幅改编。小说开篇有一段文字描述众猴如何顽耍,它们“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抛弹子,邷么儿;跑沙窝,砌宝塔;赶蜻蜓,扑蚂蜡;参老天,拜菩萨;扯葛藤,编草帓;捉虱子,咬又掐;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轻松林下任他顽,绿水涧边随洗濯”。较之顽耍叙述之细致,与劳动相关的仅有一句“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属刂黄精……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目的是为即将远行拜师的猴王送行。[3]
与小说不同,小猴劳动图像有7 分钟,分3 个片段出现在影片的开场和两个重要转折处(上集猴王龙宫夺宝后和下集猴王大闹蟠桃会后,见图1),可见劳动作为花果山小猴的日常生活,与斗争交叉上演,在调节影片松紧节奏上起着重要作用。分析片中劳动主体、劳动行为、劳动内涵和劳动场景等美术设计的各要素,可帮助理解小猴劳动图像的改编原则和思想内涵。

图1 影片小猴劳动图像分布时长/分钟
(一)劳动主体
片中作为劳动主体的猴子属于较年幼的猴子,中老年猴子并没有出现在劳动图像中,因而本文将他们称为小猴而不像小说那样称之为众猴。②片中小猴数量占绝大多数,另有少数成年和老年猴子,但是只表现了小猴劳动的场景。笔者之所以认为小猴的年龄特征为儿童(4—16 岁),是依据片中小猴的形貌特征,另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京剧、绍剧作品中都存在由儿童扮演小猴的现象,如绍剧《大闹天宫》(1957年)和《三打白骨精》(1961年),由此推测,美术片中小猴的年龄特征为儿童不仅仅是因为考虑到儿童观众这一因素,还因为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儿童是一个比以往得到更多关注和表现的群体。他们在形貌上与猴王孙悟空相似,以桃心脸、棕色毛发居多,服饰装备简单朴素,以兵、民区分。“兵”装扮者属少年模样①影片下集(1964年)临近片尾出现幼猴着“兵”服饰的图像。,上系领巾,下着甲裙,手持长矛。美术设计张光宇(1900—1965)曾画过一幅图,小猴身着京剧中跑龙套的小兵行头②该图在2018年10 月北京势象空间的“辟新路者——张光宇文献展”中首次展出,原作为张光宇之子张临春收藏。(图2),最终舍弃,而代之以系领巾、穿甲裙并打赤脚的小猴。“民”装扮者年龄稍小,身着中国典型农民背心马褂,更年幼的则一丝不挂。所有兵、民小猴一律参加劳动,但行动自由,无明确分工。
在个性塑造上,片中小猴一反小说中的唯唯诺诺,直接质疑孙悟空从龙宫那里夺来的金箍棒:“这有什么稀奇的?”③在李克弱的文学剧本中,众猴的台词是“好兵器!好宝贝!”。更是敢于捉弄太白金星、撕毁圣旨,全然一副自信而不惧权威的花果山主人姿态,凸显了平等、自由思想(图2④上面两图:京剧跑龙套小兵装扮的小猴方案(张光宇,1960年);中间三图:小猴看金箍棒“这有什么稀奇的?”,太白两次下凡(影片截图,1964年);下面三图:小猴撕毁太白手中圣旨(影片截图,1964年)。)。显然,片中小猴角色设计主要参照了中国近现代劳动人民的典型特征,在个性塑造上体现出毛泽东看待年青人的思想观念。⑤毛泽东在1957年会见留苏学生的讲话中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刘新生、赵国明:《外交官历史亲历记》,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 页。1958年毛泽东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批示,告诫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在同年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29 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并阐明自己重视年轻人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 页。

图2 小猴形象塑造
(二)行为设计和“果实”符号的意义
影片开场的劳动设计以征服自然为显著特征,呈现了几组经典图像,如小猴在藤蔓上倒挂成串采果⑥事实上,现实中猴子通常仅可单只倒挂。一串猴子倒挂的创意,最早出现在中国民间童话故事《猴子捞月》。1958年美术片《过猴山》第一次采用这种一串猴子倒挂的图像模式,之后1961年《闹》中花果山小猴劳作场景再次出现。1981年,美影厂将童话故事《猴子捞月》改编成美术片,“猴子倒挂一串”及图像遂成为广为人知的猴子协作的经典图像模式。,大大小小的芭蕉叶充当传送带和容器,最富独创性的是水帘洞可以被幕布般掀起。⑦据严定宪、林文肖夫妇回忆,这一开场当时由他们设计。张光宇于1960年绘制的一张孙悟空角色设定图中所绘陶罐并没有在片中出现,而是保持了花果山的原始属性,所有这些设计完全颠覆了小说中“铁桶金城”般无奇不有的世俗花果山形象[4],转而回归原始自然。
第二场和第三场劳动图像都表达了劳动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其中,第二场表现两只小猴采果时因逗闹导致其中一只失足跌落悬崖,被孙悟空救起后调解和好;第三场表现小猴一同采摘从天宫移植来的蟠桃。这两场都以小猴向猴王献果子的特写结束。这类一群小的簇拥一个大的图像模式常见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照片或年画等,主体通常是毛泽东、朱德或雷锋等人物与少先队员们。
三场劳动场景都以果实为核心要素。无论是花果山自产的果实,还是猴王从天宫移植来的蟠桃,主要用于被摘取、传递、展示或奉献,成为承载劳动积极内涵的特定符号,表达与劳动相关的丰收、团结、友爱等思想。“丰收”通过果实之漫山遍野、堆积如山来体现,并在小猴操练时用作前景遮挡。“团结”体现在小猴以多样方式协力采摘和搬运果实。片中有一幼猴专心拾果的图像,从形态和构图上看很可能源于张光宇一幅幼猴斗蛐蛐的草图,由玩耍到劳动的行为改变,似乎表明连最年幼的小猴也尽一己之力加入到了劳动之中。最后,“友爱”意指两点:一是小猴之间的友爱,互相谦让大果;二是猴王与小猴间的爱护或拥戴关系,图像表现为赠送或奉献果实给对方(图3①左上:幼猴斗蛐蛐草图(张光宇,1960年),右上:拾果子的小猴(影片截图,1964年);下:表达“丰收”“团结”“友爱”的图像(影片截图,1964年)。)。

图3 小猴“果实”符号设计
(三)场景设计
作为劳动环境,花果山场景设计采用中国画中的“青绿山水”风格②由张光宇和张正宇(1904—1976)作场景设计。,类似东方传统的重彩[5]105,线条硬朗利落、色彩热烈明快,常见于同时期年画和结婚证等装饰用蔬果植物图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不同于花果山上的“土产”果实,天宫蟠桃采用的是陈洪绶花鸟画法,线条更加微妙精致、色调相对柔和典雅,代表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反衬花果山的世俗与真实;而移植到花果山的蟠桃则采用儿童简笔卡通画法,象征改造后的新生事物(图4③上:花果山桃树、孙悟空“移植”到花果山的蟠桃和天宫蟠桃园(影片截图,1964年);左中:花果山土产桃(影片截图),右中:结婚证局部装饰(1959年);左下:影片中天宫的蟠桃,左中:陈洪绶花鸟画,右下:“移植”到花果山的蟠桃。)。这些绘画之间的微妙差异,在呈现视觉美感的同时,将观众立场不自觉地导向花果山,符合导演万籁鸣(1900—1997)对花果山场景的设想:“花果山阳光普照,花果盛开,是人间乐园,是人民的理想和愿望”[5]105。
综上所述,影片中小猴角色设计的参照对象是新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配以创造性征服自然的劳动行为和为大众所熟悉的劳动场景风格,营造出花果山热烈、活泼的劳动氛围,引起观者在感官上的愉悦共鸣;同时,果实成为传递与劳动相关价值观的视觉符号,表明了在平等的生产关系下劳动的积极意涵。由此,影片在劳动图像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完成了诉诸观者视觉和心理的经典劳动图像创造。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劳动在小说中的缺席与依附,还是劳动在影片中颇费心思的创造与表达,都是作品所处时代劳动观念的体现。那么,影片为何如此重视小猴劳动图像的表现?这与影片主题和所处时代有何关联?

图4 影片场景设计
二、儿童相关的劳动表达变迁
劳动相关图像表达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影厂来说毫不陌生。在1959年《闹》筹备创作前,美影厂已经制作过多部以劳动为主题的美术片,其中最早的是1952年的《小猫钓鱼》,歌词“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至今仍为许多人耳熟能详。此后,从1955年至1960年,美影厂每年至少生产一部这类主题的美术片,同样都借寓言故事歌颂劳动的伟大(表1)。因而,20世纪60年代初《闹》的劳动图像创造,可以说是在50年代中后期美术片“劳动”话语表达和集体赞美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表1 美影厂历年“劳动”主题美术片列表
这些美术片与《闹》一样都对劳动抱有一致的赞美态度,差异在于,前者以劳动为主题,侧重劳动作为美德的社会宣教,后者主题为孙悟空和天宫之间的斗争,劳动图像主要用以阐明花果山一方象征新中国劳动者的身份。主题变化导致表达内容发生变化看似平常,但是,如果梳理新中国十七年间所有与劳动表达相关的美术片,会发现这种差异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处于特定的进程之中。以1960年《小燕子》为界,劳动宣教主题美术片生产到此戛然而止,此后直至“文革”开始前,劳动表达几乎都是用以表明底层劳动者的身份。这些美术片除了《闹》外,主要还包括《庆丰收》(1960)、《人参娃娃》(1961)、《半夜鸡叫》(1964)和《草原英雄小姐妹》(1965)等。其中,《人参娃娃》和《半夜鸡叫》因主角身处旧社会遭受欺压,劳动图像突出表现劳动者的压抑和痛苦,而《闹》《庆丰收》和《草原英雄小姐妹》因劳动主体象征或代表的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从而劳动积极主动,热情豪迈。此外,由于后两部影片取材于现实,因而更为明确和直接地表达劳动在新中国集体中的光荣与责任。
较之新中国同时期故事片、年画等其他视觉形式,美术片在劳动表达上的变迁更为典型,这与美术片形式较新,并以儿童群体为主要受众有关。美影厂厂长特伟在1960年的《创造民族的美术电影》一文中谈道,在“大跃进”思想影响下,美影厂有人认为:“外面都在轰轰烈烈地大跃进,我们还只是搞小猫小狗,和时代太不相称了,我们必须反映现实生活,要闯出一条新的路子出来。”[6]因而创作开始有意识地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上转变,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教导,“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于是创作了《庆丰收》《歌唱总路线》等歌颂劳动人民的影片,解决了美术片反映现实的问题,并进一步明确“幻想应当奠基在劳动的基础上”,当时所顾虑的“现实题材能不能发挥美术片特点的问题,也通过大量的‘新童话’体裁影片的出现解决了”,并强调采用“‘更多的夸张、更多的幻想’来表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7]
因此,《闹》虽然取材于中国神话故事,但也是借相似的叙事结构讲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时代风尚的新童话体裁,因而片中的小猴角色设计、劳动行为和场景设计,以及“果实”符号承载的积极内涵,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综上所述,劳动表达是新中国美术片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反映了建国初期国家重视儿童劳动宣教的现实情况。劳动概念在建国后十年间基本完成了道德规范的形象塑造,使整个社会对劳动的集体认知和赞美共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为宣教主题的劳动应时转变为用以表明主角身份的重要载体,凸显或反衬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份的阶级优越性。这一历史浪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闹》中劳动图像的塑造方式。那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为何如此重视儿童与劳动关系的建构?这种建构与社会历史现实及思想观念有何关系?以下拟对之展开探讨。
三、儿童、劳动与阶级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
虽然人类诞生以来即有了劳动,但劳动价值在经济政治领域直至18世纪亚当·斯密那里才开始获得最大的肯定和赞扬。[8]斯密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大力赞扬生产性劳动,但他的理论忽视了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之后对劳动者(劳动主体)的发现和重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劳动政治经济学的创举。[9]但是黑格尔只看到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看不到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异化,认为精神劳动才是劳动的本质。[10]746-747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建立在斯密生产性劳动的现实性和黑格尔精神性劳动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作了扬弃和改造。马克思认为,个人是生产劳动决定的,既和他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怎样生产一致,生产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子,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劳动解放而走向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实性道路。[9]216-218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工厂的儿童劳动,认为“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因为儿童劳动教育不仅提高社会生产,还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在1919年《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为了“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10]746-747。
其实,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就有对“劳动童子团”的描述,但儿童的主要工作是“放哨”“检查烟赌”和“破除迷信打菩萨”,并“在人民学校读书”,可见劳动尚未有意识地归入童子团工作和教育的一部分。[11]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苏联“少年先锋队”组织介绍的著作大量在中国出版,但这些内容都未涉及劳动教育。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列主义儿童劳动教育理论才被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1956年,列宁《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在中国出版,其中重点论述了儿童劳动教育。[12]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同年,周恩来在《给全国少年儿童的题词》中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希望新中国的儿童们,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准备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劳动者。”[14]而后,1958—1959年间,以“教育”和“劳动”为主题的著作频繁出版,主要包括马列理论原著和中小学生劳动实践经验总结等。①这些著作包括但不限于:(1)中国青年出版社:《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2)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育研究室:《论教育与劳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摘录》,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3)湖南人民出版社:《论教育和劳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其中,毛泽东关于“劳动与不劳动是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水岭”,以及劳动是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斗争等话语,常在中学生劳动实践总结中被引用。[15]1959年,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在我们的学校里必须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使他们(儿童和青年)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16]。“教学怎样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17]到影片制作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表达演化为“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18]。
1959年《闹》开始筹备时,恰逢马列主义儿童劳动教育观在中国普及。主创严定宪、林文肖夫妇在访谈中告诉笔者,与《闹》的主要角色大多都由张光宇独立美术设计的情况不同[19],小猴作为群众演员,编剧和导演并未做具体设定,而是给创作团队极大的创作空间,编剧李克弱(1916—2001)在最初的文学剧本中有关“众猴采摘果实”“采桃,传桃”“摘了一个最大的桃子,传递献给猴王”等描述,后来被演绎为上述的劳动图像。在美影厂1960—1961年间的几次内部工作会议记录中,《闹》副导演唐澄(1919—1986)②1965年美影厂在写给上海电影局有关调查导演万籁鸣的回信中谈到,因万籁鸣在导演《闹》时已年满60 岁,精力有限,因而许多具体摄制工作交由副导演唐澄负责。信件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等人的发言屡屡提及“大跃进”一词,不仅意指社会生产劳动的“大跃进”,美影厂的美术片生产也同样纳入到“大跃进”体系;并且在那个年代,所有包括美影厂在内的单位员工,每周定期组织集体大扫除,集体劳动观念和思想改造遍布全国每个角落,影响广泛深远,直至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4年,《闹》下集刚摄制完成,尚未来得及组织内部放映,美影厂的年轻人就匆忙收拾包裹,加入“上山下乡”的劳动大军。③来源于《闹》原美术设计林文肖与笔者交流时的口述材料。
结 语
《闹》中极富时代特征的小猴劳动图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术片劳动表达热潮中应运而生的,同时又处在1960年前后美术片劳动表达由宣传教育转向劳动者身份认同的变迁之中,因而片中对劳动主体、行为、场景和劳动内涵的塑造,无一不密切反映时代价值观念,所有细节要素都围绕“劳动”这一主流思想和意涵来构建,因而呈现出形式多样、内部逻辑严谨的经典劳动图像。
这些劳动图像的思想源头要追溯到马列主义儿童劳动教育观的产生,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教育观被系统引入并全面影响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整个中国社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弥漫着更为浓厚的劳动气息,至“大跃进”开始后,劳动更进一步上升为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也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班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到《闹》制作完成时,更是迎来了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整个社会高涨的劳动热情,通过主创团队之手注入到影片小猴劳动图像创作中,使得这些图像呈现出与劳动观念一致的勃发向上的力量。如此,在历史背景下观照有意味的经典图像,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现实与经典图像之间的因果关系,客观看待和接纳政治文化与艺术之间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进而促进人们思考图像创造在当下应该如何反映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这一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