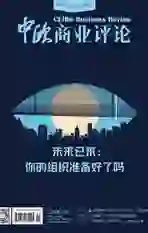笑果文化CEO贺晓曦:公司快垮了,是个段子
2020-11-06周琪
周琪
贺晓曦最近一次“出圈”,是在微博上被池子点名。
池子曾是笑果文化旗下知名艺人,双方年初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池子被贺晓曦“移出公司群聊”,随后在微博上晒出截图,贺晓曦则分享了笑果文化官方声明,指出池子已提出解约诉求,公司正寻求与其进行法律层面的协商,并表示出于对艺人的保护,暂不对此事发表其他评论。
此后,贺晓曦在微博上沉默了三个月,再一次发声,是一张皮卡丘的玩具照片,配文“好日子”,同时关闭了陌生人的评论功能,这一天,笑果文化搬家到了原属于昔日法租界的皋兰路上一栋小洋楼,皋兰路最初的法语名字——高乃依路——取自法国17世纪职业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暗示着它的戏剧血统。
戏剧性是这家由李诞领衔的喜剧演员组成的公司最不缺的东西,池子解约只是2020年众多章节中的一个,但最扎心的生活总能酝酿出最好笑的段子,笑果文化会遵循这条喜剧规律走下去吗?
以下是贺晓曦的口述。
艺术家
2020年,笑果上了好几次热搜,李诞也在节目里自嘲:“这个时候录《脱口秀大会》就是强颜欢笑,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
虽然疫情期间,线下演出停了,但其实公司上半年业务挺多的,为了“诱惑”新人,还搬了家,换了更好的工作环境。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外面都觉得公司快垮了,出去开个会,大家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在节目里说公司不行了,那只是个段子好吧。
风波会不会让我更有危机感?其实创业公司一直有危机感,倒不用风波来刺激。冷静下来思考,其实它提醒我,公司进入不同的阶段了,不是说之前的东西不对,要推翻,而是到了升级和调整的时候,收入结构、组织能力、商业模式,这些都需要调整。
笑果的定位不是一家“综艺+艺人”的演出公司,而是一家产业公司,编剧、培训、演出、节目都在做,这个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的业务边界超过我们。
我理解的产业公司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代表这个行业的形象;第二,为行业制定游戏规则,帮助同行降低交易成本。比如我们做出一些东西之后,我们的同行就不用再跟客户解释为什么脱口秀还需要编剧了。
之前我们老拿这个行业调侃,说中国干脱口秀的人加起来坐不满一辆巴士,还说,不能让这群人同坐一辆巴士,万一出车祸,中国脱口秀就完了。这两年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这个行业缺人还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摆在那里。

所以你问我,对于已经成名成“角儿”的头部演员,公司有没有帮他们规划下一步的发展路线,会不会担心果子熟了掉下来烂在地里,坦白讲,这不是我担心的事儿。脱口秀是一个很垂直细分的行业,大家愿意来,肯定是因为喜欢,那些在这个领域里获得正反馈的头部演员,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他们谈商业合作的事情会被拒绝。像这段时间,(王)建国、Rock,你去劝他们接别的活儿试试,他会跟你说,“等我(《脱口秀大会》)淘汰了再说”。他们会有一个天然的想法,就是要给观众一场好的演出,为了这个目标,其他是可以妥协的。
我观察下来,公司很多人是很“艺术家”的,哪怕李诞,如果纯粹计算投入产出比,他其实有大量更赚钱的选择,但他没有跟公司说,我要去拍电影(少数友情客串除外),一次都没有。你发现我们公司没有人去拍电影,这是很奇怪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导向还是鼓励大家当一个厉害的艺术家。
艺术家能为这个世界贡献的就是创作,真正发自内心的创作。公司有个底线,你可以不好笑,但你不能抄段子。可能有些人觉得笑果做出来的东西有点傻,没关系,就像李诞说的,水平就在这儿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原创的。
管理
脱口秀这个行业,靠内容驱动,离了人才什么都不是。作为CEO,我也被问过无数次怎么“管理”人才。但我内心其实比较抗拒这个词,它老让我联想到工业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
拿(张)博洋来说,他上一季主动退赛,这一季被淘汰了,好多人觉得他特别“丧”,缺乏自驱力,我了解他,他表现出来的“丧”一部分是个性使然。还有一部分是艺术加工,作为老板,我反正不会去针对他个人做些什么,来企图点燃所谓的“自驱力”。
我理解的自驱力不是针对个体的,否则就变成带孩子的逻辑了。自驱力是一种机制,一个标准,当个体达到了这个标准,就会获得体系给予的正向反馈。

博洋虽然被淘汰了,但他在脱口秀演员互相投票中的排名一直很高,这说明大家赞同他的喜剧审美,赞同他的自我突破和在艺术上的不断追求,虽然如果他不那么纠结就更好了。这恰恰说明我们构建的这套自驱力机制在发挥作用,不是吗?
前几年,公司做的事儿大多是为了解决脱口秀不被人知道的问题,毕竟,你得让人相信这个行业是有奔头的,有能力的人才会来,最近我们也在反思,不能因为步子太快,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就像段子需要打磨,人才需要时间沉淀,有的人可能两年(就能冒出来),有的人可能三年甚至更久,既然不存在刚性的规律,也就很难有一套标准的管理动作。
能力不是管理出来的,激发、鼓励、点燃……你用什么词都可以,唯独“管理”不行。
《脱口秀大会》激发了大家的创作,让大家保持好的状态,你可以把《脱口秀大会》理解为笑果“管理”员工的一种方式,它提供一个舞台,一档节目来检验“老人”过去一年的积累,也奖励新人的快速成长。
盲盒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结束的时候,李诞有一句评价挺中肯,“啥都好,就是赛制不够激烈”。到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大家发现我们在玩一些更刺激的东西。
节目播出后,网上有人说赛制也太刺激了,跟“隔壁”《创造营》似的,我觉得太刺激总好过不温不火、没人讨论,对吧?
第一场PK赛50进25的时候,如果照“狠”的来,25个晋级名额满的那一刻,比赛就结束了,但我们临时决定,让剩下的7个人站上舞台,完成他们的表演。大家批评赛制随意,我能理解,也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因为之前没做过,赛前推演做得不够细致;二来还是舍不得,那7个朋友在场上坐了一天,事实上他们为了这场比赛等了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他们就想要一个表演的机会,这让我们狠不下心让人家就这么离开。
如果是其他行业,真的相对简单一点,因为那个东西,客观讲,跟我们没有关系,人也不认识。乐队也好,街舞也罢,淘汰就淘汰,我不会管你等了一年还是两年,“天地不仁”,就像奥运会,运动员准备了四年,说不办就不办了。但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长出来的公司,你知道人家有多难,所以狠不下这个心。
李诞当评委给选手提意见,比如觉得Norah的段子让人有压迫感,被吐槽“爹味”“好为人师”什么的,我反而觉得没必要“收”,挺好的。因为这一季他主动退后,更像一个教练或者联盟的组织者,他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助选手把线下的状态更好地呈现出来。
过去,干线下的会瞧不起干线上的,觉得“不就是个节目吗?线下我们还是厉害”,今年周奇墨来了之后,这种声音渐渐小了,大家开始意识到,从线下到线上,不仅仅是录制然后播出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你想成为一个大众媒体意义上的脱口秀艺人,文本、表演甚至整个表达结构都要在线下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比如OG(元老)周奇墨,他线下确实好,线上的传播力度或者说穿透力可能不如其他一些演员,再比如“网红”李雪琴,她从不去线下说开放麦,刚开始谁都对她不抱希望,但人家线上就是“炸”,拦也拦不住。



這个节目很像一个试验场,充满了变数和意外,看录制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团建,每次看都像开一个“盲盒”,有超出预期的惊喜。它也提供了一些样本,促使我们去思考、总结行业人才不同的成长路径。
我们做的节目,从运营层面说都是冒险。什么是既保险又划算的做法?就是《吐槽大会》成功了,找几个平台都开一个类似的做一做。《脱口秀大会》之前,如果找个业内的人问要不要做这么一档节目,他多半不会看好。这就好比造汽车前,你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说要个更快的马车。这么说不是不在乎同行的看法,只是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节目播出到现在,对赛制和比赛结果不满的声音肯定有,但你去问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他们还是觉得这一季《脱口秀大会》是厉害的,因为我们选择了冒险,把这个行业往前推了一推,宁愿这个东西不完美,也不要它停留在原来的逻辑,所以它在豆瓣上的评分永远不会很高,就像演员说段子,可以不好笑,但不可以不真诚。
至于有人质疑李诞“操纵式拍灯”,很开心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就像世界杯每一次分组抽签都有人怀疑“暗箱操作”一样,说明这个行业开始被人以观看球赛的心态去围观,要“出圈”了。我倒觉得没必要高估“操纵”这件事,因为如果你一直追着看下去,就会发现比赛最终还是公平的,水平特别烂的人留到最后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至于节目会不会爆款下去,我一直看得挺开,爆款是“非常态”,与其追求爆款,不如追求好的节目。爆款会带来诅咒,但优秀的节目不会。我又要拿运动打比方了,你永远不会从任何一位世界足联主席嘴里听到“我要打造爆款”这句话,但又有哪一届世界杯不是爆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