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从画家到诗人的转变轨迹管窥
2020-11-03周翔华
周翔华
(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近年来学界对艾青诗歌的绘画性日渐关注,旨在从绘画的视角探究艾青诗歌的特质和多元性,这一视角丰富了艾青诗歌研究、评价的多元维度,拓展了艾青研究的新面向。但是从绘画的维度来研究艾青的诗歌,也需要切中肯綮。倘若习焉不察笼统援引传统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理论来分析解读艾青诗作,则容易使研究耽于陈陈相因而陷入误区,乃至与艾青诗歌的审美取向相去甚远,在某种程度上消弥绘画维度研究艾青诗作的有效性和价值。实际上,在开展艾青诗歌绘画性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艾青与美术的关系进行多重透视,探究艾青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美术创作资源,又体现出什么样的艺术审美指向?管窥艾青由画家到诗人“偶然性”转变背后的深层轨迹,以及这种跨界的审美给艾青诗歌创作带来何种可能性?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不足之处是难免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母鸡下鸭蛋”之滥觞谈起
艾青一生中曾多次与人谈及、撰文述及自己与美术的生命情缘,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莫过于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了。文章以几句近乎玩笑的问话引出:
一天,有个小伙子对我说:“有人说你是母鸡,可是下的是鸭蛋。”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原来学的是美术,后来却写诗。”
这几句话,引起我不少的回忆与感慨。
随后,艾青以洋洋洒洒充满沧桑感的数千言,回忆述及自己学习美术后来却写诗这一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对于艾青的美术修养,很多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便研究成果“如此众多”,却从未真正触及埋藏于艾青内心深处的隐秘情结:美术。正是这个被人忽略的美术,在艾青的生活、作品和生命里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美术成为他终身热爱且钟情的一种艺术符号,是他探索诗歌、文字可能性的一种召唤,形成与诗歌相印证的一种生命体验和感悟。“爱上诗歌远在爱上美术之后”[1]62-69,艾青如是说。然而,一辈子两次被迫与心爱的美术擦肩而过①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指20 世纪30 年代初,作为美术青年的艾青身陷囹圄,狱中客观条件所限,促成他由画画转向写诗。第二次“转向”是指50 年代初期,北京解放时,已经成为著名诗人的艾青,随军进入古都,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接管中央美院的工作。处在绘画的艺术气氛里,面对着一个个全新的生活情境,艾青又一次强烈地燃起重新搞美术工作的希望,试图从文学工作转向从事美术工作。但是,时间不久,大概只有一年,又把艾青从美术工作调到文学工作里了。,艾青为没能用画笔而不得不改用诗笔来表达自己的内在生活,充满了无法言表的内伤。“所有这些,只是我对美术的一种含情脉脉的回顾,一种遥远的怀念”,他甚至调侃自己“好像是被嫁出去了的人”,对美术只能是“走亲戚”的关系。这一连串的“夫子自道”实则显得意味深长:艾青对自己的美术才情十分自信,对艺术的感情坚定不移,但对两次“错过”深感不服,终不免遗憾。否则,他不必到晚年还如此耿耿于怀,而且在他的笔下无法掩饰地流露了出来。此一点,至今仍令笔者为之感佩、为之叹惋不已。也有人说艾青“假如不是因为身陷囹圄无法作画而改拿诗笔,也许中国当代画坛就会多了一位大画家,也许中国诗坛便会少了一位大诗人”。[2]688可是历史总无法假设,艺术更不能有那么多的“如果”。
不过,尽管如此,艾青的一生与绘画并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即便他后来转为写诗,仍对形体、色彩、调子和距离有一定的经验。他认为,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对于色彩、气味、物体的距离等东西,应该具有敏锐的而且准确的感受能力。虽然艾青的诗名远远地盖过他的画名,他的绘画并不格外的引人注目,但是他对美术的热情,他对绘画异乎寻常的敏感,对于要充分估量艾青诗歌创作地位和探究他心灵秘密来说,是极为宝贵的线索。了解艾青的绘画源泉,对了解艾青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源泉给他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答案,使诗作所表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字面所显露的。因此,倘若我们能够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去接近他,触摸那颗跳动着的灵魂,那么回顾艾青所走过的美术历程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事,相反,很可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二、“画学生时代”②“画学生时代”是笔者借用艾青在《忆杭州》一文中的提法,来概括艾青从小时候起到入杭州国立艺术院这一学生时代热爱和追求美术的一段历程。:从叛逆到追求
艾青的美术探寻之路与他的诗艺追求历程,因为融合了时代文化、历史的进程以及个体的真切体验而显得曲折和具体。
“我从小爱美术,喜欢图画和手工艺”,但艾青的这一爱好,与他的那位作为乡村地主又喜欢舞文弄墨、性情飘逸俨然旧式文人骚客的父亲,并无实质上的关联。刚出生不久,就成为地主家庭“弃儿”的遭遇,直接激发幼年艾青与他所出身的旧家庭以及父母的疏离、叛逆与反抗,而与生俱来就与他的乳母大堰河这样贫苦的人们和他们喜爱的艺术亲近。寄养在大堰河家时,大堰河终日劳作却始终含着微笑,艾青画“大红大绿的关云长”,大堰河像挂喜气洋洋的年画一样,把它贴在灶边的墙上。得到大堰河母亲的鼓励,艾青对美术就更有兴趣了。他喜欢用红泥土捏各类小动物玩,并从“贫民习艺所”(廉价的工艺美术作坊)的产品中发现“美”,从此对工艺美术有了好感。艾青5 岁以后,从大堰河家回到了“家”,他父亲对他更是无缘无故的打骂和呵斥,有一次,艾青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父贼打我”。艾青身上的这种叛逆和反抗的意志就更加强烈了,转而就从美术中寻求安慰。而美术,自然不能从父亲那儿习得传统笔墨,也与传统旧文艺有了相当隔阂,他从不画传统的国画,不看旧小说,不听旧戏。“反抗父性权威似乎先天就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内蕴。艾青对父亲的背弃和挑战同时与他的文化反叛交相辉映着。”[3]179
从6 岁就读小学到14 岁高小毕业,艾青接受小学教育的1916 年至1924 年期间,恰逢“革故鼎新”“开启民智”的新文化启蒙潮流高涨,科举教育为重视科学知识包括美术教育的学校教育取代,“美术”在变革中国社会的运动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借外来文化之力对积数千年流弊于一体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深刻的反省。1906 年,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学者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文中强调美育的精神作用和潜移默化改造人心的作用。1913 年鲁迅在北京任职教育部期间,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阐述播布美术之方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4]48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新式教育政策,他将“美育”列为国民教育的五项宗旨之一。在他推行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小学教则》和《中学教则》都明确规定了“图画要旨”,培养学生“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涵养美感”。1916 年,蔡元培主张“行人道主义之教育,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5]55,后来又提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6]43。1919 年他进一步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6]44。国民教育中重视艺术教育的方针延续了下来,各种教育社团纷纷成立,美术学校得以开办,中小学校纷纷开设美术教程,配有专门的美术教员。艾青的小学美术老师不仅画很好,工艺美术也较擅长,能给演“文明戏”的画舞台背景。在读高小时,艾青的图画和美工两门课的成绩最好。艾青自身的叛逆和追求从此有所托付,从新的审美思潮带来的美术中寻找到安慰,又得到时代潮流认可。“从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起,我就学会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旧文艺。”[7]192极端地叛逆什么?又强烈地追求什么?这种极其尖锐鲜明、相反相成的心理特征都集中在艾青身上,构成其童年、少年时期成长的主要心态。以往的评论者多从叛逆的性格心理的角度来分析早年艾青对传统旧文艺的反叛和否定,却少有人从他所接受的新教育的角度来讨论艾青的精神追求。
1925 年9 月,艾青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初中三年期间,我的功课数绘画最好”。[2]250作为民国初年以来“新教育”方针以及“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接受者,艾青一起步就是学习西方来的“爱忒”——民国初年以来颇为时髦的“美术”之素描、水彩、速写等各种直面生活、体现个性的写生训练和自由的创作。较之于前一代美术家,艾青的美术背景“相对纯粹”,少有传统文化层层因袭的束缚,而具有了更为自由的艺术精神和个性。除了课堂上偷偷地给上课的老师们“画像”,艾青还常常逃课跑到户外去写生——画风景。大雪天,艾青会去画雪景。课余时间,艾青反复地画老佣人陈家的草房和她的主人,自觉地运用美术的眼光来凝视人生的“痛苦和忧郁”。艾青的画作在学校画展中展出,少年艾青以一个“画者”的名义让自己“安身立命”。美术帮助他度过一段孤独寂寞的时光,而且给他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提供了线索,教他寻找和品味到了实际的人生。
1928 年秋天,艾青考入杭州西湖边上的国立艺术院,成为该校绘画系第一届第二期的学生。这是艾青迈出自己人生理想追求的第一步,也是与他终身热爱的印象主义绘画最初的兴会。艾青屡屡谈及西湖对他是“起点”的意义,深情谈及校长林风眠对他的知遇之恩。当时,因为校长林风眠的劝说,艾青于第二年春天奔赴巴黎学画。有传记者认为艾青“羁留这里(国立艺术院)的日子实在太短,印象轻浅,究竟缺少‘写’的兴味”,[8]57而匆匆一笔带过。但笔者以为,无论从现实的意义还是从艺术风格影响的层面上而言,“国立艺术院”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西湖”作为“摇篮”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正是这所走在当时全国美术界最前沿的新式美术学校,宽松的艺术环境使艾青敢“逆”敢“变”的敏锐天性有机会得以生长,把艾青送上了艺术人生的航船,赋予他以无可推卸的探求重任。在这里,他受哺于众多的从海外学习油画归来的老师,接触到各种新观念和专业化的西画训练,“遇到”了令他后来一直感佩并且无比尊重的老师兼挚友——美术家林风眠。艾青夫人高瑛回忆说:“艾青在美术界确实有许多较好的朋友,但唯有对画家林风眠一个,艾青是从头到尾百分百地接受。”①根据笔者于2008 年3 月5 日前往北京高瑛寓所,拜访高瑛时的谈话录音。也许未必真的“百分百接受”,但林风眠的艺术思想融进艾青的接受视阈,打下艾青一生的思想行为和艺术活动的基础,则毋庸置疑。
国立艺术院是当时画坛上“前卫派”如西方派画家林文铮、吴大羽、孙福熙、蔡威廉等云集之地,课程设置有重西轻中的倾向,往往油画课占绝对优势。艾青“班里的油画老师是王月芝(台湾人),木炭画也由他教。中国画老师是潘天寿,水彩画是孙福熙”[1]62-69。其中,教油画与木炭画的王月芝,虽非留学法国,但他从日本“外光派”老师那里间接地学习到印象派画风。
印象主义绘画在法国滥觞的时候,曾被视为“洪水”和“猛兽”,但是到了20 世纪初期,巴黎各种美术院校都不同程度上接纳了印象主义绘画,并以印象主义绘画技法、观念、作品作为日常教学的内容。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办之初其教学、学术空气中刮的也是印象主义风。对印象主义绘画的积极引介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校长林风眠,因为办学者的思路、教育思想、艺术主张往往成为关系学校发展的核心要素。国立艺术院的学生吴冠中说:“其实,(中国)学过西方绘画的,不管你是直接或间接,专业或业余,教授或学生都吃过印象主义的奶”[9]。
校长林风眠深受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影响,具体落实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提倡中西融合、兼容并包,学校艺术空气浓厚,艺术思想开放。同时他又属于专心于创作探索型的巨匠,具有强烈的革新精神,但他用以改革传统绘画的“武器”不是徐悲鸿所采用的写实主义的古典传统,而是19 世纪末以来的新传统,他借印象派这“他山之石”来攻中国绘画这块“玉”。在他眼里,印象派开创的绘画以背叛的姿态向绘画传统提出强烈的反抗,其形式语言、色彩语言和现代意识都是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存在的。“塞尚、莫奈、马蒂斯、莫底格里阿尼、毕加索,都悄悄进入他的画幅(中国画)而又不露痕迹。从一定意义说,他选择的近代西方传统比古典写实传统更接近中国艺术精神,……他上追汉唐,广泛吸取民间美术的营养。”[10]120林风眠在早期作品中表现人类的苦难和奋斗,洋溢着对人生世界的热烈关怀和注视,以及他相对内向的性格,对人生孤独感的体验、对爱和人道的渴求,对苦难的特殊敏感,都给艾青以深刻的启迪。“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有着羞涩的避嫌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2]3
艾青最初接近和喜爱西方印象主义画家和他们的绘画,不能不说受到林风眠的影响。了解和接近当时最具革新意义的前沿艺术印象派,的确很符合艾青的口味。印象派绘画内在包蕴的自由精神的追求对艾青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爱大卫德,德拉克罗亚,为的他们如实地描绘过他们生存的时代,为历史留下宝贵的美术遗产,但他更爱法国印象派画家”。[11]强烈排斥“学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艺术上“求新、求变”,以及艺术家对于人类的担当意识等许多方面的一致性,大概也是艾青认同林风眠的原因所在吧。艾青对人生、对艺术上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似乎可以在林风眠那里找到源头。半个多世纪以后,艾青依然“常思念林风眠先生,常想起国立艺术学院。”[12]750
虽说艾青在西湖国立艺术院求学只有短短半年,但其收获与成长却是一大步的。“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西湖岁月写下了一位现代青年在艺术成长中迈出步伐时的彷徨矛盾与自信冒险,而这恰恰是艺术创造者所必经的。如果没有这“彳亍在西湖边上”“用自己喜欢的灰暗的调子,诚真的心,去描画自己喜爱的景色”的艾青,那么我们的印象也会难以与日后那一位徘徊在塞纳河畔满怀艳丽感伤的画者艾青相衔接。艾青在西湖求学时期所画的一些素描、水彩、速写等作业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无法对此加以评说。然而,其思想的接受情况却是有迹可寻的,西湖时期,奠定了艾青一生以艺术为追求的思想基础,培养了具有现代艺术倾向的艾青。与其说这个摇篮传授的是油画、素描、水彩等的艺术上的新技法和新观念,毋宁说孕育的是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一种现代的文化精神,一种神圣的人道之爱。
三、“巴黎三年”:虔诚的印象主义绘画巡礼者
作为近代各种美术潮流的发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巴黎已经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也是中国美术留学生最为向往、集中奔赴的地方。1929 年春,艾青与他艺术院的老师、同学结伴前往巴黎。艾青在巴黎主要是半工半读,上午在一个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下午到蒙巴那司大街一家“自由画室”画人体素描和速写。“自由画室”所收取的门票比较便宜,来这个画室的多半是穷苦留学生和流浪的艺术家,好在这个画室经常雇有模特,使他可以画好素描,为油画上的发展打好基础。而半工半读的穷留学生是很苦的。关于艾青在巴黎的经历,作为同是中国留学生,后来成为艾青好朋友的李又然回忆说,“艾青学画,先在西湖艺专,后到巴黎。他不进保守的学院,而进了名画家的私人画室。他也爱古典画,但更爱现代画”“他身上当然有旧东西,但他根本,本质上是现代的——革命的”。“他住在葡萄牙人开的一家小旅馆的屋顶楼上,冷天冷热天热,的确很简陋:什么陈设都没有,只有一些书,主要是画册和诗集,再就是粘土、和搞雕塑的木架子,颜料,画笔……”“他引导我接近艺术,我带他到大学听课”“听课时,他有时速写老教授的秃头,挺滑稽的。”[13]35-36这些回忆很能勾起读者的想象:一个穷学生、一个流浪汉艺术家在巴黎生活的一些情景。从1929 年春到法国直至1932 年1 月回国,这就是艾青常说的“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在巴黎的三年,正是艾青成长非常重要的时期,艾青所学的依然是西方美术,但不同于“画学生时代”,此时心态已然超越了当年“彳亍在西湖边上”接受学校教育“勤苦的画学生”的心理,而转变成无论精神和行动上都更为自由无羁的“波希米亚人”了。从杭州走向巴黎,独自一人漂泊在异国他乡,艾青对这种“波希米亚”艺术家的感受尤为突出和鲜明。艾青在30 年代有许多首诗都传达出早年在巴黎的这种为艺术而感伤的“Bohemien”微妙复杂的心理。
如今
无定的行旅已把我抛到这
陌生的海角的边滩上了。
——《马赛》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
在那里,
我曾饿着肚子
把芦笛自矜的吹,
人们嘲笑我的姿态,
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
——《芦笛》
沿着塞纳河
我想起:
昨夜锣鼓咚咚的梦里
生我的村庄的广场上,
跨过江南和江北的游艺者手里的
那方凄艳的红布,……
……
汽笛的呼嚷一阵阵的带去了
我这浪客的回想
从蒙马特到蒙巴那司,
我终日无目的的走着……
如今啊
我也是个Bohemien 了!
——但愿在色彩的领域里
不要有家邦和种族的嗤笑。
……
愿这片暗绿的大地
将是一切流浪者们的王国。
——《画者的行吟》
对于流浪的生活有着切身体验,“浪客”“流浪者”“无定的行旅”“行吟”等字眼频频出现在艾青早期诗中,显然艾青对自己是“Bohemien”深以为然,“我曾饿着肚子/ 把芦笛自矜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行吟在大西洋边上的艾青此时主体意识增强,胸怀开阔,完全引波希米亚艺术家独立不羁的姿态为自己的姿态,美术家的特殊气质在这里得到清晰展示。
“波希米亚人”一词作为“称呼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与作家以及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人”的涵义,源于19 世纪初期的法国。19 世纪以来的波德莱尔、缪尔杰、库尔贝、塞尚、梵高、高更、毕加索等都崇尚波希米亚,自外于传统社会,甘于四处漂泊贫困,为的是不受传统的束缚,达到心灵自由,获得一些神秘的创造的启示。巴黎的蒙马特区和蒙巴那司区就是著名的波希米亚社区,那里往往是法国文学和艺术新思潮的诞生地。
正像多数奔赴巴黎的外省艺术家一样,艾青感受到别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对自己的冲击,而这一经历和人生体验似乎给他一生的艺术(绘画和诗歌)创作铺垫了某种浓郁的“巴黎”气质的调子。诚如李又然所言“他身上当然有旧东西,但他根本,本质上是现代的——革命的”。而就艾青艺术创作中潜藏的法国巴黎现代艺术气质,在艾青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不久,评论家杜衡就敏锐地“闻”到这一点。杜衡的那篇《读〈大堰河〉》直至今天都有重读的价值和意义。梵高当年初到巴黎,看到巴黎正在流行的艺术新风印象主义绘画的时候,感到震惊、惶惑:油画的色彩竟然可以那样的鲜艳、光线可以那样的璀灿,画面中还有空气的颤动呢。于是他下决心向印象派画家学习,改变自己调色板上的颜色,驱除晦暗,迎接光明。巴黎使梵高“脱毛”“进化”,经历了从过去进入现代的过程。而巴黎对于艾青的震撼程度着实也不小,那种初来乍到感受到巴黎的傲慢和对自己弱国子民家邦和种族的歧视自不待言,仅就艾青艺术精神世界的感受来说,冲击也是巨大的。艾青面对的世界不再是畈田蒋村和杭州了,而是巴黎,一个世界公认的前卫派中心,一个多面复杂、开放与包容的世界性现代都市,对任何一位前来巴黎朝圣的艺术家都有可能一起来参与和讨论新异的创造奥秘。艾青身处艺都之中,可以更加切身敏锐地体验到当时正在激荡起伏的艺术潮流对他的影响。
但是,问题在于艾青当时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地学习和阅读,只能接触到什么就吸收什么,“所受的影响主要不是理论的灌输而是艺术的感染,情绪的共鸣、意象的启发、感觉的契合等等。同时,这些艺术家并不是‘整个’地进入他的学习视野的,他们的形象很可能就局限在艾青当时接触到的那一部作品之内。”[14]87艾青在巴黎常去的地方除了画人体素描的“自由画室”外,就是卢浮宫和巴黎各大大小小的画廊。因此,他亲眼目睹法国艺术从古典艺术到印象派以至现代诸多流派的作品,是他接受和学习法国艺术最主要的方式。
对于自己在法国三年(1929 年春—1932 年初)巴黎具体的艺术氛围,艾青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说明。(1930—1934 年)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秦宣夫,则描述了这一时期巴黎的状况:
1931 年的巴黎艺坛对于一个初到巴黎的中国青年来说是非常混乱的。法国美术学院、高等美术学院、春季沙龙在制度上代表官方的艺术。美术学院表面上是法国传统的维护者,但美术学院没有一个鲜明的艺术思想。高等美术学校虽有几个老院士在支撑场面,但没有认真负责的教学制度及严格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春季沙龙实际上早已商业化了。学院之外就是现代派的汪洋大海,最新的东西是超现实主义、立方派、野兽派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毕加索和马提斯仍然是许多青年的偶像。在卢浮宫中虽然可以看到欧洲绘画的丰富多彩的遗产,但现代派的形形色色的产品则分别陈列在成百的画廊中等待顾客。一个中国的青年如何批判和接受这些遗产,如何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5]
20 世纪30 年代初的法国巴黎依然是各种先锋派艺术漩涡中心,各路艺术流派云集,纷纷标新立异。作为现代派源头的印象主义艺术,已回到故乡巴黎确立了地位,并渐渐处于上升阶段。现代派也不只是一个复杂的文艺现象,而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处于生活、艺术潮流漩涡中骚动不安的人们积极寻找一种精神解放的艺术。在新旧杂陈、标新立异、迭相更新的巴黎现代派强烈的氛围挟裹中,艾青不能不耳濡目染而受其影响。然而,艾青并没有迷惑于上述秦宣夫所言的中国青年“艺术道路的选择问题”。叛逆的性格,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以及波希米亚人的自尊和自傲,使他靠近印象派、现代派美术,远离古典写实的绘画。选择学院之外的“自由画室”习画,以“波希米亚人”的姿态穿梭于各大大小小的画廊,巡礼观览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许多作品,看来倒是一条非常适合艾青主观感受种种新异艺术氛围,汲取现代精神的理想途径。艾青自己早年作为画家习作的风格就深受现代派画家的影响。从《检票员》(图1)和《篱》(图2)艾青早期这两幅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窥见现代派绘画风格在其画面中的留痕。

图1 《检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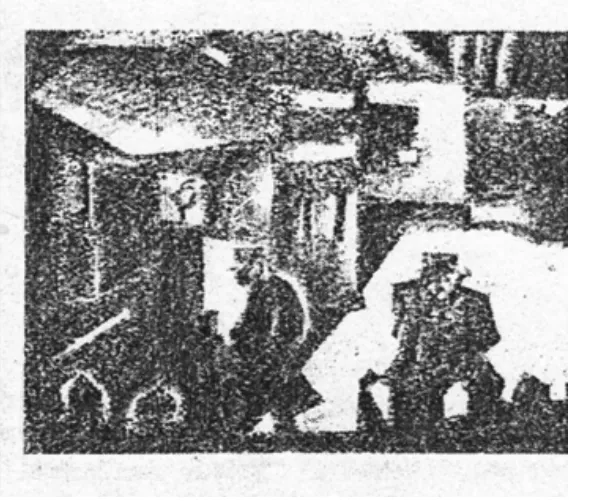
图2 《篱》
艾青所了解到的西方美术流派十分广泛,就近现代而言,有印象派、象征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而了解的西方画家就更多了,诸如达文西、拉斐尔、达维特、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米勒、杜米埃、莫奈、马奈、雷诺阿、德加、塞尚、梵高、高更、莫迪利阿尼、杜飞、毕加索、尤特里罗、夏加尔等。当时,散布在巴黎各处收藏馆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对异国的青年艾青颇具有吸引力。程光炜的《艾青传》中详述了艾青初到巴黎观看印象派画展了解到印象派画家们不同寻常的“经历”时激动的情景,他读到左拉那篇对马奈的评论文章《爱德华·马奈》后,“马奈对事物深刻、准确的表现力给了他强烈的震动。”[8]73直面印象主义画家们画面中的光、色语言艺术,绘画技法上的不因袭陈腐,不拘泥一格的画风,艾青深受感染。以反传统反学院派著称的印象主义画家们所开创的印象主义绘画不仅是对欧洲油画传统观念的一次巨大反拨和挑战,而且开启了现代艺术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之路。这些都与艾青内在的激扬和反叛的情绪一拍即合,生活和艺术瞬间拉近了距离,“我爱上‘后期印象派’莫内、马内、雷诺尔、德加、莫第格里阿尼、杜飞、毕加索、尤脱里俄等等。强烈排斥‘学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结合起来了”[1]62-69。可见,印象主义美术已渗入到艾青的人生态度中去了,这种喜爱之情又在艾青的生命中体现得那么牢固、结实。印象主义的画风,都几乎成为他日后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习惯,就连“用语言作画”艾青也最爱以印象主义画家画画的方式来捕捉“美”的瞬间,“美”的事物。当时,他“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失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1]62-69。“它最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艾青诗歌与印象主义画派的那种血缘联系”[14]90。这一切,艾青不是从严格的“学院式”的探究中得来,而是从作品的艺术感染、情绪共鸣和整个前卫派艺术氛围的洗礼感受中获得的。那时的所谓作画,“也只不过通过简练的线条去捕捉一些动态,很少有机会画油画。只记得曾有一张画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参加了‘独立沙龙’的展览。那张画上我第一次用了化名‘OKA’,后来我有一些诗就用了‘莪伽’这个笔名。”[1]62-69
这里需指出的是:把印象派画家莫内、马内、雷诺尔也归为“后期印象派”①关于艺术史上的Post-Impressionism 一词的名称及其内涵,美术理论家、批评家历来聚讼风云,莫衷一是,尤其是经过汉译以后,其提法更是各异。我国美术界对这个派别的名称有几种译法,如“后期印象派”“后印象派”“印象主义之后”“印象后派”等。有人认为Post-Impressionism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不宜译成“某某派”,而应译成“某某主义”,这种见解有其可取之处,但国人仍习惯于称之为“某某派”。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认为“后印象派虽然同印象派有瓜葛,可是在更多的方面是反印象派的,Post-Impressionism 这个词长期以来被译成‘后期印象主义’是受了日文译法的影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印象主义后期的误解。”“我想可以参照Post-Impressionism 的译法,译作‘后印象主义’,既可以表示它是印象主义之后的这层意思,又显示出它与印象主义的渊源关系。”(参见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21 页)这一说法为今天多数人所接受,现在常用的译法为“后印象主义”或人们习惯上说的“后印象派”。本论文所采用“后印象主义”或“后印象派”这一说法,其流派代表人物是塞尚、高更、梵高。,其实是艾青的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反映了“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范畴的广义性、印象主义运动在西方美术史的转折时期其前后联系上的绵延性。艾青所开列的这些他“爱上”的西方艺术家中实际上包括了印象派和现代派诸画家。联系艾青后来的诗作、文论及朋友的回顾,艾青的所爱之中有两位“后印象主义”的画家梵高和高更,是不应遗漏的。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欧洲传统的绘画进行了一场革命,印象派确实是传统艺术与现代派美术之间的分水岭。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派美术,起源于印象派,或者确切地说,起源于后印象主义画家塞尚、梵高和高更,他们各自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世界,因为特别坚持各自的原则,而且向艺术的习俗的传统挑战,从而引发20 世纪初现代派美术的发生和变革。印象派、后印象派和现代派之间的确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渊源联系。艾青的“误读”之中折射出“后期印象派”对现代画家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表明艾青对“后期印象派”的推崇和喜爱,他的意识是和某种新的、非传统的、非学院派的,反封建反保守的艺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总而观之,艾青对西方美术的兴趣、接受和理解,主要集中在西方绘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捩和变革时期的艺术——“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这一块,偶尔也旁及此前、此后的艺术。可以说,艾青所接受的也是广义的“西方印象主义绘画”。或许可以将之概括为:从莫奈到毕加索。艾青对这些画家及其艺术的了解最为深入,而印象主义绘画艺术也成为艾青创作最重要的源泉。
艾青说:在法国,我知道的印象派画家很多,但知道的诗人却很少。[16]482那时,他读到汉文翻译的果戈理的《外套》、屠格涅夫的《烟》、妥斯退也夫斯基的《穷人》、安特列夫的《假面舞会》。通过学习法语,他接触到了法文翻译的俄罗斯诗集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叶赛宁的《一个流浪汉的忏悔》《普希金诗选》。也读了一些法文诗《法国现代诗选》、阿波里内尔的《醇酒集》等,“如此而已”。“我的法文基础很差,但我却有不差的理解力”[1]62-69。
在巴黎,有几位艾青深入了解过的诗人是不能不提的,法国现代大诗人阿波里内尔、兰波以及当时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阿波里内尔也是画家中的诗人,与毕加索交往甚厚,他写诗受到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影响,他从接受画家反传统的精神着手,开始改造自己的诗风,发现了形式与色彩的世界,投身于诗歌形式的革命。《坩埚》一诗中的分解法是从毕加索的绘画中得到的启示。他的主要诗集《醇酒集》就是他艺术思想和诗歌理论的最好体现。源于立体派绘画的启示,他的图画诗将诗歌词汇和形式上的创新推到极高的地位,而且对俄国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阿波里内尔从毕加索的绘画中汲取灵感,对艾青由画而诗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艾青也热爱画家毕加索。事隔多年以后,一位深受艾青影响的诗人牛汉屡屡述及上述这种艺术上的亲缘联系。
艾青喜欢法国诗人兰波,但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凡尔哈仑是艾青在巴黎为学习法语而开始阅读法文现代诗时接触到的诗人,他在诗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17]96,这一独特的艺术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艾青,占据着艾青的文学兴趣中心。事实上,凡尔哈仑的诗与梵高的画也多有共鸣之处。据记载,凡尔哈仑和梵高曾同时参加过比利时的“二十人的画展”,那是梵高生前参加过的为数不多的一次重要画展。[18]282-284他们都从原野和人性的角度出发,对近现代西方大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因素用艺术的方式表示朴素的否定,而这一点并不为人所注意。艾青的艺术却收摄了他们相通的艺术意蕴。艾青在回国后不久身陷囹圄,在狱中重温了凡尔哈仑的诗集,利用手头的一本法文字典,断断续续译出了凡尔哈仑的《原野》《城市》《群众》《穷人们》《来客》《惊醒的时间》《寒冷》《风》《小处女》九首诗。凡尔哈仑对艾青由画画到写诗的转变,的确也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诚然,艾青的“耽爱”和“喜欢”既有思想的,也有艺术的,对西方文化资源的汲取是广泛而又多元的:美术的、文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况且各种艺术的启示常常是潜移默化的,各种艺术思潮之间相互撞击,产生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当美术领域印象派勃兴时,在诗歌中则表现为象征派的风行;文学领域的未来主义影响了美术领域的未来主义,美术上形式的变革启发了诗歌结构、形式的创新等。先锋派的画家和现代诗人们对时代的敏锐的感受和艺术家内在的革命性,也都给艾青的主体精神世界灌注了浓郁的现代气息。在艾青整体感受这些文化资源的时候,各种艺术因子常常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比如当他接近于波德莱尔的“欧罗巴”时,阿波里内尔却又在不远处召唤他向往革命,向往未来,而不至于使他的内心流于象征主义的神秘与颓废;当他迷恋巴黎自由开放的现代艺术氛围时,却又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处处对他投以家邦和种族的歧视,感到深刻耻辱和仇恨。这对极具反叛性格的他来说,不能不激发出满腔的愤懑:“等时间到了/ 就整饬着队伍/兴兵而来”。巴黎三年,艾青的成长是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艺术领域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是“和那些叛乱的书籍、和那些狂热的画幅、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耻辱和仇恨”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都促成艾青成为一个革命性的青年。1932 年1 月16 日晚,艾青和李又然参加了在巴黎的一次东亚青年反帝大同盟的集会,参会者多为东亚青年,可能饱受歧视的缘故,参会者满腔愤懑。情绪激动的艾青随手记下了几句跳跃的诗句,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会合》,从美术向文学首次移动,就具有明显的先锋派艺术的意味。艾青本质上是现代的、革命的,他写诗与他的为人基本上是一致的。
李又然回忆述及艾青归国途中的一件事,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青年艾青形象:
在印度洋上,有个欧洲人,深深中了殖民主义的毒,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说中国没有人。一个留法同学说:“我们有冯玉祥!”“我们有红军!”艾青大喝一声。这一声大喝,压倒了印度洋上的波涛——我这是说威势,不是指声音。[13]36
“这一声大喝”喝出了威势,也裁剪出艾青性格的一个侧影。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艾青对于殖民主义的反叛和一位美术青年内在的革命性,这也是时代氛围与青年人个性相融合的产物。了解这些对感受和理解艾青是非常重要的。上面提到的多位画家和诗人,正是青年艺术家艾青的知音或引路人。艾青因此走上了接受法国印象主义、现代主义艺术影响的漫长路途。艺术上反保守的古典主义传统、反学院派,政治上反封建、反帝反殖民主义侵略,这一多重反叛成为艾青学习、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近代外国文艺时的共鸣点、敏感点。他用现代精神来审视文学和艺术,这也决定了艾青的择取、吸收、迎拒和扬弃。
四、身陷囹圄:由画而诗
1932 年春夏之交,艾青回到祖国后,他以一个革命的青年美术家的身份出现在上海美术界。是年5 月,艾青与于海、江丰、力扬、黄山定等十几个革命的美术青年成立了“春地美术研究所”,又名“春地画会”。6 月,艾青撰写了两篇文艺评论同时刊登在6 月6 日的《文艺新闻》上。艾青以“莪伽”署名在“美术版”发表《乌脱里育》一文介绍法国野兽派画家乌脱里育,指出画家不仅在色彩、笔触、构图方面独特的天分,在对巴黎底层的市民生活的巢穴、穷苦的老妇、小手工业者、泥水匠,“感受得最为真挚,于是表现得也较为迫切些”“作者的命运是和这城市的命运相联系着”[2]338。同时,艾青以“伽”署名在“诗歌版”上发表《十二个诗人》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在去年夏天,巴黎国际社会出版局印了一本革命诗集——法国左翼文坛的诗集《十二个诗人》”。6 月下旬,春地画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开展革命美术活动,展出沪杭两地约一百幅木刻、油画、漫画、粉画等作品。鲁迅先生拿出他自己珍藏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精印版画《织工暴动》《农民战争》在这个展览会上同时展出,给予热情的支持。艾青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的是一幅纯粹属于抽象派的画。春地美术研究所又附设漫画研究会、木刻研究会,并招收学员,传播进步思想,传授美术技法,培养进步有为的美术人才。艾青当时所担任的主要是石膏素描等方面的美术辅导,也从事文艺评论等介绍。春地画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引起了伪当局的严密注视。7 月12 日晚,艾青与其他12 名美术青年被捕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从此艾青开始了囚徒生活。
监狱中,失去了画油画的颜料和工具的艾青,就不能画画了,但是这种外在的囚禁又岂能框囿得住青年艾青内在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失去画笔的艾青,开始转向诗歌创作,“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芦笛》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决定我从绘画转变到诗,使母鸡下起鸭蛋的关键,是监狱生活”“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1]62-69三年牢狱期间他写下了25 首诗,加上他在巴黎和回国途中写下的4 首诗,这些诗他托李又然或者其他朋友、律师带出监狱,再由李又然辗转投寄或送至上海一些诗歌刊物。其中,《当黎明穿上白衣》《阳光在远处》《那边》《马赛》《泡影》等诗作刊登在《现代》杂志上;《监房的夜》《叫喊》《聆听》等发表于《春光》杂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载于《诗歌月报》;《铁窗里》载于《新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从狱中被带出来,辗转发表在《春光》杂志上,“传到日本,轰动一时,有人读了流泪,有人译成日文”。[13]37这些诗的创作和发表作为艾青由美术向诗歌移动创作出的第一批成果。1936 年,艾青出狱后不久,选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画者的行吟》《芦笛》《巴黎》等9 首诗结集,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艾青的新诗艺术一出现就呈“诗文与图画并作”的特点。艾青亲自为诗集《大堰河》设计封面和插画。《大堰河》封面画是借用一位法国画家的作品:浅米色的页面右方,是一幅由几笔简练的浅绿色线条勾勒而成的速写。除了诗歌作品外,诗集还附有四幅图画:第一幅插画则是俄国画家“Chagall”的作品,第二幅题名为《夜》,第三幅插画是艾青自己的作品,题为《篱》,第四幅插画《检票员》也是艾青的作品,据说画的是巴黎地铁的检票员,画风颇有现代派意味。艾青的诗集《大堰河》出版不久,倍受左翼文学批评家茅盾和胡风的青睐。属于不同阵营的杜衡也发表《读〈大堰河〉》,并触发了文艺界内部的一场争论。那时,新诗人艾青的诗作也在上海几家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艾青的诗一举轰动文坛传遍大江南北,深受读者喜爱。
结语
可以说,在30 年代的现代诗坛,艾青横空出世,但人们往往迷惑于没有受过多少学院式的诗歌写作的教育,加上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匮乏的美术青年艾青,何以一出狱后就成为新诗坛的著名诗人;迷惑于艾青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忧郁而激愤的吹奏,怎么会一下子轰动了30 年代的中国南方和北方[14]85。
其实,艾青从画家到诗人“偶然性”转变的背后,实有其内在深层的可探寻的轨迹,艾青所钟情的西方现代美术给出了答案。在艾青由画而诗,写诗之前他最主要的素养准备和积累,都集中在了对西方现代美术的兴趣和爱好上,但他是极少数能从具象艺术的领域获取到从另一个视角来把握诗歌语言文字抽象性特点的诗人之一,他写诗时感受世界和艺术地再现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来自印象主义画家的。因此,考察艾青早期的诗歌必须将之与艾青所钟情的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绘画艺术联系在一起。否则艾青的诗歌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艾青诗歌的赏析与评价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据与标准。从画学生到Bohemien 到革命的美术青年到新诗人,艾青找到了他传达心声的恰当语言,那是“语言”受绘画艺术潜移默化巨大影响的结果,也是一个叛逆的、革命的青年带着镣铐的泣血的吟唱。
